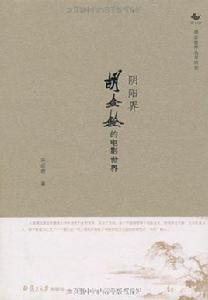內容簡介
 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
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人是通過現世和黃泉之間的地帶而去到冥界,成為亡靈的。這箇中間地帶有個陰陽法王,給他抓住的話,又不能成菇人,也不能成為亡靈了……我們這一代,就剛好像影片中被陰陽法王捉住的那些在“中間”的人。本書是國內外全面解讀胡金銓執導電影的第一本著作,立足對胡金銓電影的影像解讀,結合胡金銓本人一手論述資料,總體揭示胡金銓在中國兩岸三地政治分置和文化對峙的現實語境中,通過電影書寫追索人的精神家園的根本追求,並具體落實在胡金銓電影內在的美學、家國、信仰三重觀照上,而其中貫注著胡金銓所代表的“南下影人”一代人的疏離他者並自我疏離的懸置性精神處境。
書稿通過“總-分-總”式章節總體結構(導論,第一至五章,結語),由總體到局部,整部書稿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同時,本書始終注重將電影的影像元素分析和思想闡述結合而論,既在避免純技術分析,也在避免純理論玄談。
本書資料較為豐富翔實,通過各種途徑搜尋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匹茲堡大學圖書館、法國高校圖書館等港台和英美法的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胡金銓電影的全面分析。
作者簡介
 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
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吳迎君,江蘇沭陽人,四川大學影視文藝美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學學人。在《電影藝術》、《當代電影》、《當代電影》、《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等核心期刊上發表《論胡金銓電影的“中國美學”體系》、《中國“影戲”表演理論的現代闡釋》等十餘篇論文,其中《反思電影敘述學的研究誤區》、《“景觀電影”,或曰“奇觀電影”的知識學勘察》為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
目錄
導論
在通向一種“陰陽界”的路上
第一章
胡金銓電影的影像三原色
導言
第一節“電影技巧至上”背後的文化救亡情結
第二節“亂世明朝圖景”背後的幽深家國情懷
第三節世俗性信念到超越性信仰的人性追尋
第二章
“文化救亡”情結下的胡金銓電影美學
導言
 書影
書影第一節穿過風景或他人的個人身影
第二節周旋迂迴情境中的二人交鋒
第三節面具偽裝下的三個人和四個人場景
第四節多人場面的文戲、武戲、文武戲
第五節革新古典戲劇美學的“摺子影戲”
第三章
現實家國隱喻的“亂世明朝”影像
導言
第一節官方背景與非官方背景的俠客
第二節官方背景與非官方背景的反角
第三節走在精神救渡路上的僧侶和居士形象
第四節人世出世間的道士和“中間者”形象
第五節“無家可歸”的亂世家國影像
第四章
信念信仰觀照下的人性困境呈現和省思
導言
 書影
書影第一節生死事大的生命反思
第二節男歡女愛的刻意壓抑
第三節權力爭奪的欲望批判
第四節人性複雜多變的觀照
第五章
“陰陽界”的精神世界
導言
第一節去立場化的立場的影像精神
第二節自我悖逆和弔詭的作者精神
第三節兩種作者的精神同一與精神分裂
第四節在“陰陽界”創作藝術的得與失
結語“陰陽界”的靈光與暗點
人名片名索引
附錄:胡金銓電影研究資料彙編
後記:摹繪影像沙畫
相關評價
胡金銓:托情書劍靜觀浮生
——讀《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
遆存磊
 讀《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
讀《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在他的電影語言的闡釋下,蕭蕭風過之處,搖盪的蘆葦叢中,依稀拂不掉千年的民族孤寂。”董橋的如此論說,所評何人?正是胡金銓導演。我們想《大醉俠》的鼓樂絲竹聲中金燕子在石橋上的出場,《龍門客棧》正邪雙方於封閉空間的對峙角逐,《俠女》的竹林之戰以人為毫墨盡情揮灑飄逸與凌厲……如許有中國氣派的作品雖不好說空谷絕響,但斯人已逝難以再求卻毋庸諱言。胡金銓說自己“涵泳在古典劇場的血脈中”,傳統文化與文人情懷是根植於他的意識深處的,施諸於光影的創作濃烈地灌注著其美學追求,視景開闊,意念沉潛,家國寓言雖隱亦可彰顯於明眼人之目前。《陰陽界———胡金銓的電影世界》一書,有意味之處就在於拈出一個懸置的“中間世界”,讀解胡金銓電影創作所透露出的精神困境,雖無“四郎探母”般背叛與救贖的撕裂,但疏離與不可求的糾葛卻是昭然的。
熟悉胡金銓電影的人都知道,他的十三部作品中大多為武俠類型電影,且時代背景均放在明朝。那是一個亂世,“一個人際關係、身份、面孔急劇轉變的年代”,給胡金銓足夠的空間描摹人物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局中人雖在不斷地行走,但其焦慮、恐慌、危機感仍是揮之不去,寄寓著創作者微妙與複雜的心緒。胡金銓生於北平,移居香港,後又赴台灣工作,其所處時代正是大動盪、大裂變的亂世浮生,國家不得統一,知識分子備受摧殘,文化記憶與想像飽受抑制與拘囿。在如此的背景下,如胡金銓這樣的知識分子揀盡寒枝,無所棲身,實體的家國難覓,文化中國圖景大約即為最佳的去處,這也是胡金銓自《龍門客棧》、《俠女》、《迎春閣之風波》向《山中傳奇》、《空山靈雨》過渡的根本原因了。
這種轉變有一清晰的脈絡可尋,《龍門客棧》等作品暗含對現實政治的隱喻,不管是威權統治、特務手段,抑或民間對抗、指斥暴政,有識者均可與現實狀況兩兩對照,會然於心;而自《山中傳奇》始,直至《空山靈雨》、《畫皮之陰陽法王》,胡金銓脫離對現實政治的直接關照,而是轉向了對潛藏的文化記憶與想像的追索,也即構建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中國),茲事體大,所為不易,胡金銓難免處於高渺的精神樓閣中,理解者寡,和者甚少,寂寞之處境就不可避免了。
在此時期,有一個著名的事件,香港的徐克導演邀胡金銓籌拍《笑傲江湖》,胡金銓欣然前往,但結果兩人創作理念不合致使胡金銓黯然離去,釀成了當年電影圈內的一場軒然大波,許多電影人捲入其內,如許鞍華憤然出頭為恩師說話,等等。而我們自成片來看,胡金銓的印記俯拾皆是,如服裝設計、道具、人物造型,以及開闊的場景和水墨畫韻味的空鏡頭等,也即是說,徐克並未排斥這些東西,那胡和徐的根本分歧在哪裡呢?似乎未見過有論者明確講述過,而我的猜測是,兩人的矛盾應在於《笑傲江湖》的精神核心之處理上。觀徐克主導的《笑傲江湖》,充溢著對現實政治的映射,即使有“滄海一聲笑”曠達情懷的衝擊,也濃烈得化不開;我想,此時的胡金銓大約已不願再拍直接指向政治隱喻的影片,他的興趣主要轉向對文化共同圖景的追求,因此與晚輩徐克的創作理念之分歧也就莫足為怪了。不過有意思的是,徐克雖然開罪過胡金銓,但仍是極喜歡翻拍胡的作品,先是《新龍門客棧》,後來再攝《龍門飛甲》,樂此不疲,說明胡的豐沛原創性實在是可以救創作力匱乏之急的。
其實,胡金銓的創作歷程與精神求索固然孤獨,但並不是沒有藝術同道的,如托爾斯泰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向《復活》的轉變,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罪與罰》、《群魔》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轉向,均是面臨著對精神烏托邦的苦苦求索。但胡金銓的另一困境在於,電影終究具有極強的商業屬性,他一旦加入精神的探索,票房必定大受影響。胡金銓意圖自《俠女》開始建構自己的精神圖景,此片對佛禪境界的探索是極有開創性和藝術進境的,無奈曲高和寡,票房慘澹。而胡金銓作為一位電影領域的創作者,悲劇性在於,明知前途坎坷,個人的精神索求與作品載體的工業屬性難以兼容,但服從於藝術良心的他只能“一意孤行”,不願為了外界的因素勉強自己去拍無謂的片子。
身處名利場,胡金銓卻自覺地疏離其間,有大勇氣探求個與群在大時代的生存困境與突圍,即使擺脫不了漂泊的命運,亦其猶未悔。如果能卸卻導演的身份,胡金銓毋寧說是一個讀書人,他博古通今,瞭然於西方文化,以之觀照本民族的傳統文明,一往情深,執意做古典的守望者。昔者不可追,他只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重現那一抹榮光,即使短暫,勝於虛無。“蕭蕭風過之處,搖盪的蘆葦叢中”,我們或許感知到清冷的涼意,但在此獨有的形式下,有著胡金銓的文化圖存情結,隱含脈脈的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