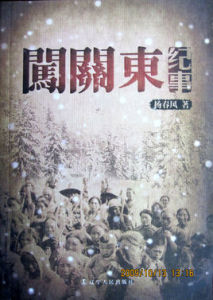內容簡介
闖關東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移民活動,是世界移民史上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以暢達而鋒利的文筆,從史學、社會學的巨觀視角出發,對闖關東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多方位的解讀,著力展現了闖關東廣闊而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闖關東人在東北特有環境下形成的歷史風貌、民俗風情、性格特點等。本書圖文並茂,雅俗共賞,是一本全面、完整反映這一重大移民事件的通俗性歷史讀本。
圖書目錄
序言 史學、社會學的解讀與文學表述
大背景:在對故土喪失信仰之前
悄然膨脹的人口
精疲力竭的土地
人地失衡的罹難
難以為繼的生活
闖關東:生存權利的徵求形式之一種
當移植已成為生存的必需
當關外已然是唯一的去處
當遷徙遭遇到梗阻
當限制演化為封禁
當針尖與麥芒迎頭相撞
當驅逐與迫返雙雙失效
窮則變:變通的只是對四季的追逐
時移事易,唯有解禁
被迫而為,猶抱琵琶
帶我離開,到你所在
改朝換代,民生依舊
日月輪迴,溫暖得現
舊路新途,舊俗新意
人與地:我的福祉取決於你的肥瘠
農業:富足於對土地的感恩戴德
工業:尚存秋季之處即繁華所在
商業:興起並發展於豐肥的熱土
城鎮:追隨並繁茂著土地的四季
關東風:奔突於黑土地上的中華血脈
移民:古老的全球性血脈奔突
文化:白山黑水間的生命密碼
風俗:以地域的姿態得以獨立
語言:不易混淆亦不輕容相忘
後記
圖書選摘
之一:
這個世間有很多事情,總要拖延到回顧之際才會變得明晰,在事情的進程中卻不能產生敏捷的反應,從而及時意識到它的嚴酷,倘若事情的後果當真有必要勞煩“嚴酷”的話。緩慢的塵埃落定之日,也並非悉數等同於蓋棺論定之時,認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並不意味著事情的性質就能得到公認。公認,公眾或者擁有發言權之資質的全體人士的統一口徑,無疑是個奢侈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名義下。
如此,對中國人口於清朝時期那番史無前例的增長,究竟是否應當給予一個“人口危機”或者“人口過剩”的概括,也就不足為奇會成為一件讓眾學者撓頭的事情,給有給的理由,不給有不給的論據,兩相爭議的聲音是如此之響,且始終不見拍板定音。
好在事情業已過去,無論到底該如何定性,人口的增長總還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事實是,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極為壯觀的一次人口膨脹:連續突破2億、3億和4億大關,至鹹豐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億人之多。至於這個龐大數字的基數,則至今,或者說以後,以及永遠,都將無法得到精準的確定。這緣於彼時不曾進行過可資信賴的全國人口普查。
清朝從順治八年(1651年)首次進行丁冊的編審,接下來五年一次,持續到乾隆六年(1741年)戶口制度做出重大改革。這期間留下來的唯一數據,就是豐富的丁數。不過有很多事實表明,這些數據雖名義上為“人丁”統計,卻既不代表全國確切的丁(16-60歲的成年男子)數,更不代表含“大小婦男”在內的人口數或者戶數,而是且只是納稅單位;至“攤丁入地”導致丁稅不存之後,此類不足盡信的數據就愈加漫不經心。因此對於清前期中國人口數據的復原,無論治學如何謹嚴的學者,都只能採用估計的方法,估計出當時的平均每戶人口數,再與這些模稜兩可的丁數相乘。史上曾被諸多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可為“最有見識”的估計是:順治八年中國的人口大致為6500萬。
之二:
隨著時間慢條斯理的前行,在日漸冷漠的太陽光下,或煮或蒸以致堪食的地瓜,也被中國農民越來越頻繁地端上越來越無法保證體面的餐桌,而日益成為他們的主要口糧。當人口數量逐漸抵臨甚或超出社會資源的警戒線,努力讓自己的肚腹適應並滿足於粗劣的食物,也就成了儘可能保障更多人能得以存活的最簡便的有效途徑。
不過這種途徑也並非沒有限度。如果說在現實逼迫——人口仍在一意孤行地激增,耕地的增長卻已力不從心——的狀況下,“肉食”可以轉化為“素食”,“素食”亦可降格為“粗食”,那么也就似乎找不出理由,來阻止“粗食”向“不得食”的過渡。
這種無疑會帶來普遍絕望情緒的過渡,將發生於何時?
——唯有土地能作答。
之三:
也因此,相對於後來者而言,在1668年之前就把自己給移植了的人,實在是幸運的,他們不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山海關,而且這樣的流動還被人鼓勵受人歡迎。無需“闖”就可以達成移民的目的,是後來的移民者一度無緣擎受的福分。
這裡有必要分析一下“闖”字。《說文解字》說,“闖”字從馬從門,表示馬從門中猛衝而過,其本義為向前猛衝,兼有一往無前和無所顧忌之義。此外,“闖”字還有經歷、歷練的含義。基於此,方可以相對嚴格地闡述一下“闖關東”。
作為一個歷史性名詞,“闖關東”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闖關東”,是指1668-1860年間,中國華北平原的農民向東北移民的過程;廣義的“闖關東”,則可泛指有清一朝至民國前期(1644-1931年,亦有人將時間延至1949年,不過九一八之後的移民性質與此前迥然不同,故本書不將其列入其中),中國華北平原的農民向東北移民的整個過程。
之所以如此分劃,恰恰在於這個“闖”字。唯有當遷移遭遇到梗阻,才具備針鋒相對的矛盾,才能產生“闖”的要求,才可生成“闖”的事實,也才符合“闖”的本義;而無論在1668年以前,還是在1860年以後,儘管移民東北的華北農民都有存在甚至更多,卻都沒有梗阻的因素存在,故而這兩個時期的“闖關東”之“闖”字,只是“闖蕩、歷練”之意。意即,唯有遷移和梗阻同時在場,才是嚴格意義上的“闖關東”,否則是寬泛意義上的。
很難考證“闖關東”的原創究竟屬於民間還是政府,無論是誰,都堪稱天才。有清一朝的大型區域性移民很是不少,卻不曾有一個的命名含蘊了如此顯明的梗阻之意。比如“填四川”的“填”,“走西口”的“走”,“下南洋”的“下”,都只是單純的一個動態字眼,充其量能說“填”字含有點“迫不及待”之意。“闖關東”的“闖”字,則蘊有衝突,含有矛盾,一個欲走及非走不可,一個不讓及堅決不讓。更富戲劇性的是,“闖關東”當真需要“闖”過一道“關”——山海關,而清政府于山海關的封禁,也正是這矛盾的焦點所在。
之四:
求食,很卑微的希望,卻讓人保持了求生的意志,也讓那些卑微的流民,不肯識趣地讓出所占耕地而悄悄離開,儘管他們未必沒看到政府那張已然陰得能擰出水來的臉。他們在這臉前垂下眼瞼,摸索著自己寒酸的衣衫,有點無地自容。他們發現自己的存在很討人嫌,這樣的發現讓他們發窘,臉紅一下,再紅一下。然而他們還是不肯走。他們知道自己的走,會令天下皆大歡喜,除了他們自己。思來想去,他們卻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安措自己,於是他們堅持著不走。他們是草民,是農夫,他們顯然沒啥氣節,還不能達到寧肯餓死自己,也不看別人臉色的精神境界。他們以及他們的祖先,從未擎受過被呵護被關照的待遇,這使他們的頭腦里幾乎不存一絲優越的影子,也就使他們從來不會要求別人來尊貴自己,哪怕面對面地給自己擺出一張可以擰出水來的臉,都可以窘一陣子就算了。
否則,還能怎么樣呢?老人說淹過沒死的人,就再也不會被淹死了,卻從沒聽哪位老人講餓過沒死的人,就再也不會被餓死了。自尊與剛強是需要資本的,流民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流民們也就要不起剛強,養不起自尊,儘管他們未必不知道那是好東西。於是,流民們堅忍地賴在那塊土地上,賴得讓人發愁,讓人生氣,也還讓個別地官方因此倒了點小霉。
之五:
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沒有誰喜歡;被侮辱與被踐踏之時,對方卻並不會徵求你的意見。因而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注定是一種被動的心理反應,當你品嘗到這種滋味時,侮辱與踐踏的行為都已實際上發生,不管你有沒有做好準備,無論你是否有接受的習慣。此刻你所能做的,僅是背負著這侮辱與踐踏,去做一番抗爭,還未必一準兒能翻身,因為舉凡侮辱與踐踏的施與都不是空穴來風,都是對方在做了一番認真權衡之後才賞給了你的。
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此刻清政府正在體嘗著,其味道的濃烈,已超出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清政府會按照世事的慣常模式,來做一番抗爭嗎?哪怕做得並不漂亮,哪怕僅是硬著頭皮?
之六:
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一個極具優越感的民族,即使他們出於儒學修養得來的謙遜風度,從不曾說過自己是“上帝唯一選民”之類蹶詞,卻也還是一個很拿自己當回事的群體,很講究自尊,很受不了他人漫無期限的忽視。故而當他們在清前期遭到清廷或明或顯的蓄意貶低,尤其還給貶低到了蒙古族人之後,即使他們本身並不具有覺醒的民族意識,單只是出於個人優越感的實際受挫,也足夠令其難過的了。於是漢族精英們與清廷的貌合神離,一度地收拾無望。這樣的惡性循環,一方面使清廷更為堅定了唯旗系才是重要的忠誠紐帶之認識,一方面也使漢族精英們更為氣餒神傷。反抗之後,失敗之後,倖存下來之後,很多人也就謝絕了社會的呼喚,默然將一顆受傷的心,長久地埋藏於故紙堆中。
蒙元的種族分級,曾催生出很多逸于山林的大畫家,使中國寫意畫得到了空前也很可能是絕後的發展;滿清的種族分級,則令很多漢族精英隱身於書房,做出了大量咬文嚼字的紙上功夫。從清初開始,社會就似乎安靜了許多,或者,也就權當它是安靜的好了,既然能做的努力都已宣布無效,既然所蓄的熱情都已統統花光。接下來乾隆的文字獄,依然使漢族精英們,這些被冠名為知識分子的學而優者,一度地集體失聲。
是世界的變幻,令漢族精英再度睜開了眼睛;是屢戰屢敗的屈辱,使漢族精英再度撿起“學以致用”的古老傳統,並相繼發出了聲音。“移民實邊”即是其一。
之七:
於是,一年年地,他們一步步往北走,南來的春天一寸寸緊攆著,若被超過了,在他們進入東北之時,可能就已經下過了幾場陣雨。他們或者受僱於土地持有者,繼續乾耕種的老本行;或者留在正蒸蒸日上的城市裡,嘗試些新鮮的行當。總之他們不會讓自己閒著。他們大多只帶有一身力氣,也大多只有一身力氣可資出賣。好在東北正急缺力氣,他們閒不著。
想來平日裡也少不了受些委屈,遭些挫敗,只是身邊沒有女人,這委屈和挫敗也就沒辦法轉化。他們應該運用過各種方法,來嘗試著讓自己保持振作,振作在異鄉,這是尤其的必要。他們得讓自己時刻擁有健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生氣蓬勃。他們將時間分劃成兩塊,一塊用來流汗,另一塊用來睡覺,如果有夢,夢也可以參與到睡覺中來。他們活得如此平常,或者已很粗俗,卻從來也不會感到內疚。他們想著好訊息,盼著沒有壞訊息。他們討厭也打怵戰爭、饑荒和瘟疫,知道它們哪一個都不會戴著花兒來,會讓他們很難好好安排。他們就好好地活在暫且還沒有戰爭、災荒與瘟疫的日子裡,期待著它們永遠也別再找上頭來。
秋深深的了,冬天緩慢地來了,他們將所有的工錢貼身裝好,讓它浸著身體的熱氣。家裡的老婆和孩子或者還有高堂,都在等著,等著他,和他的工錢;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工錢,都最好不要出半點差錯。帶著所有工錢回家,這是他們的幸事,相對於1931年之後的華北勞工而言。九一八事變之後求生於東北的華北農民,後來已發展到大多只被允許攜50元回鄉,而不能是所有。偽滿洲國的主子日本人說:“聽說漢人有把大部分所得工資帶回故鄉的習慣,這也許會有利於他們的故鄉,但滿洲的購買力不會提高”。對中國人總是把工錢帶回家裡的習慣,日本人顯然不快,更不解。
好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到來。他們早已習慣於帶錢回家,幾乎沒有人問過這是什麼理由。還要理由么,她已經在家守望了整整一年?或許她也早已習慣於這種守望。她侍弄家裡的菜園或者幾畝薄田,侍候家裡的老人或者幾個孩子。她應該很少哭或者從來不哭,現實生活有理由讓她不再天真和幼稚,還能相信眼淚和哭泣的效用。她在等待中麻木於負重,也在等待中漸漸老去。等待是她的生活常態,就如奔波是他的生存必需。
然而他們還是會盼著早一點相聚,哪怕不斷的交談從來就不是他們必要的相處方式;獨自一人的生活,以及生活的長期窘迫,早已縮萎了他們各自的辭彙。他們也還是會盼著一起過年,哪怕年節的喜慶如若不足,他們也從來不會以幽默人為地製造出一點點來。他們只是盼著相聚,盼著在一起過年,沒有明確理由,只受習慣驅使,就能保證他們年復一年地這樣過下去。每一個冬天,都使他們溫暖,他們手頭有點兒錢,又守在一起。她屋裡屋外地忙乎,他心滿意足地休息。
再一個春天就要來了。他打點行襄,她說:你帶我走。他短暫的錯愕,始才感覺到這樣的打算,已經有了實現的可能。
風輕快地吹著,裹挾著輕浮的塵。風裡有成群的人,在朝一個方向走。他們發現自己的嘆息短促而稀少了很多,儘管他們比往年多了幾個孩子需要照顧,可是也比往年多了一個女人來照顧自己。一顆眼淚如果掰成兩瓣,苦澀原來也會減掉一半。在生活的困厄里,倘若不主動尋求改善,就有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厄,尤其是,當他們的困厄並不足以引發政府的罪感,不管這種罪感政府是多么的應該具有,他們的困厄也就更需要由自己來解決。此刻,他們已經在主動地尋求解決了,不是么?
他不再是候鳥,犁杖與鋤頭之外,也還將爐灶也安置在了東北大地上,哪裡有青青的炊煙升起,哪裡就是家。女人的雙手顯示了神奇,讓一間粗糙的土坯房或草房,也或許只是一間半地穴式的地窨,都裝滿了濃郁的家的氣息。女人又借來幾枚雞蛋或者鴨蛋或者鵝蛋,20幾天過去,家的氣息里也就有了家禽的贊助,它們一天天低吟淺叫著,蹣跚地,在院裡院外兜著彎兒,描畫出一個個小心翼翼的希望。他早出晚歸地流著汗水,她則仍然忙乎於屋裡屋外,偶爾,也會在沒有報時鐘聲的夜裡,想一想家鄉老屋的後園子裡,此刻有沒有新的蔥芽或韭芽發出來。
圖書後記
人的苦難有多種由頭,社會財富的分配失當是其一;社會財富的分配失當有多種表現,人的苦難是最直接最迅捷的後果。
在以土地為主要財富來源的年代,土地的所有狀態就是衡量社會財富是否分配失當的重要標尺,倘若這標盡嚴重失衡,人的苦難就避不可免,症狀是飢餓、動盪與流浪。基於求生本能,受難的人會自發以遷徙來適應客觀情境,試圖找到一個生活的出口,無論這樣的目的能否達成,移動也由此成了大眾的生存狀態,哪怕只是一度。
解讀綿延於整個清朝及民國前中期的關內移民行為,僅是對一樁歷史事件的企圖破譯,即使問題不大會出錯,也不必對答案抱有與真相嚴絲合縫的奢望。既為史,即屬過去,對過去事項的任何一種解釋,縱力求審慎也仍難擺脫揣測性質,充其量減少些許誤差而已。同理,若世間傳來一種聲音,聲言自己對歷史的解析最為恰切,無論如何都似乎不妥,被詮釋者的所處境況尤其心理,都已是一種永無對證。事實是不管如何追求客觀,在對歷史的回顧中,都要多多少少摻和進現時的生活體悟,亦屬正常,畢竟歷史的價值之一是要令人自省,儘管並非自省的技藝不曾丟失,就能將生活的現實難題逐個解決。
如果說人們生存的不確定性、不可靠性與不安全性,是所謂後現代社會的特徵,那么在“闖關東”的移民身上,或許有理由發現這樣的特徵其實早已存在,時下僅是將其普世化與明朗化罷了,那已經成為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闖關東”的移民,以東北大地為生活的出口;後現代的人類全體,則至今還沒有找到生命的歸宿。
——歷史與現實,有很多機會彼此憐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