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 者: 鄧建鵬 著
叢 書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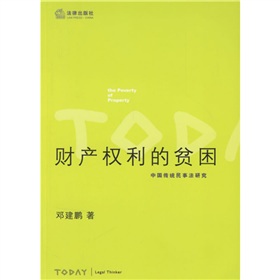 財產權利的貧困:中國傳統民事法研究
財產權利的貧困:中國傳統民事法研究內容簡介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鄧建鵬君的第一本法律史學專著付梓,囑託我寫篇序言。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因為我們有江西同鄉、燕園校友的緣份,似乎或多或少也有些對樂平洪岩鎮出身的洪皓、洪邁父子道德文章的共通興趣,另外還有因京都大學法學院教授、老朋友寺田浩明從中介紹而接上聯繫的一段佳話。仔細閱讀書稿之後,我發現儘管題目很宏大,乍一看容易給人以史論色彩太濃的印象,但作者其實非常重視史料的梳理和經驗性分析,考據、記述、推演、比較以及法理上的推敲論證等都不乏足可稱道的優點,字裡行間還飄溢著贛南“文鄉詩國”獨特的靈氣。順便加個註腳,迄今為止我與建鵬還沒有任何晤談交往,故此處評價絕非出自私誼或礙於情面。
眾所周知,傳統的國家秩序以義務為本位而缺乏權利保障,這個學術命題並不新穎。從官民對立的視角來考察社會結構,就分析框架而言甚至還會引起“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慨,畢竟在近一二十年間,中國法制史研究的範式和方法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鮑爾?科恩提倡“就中國論中國”的視點而擯斥“傳統對現代”的兩分法,黃宗智認為中國的司法運作存在介於官與民兩者之間的“第三領域”,杜贊奇試圖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建構某種社會史學的新體系。但是,建鵬卻能以舊瓶裝滿香醇的新酒,並指著那似乎已塵埃落定的地方告訴人們:“甚囂,且塵上矣。”定睛一看,果然。進而有“何故惹塵埃”一問。於是作者不慌不忙地把近年發現的張家山漢簡、走馬樓吳簡、黃岩訴訟檔案、筆記、卷宗等都逐一展示出來,與典章制度、經史子集以及當代研究成果等互相對照和印證,並別出心裁地作出某些饒有新意的闡發或者判斷。
例如,關於歷史上的民事權利觀念,本書以農耕社會最基本的財產——田宅為考察對象,把焦點對準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最突出的特點——早熟的土地私有制和不動產轉讓關係,並始終扣緊這樣的核心問題:為什麼民間的土地權利不能擺脫政府的頻繁滲透、干預甚至掠奪?作者根據史學界的定說和新知指出.古代中國土地名為私人所有,實際上是權原為國家壟斷。也就是說,王朝是一切土地的終極所有者,對土地的支配是帝室財政收入的最穩固的基礎。在這樣否定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條件下,地主和自耕農享有的其實大都只是永久性承包經營權,真正的私人土地,其規模以及對民生整體的影響並不很大。土地權益的買賣也受到國家在產業上抑制兼併、在分配上調整貧富等政策的制約,不是完全自由的。
在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所謂“官有”與“私有”、“民富”與“民窮”不斷顛倒轉化的循環系的記敘。雖然文藝復興期間的義大利分割所有權理論提出過“下級所有權(dominium utile)”和“上級所有權(d0miniumdin~tum)”對峙的制度框架,但兩者的權利義務關係是明確的、固定不變的.而中國的情形則不同,“損有餘、補不足”的財富輪迴周流不僅得到制度上的承認,而且得到政策上的鼓勵。正是土地享有關係的易學式動態結構,使得某種關於確定的、穩固的甚至絕對的私人權利觀念無從發育,也使得國家沒有必要僅依賴徵稅作為行政財源,還可以採取其他獲利方式來滿足維持官僚制運作的需要。從而中國的歷代王朝缺乏為了徵稅而不得不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或行政服務作為代價的動機,在一定範圍內,也就免除或者減弱了人民要求派代表參與政治決策的潛在壓力。因此,作者根據史料分析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地產為身份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所以“財產權在中國政治話語中扮演了一個消極的角色”。
從已有的實例和敘事脈絡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傳統的土地權利基本上是按照交換價值(其主要表現形態先是承佃契約,後為買賣契約)來定義的,B.Windscheid所強調的意志之力受到極大的限制。與此相關,中國的經濟觀也始終以場地坩租式的營利為基調。限制國家與庶族地主、自耕農之間交易條件以及國家機關憑藉暴力改變交易條件僅限於生存權、承包經營協定以及強者的仁慈恩惠之類的構想。在這樣的意義上,國家本身就構成一座超級“收租院”,流露出非常明顯的營利氣質,往往不大顧忌“與民爭利”的指責。除此之外,國家的營利性還體現為通過官營或專賣等方式徹底壟斷具有高額利潤的行業,即使在向社會提供均輸、平準、賑災等公共物品(政策性舉措)之際,也總是採取商業化操作的行為方式。實際上,從周禮的制度設計開始,“面朝、後市”就已成定局,形成某種與市場經濟頗親近的專制主義政治結構,也導致公私不分的弊端。既然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那么臣民也就比較難以產生出那種“以犧牲小我而實現大我”的大公無私精神以及社會責任感,即使有也不多見或者很淡薄。
本書的敏銳之處是透過從均田制到土地使用權交易自由的歷史現象,看清楚了私權與公法之間關係的一個樞紐或者關鍵,即稅收的存在方式。按照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比喻.“國家就像一個以稅金為價格而販賣治安的商社”,似乎也能適用於中國的歷史研究。由此可以推論,既然中國王朝的財政不必完全依賴徵稅,那么人民就該廉價購人行政服務;相反,假如稅賦頗苛重,那么人民就該要求高質量的行政服務。但是,這樣兩種事態實際上卻都沒有發生。為什麼?根據我對本書內容的理解,正因為中國統治者歷來採取“利出一孔”的壟斷政策,獨占了對土地的支配權以及對高利潤產業的經營權和專賣權,所以王朝財政收入具有直接的和確定不移的來源並可以按照當局意願和監控能力達到最大化。然而,“以田為累”等史實卻表明,政府汲取能力的過分強化和任意化也有可能反過來,破壞稅收與財政之間合理關係的基礎以及國家的其他制度條件。國家壟斷土地和產業還會引起一個思維方式上的問題,就是讓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按照不是"人民養政府,而是政府養人民”的邏輯去說話、辦事,無從真正形成和落實“公僕”的職責是提供行政服務之類的觀念,也很難確保用於公共事務(如審理訴訟案件)的財政開支款項。
在通過土地考察實體性私權的生態之後,作者把視線投向程式性的訴權,特別是“健訟”現象與嫌訟傾向並存的悖論。在這裡,饒有趣味的是關於在中國特色的稅收之下財政支出也頗有不同之處的潛台詞。按理說,政府既然可以最大限度獲得稅賦,而訴訟幾乎是政府向人民提供的唯一的日常性服務,那么司法經費應該很充足才對。可是由於國家壟斷土地和產業,並沒有向私人集資(徵稅)以滿足公共需要同時作為補償向私人權益提供制度化保護和服務的觀念,結果形成了所謂“權力最大化、責任最小化”的奇異格局,出現了這樣的咄咄怪事:司法經費少得可憐,另行徵收卻又難以公然出口(據建鵬的考據,正式的訴訟收費制度直到1907年才終於設定),為了維護“法無二解”的原則還得嚴格禁止訴訟當事者自己委託代理人,有關當局其實也根本不情願審理只涉及私人利益的民訴案件。正是在民訴之門過於狹窄的背景下,當事人為了引起政府重視,打破官吏不作為的沉悶氛圍,不得不誇大糾紛的嚴重性,把認定私人權利的問題轉化成事關公序良俗的重案,就像當今上訪民眾中流行的“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諺語一樣。這就很容易誘發誣告和教唆,也很容易為取締訟師的命令、罰則提供各種口實或者正當性根據。
在稅收和財政的關係這樣的公法層面上分析作為私法現象的民事法權和民事訴訟,是本書提示的一個很新穎的視角。正因為中國的傳統是公私不分或者公私區隔不徹底,所以幾乎不存在純粹私法意義上的問題意識,大多數制度化作業都停留在私權與公權的交會處固步自封。私權為了避免被侵害或者尋求救濟,也不得不主動地往自己身上塗抹一些公法色彩。例如,通過“掛靠”國家權力的方式爭取重視和保護,於是更給官吏的恣意干預以及對民間利益的鯨吞蠶食留下了方便之門。在智慧財產權方面也如此。作者通過豐富的實例和細緻周到的分析證明,雖然民間早就存在保護著作權的要求,但政府輕視私人合法利益的保護。而只注重與社會秩序相關的出版管制法令,其結果,人們出於無奈不得不致力於“將私人利益塗抹上與王朝利益一致的色彩”,說得難聽些也就是假公濟私。
看得出來,在收集史料並進行梳理、分析、推論方面,作者的確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因此實例和前人學說的引用顯得豐富多彩。有關描述、解釋以及個人見解也多有啟迪,很值得參考。就各部分的主題和論述內容而言,雖然已經存在許多先行研究的成果。但這本著作在稅收、財政開支、市場競爭機制等不同層次探索公與私、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公權私有化和私權公有化的雙重變異中追問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問題,足以給人別開生面的印象。毋庸諱言,該書並非完璧無缺,或多或少還存在某些需要進一步推敲、改善的地方。然而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技術性的微瑕,無損於整體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強烈的現實關懷促使作者把治史與對法與社會發展的沉思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注重客觀因果關係的實證以及規律性現象的追究。相信讀者能從中獲得很多助益。
·收起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