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安伯托·艾柯
安伯托·艾柯 艾柯誕生於義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亞歷山大,這個小山城有著不同於義大利其它地區的文化氛圍,更接近於法國式的冷靜平淡而非義大利式的熱情漾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這種環境塑造了他的氣質:“懷疑主義、對花言巧語的厭惡、從不過激、從不做誇大其詞的斷言”。Eco這個名字據說原是一位“先知”給他祖父取的名字,是ex caelis oblatus 的首字母縮寫,意為“上天所賜”。艾柯的父親是一名會計師,祖母達觀幽默,從她那裡艾柯獲益良多。當時的義大利天主教氛圍濃郁,自20年代興起的新托馬斯運動方興未艾,以致於13歲的艾柯就參加了義大利天主教行動青年團,還在方濟各修會做過一段時間的修道士。正是這段經歷使他接觸了天主教的哲學核心——托馬斯主義。後來,艾柯進入都靈大學哲學系學習,在美學教授、存在主義哲學家路易斯·帕萊松(Luigi Pareyson)的指導下,於1954年完成了博士論文《聖托馬斯的美學問題》,經過修改的論文於1957年出版,更名為《托馬斯·阿奎那的美學問題》(The Aesthetics of Thomas Aquinas,1956),是為艾柯的第一部專著。這本著作加上數年後出版的另一部專著《中世紀的藝術與美》(Art and Beauty in the Middle Ages,1959),初步奠定了他作為“中世紀學者”(medieval scholar)的地位。
個人生活
在都靈大學
 安伯托·艾柯
安伯托·艾柯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是一位享譽世界的哲學家、符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小說家。艾柯出生於義大利皮埃蒙特大區亞歷山德里亞。其父古里奧是一名會計,一生中曾經被政府徵召參加了三次戰爭。在二戰期間,埃可與母親喬瓦娜搬到皮德蒙特山區的一個小村莊居住。埃可共有12個兄弟姐妹。艾柯年輕時尊從父願進入都靈大學學習法律,隨後輟學,不顧父親反對而改學中世紀哲學與文學。於1954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有關基督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納的研究。其後埃可成為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的文化部編輯,同時在都靈大學任教。此間,艾柯與一些前衛藝術家有密切的接觸。這些人這對他以後的寫作有重要的影響。
在新聞傳媒界
就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由於一批左傾的青年學生與教皇發生矛盾,艾柯與天主教行動青年團決裂,研究的重點也從托馬斯·阿奎那轉向詹姆斯·喬伊斯。畢業後不久,艾柯進入了新聞傳媒界,在位於米蘭的義大利國營廣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負責編輯電視文化節目。這份工作為他從傳媒角度觀察現代文化提供了平台。同時,他開始與一批前衛的作家、音樂家和畫家交往。5年之後,他離開電視台,到米蘭的一家期刊社當了非文學類欄目編輯,這份工作他做了16年之久。這期間,他也為另外幾份報刊撰稿、開設專欄,成為義大利先鋒運動團體“63集團”(Group 63)的中流砥柱。
學術概述
艾柯的這些雜文作品起初與羅蘭·巴特的風格比較接近,但在研讀了巴特的著作之後,他深感“無地自容”,於是轉向更為綜合的風格,將前衛文化、大眾文化、語言學和符號學融為一體。在1962年,他發表了成名作:《開放的作品》(TheOpenWork,1962),憑藉此書成為義大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主將。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從1964年開始,他成為米蘭大學建築系教授,講授“可視交往”(VisualCommunication)理論,關注建築中的“符號”問題,也就是建築傳達特定社會與政治含義的方式。1965年,他的論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結合方法》發表於法國符號學陣地《通訊》雜誌上,意味著他已經躋身於以羅蘭·巴特為核心的符號學陣營。同一時期他又將《開放的作品》中有關詹姆斯·喬伊斯的部分修改出版,是為《混沌詩學:喬伊斯的中世紀》(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 The Middle Ages ofJames Joyce,1966)。這種將《007系列》與《芬尼根守靈夜》平等對待的態度,顯示出艾柯非同尋常的廣闊視野。
成名作
艾柯的雜文作品起初與羅蘭·巴特的風格比較接近,《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1962),憑藉此書成為義大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主將。
 誤讀
誤讀 1962年9月,他與Renate Ramge結婚。Renate Ramge是一名德國藝術教師。
除了嚴肅的學術著作外,著有大量的小說和雜文,長年給雜誌專欄撰寫以睿智、諷刺風格見長的小品文。最馳名的作品為小說《玫瑰之名》與他的雜文集。艾柯現任教於博羅尼亞大學,居住在米蘭。
個人作品
文學作品
《啟示錄派與綜合派》
1964年,羅蘭·巴特發表《符號學原理》,標誌著符號學進入新階段。同年,馬爾庫塞發表《單向度的人》、麥克盧漢發表《媒體論》,為學術界開闢了媒體符號研究的新領域。也是在這一年,艾柯發表了論著《啟示錄派與綜合派》(Apocalyptic and Integrated Intellectual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ories of Mass Culture,1964),自覺嘗試使用符號學方法研究媒體文化問題,這標誌著他已經站在了義大利學術界的前沿。此前,他已經在都靈、米蘭、佛羅倫斯等地的大學講授美學。
《不存在的結構》
到1968年,《不存在的結構》(The Absent Structure)出版,這是他數年研究建築符號學的成就,也是他第一部純學術化的符號學著作,奠定了他在符號學領域內的重要地位。進入70年代,艾柯的成就進一步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肯定。1971年,他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創立了國際上第一個符號學講席;1974年他組織了第一屆國際符號學會議,擔任學會秘書長;1975年發表符號學權威論著《符號學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1975,英文版本在1976年出版),並成為博洛尼亞大學符號學講座的終身教授;1979年用英文在美國出版了論文集《讀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1979)。此外,艾柯還在美國西北大學(1972)、耶魯大學(1977)、哥倫比亞大學(1978)等著名院校授課,以符號學家聲名遠揚。
《玫瑰之名》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早在1952年,艾柯已經有意寫作一本名為《修道院謀殺案》的小說,但直到1978年3月他才正式動筆。他將小說背景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中世紀,並從一篇中世紀的散文作品中找到了合適的題目。1980年,長篇小說《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出版,出版商原計畫印刷3萬冊,沒想到銷量很快達到200萬冊,迄今則已經翻譯成35種文字,銷售了1600萬冊。《玫瑰之名》的故事發生在14世紀,當時教權與王權、貴族與平民、信仰與理性正處於複雜的鬥爭狀態,博學而開明的威廉修士帶著見習僧阿德索來到一所著名的修道院,為即將召開的高層會議做準備。但就在他們抵達的前一天,修道院裡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兇殺案,修道院院長委託擅長推理的威廉進行調查、找出元兇。而在以後的數天裡,每天都有新的離奇血案,原本已經被異端和欲望搞得烏煙瘴氣的修道院,氣氛變得日漸陰森恐怖。威廉推測兇手可能是從《聖經·啟示錄》中得到殺人的靈感,他把注意力集中於修道院的圖書館——這是當時西方世界最大的圖書館之一。憑著對符號、象徵、代碼的深刻理解,憑著在哲學、文字學、版本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深厚造詣,威廉發現了真兇,揭開了謎底。兇手是個博學而虔誠的、雙目失明的老修士,他的殺人動機非常別致:他要保護一本禁書,不希望被他人閱讀,因為這本書可能會摧垮整個神聖的基督教世界,而這本書就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下卷。此書1986年被改編為同名電影,由拍攝過《熊》、《情人》的法國大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影壇巨星肖恩·康納利主演,創下極佳票房紀錄,轟動全球,更一舉囊括英國影藝學會、法國愷撒獎、德國電影獎、義大利國家影評人獎等多項殊榮。《玫瑰之名》使“安伯托·艾柯之名”蜚聲世界,躋身於第一流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家之列。有意思的是,《玫瑰之名》一出,各種研究論文和專著源源不絕,特別是關於“玫瑰之名”的闡釋幾乎構成一場20世紀末期的“闡釋大戰”。由於艾柯此前就關注“開放的作品”、“讀者的角色”等等問題,對闡釋學頗有心得,加之一直關心研究者對自己作品的分析,所以他不斷站出來澄清、挑戰或是回應,於是有了《;備忘錄》(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1984)、《詮釋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1990)等專著。最著名的事件是,1990年劍橋大學丹納講座(Tanner Lectures)就闡釋學問題邀請艾柯和著名學者理察·羅蒂(Richard Rotry)、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以及克利斯蒂娜·布魯克-羅斯(Christine Brooke-Rose)展開辯論,最後結集為《詮釋與過度詮釋》(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在1992年出版,一時洛陽紙貴。
《傅科擺》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作為小說家的艾柯繼《玫瑰之名》以後,又陸續發表了另外四部長篇小說:《傅科擺》(Foucault’s Pendulum,1988)、《昨日之島》(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1994)和《波多里諾》(Baudolino,2001),部部暢銷,好評如潮。為此,當代文學史往往將艾柯視為與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和伊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齊名的、20世紀最優秀的義大利作家。艾柯最新小說《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lamma della regina Loana)
《傅科擺》的主人公卡素朋是位治中世紀史的專家,他的朋友貝爾勃和狄歐塔列弗則是一家學術出版社的資深編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愛好:研究中世紀聖堂武士的傳說。根據掌握的一份神秘檔案,他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每過120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歐洲各地的36名聖堂武士將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們手上斷簡殘篇的信息,以便掌握一種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類前途的巨大能量。據說西方歷史上的種種神秘社團,比如薔薇十字會、大白兄弟會、共濟會等等,一直在追求著這種比核武器還要恐怖的能量。據說莎士比亞、培根、馬克思乃至愛因斯坦等歷史名人,也都是聖堂武士的傳人。卡素朋的女友莉雅通過研究檔案得出另外的結論:根本就沒有什麼聖堂武士的秘密,那份檔案不過是個送貨-購物清單。但已經走火入魔的三人根本不相信她的解釋,同時,許多“要將秘密知識據為己有的人”開始關注此事。最後,狄歐塔列弗死了,貝爾勃因之喪生,卡素朋知道自己也難逃毒手——雖然所謂的秘密不過是他們三人自己的發明。
《昨日之島》
《昨日之島》的故事發生在1643年,一艘擔負著尋找180度經線任務的商船遇到海難,年輕人羅貝托成了惟一的倖存者,他被浪潮衝上了另一艘棄船達芙妮號。羅貝托患有疑心病、妄想症和畏光症,所以儘管不遠處有一個美麗的小島,但是羅貝托可望而不可及。他勉強依靠達芙妮號上殘存的東西維生,每天靠書寫打發時光。他寫情書,寫回憶、最後演變成寫小說、寫一切樣式和內容的小說,甚至還幻想出一個弟弟“費杭德”……真實與虛構漸漸分不出界限。到最後,他離開達芙妮號,奮力游向未知的結局。
《波多里諾》
《波多里諾》的故事發生在1204年,十字軍東征中君士坦丁堡遭到劫掠,混亂中主人公鮑都里諾救了拜占庭史學家尼基塔,在隨後的避難途中,鮑都里諾向尼基塔講述了自己傳奇的經歷。他自稱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雷德里克收養的義子,皇帝的舅舅奧圖是他的老師。在巴黎求學的時候,鮑都里諾和朋友們想像出一個“約翰大主教統治的遙遠的東方王國”,他還把親生父親的破木碗當成“聖杯”獻給養父,以說服皇帝讓他們去尋找那個構想出來的國度。一路上他們經歷了重重神話和傳奇里才有的奇境……最後,尼基塔相信鮑都里諾是個說謊者,他的經歷都是編造出來的,但畢竟,這是一個偉大的故事。
由中年步入老年的艾柯視野愈加擴大,在學科與學科之間、歷史與現實之間、學院與社會之間遊刃有餘地縱橫穿梭。作為學者的艾柯一方面修改完善了自青年時代起就深為關注的中世紀研究;另一方面繼續完善其符號學-闡釋學理論,延伸或部分修正了昔日的觀點。他陸續發表了《符號論與語言哲學》(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84)、《完美語言的探索》(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Language,1993)等專著,編著了近20本書籍,並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1984)、劍橋大學(1990)、哈佛大學(1992-1993)、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996)等一流名校講學,還獲得了全世界二十多個大學的名譽博士稱號。與此同時,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艾柯也極為活躍,先後發表了《帶著鮭魚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1992)、《康德與鴨嘴獸》(Kant and the Platypus,1997)、《五個道德斷片》(Five Moral Pieces,2001)等亦莊亦諧的雜文集,甚至為兒童寫了兩部作品。自1995年始,更是積極投身於電子百科辭典的編修工作,主持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部分,並在各地發表題為《書的未來》的長篇演說。
學術論文雜文
《托馬斯·阿奎納斯的審美觀念》(1988年,Revised) ( Il problema estetico in San Tommaso,1956年)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中世紀藝術與美學》(1985年) (" Sviluppo dell'estetica medievale" in "Momenti e problemi di storia dell'estetica",1959年)
《開放的作品》 (1989年) (from the 1976 edition of Opera Aperta,1962年,with other essays added).《誤讀》 (1993年) (Diario minimo,1963年)
《世界末日的推遲》(1994年) ( Apocalittici e integrati,1964年; partial translation,with other texts added)《詹姆斯·喬伊斯的詩文》(AKA The Aesthetics of Chaosmos) (1989年) ( Le poetiche di Joyce,1965年)
《超現實旅行》(AKA Faith in Fakes) (1986年) ( Il costume di casa,1973年, Dalla periferia dell'impero,1977年, Sette anni di desiderio,1983年)
《符號學理論》(1976年)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1975年)
《讀者的作用》 (1979年)《〈玫瑰的名字〉後記》(1984年) ( Postille al nome della rosa1983年)
《符號學與語言哲學》(1984年) ( Semiotica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1984年)
《翻譯的局限性》(Advances in Semiotics)" (1990年) ( 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1990年)
《帶著鮭魚去旅行》(1998年) (Partial translation of Il secondo diario minimo,1994年)
《翻譯與過度翻譯》(1992年)(with R. Rorty,J. Culler,C. Brooke-Rose; Edited by S.Collini)
《尋找完美的語言》(The Making of Europe)" (1995年) ( La ricerca della lingua perfetta nella cultura europea,1993年) on auxiliary and philosophical languages.
《悠遊小說林》"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1994年)"Incontro - Encounter - Rencontre (1996年) (in Italian,English,French)
《信或不信? 》( In cosa crede chi non crede?(with Carlo Maria Martini),1996年).
《論道德》 ( Cinque scritti morali,1997年)《康德與鴨嘴獸:論語言與認知》( Kant e l’ornitorinco,1997年)
《不靳的語言》(Language and Lunacy" 1998年)
《論翻譯》(2000年)
《大鼠還是小鼠?》(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 2003年)
《論美》( Storia della bellezza,2004年; Edited by U.Eco,coauthored by Girolamo de Michele).
《論文學》( Sulla letteratura,2003年)
中文譯本
【1987年】
林泰等翻譯的《玫瑰之名》由重慶出版社出版,是艾柯作品首次進入中國。
李幼蒸編譯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由三聯書店出版,內收艾柯文章一篇。
【1988年】
閔炳君翻譯的《玫瑰的名字》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1990年】
盧德平翻譯的艾柯學術著作《符號學原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6年】
張學斌文章《寫小說的符號學家》在《讀書》11月號發表。
【1997年】
王宇根翻譯的艾柯學術著作《詮釋與過度詮釋》由三聯書店出版。
【1998年】
南帆文章《闡釋與歷史語境》在《讀書》上發表,對艾柯的闡釋學作了介紹。
【1999年】
李幼蒸的《理論符號學導論》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中列艾柯一章。
王東亮文章《艾柯的‘小辭’》在《讀書》上發表,對艾柯的散文隨筆作了介紹。
【2001年】
作家出版社引進台灣謝瑤玲翻譯的《玫瑰的名字》及《昨日之島》。
日本學者筱原資明的《埃柯:符號的時空》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2年】
李幼蒸的《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更名為《電影與方法:符號學文選》,三聯出版。
《當代外國文學》第3期發表《恩貝托·埃科訪談錄》。
【2003年】
謝瑤玲翻譯的《傅科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讀書》2003年第3期,發表了馬凌的文章《玫瑰就是玫瑰》,介紹艾柯的闡釋學理論
【2004年】
馬淑艷、殳俏等翻譯的艾柯文集《帶著鮭魚去旅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台灣張大春文集《小說稗類》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含評論艾柯的文章兩篇。
艾柯來中國主持了國際符號學會議,在國內學者中開始有了較強的反響。
【2005年】
劉儒庭翻譯的艾柯成名作《開放的作品》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俞冰夏翻譯的《悠遊小說林》由三聯書店出版,《詮釋與過度詮釋》再版。
【2006年】
王天清翻譯的艾柯學術著作《符號學與語言哲學》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7年】
中央編譯出版社3月推出《美的歷史》,譯者彭懷棟(台灣)
上海譯文出版社3月推出《波多里諾》,譯者楊孟哲(台灣),並將陸續再版小說《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島》和《傅科擺》,以及艾柯隨筆 《密涅瓦火柴盒》(La bustina di Minerva)新作《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lamma della regina Loana)等。
學術觀點
埃可的學術作品強調中世紀美學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差異。對於此,他如此說:“(中世紀美學)在理論上是一個由幾何與理性構架的有機體,然而在實踐中卻是一種完全不設框架的由形體與意象自然生成的藝術生命”。埃可於1959年發表了他的第二本書《中世紀美學的發展》(Sviluppo dell'estetico Medievale),一舉奠定了他在中世紀研究與文學界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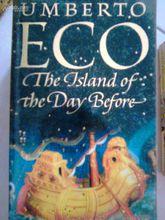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埃可的哲學論著大多都與符號學,語言學,美學與倫理學有關。
重要作品
他的學術性作品有《缺席的結構》(1968年)、《論一般符號學》(1975年)、《神話中的讀者》(1979年)、《關於鏡子》(1985年)、《闡釋的極限》(1990年),以及在各報紙雜誌發表的文章結集《來自帝國的邊沿》(1997年)。《開放的作品》(1962年)被公認為是他學術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艾柯1980年出版第一部小說《玫瑰的名字》(獲1981年斯特雷加獎),1988年又出版了《福科擺》(獲1989年邦卡雷拉獎),1994年出版《昨日之島》。1963年出版《小記事》之後過了三十年才於1992年出版了《小記事第二集》。其他作品還有:《悠遊小說林》(1994年)、《康德和鴨嘴獸》(1997年)、《倫理作品五篇》(1997年)和《謊言和譏諷》(2000年)。
艾柯訪談
安伯托·艾柯是當代歐洲最著名的學者和作家。《劍橋義大利文學史》將昂貝爾托·艾柯(Umberto Eco,1932-)譽為20世紀後半期最耀眼的義大利作家,並盛讚他那“貫穿於職業生涯的‘調停者’和‘綜合者’意識”。艾柯的世界遼闊而又多重,除了隨筆、雜文和小說,還有大量論文、論著和編著,研究者將其粗略分為8大類52種,包含中世紀神學研究、美學研究、文學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符號學研究和闡釋學研究等。而艾柯最引人矚目的,是他在多個世界間輕鬆遊走的能力、還有那不保守也不過激的精神。正是這種能力和精神,使他既感興趣於最經院主義的托馬斯·阿奎那,也熱衷於最現代主義的詹姆斯·喬伊斯;既強調闡釋的力量,又擔心過度闡釋的危害;既能使作品成為行銷全球、印數千萬的暢銷書,也能吸引研究者為之寫出數以千計的論文和專著。
語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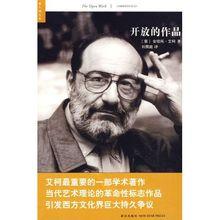 翁貝托·埃可
翁貝托·埃可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年出生於義大利的亞歷山德里亞。博洛尼亞大學符號學教授,住在米蘭,VS雜誌領導人。艾柯身兼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家等多種身分,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記號語言學權威。他的學術研究範圍廣泛,從聖多瑪斯·阿奎納到詹姆斯·喬伊思乃至於超人,知識極為淵博。個人藏書超過三萬冊,已發表過十餘本重要的學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讀者的角色——記號語言學探討》一書。2007年03月15日12:16 《南方周末》記者 夏榆
3月8日北京天氣寒冷,艾柯頭戴黑色禮帽、身穿軍綠呢制風衣夾著黑色皮包步伐快捷地走在冷風中,風吹動的時候,軍綠的風衣勾勒出艾柯高大穩健的身軀。同行的中國女翻譯打趣艾柯酷得像義大利黑手黨,艾柯迎著冷風放聲大笑,笑聲硬朗,中氣十足。
開始採訪之前,記者把隨身攜帶的艾柯的7本中譯本放在和艾柯相對的沙發扶手間。看到那些裝幀不同、面貌各異的書,艾柯很高興,一本一本地翻開看。艾柯隨身帶一隻“掌中寶”計算器,一沓填得密密麻麻的表格。艾柯說這些表格記錄他在各個國家能見到的不同語種的艾柯作品,很多是盜版,一旦發現就記錄在案。
“我想拿走這些書,很多書我自己都沒有見過。”
記者:遇見盜版書您會生氣嗎?通常您怎么處理書被盜印的情況?
艾柯:我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書被盜版),可能很多。我是個自由派,如果是出於教育的目的,給年輕人、給學生看的,用就用了,著作權我不追究。不過還是希望出我書的人能跟我聯繫。
以前有日本的譯者來義大利跟我溝通,我非常高興,他問了很多問題,讓我給他解釋某些詞是什麼意思,儘管我不會說日語,我還是很高興。多種語言我都不會,比如俄語、匈牙利語,但這些譯者很多都跟我進行過溝通,我很高興。很遺憾,中國的譯者還沒有跟我進行過這樣的溝通。也許在以前沒有國際公約,不能按照國際慣例進行溝通,不過現在有這么多的交流方式,我希望中國的譯者也能夠跟我進行溝通。
記者:世上大概有兩類作家,一種是像卡爾維諾這樣的作家,另一種像馬爾克斯那樣的作家,前者更關注文學形式或者文體試驗,後者更關注現實人生和社會公共事務。您認為哪種作家更重要,更有價值?
艾柯:我不覺得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卡爾維諾第一部小說其實更多的是關於政治、關於戰爭的,他在政治上很活躍。他最後一部書是純文學的,但我不覺得這種純文學就對現實沒有意義。有很多評論說我的一些小說題材跟現實無關。有些人就說《玫瑰的名字》是歷史小說,因為我寫的是中世紀,但我是借用一個歷史題材反映義大利現實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記者:在中國大陸有個說法是,“文學已死”,您經歷過半個世紀的寫作,了解過世界各種文學潮流,您怎么看“文學已死”的說法?
艾柯:我今年75歲了,在過去的60年間這樣的說法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會兒說“文學死了”,一會兒說“小說死了”,更瘋狂的說法是“書已經死了”,但事實上,我還不斷地在閱讀、在寫作。我認為那樣的說法非常愚蠢。
記者:網際網路的出現還是對文學構成了影響,網際網路的存在對傳統閱讀方式的挑戰也是事實。您怎么看網際網路,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艾柯:就像不會因為有了飛機就說汽車死了一樣,網際網路對於閱讀的影響也應該分成兩類,對像我這樣的學者的影響和對普通人的影響,我認為是有區別的。就像人們看電視一樣,很多人其實成了電視的奴隸,很多人像呆子一樣看電視。作為一個學者,或者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作家,我是利用網際網路而不是被網際網路利用的對象。我把網際網路當成一個工具,通過它獲得信息,甚至我有大量的書也是讀者通過網際網路來購買。網際網路促進了書的流通,原來書的銷售要通過書店,現在可以通過網路書店訂購,但這跟青少年玩電子遊戲、玩網路遊戲,跟成年人的色情娛樂完全不同。很多人利用網際網路——他不是要找一個女人現實地做愛,他把機器當成做愛的對象,滿足一種色情的刺激。網際網路使一些人完全成為壞信息的受害者,但它對另一些人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網際網路對我而言是一個好工具。
語錄二
“最關心的問題是 怎樣繼續活下去”
記者:您有多種身份,要是請您介紹自己,您怎么說?除了說您是小說家、哲學家和美學家以外,還有一個詞是“公共知識分子”,您是怎樣的公共知識分子?
艾柯:一個大學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會寫小說;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我是一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學裡教書的作家。至於公共知識分子,我在一個州的報紙有一個專欄,寫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上個星期我寫了關於義大利選舉的文章。我已經出版了若干本書,其中就包括到2005年之前所有的這種新聞性評論文章,這本書的其他語言的版本已經出版了,英文版幾個月之後就會出版。還有,比如在今天的會議上,我也作了發言,表達對戰爭的看法,那么在其他的文章當中,我也會對公共領域、政治方面的問題,作出自己的評論和批評。
記者:什麼問題是您目前最關心的?
艾柯: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怎樣繼續活下去,因為我已經很大了。在2001年的時候,我才有了惟一的孫子,我一直很關心這個小孩的成長。我這么關心這個小孩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孩子將來生活的環境比較艱難,因為現在這個世界面臨比如生態的危機,還有其他的問題,隨著我年齡的增大,我越來越悲觀了。
記者:您說悲觀我很意外。看您的書和聽您今天的發言,您的表達和思想的姿態都是強有力的。
艾柯:媒體總是對知識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實到目前為止我認為知識分子對很多事情是無能為力的,好像這座房子著火了,你手頭有一本詩集,但是這個詩集對你來說根本沒有用,你要滅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隊員,詩對你來說,可能以後才會派上用場。對於全世界來說——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可能的情況是,很多地方房子著火了,但他們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沒著火的房子裡捧著詩集看。
記者:您使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精神的變化,以前的知識分子好像不是這樣的,比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像您同時代的薩特、加繆、羅蘭·巴特,還有1990年代的德希達,在社會失去正義的時候,他們會走到街頭表達自己抗議的聲音。
艾柯:並不是薩特自己上街去進行示威,而是那裡已經有人示威了。如果沒有這些人,即使薩特名望再高,他個人也無能為力。你應該問為什麼沒有那么多人——普通大眾上街去遊行示威,而不是說為什麼沒有知識分子去上街示威。
記者:這個問題您可以回答嗎?
艾柯:不要把知識分子的行動和公民的行動混在一起,薩特去遊行是作為一個公民去的,而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去的。作為知識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寫書、為社會和民眾指引未來的道路和方向。但作為公民來講,他有權利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比如有人寫了一份請願書,針對環境污染的問題向政府請願,如果我簽了名,那么我簽名首先是作為一個公民,而不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別人發現我簽了名,才知道我是個知識分子。所以在義大利的大選中,我非常積極地參與,因為我是公民。
語錄三
“誰能清晰地 看見這個世界”
 安伯托·艾柯
安伯托·艾柯 記者:熟悉您第一次中國之行的人清晰地記得您有過“中國沒有城市”的感慨,為什麼這樣說?當時的情景您還能記得嗎?時隔十幾年再到中國,您對中國的印象有改變嗎?
艾柯:“中國沒有像樣的城市”這樣的話我說不出來。可能是阿蘭·貝特教授說過這個話,因為阿蘭在中國丟了行李,這已經是他第二次丟行李,第一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為他丟了行李非常著急,說出這樣的話,我是不太可能講出這樣的話。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當時我的感受是很複雜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 、廣東、北京、西安 、烏魯木齊,然後又回到香港和澳門 ,所以這個行程很複雜,我也很難用很簡短的話來概括。我覺得中國在很多方面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當我到了北京之後覺得就像到了洛杉磯。我只能告訴您我第一次對中國的印象,因為第二次我還只見了記者,別的什麼人都還沒有接觸
記者:這次您到北京作“治與亂”的發言,有學者討論您的講話,有人認為您的講話其實是在支持戰爭,還有人認為,至少您認為後現代戰爭不如古典戰爭,認為古典戰爭還要好一些。
艾柯:我的發言只是說戰爭還沒有消失,到現在為止,要消除戰爭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產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個也都是錯誤。我只是對戰爭的情況作了一個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戰爭。因為我認為戰爭創造了新的平衡這種說法不對。戰爭很有可能導致新的不平衡。現在看來,戰爭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瘋狂,為打擊恐怖主義而投下炸彈,但是炸彈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義者藏身的地方。
記者:您有一本書叫《小記事》,中譯本叫《誤讀》,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經常經歷“誤讀”?
艾柯:這是書的名字,但是看你怎么理解這個詞。誤讀,對我來說是經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來講我反對戰爭,但結果還是被誤讀成贊成戰爭。如果我寫一本哲學類的書,我寫的是這樣的東西,別人說是另外的東西,我必須馬上說“不”。但遇到簡單的問題,比如說剛才那兩種誤讀,贊成戰爭或者說中國沒有城市,這都無所謂,我不願意辯解。
如果我寫小說或者哲學,別人對我的本意有誤解的話,通常有兩種可能性:我不這樣認為,但你有權利那樣認為。我的本意是說,我不想跟別人說你應該怎么理解我,或者你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許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還深,這也說不定。有時候我覺得書比主人更有哲學性,更像知識分子。我的譯者也經常這樣問我,一個字我用的意思是A還是B,我的本意是想用A,但是譯者用B的時候,比我原來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準確。
記者:您長久地生活在學院裡面,作為作家,大學的體制更有利於您的創作嗎?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一樣,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種類,有的作家寫小說,有的作家寫詩,有的還寫別的。大學不一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組成,不是說大學裡面的人都是天才,可能有些人還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學教授,但是並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學裡。我在50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有的學者在講課之餘踢球、彈吉他,我是用來寫小說。做學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讓我快樂的事情是做一個作家。18年來我最高興的事就是一有時間就坐下來寫作。
記者:早年您做過電台的編輯,後來是學者的生涯,您的寫作也處於兩極,既有複雜宏大的書寫,也有日常的表達,您是一個可以複雜也可以簡單的人嗎?
艾柯:從多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不管什麼樣的工作。我有個專欄,每個星期都要寫,我寫書,還寫論文,在這個之間連線是很嚴密的。比如說寫學術的書,其實很多論點就是從每個禮拜的專欄裡面來的,(專欄文字)只不過我是用一種更易懂、簡單的方法,面對更多的人在寫。很多人會覺得為什麼學術的書跟專欄之間有那么大的差別,對我個人來講,很多論點其實在每個星期的專欄里都寫了,而且是用更簡單的方式寫。我是用記者的眼光研究學問,在我這裡,記者、作家和教授是一體的。
記者:您寫過那么多舊的、新的書,寫出過那么多透徹的文字,能說您是一個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嗎?
艾柯:誰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誰也無法清晰地看清楚這個世界,我從來沒有見過誰能清晰地看見這個世界。如果你認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紹給我。
(本文採訪得到北京外國語學院趙媛、哥德學院北京分院崔嶠的協助,在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