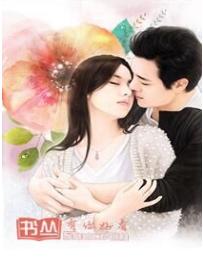初章試讀
舒蔻穿著一條白色的真絲睡裙,渾身緊張的直打寒噤。
徐徐的晚風從樓道的窗戶吹進來,讓她臉上的每一寸肌膚都像被冰刀刮著,割著,痛著,最後連她的心,都如同被綱絲勒緊停止了跳動。
她被牽著往別墅二樓爬時,腳下打了個趔趄,幸好,身邊的女傭及時扶住她。
兩人沿著一條幽深的長廊,在一道對開的雕花橡木門前站定。
女傭拿出早就準備好的眼罩,不由分說幫她戴起來。
“為……為什麼要戴眼罩?”她雙唇微啟,恐駭的咽了咽口水。
對方沒有回答,只是一語不發的幫她推開橡木門,把她送進去,讓她坐在正對大門的床腳。
女傭隨後闔門而去。
這是個燈火通明,金碧輝煌的臥室。奢靡之氣,隨處可見,僅她座下的貢緞提花床單,就雍容華貴,仿如宮廷畫師的鼎力之作。
不過,舒蔻看不見。她低下頭,用手摸了摸臉上的眼罩,不理解這位僱主,明明知道她是個什麼也看不到的瞎子,為什麼還會有如此舉動。
這時,房門被推開,來人正好把她唇角的一抹淺笑收入眼底。那就像朵晨間帶露的豌豆花,清新,自然。但這朵花,隨著來人的靠近頃刻凋零。
舒蔻的心又懸到了嗓子眼,她兩隻手無意識的搓弄著裙擺。
“脫吧!”來人啪啪兩下,利索的關掉了臥室的燈。在黑暗裡,居高臨下的衝著她命令道。
這聲音比她想像的要年輕,要冷冽,要陰鷙。舒蔻的大腦一片空白,她雙手哆嗦著,像提線的木偶,機械的脫掉身上僅有的睡裙……
僅管一片漆黑,但她柔嫩的肌膚在月光的蕩漾下,依舊泛著珍珠般的光澤。
那男人帶著危險的氣息迎面撲來,她驚慌的想推開對方,卻無意中扇到對方的臉。
這一巴掌並不重,只如蚊蟲輕嚀了一下,但對方明顯被她的這個動作激怒,猛然抓住她纖細的手腕,不知用什麼把她的手快速桎/梏在床頭。
她身不由己的跌在床上,還沒來得及痛呼,一具沉甸甸的身體已經壓上來,接著,是撕/裂般的痛苦……
整個夜晚,舒蔻都仿佛游離在地獄的邊緣。因為那男人就像一頭處在發/情期的野獸,一次一次,不知索要了她多少回。
她不得不用殘存的理智抵抗,用孱弱的身體去承受,但除了疼,除了粗重的喘息,健碩的體格和旺盛的精力,是那男人刻在她腦海里唯一的記憶。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時,舒蔻綁在床頭上的手才得以鬆開。
她頭痛欲裂,四肢酸痛的幾近麻木。等大門處傳來一陣開關聲,她才掀開被子,撐著支離破碎的身體勉強坐起來。
那男人走了嗎?
她取下臉上的眼罩。其實,取下眼罩和戴上眼罩與她沒有區別。因為看不見,所以,舒蔻其它的感官都特別敏銳。
臥室的門,再一次被推開。舒蔻的心一緊,連忙用被子裹緊一絲/不掛的身體。
零碎的腳步聲,說明來的是好幾個人。幾個女傭抬來熱水,擰著毛巾,幫她精心的梳洗一番,穿戴整齊。
她們的動作還算溫柔,只是目光,在落到舒蔻滿身淤痕和床單上的血跡時,交換了一下眼色。
很快,舒蔻又被人帶離臥室,回到樓下她自己的房間。
當門在她背後合上時,她像一癱軟泥跌坐在地上,抱緊自己,失聲痛哭起來。
相比較體表的傷痛,內心的屈辱更令她感到難過。
昨天晚上那男人對她無休無止的占有和蹂/躪,讓她不知道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對,還是錯……
就在兩個月前,有人帶著一張巨額支票找到舒家,向她父母提出,只要舒蔻能幫他們家的主人,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不但可以收穫支票,而且對方還願意送舒蔻去國外最好的醫院,接受眼部手術。
這條件是誘人的,而且支票上的數額,也足以讓他們一家四口,下半輩子衣食無憂。
十歲那年的一次意外,讓舒蔻不得不在黑暗裡生活了八年。她早就厭倦了黑暗,希望能重見光明,重新走進久違的學校和課堂,像個正常人一樣的生活。
僅管當時對方並沒告知他主人的身份,只說是因為家裡沒有子嗣,所以才出此下策。但舒蔻還是迫不及待的一口答應了。
“我說你是不是瘋了?對方提供的照片我看過,一個七八十歲滿臉皺紋,牙齒都快掉光的老頭,讓那樣的人趴在你身上,你不噁心,我都覺得噁心。”舒蔻的姐姐,那時曾明明確確的提醒過她。
而舒蔻心裡,也早就做好了思想準備。只是,她沒有想到,這七八十歲的老頭,居然會有這么強勁的體魄和令人咋舌的力道。
經過昨天晚上,她會懷上孩子嗎?如果懷不上,她是不是還得再次面對像昨天晚上一樣的噩夢?
這時,有人輕輕叩響了她的房門。舒蔻連忙抹了把眼淚,站起來,讓到一邊。
門開了,走進來的人是年近五旬,穿著僕人制服的余媽。自從三天前,舒蔻搬進這幢別墅後,就由對方一直在照顧她。
余媽抬著她的早點,擱在陽台前的一張方桌上,爾後,走過來,扶著她,坐到桌前。
“對不起,我沒有胃口,不想吃。”舒蔻囁嚅著。事實上,除了補覺,她只想洗澡,好好洗乾淨昨天晚上那老頭留在她身上的氣息。
余媽幫她添了碗熱乎乎的瘦肉粥,輕笑道,“瞧你這身子骨,不吃可不行,當初先生看到你的照片,啥也不嫌,就嫌你太瘦。怕你耐不住,不能生。”
舒蔻只好抬著碗筷,食不知味地扒了幾口,遲疑地又問,“余媽,您能告訴我……你們家的先生到底姓什麼嗎?”
雖然,她看不到那男人的臉,也許永遠也無法看到。但她想,她至少有權利知道,這個奪走她初/夜的男人到底是誰!
余媽頓時支支吾吾,為難地說,“舒小姐,先生吩咐過,不許我多嘴,你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謹言慎行,恪守本份就好。”
舒蔻當然清楚自己的身份。她只是個借腹產子的工具!對方當初不嫌她瘦,大概就看中了她是個瞎子。只要僱主不把自己真實的信息透露給她,便能在她生完孩子後,輕而易舉的斬斷和她的一切聯繫!
高高在上的有錢人,永遠也不會顧忌她這種工具的感受。
“那我能打個電話回家嗎?”舒蔻抬起頭企盼地問,來到這兒的第一天,她的手機就被沒收。僅管對方聲稱已經向她家人報平安,但她心裡始終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