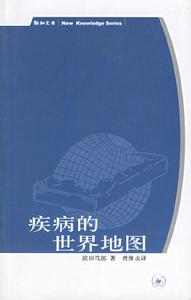編輯推薦
本書講的是旅行和疾病長達三千年的複雜關係,也要讓讀者在旅途中玩得健康、快樂。書中提出了兩個新概念:“古典旅游醫學”和“現代旅遊醫學”。
16世紀起,西歐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紛紛朝熱帶地區前進。殖民者和士兵背負著國家的興衰,被派到世界各地;而維護他們的健康,也就成了國家重要的課題。針對殖民者健康問題的熱帶醫學,以及針對士兵健康問題的軍事醫學,就是誕生於這樣的時代。這兩種殖民地時代的醫學是旅遊醫學的原型,本書稱之為“古典旅遊醫學”。
19世紀後半葉,由於列強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再加上微生物學的急速發展,古典旅遊醫學在歐美各國一時鼎沸。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古典旅遊醫學終因民族主義抬頭而消失。直到1960年代,歐美才開始產生以國外旅行為對象的新旅遊醫學,即“現代旅遊醫學”。
內容簡介
本書兼顧歷史的深度和地理的廣度,探討旅行與疾病三千年來的發展與互動影響,也從20世紀“旅遊醫學”的角度,提供各種旅行醫療知識,為現代旅行者的安康提供經驗和建議。
本書講的是旅行和疾病長達三千年的複雜關係,也要讓讀者在旅途中玩得健康、快樂。書中提出了兩個新概念:“古典旅遊醫學”和“現代旅遊醫學”。 16世紀起,西歐各國為了拓展殖民地,紛紛朝熱帶地區前進。殖民者和士兵背負著國家的興衰,被派到世界各地;而維護他們的健康,也就成了國家重要的課題。針對殖民者健康問題的熱帶醫學,以及針對士兵健康問題的軍事醫學,就是誕生於這樣的時代。這兩種殖民地時代的醫學是旅遊醫學的原型,本書稱之為“古典旅遊醫學”。 19世紀後半葉,由於列強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再加上微生物學的急速發展,古典旅遊醫學在歐美各國一時鼎沸。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古典旅遊醫學終因民族主義抬頭而消失。直到1960年代,歐美才開始產生以國外旅行為對象的新旅遊醫學,即“現代旅遊醫學”。
作者簡介
濱田篤郎(Hamada Atsuo),1955年生於日本東京。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畢業,留美後回到該大學擔任熱帶醫學研究室講師。現任日本海外就業健康管理中心研修交流部長,負責診療海外的日本人;併兼任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等大學講師,日本旅遊醫學全國性組織“出國者健康關懷會”理事。合著有《國外旅行健康必攜》、《預防職場傳染病》等書。
譯者簡介:曾維貞,高雄市人。輔仁大學日文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碩士。現職編輯,譯著有夢野久作小說集《死後之戀》。
目錄
序言 《魂斷威尼斯》的真相
笫1章 旅行者與疾病
第2章 由旅行者傳入的疾病
笫3章 古典旅遊醫學時代
第4章 古典旅遊醫學的興盛與終結
第5章 現代旅遊醫學的誕生
第6章 現代旅遊醫學的醫療指標
第7章 旅遊醫學與傳染病的現況
第8章 古典旅遊醫學的遺產
第9章 引日本為鑑
結語太空旅行時代,近在眼前
跋
書摘
兩次世界大戰和古典旅遊醫學的終結
經過全盛期的古典旅遊醫學,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發出最後的光芒。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不僅限於歐洲,更包含廣大熱帶地區的殖民地,因此,這兩次世界大戰也是各國在古典旅遊醫學發展成熟度上彼此較勁的戰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軍隊中已沒有大規模痢疾和傷寒的流行。斑疹傷寒也證實是由虱子傳播,士兵的衣服必須經過消毒來驅除虱子。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軍戰況每況愈下,而疏於驅除虱子,最後導致東戰線上發生大規模斑疹傷寒的流行。此次流行波及俄國境內,加上當時俄國因革命而動盪不堪,患者人數多達2000萬人以上。
雖然瘧疾已有奎寧這種治療藥可醫治,但在殖民非洲、亞洲等地的部隊仍發生了大流行,特別是在東非的英軍,感染瘧疾喪生者達10萬以上。奎寧的供給足以左右殖民地戰爭的勝負。德國因為經濟被封鎖,無法取得奎寧的原料金雞納,加速研發新藥的腳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防止傳染病人侵,各國軍隊皆以近代化方法嚴加戒備,但因方法不夠周全,各地仍不時爆發流行。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微生物學上不斷有新的發現。1930年,持續研發瘧疾新藥的德國終於成功開發瘧滌平(Atebrin)(譯註:瘧疾的預防與治療用藥奎納克林[quinaeiine]的英國商標);這是第一種不需要金雞納的抗瘧疾治療藥。此後,德國仍不斷研發新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又成功開發了磷酸氯奎寧(chloroqlzine)。1928年,英國的弗萊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則發現了青黴素(pellidllin),也就是盤尼西林,來治療大範圍的細菌性傳染病。不過,1941年戰爭爆發後,青黴素才開始批量生產。而黃熱病等病毒性傳染病的病原體也相繼被發現,各種疫苗陸續成功開發出來。
在那個時代,各國的當務之急是將軍事醫學領域裡的新知識運用在軍隊里,嚴加防範傳染病,為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日本政府、軍方與醫學界也隨著軍國主義的高漲,全面加強軍事醫學。
由於傳染病的病原體己被發現,各國用來確保士兵健康的疫苗和治療法首度發揮了效用,但生化武器也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逐漸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和歐美各國在軍事醫學的發展上已有失控的現象。
1939年在歐洲戰線揭開序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面對抗傳染病的一場戰爭。戰線不限於歐洲,後來更擴及非洲和中東、近東,但士兵不畏傳染病,奮勇作戰。當日本加入戰局時,原本全面武裝的同盟國已開始鬆懈。原來,日軍自開戰以來即猛攻爪哇,更積極奪取原來由荷蘭管理的金雞納農園,以斷絕同盟國的奎寧來源。此舉嚴重影響在非洲戰線作戰的同盟國軍隊,許多士兵因此暴露於感染瘧疾的危險之中。同盟國後來順利取得奎寧的代替新藥瘧滌平,在非洲打勝。
日本參戰後引發的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一帶的戰局,是日本和歐美各國在古典旅遊醫學水準上較量的最後一戰。雙方陣營皆運用了過去所累積的知識和技術,全力迎戰。歐美在軍隊調度上以經驗豐富取勝,尤其是瘧疾的防疫政策略勝一籌。戰爭期間,美日雙方的軍隊都服用奎寧和瘧滌平來預防瘧疾,但是美軍因為有建設巴拿馬運河的經驗,不忘對士兵施以充分的衛生教育,徹底落實驅蚊的工作。不僅如此,他們預測到兵力會因為瘧疾而減弱,早已事先編制預備軍。最後,日本的補給線遭斷絕,藥劑不足,各地日軍在遭受美軍攻擊以前,就被瘧疾瓦解。如此一來,這場戰爭已分出勝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軍事醫學和熱帶醫學在敗戰國日本的國內,都被視為往事塵封起來。軍事醫學留有軍國主義的殘影,熱帶醫學仍帶有帝國主義的氣息;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樣的醫學是不被允許的。以這兩種醫學為基礎的古典旅遊醫學更被視為禁忌,受到壓抑。
另一方面,古典旅遊醫學的發展在歐美各國內也被迫中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在民族主義的聲浪中紛紛獨立,群起指責戰前的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風潮。在這樣的國際社會背景下,熱帶醫學不得不轉型,只負責解決熱帶地區居民的健康問題。隨著和平時代的來臨,公然研究軍事醫學的風潮也已消褪。而冷戰開始,古典旅遊醫學更變成一種軍事機密,埋沒在大家注意不到的角落。
古典旅遊醫學於戰後隨即消失,相較之下,現代旅遊醫學在歐美正是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