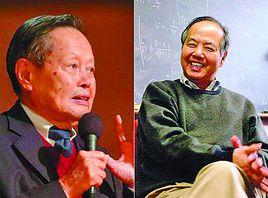事件背景
2009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瑞典舉行,同日,由季羨林之子季承執筆的《李政道傳》在西單圖書大廈首發。季承曾為李政道助手12年,在本書30萬字的篇幅中,季承全面系統地披露李政道與楊振寧決裂半世紀的學術恩怨內幕:名字排序之爭。
季承坦言,“我寫他們的恩怨,是抱著客觀的態度寫歷史,歷述事實,不偏不倚,不做結論。”對於這段恩怨,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深以為憾,但各執一詞。楊振寧雖然認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遺憾,但是他最先對外公開“事實真相”。楊振寧還曾引用蘇東坡與其弟詩“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不了因”,來表達他對蘇軾兄弟情誼的羨慕,他說:“很遺憾,我和李政道沒能做到這點。”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開發表一封信,“我和楊振寧的分裂,無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很大的悲劇,但它是事實,無法迴避。”同時對真相作了公開說明,“我和楊振寧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在1956年我們合作發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中,有關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是誰首先提出來的。”
詳細經過
初識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聯大讀二年級。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覺得核子彈很重要,也要造核子彈。他找到西南聯大的物理教授吳大猷、化學教授曾昭掄和數學教授華羅庚,對他們說,給你們十萬美元,一個大禮堂作為工作場所,請你們造核子彈。
吳大猷他們說,造核子彈要先培養人才,建議選拔一些人去美國學習。
李政道被選中,於1946年來到美國。但由於美國並不開放核子彈製造技術,考察小組只能解散。據指示,他們可以用領取到的經費在美國深造。於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學起了理論物理。
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面。
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二人開始聯名發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學後不久,由於他有雙份獎學金,經濟上比較寬裕,就買了一輛二手小轎車。1947年夏天,他和楊振寧、凌寧開著這輛車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峽谷遇險的故事外,書中披露,李政道還說起一個有趣的細節:出發前,楊振寧提議三人按比例出錢,把那部車子買下來,回來後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錢買下車子。楊振寧的這個提議究竟意味著什麼,後來李政道才琢磨過味來。他對楊振寧的精於算計頗有感觸。
合作
博士畢業後,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作,擔任物理系助教。當時,韓戰爆發,加州地方反華氣焰囂張,因而李政道在加州並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楊振寧來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訪問成員。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況,於是兩人商量,李政道也來普林斯頓,可以一起作研究。
書中寫道,楊振寧去找了院長奧本海默(美國“核子彈之父”),請他給李政道發出邀請信。於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來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李楊兩家比鄰而居,兩家人來往密切。楊振寧正在進行兩維伊辛模型的磁化計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這是他們合作的真正開始。”季承寫道。
1951年秋,他們寫了兩篇統計力學論文,首次給出了不同熱力學函式的嚴格定義。在此基礎上他們發現不同的熱力學函式在有相變的情況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這個發現揭開了統計力學研究新的一頁。
兩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論文引起了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重視。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與愛因斯坦見面。談話時間很長,愛因斯坦問得很多,很細。最後,他站起來同李政道握手,懇切地對他說:“祝你未來在物理上成功。”
兩位年輕人在普林斯頓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們個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的親密關係,一時傳為佳話。奧本海默曾說,李政道和楊振寧坐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討論問題,是一道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頓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時糾紛卻發生了,由頭是他們合寫的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問題。
這兩篇論文的總標題是《狀態方程和相變的統計理論》,第一篇《凝聚理論》署名是楊振寧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氣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楊振寧。
季承寫道,在第一篇論文完成後,按慣例合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順序排列,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是,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對這一要求很吃驚,勉強同意。
在第二篇論文署名時,李政道說服楊振寧按國際慣例改了過來。
署名問題給二人帶來裂隙,李政道決定不再和楊振寧合作。之後,雖然他在普林斯頓又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但是他們沒有再合著論文。
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那時,他並不知道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的長女)也參與其間。據楊振寧回憶,上述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楊振寧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為李畢業後科學事業一直不順利,要幫助他,可是杜致禮根據“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說李政道這個人不值得他這樣信任。
李政道決定離開普林斯頓,去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三年後,1956年,他29歲時,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
共獲諾貝爾獎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本來就是想和楊振寧拉開距離。一件偶然的事情,卻使二人恢復了合作。
1953年,楊振寧曾去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工作一年,和米爾斯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同位旋守恆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其中提出了後來十分有名的楊-米爾斯規範場方程。
但是,當時李政道對這篇論文的出發點是否正確持嚴重懷疑。一次,楊振寧到哥倫比亞大學來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楊。經過激烈的討論,楊同意了李的意見,還共同署名,李前楊後,發表了論文《重粒子守恆和普適規範轉換》。
這件事使他們重拾合作,這也是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稱》中有如下描述:“從1956年到1962年,楊和我共同寫了32篇論文,範圍從粒子物理到統計力學⋯⋯合作緊密而富有成果,有競爭也有協調。我們在一起工作,發揮出我們每個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於每個人單獨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生在這個時期。
宇稱不守恆的發現,被譽為20世紀物理學中的革命。根據《李政道傳》所寫,這一發現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約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楊振寧開車從長島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看李政道,在李的辦公室里進行了討論。不久,楊振寧要移動他停在街上的汽車,他們就走到街上。把車停好後,由於飯館都還沒開門,他們就近在125街和百老匯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廳邊喝咖啡邊討論。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性想法,統統告訴了楊振寧。
楊振寧激烈地反對李政道所說的一切。但經過反覆的討論,他逐漸被說服。午飯後,他們回到李政道的辦公室,楊已經完全被說服,並表示願意與李合作。他還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建議,就是勸李不要急忙發表上述那篇論文。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突破,應該用最快的速度,將整個弱作用領域一下子都占領下來。這樣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義。
李政道覺得十分有道理,同時覺得如有楊振寧的參加,會使整個事情做的更好。
兩人開始了友好的競賽。他們在大約兩周內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這需要進行大量計算。兩人在計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貢獻。
一個月後他們完成了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寫出了論文。這篇論文是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這就是轟動一時後來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
決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導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
“沒有想到”,書中寫道,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么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箬。秦惠箬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
這是一個插曲,李政道雖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諾獎的榮耀沖淡。而不久後的一篇文章卻讓他們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國《紐約客》雜誌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寫的《宇稱問題側記》,記述李楊合作發現宇稱不守恆的故事。
當時,李政道已經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樣,沒作什麼修改。可是楊振寧卻提出了許多意見。他說,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討論。
楊振寧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寫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禮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箬之前,因為杜致禮年長一歲。第二天,楊振寧到李政道家裡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楊寫了⋯⋯”的地方都要加一個注,說明是出於字母排序的習慣。
對楊振寧的這些要求,李政道覺得太無聊。當天晚上,楊又打來電話,說那些注或許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寫成“楊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議他們今後不再合作。書中說,楊振寧隨即變得十分激動,開始哭起來,說他是非常願意繼續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無可奈何。最後他們都同意暫停合作。
當年11月,李政道向奧本海默遞交了辭職書。奧本海默對此感到非常遺憾,他尖銳地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
各執一詞
當然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傳》中,作者季承也儘量引入楊振寧的表述,以求平衡。
楊振寧寫於1982年,於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識李政道》一文里寫道:“他才華出眾,刻苦用功。我們相處得頗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費米做了他的學位論文導師,但他總是轉而向我尋求指導。因此,在芝加哥的歲月里,事實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師。”
在《和李政道的最後的合作》一文的後記里,楊振寧對兩人的合作做了總結:“我對他就像一位兄長。在粒子物理和統計力學領域裡,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經成了名。我們的合作關係中,我是資深的一方。敏銳地警覺到不應該擋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識地往後靠,儘量在事業上扶持他,同時,在公開場合對我們合作關係的實質嚴格地保持緘默⋯⋯”
在寫於1982年的《獲諾貝爾獎的論文產生經過》一文後記里,楊振寧的版本與李政道截然不同:“我們的討論集中在θ-τ之謎上面。在一個節骨眼上,我想到了,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同衰變過程分離開來。於是,如果人們假設宇稱只在強作用中守恆,在弱作用中則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個粒子且自旋、宇稱為0-(這一點是由強作用推斷出的)的結論就不會遇到困難⋯⋯李政道先是反對這種觀點。我力圖說服他,⋯⋯後來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無解的謎局
李楊之間的恩怨,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個人範疇,延伸到了日後中國基礎學科的發展。
197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先後回國訪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季承寫道, 圍繞著高能物理的發展,過去在中國素來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自從李楊這兩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自天外歸來、陸續回國訪問並介入其間,這一分歧就帶有了濃厚的個人意氣的色彩,成了李楊不和的易地之戰。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張建高能加速器,楊振寧反對;李政道主張重視基礎科學,楊振寧力主搞套用科學;李政道創立特殊的考試辦法幫助中國學子赴美留學,楊振寧就說是“喪權辱國”,等等。
“他對中國高能物理髮展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甚至主張凍結基礎研究的經費,說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張科學院要以發展性研究為主,從而‘生產第一,生產第一,生產第一’。”書中這樣對楊振寧的態度作總結。
季承寫道:“推而廣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贊成的,楊振寧就反對。楊振寧的個人意氣遠超出了高能物理領域。意氣的來源完全在楊振寧。相反,李政道卻沒有表示出對楊振寧回國後所作所為的個人意氣。人們看不到‘只要楊振寧主張,李政道就反對’這種現象。”
季承對本刊記者表示:“我寫他們的恩怨,是抱著客觀的態度歷述事實,不偏不倚,不做結論。”
“他們之間的分歧,已經是一個科學史的問題了。其是非曲直,應該由歷史來判斷,應該由科學史家來研究。至於結論,這恐怕是沒有人,沒有什麼機構,可以做出的。”季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