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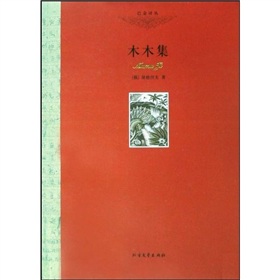 木木集
木木集叢 書 名:巴金譯叢
出 版 社:北方文藝出版社
ISBN:9787531723158
出版時間:2008-01-01
版 次:1
頁 數:111
裝 幀:平裝
開 本:16開
內容簡介
《木木集》收入了屠格涅夫兩篇小說。《木木集》是一篇真實的故事,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加萊爾說這是世界上最感動人的故事,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家高爾斯華綏也說:“在藝術的領域中從來沒有比這個更大的對於專橫暴虐的抗議。”屠格涅夫逝世遺體運回俄國以後,俄國防止虐待動物會為了這篇小說曾派代表參加他的葬禮。《普寧與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這是一篇半自傳體的小說。《獵人日記》的作者日後的輝煌的文學生涯可以說是從此篇主人公普寧的啟蒙開始,英國愛德華-加爾奈特甚至讚美說,理想主義者普寧這個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長的繪像相比。
目錄
《巴金譯叢》代序(巴金)
·木木集·
木木
譯後記
·普寧與巴布林·
普寧與巴布林
譯後記
前言
一
三聯書店準備為我出版一套譯文選集,他們挑選了十種,多數都是薄薄的小書,而且多年未印了。他們也知道這些書不會有大的銷路,重印它們無非為了對我過去的翻譯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勵。我感謝他們的好意,可是說真話,在這方面我並無什麼成就。
我常說我不是文學家,這並非違心之論。同樣,我也不是翻澤家。我寫文章,發表作品,因為我有話要說,我希望我的筆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起一點作用。我翻譯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過是借別人的口講自己的心裡話。所以我只介紹我喜歡的文章。
我承認自己並不精通一種外語,我只是懂一點皮毛。我喜歡一篇作品,總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覆背誦,不斷思考,根據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筆表達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別人的文章打動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譯文打動更多人的心。不用說,我的努力始終達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別人的作品變成我的武器。
我並不滿意自己的譯文,常常稱它們為“試譯”,因為嚴格地說它們不符合“信、達、稚”的條件,不是合格的翻譯。可能有人說它們“四不像”:不像翻譯,也不像創作,不像外國前輩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時信筆寫出的東西。但是我像進行創作那樣把我的感情傾注在這些作品上面。丟失了原著的風格和精神,我只保留著我自己的那些東西。可見我的譯文是跟我的創作分不開的。我記得有一位外國記者問過我:作家一般只搞創作,為什麼我和我的一些前輩卻花費不少時間做翻澤工作。我回答說,我寫作只是為了戰鬥,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後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鬥,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術教師學習。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揀來的別人的武器戰鬥了一生。在今天擱筆的時候我還不能說是已經取得多大的戰果,封建的幽靈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還要重上戰場。
回顧過去,我對幾十年中使用過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雖然是“試譯”,我重讀它們還不能不十分激動,它們仍然強烈地打動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譯文,它們也曾幫助我進行戰鬥,可以說它們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謝三聯書店給我一個機會,現在的確是編輯我的譯文選集的時候了。
二
我不知道從哪裡講起好。在創作上我沒有完成自己的諾言,我預告要寫的小說不曾寫出來。在翻譯方面我也沒有完成自己的計畫,赫爾岑的同憶錄還有四分之三未譯。幸而有一位朋友願意替我做完這個工作,他的譯文全稿將一次出版。這樣我才可以不帶著內疚去見“上帝”。前一個時期我常常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坐立不安,現在平靜下來了。沒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筆不曾償還的欠債,雖然翻譯不是我的“正業”,但對讀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遺憾。
有些事我做過就忘得乾乾淨淨,可是細心的讀者偏偏要我記起它們。前些時候還有人寫信問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藝月刊上發表過翻譯小說《信號》。對,我想起來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號》是我的第一篇譯文。我喜歡迦爾洵的這個短篇,從英譯本《俄國短篇小說集》中選譯了它,譯文沒有給保存下來,故事卻長留在我的腦子裡。在我的頭一本小說《滅亡》中我還引用過《信號》里人物的對話。二三十年後(即五十年代初)我以同樣激動的心情第二次翻譯了它。我愛它超過愛自己的作品。我在那裡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師,我譯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師,我翻譯首先是為了學習。
那么翻譯《信號》就是學習人道主義吧。我這一生很難擺脫迦爾洵的影響,我經常想起他寫小說寫到一半忽然埋頭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寫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說我的寫作生活就是從人道主義開始的。《滅亡》,我的第一本書,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學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殺人被殺中毀滅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犧牲精神的不仍是對生活、對人的熱愛嗎?
《寒夜》,我最後一個中篇(或長篇),我含著眼淚寫完了它。那個善良的知識分子不肯傷害任何人,卻讓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為了愛生活、愛人……嗎?
還有,我最近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時間寫成的《隨想錄》不也是為同一個目標?
三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也願意做一個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說什麼“使命感”、“責任感”……但是我活著絕不想浪費任何人的寶貴時間。
我的創作是這樣,我的翻譯也是這樣。
從一九二二年翻譯短篇《信號》開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斷左腿為止,六十年中間我譯出的作品,長的短的加在一起,比這套選集多好幾倍。作者屬於不同的國籍,都是十九世紀或者二十世紀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讀他們的書,仿佛還聽見他們的心在紙上跳動。我和他們之間有不小的距離,我沒有才華,沒有文采,但我們同樣是人,同樣有愛,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們,我也相信讀者理解他們。
別的我不多說了。
巴金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精彩書摘
在莫斯科的一條偏僻的街上,有一所灰色的宅子,這所宅子有白色圓柱,有閣樓,還有一個歪斜的陽台;從前有一位太太住在這兒,她是一個寡婦,周圍還有一大群家奴。她的兒子全在彼得堡的政府機關里服務,她的女兒都出嫁了;她很少出門,只是在家孤寂地度過她那吝嗇的、枯燥無味的餘年。她的生活里的白天,那沒有歡樂的、陰雨的日子,早已過去了;可是她的黃昏比黑夜還要黑。
在所有她的奴僕當中最出色的人物是那個打掃院子的人蓋拉新,他身長十二維爾肖克,體格魁偉像一個民間傳說中的大力士。他生來就又聾又啞。太太把他從鄉下帶到城裡來,在村子裡他一個人住在一間小屋裡,跟他的弟兄們不在一塊兒,在太太的繳租農人中間,他算是最信實可靠、能按時繳租的一個。他生就了驚人的大力氣,一個人乾四個人的活兒,他動手做起事來非常順利。而且在他耕地的時候,把他的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用不著他那匹小馬幫忙,他一個人就切開了大地的有彈性的胸脯似的,或者在聖彼得節里,他很勇猛地揮舞鐮刀,仿佛要把一座年輕的白樺林子連根砍掉一樣,或者在他輕快地、不間斷地用三俄尺長的連枷打穀子的時候,他肩膀上橢圓形的、堅硬的肌肉一起一落,就像槓桿一般——這些景象看起來都叫人高興。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那不倦的勞動顯得更莊嚴。他本來是一個出色的農人,要不是為了他這個殘疾,任何一個女孩子都肯嫁給他。……可是蓋拉新給帶到莫斯科來了,人家還給他買了靴子,做了夏天穿的長裾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外套,又塞了一把掃帚和一根鐵鏟在他的手裡,派他當一個打掃院子的人。
起初他很不喜歡他的新生活。他自小就習慣了種田,習慣了鄉村生活。他由於自己的殘疾一直跟人群隔離,長大起來,又聾又啞,而且力氣很大,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長的一棵樹。……他給人帶進城市以後,倒不明白該怎么辦了,他發悶,發獃,就好像一頭很壯的小公牛在發獃那樣,這頭牛在那塊茂密的青草長到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場上嚼草,忽然讓人牽走了,放在鐵路的貨車上,啊,它的結實的身體一下子讓煤煙和火花包住了,一下子又是一股一股的水蒸汽淹沒了它,它給拖著向前飛奔,跟著隆隆聲和尖銳聲飛奔,飛奔到哪兒去呢——只有上帝知道!蓋拉新自來作慣了農人的苦工,所以他把這個新職務需要他幹的活並不當作一回事;每天只花半個鐘頭他的活就幹完了,他便又站在院子中間,張開嘴,出神地望著所有過路的人,好像他想從他們那兒得到一個可以說明他這個莫名其妙的處境的解答;或者他就突然跑到某一個角落裡,把手裡的掃帚和鐵鏟擲得遠遠的,自己頭朝著地撲下去,在地上躺幾個鐘頭,連動也不動一下,仿佛是一頭關在籠里的野獸。可是人對什麼事情都會習慣,蓋拉新後來也習慣城裡的生活了。他的工作並不多,他的全部職務不過是,把院子打掃乾淨,每天分兩次取兩桶水,運柴、劈柴給廚房和整個宅子使用,白天不讓生人進來,夜間小心守夜。應當說,他的確熱心執行了他的職務。院子裡從來不曾有過一片木屑,也沒有見過一點垃圾;遇到下雨路爛的時候,帶著桶去取水的老馬在路上什麼地方陷在泥里走不動了,他只用肩頭一推,不單是車子,連馬也給推著走了。要是他動手劈柴,斧頭會發出玻璃似的響聲,木片、木塊會朝四面八方飛散。至於生人呢,自從某一天晚上他捉住了兩個小偷,把兩個腦袋在一塊兒狠狠地碰了幾下(碰得那樣厲害,簡直用不著再把他們送到警察局去了)以後,附近這一帶地方人人都非常尊敬他。即使在白天,有些過路人,他們絕不是賊,不過是陌生人罷了,看見像他這樣一個可怕的打掃院子的人,他們連忙向他揮手、叫喊,就好像他能夠聽見他們的叫聲似的。蓋拉新同這個家裡男女僕人的關係並不親密(岡為他們怕他),但也不疏遠;他把他們當作自己人看待。他們用手勢跟他講話,他都明白,主人命令他做的事他全照樣做了,可是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權利,沒有人敢在飯桌上坐他的位子。一般地說,蓋拉新的性情是嚴厲的、一本正經的,他喜歡什麼事情都有秩序。連公雞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則,它們就該倒霉了!他馬上捉住它們的腿,把它們當輪子一樣在空中轉個十來回,然後朝各個方向拋出去。太太的院子裡也養得有鵝;可是鵝是出名的一種尊貴的、懂道理的家禽;蓋拉新尊敬它們,他照料它們,他餵它們;他自己就像是一隻很神氣的鵝。他們分派了一間廚房上面的頂樓給他;他照他自己的趣味布置了這問屋子,他用橡木板做了一張床,床腳是用四個木頭墩子做的——這真是一張民間傳說中大力士睡的床了;它載得起一百普特的重量,不會塌下去;床底下放了一口堅固的木箱;一個角落裡立著一張同樣牢固的小桌子,桌子旁邊有一把三隻腳的椅子,椅子非常結實、矮小,所以蓋拉新常常把它舉起來,又丟下去,一邊高興地微笑。這頂樓是用掛鎖鎖住的,鎖的形狀倒像“喀拉蚩”,不過它是黑色的罷了;蓋拉新總是拿這把鎖的鑰匙掛在自己的腰帶上。他不喜歡別人走進他的頂樓去。
就這樣地過了一年,在這年的年尾蓋拉新遇到了一樁小小的意外事情。
那位老太太(蓋拉新就是在她的宅子裡當打掃院子的人)對什麼事情都遵照古法辦理,她養了一大群傭人:在她的宅子裡不僅有洗衣女人、縫衣女人、細木匠、男裁縫、女裁縫等等,甚至還有一個馬具匠,他也兼作獸醫,並且還要給用人看病,宅子裡另外有一個專給女主人看病的家醫;此外還有一個鞋匠,叫作卡皮統·克里莫夫,是一個無可救藥的酒鬼。克里莫夫一直認為自己受了委屈,沒有人認識他的真正價值,他原本是一個有教養的京城裡的人,不應當連一個職業也沒有,在莫斯科郊外這種偏僻地方住下來。要是他喝酒(他自己這樣說,而且在說話的時候還時常停頓,用手打他自己的胸膛),那就是在借酒消愁。有一天太太跟她的管家加夫利洛談到他的事情(加夫利洛是這樣一個人:單從他那對又黃又小的眼睛和他那個鴨嘴般的塌鼻子看來,就知道他是一個命中注定要指揮別人的人物)。太太在惋惜卡皮統的墮落,剛巧前一個晚上還有人看見他醉倒在路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