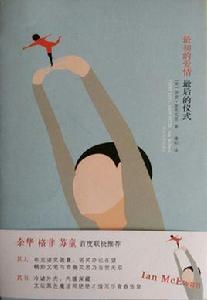編輯推薦
余華長序導讀
潘帕傾力迻譯
英國文壇大家驚世成名作
其人
布克諸獎盈囊,諾獎亦已在望
精妙文筆與奇崛文思乃當世無雙
其書
冷謔外殼,內暖深藏
文壇黑色魔法師絕艷才情寫盡青春張皇
趙毅衡 蘇童 格非 毛尖 張悅然聯袂推薦
麥克尤恩的八個短篇一口氣讀完了。我經常讀到好書,可是讓我如此喜歡的書已經很久沒有讀到了。麥克尤恩在中國少為人知是不正常的,我相信他很快會引起中國讀者的喜愛,我願意為此而努力。
——余華
書中的八篇小說,在幾個月中,我反覆讀了好幾遍。重讀,並不僅僅因為喜愛,而是不能確信抓住了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東西。它們非常隱約,細微,像春天裡和著花粉的塵埃。我必須一再誦讀,這些收信人不明的情書。
——張悅然
麥克尤恩的虛構世界融合了德·基里科的城市畫面荒涼迷夢般的特質和巴爾蒂斯油畫中奇異的情慾色彩。文字的壟溝中時有臥虎潛藏,詭異之事就那么若無其事,那么沉著地走出來。
——《紐約時報》
珍罕之書,為英國小說開闢了新方向。
——Encounter
他的作品精確,細膩,風趣,妖異,擾人。
——《時代周刊》
一位真正具有想像力的天才。
——朱利安·巴恩斯
書評
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節選)
余華
我第一次聽到伊恩·麥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國,也可能在法國或者義大利,人們在談論這位生機勃勃的英國作家時,表情和語氣里洋溢著尊敬,仿佛是在談論某位步履蹣跚的經典作家。那時候我三十多歲,麥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歲,還不到五十。我心想這傢伙是誰呀?這個年紀就享受起了祖父級的榮耀。
然後開始在中國的媒體上零星地看到有關他的報導:“伊恩·麥克尤恩出版了新書”,“伊恩·麥克尤恩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改編成了電影”……這幾年中國的出版界興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麥克尤恩的著名小說,《水泥花園》、《阿姆斯特丹》、《時間中的孩子》和《贖罪》。可是中國的文學界和讀者們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這位文學巨人。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也許麥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讓中國讀者了解他。現在麥克尤恩的第一部書《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說在中國的命運可以趁機輪迴了。從頭開始,再來一次。
這是一部由八個短篇小說組成的書,在麥克尤恩27歲的時候首次出版。根據介紹,這部書在英國出版後引起巨大轟動。可以想像當初英國的讀者是如何驚愕,時隔三十多年之後,我,一個遙遠的中國讀者,在閱讀了這些故事之後仍然驚愕。麥克尤恩的這些短篇小說猶如鋒利的刀片,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撫摸刀刃的過程,而且是用神經和情感去撫摸,然後發現自己的神經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劃痕。我曾經用一種醫學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傑出:那就是在閱讀了這個作家的作品之後,是否留下了閱讀後遺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麥克尤恩名字時的情景,我明白了當初坐在我身邊的這些人都是“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患者。
我感到這八個獨立的故事之間存在著一份關於敘述的內部協定,於是《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一書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組曲,一首擁有八個樂章的組曲。就像麥克尤恩自己所說的:“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邊緣人、孤獨不合群的人、怪人,他們都是和我有相似之處。我想,他們是對我在社會上的孤獨感,和對社會的無知感,深刻的無知感的一種戲劇化表達。”然後麥克尤恩在《立體幾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當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煩躁,而且煩躁是那么的生機勃勃;讓《家庭製造》粗俗不堪,讓這個亂倫的故事擁有了觸目驚心的天真;《夏日裡的最後一天》可能是這本書中最為溫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結束以後,憂傷的情緒從此細水長流;《舞台上的柯克爾》的敘述誇張風趣,指桑罵槐。麥克尤恩讓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還有一個人物是導演,導演要求小伙子們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導演說:“如果給我見到勃起,就滾蛋,這可是一場體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過程冷靜的令人心碎;《與櫥中人對話》看似荒誕,其實講述的是我們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結尾時所表達的一樣,我們人人都會在心裡突然升起回到一歲的願望;《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是沒有愛情的愛情,沒有儀式的儀式,還有隨波逐流的時光。麥克尤恩給這些無所事事的時光塗上夕陽的餘輝,有些溫暖,也有些失落;《偽裝》是在品嘗畸形成長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這裡俯拾即是。
這就是伊恩·麥克尤恩,他的敘述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溫暖、荒誕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邊界上,然後他的敘述兩者皆有。就像國王擁有幅員遼闊的疆土一樣,麥克尤恩的邊界敘述讓他擁有了廣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寫下希望的時候也寫下了失望,寫下恐怖的時候也寫下了安慰,寫下寒冷的時候也寫下了溫暖,寫下荒誕的時候也寫下了逼真,寫下暴力的時候也寫下了柔弱,寫下理智冷靜的時候也寫下了情感衝動。
麥克尤恩在這些初出茅廬的故事裡,輕而易舉地顯示出了獨特的才能,他的敘述有時候極其鋒利,有時候又是極其溫和;有時候極其優雅,有時候又是極其粗俗;有時候極其強壯,有時候又是極其柔弱……這傢伙在敘述的時候,要什麼有什麼,而且恰到好處。與此同時,麥克尤恩又通過自己獨特的文學,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學,或者說是讓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遠流長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繼續。什麼是文學天才?那就是讓讀者在閱讀自己的作品時,從獨特出發,抵達普遍。麥克尤恩就是這樣,閱讀他作品的時候,可以讓讀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後落葉歸根,最終讓讀者不斷的地發現自己。我曾經說過,文學就像是道路一樣,兩端都是方向。人們的閱讀之旅在經過伊恩·麥克尤恩之後,來到了納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羅斯等人的車站;反過來,經過了納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羅斯等人,同樣也能抵達伊恩·麥克尤恩的車站。這就是為什麼伊恩·麥克尤恩的敘述會讓我們的閱讀百感交集。
我的意思是說,當讀者們開始為麥克尤恩的作品尋找文學源頭的時候,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現實處境尋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畫像。讀者的好奇心促使他們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喚醒自己過去閱讀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後又讓自己與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場,如此周而復始的聯想和聯想之後的激動,就會讓兒歌般的單純閱讀變成了交響樂般的豐富閱讀。
什麼是伊恩·麥克尤恩後遺症?這就是。
最初和最後之間
毛尖
潘帕譯了《芒果街上的小屋》,我就成了他的冬粉,所以,拿起《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一大半倒是因為潘帕,他的譯筆表達了:青春。早泄。靈感。普遍。暴烈。溫柔。夢幻。深淵。
呵呵,你一定發現了,這些辭彙,不就是《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的關鍵字嗎!可是,讓我再堅持一下,這八個短篇也可以說是潘帕的故事,因為首先,麥克尤恩的這個處女短篇集,還沒有形成《贖罪》那種後英國風格,倒是譯者的風格比作者的口吻更統一;其次,八個短篇,全部是從青少年的男性視角出發,幾乎是每一個少男都會做的夢,溫柔也好,恐怖也好,可以和所有人的處男時代對話,要是允許想像,潘帕的青春期也可以這樣瘋魔又傷感。
這么說,既不是要讚美譯者,也不是要奚落作者,我想說的是,看完這八個短篇,最大的感受是,青春,與其說是一種題材,不如說是一種體裁。在這個體裁里,誘姦顯出了天真,亂倫包藏了歡樂,殺人展示了才華,性愛混雜了幽默,所以,麥克尤恩的虛構世界,怪力亂神的一面解釋了史蒂芬金的恐怖,臥虎藏龍的腔調卻是對亨利米勒的調戲,其中,我們也能一目了然地追蹤出他的二十歲讀物,包括一個自卑的卡夫卡,一個希區柯克狀態的弗洛伊德,以及一個溫柔甜蜜頹喪又變態的托馬斯曼。
這個體裁決定了二十七歲的麥克尤恩還無力於自我塑造,他在兩極間奔走,既鍾情於最初的愛情,又迷戀最後的儀式,而龐大的介於最初和最後的“中年期”,這個作為另一種體裁的“中年期”,還要等待另一個二十七年。
作為英國文學的保守愛好者,我自己一直不特別對麥克尤恩感興趣,比如說他這部成名作,透著歐洲大陸和美國文學的時髦痕跡,反而牢牢地壓抑了母國中最細膩激情的那一支血脈,比如維吉尼亞沃爾夫代表的傳統。不過,看完這八個短篇,回思他後來的《阿姆斯特丹》《在切瑟爾沙灘上》,才真正感到一個國家的文學傳統可以多么強悍,這不,當年那個要反出英國傳統的“恐怖伊恩”最後不是乖乖地抒情地回到了奧斯汀身邊,他老鳥回巢,雖然嘴裡談的還是索爾貝婁,但史蒂芬金這些影子都進了字紙簍。
現在,他白襯衫,休閒褲,臉上是大英帝國的落日餘暉,這百分百的英國儀式讓他自己感動,想到“那年我十二歲”這個處子句式,對自己的處女作湧起很多柔情。
長大就發生在那一刻
張悅然
這是一篇遲遲沒有動筆的書評。因為我一直希望把它寫得別致而又生機勃勃,才能與這本伊恩二十七歲的處女作相配。
書中的八篇小說,在幾個月中,我反覆讀了好幾遍。重讀,並不僅僅因為喜愛,而是不能確信抓住了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東西。它們非常隱約,細微,像春天裡和著花粉的塵埃,我感到鼻子聳動,陣陣發酸。這是少年時代的氣味,並不陌生,因為它還沒有離開我太久。少年時代,對於迥異的兩個人,卻似乎是相通的。有一種屬於青春期的特殊語言,飛掠過國籍和歲月的圍牆,散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所以,麥克尤恩打動了我,毫不費力。可是,就像永遠也無法捕捉那個少女時代的我,究竟想說和想要的是什麼一樣,我始終不能保證,自己明白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中的男孩們的心緒。我必須一再誦讀,這些收信人不明的情書。
《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這個短篇小說的主角,是一隻瘋狂老鼠,以及一對冷冰凍的小情侶,還有一個配角不能忽略,就是那個精力旺盛的表弟。小說里寫的,是一段非常奇怪的初戀,既不熱烈,也不歡快,如果不是老鼠和表弟連番搗亂,它也許會沉悶得讓所有讀者睡過去。難道這就是我們最初的愛情嗎?可是,也許我們應該更坦誠一點,把初戀的果實,剖開來看一看。將美好、純潔、熱烈等一層層的葉片和果皮剝去,我們得到一枚非常嬌嫩的白色果核。它是那么敏感而脆弱,哪怕沒有風,不被觸碰,只是裸露在空氣里,也會迅速萎黃變質。所以牆角一隻老鼠發出的聲音,也足以驚擾到這份感情。老鼠作為一個強大的敵人,最終被消滅。然而他們的情感,也穿出了最初的青澀時期,進入一個嶄新而成熟的階段。在老鼠的葬禮上,同時埋葬的,還有那顆幼嫩的情感胚芽。結尾處,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年輕男人和一個年輕女人,他們將並肩面對前路未卜的生活。男孩對於長大,是有一些恐懼的。小說中有一段,是講男孩去西瑟爾上班的地方接她,忽然感到她淹沒在一群婦女當中,再也找不到。那些婦女穿著油膩的制服,抽著煙,匆匆忙忙地趕回家做飯。在男孩看來,她們代表著一種庸俗不堪的成人生活。可是不管怎么抗拒,他還是長大了。青春正在遠逝,這是多么悲傷的事。
在另一篇叫做《化裝》的小說中,男孩的年齡還要更小一些。可是他卻非常早熟。他正極力擺脫姨母給他套上的女人衣服,希望自己可以像一個年輕男子那樣,走向自己心儀的姑娘,向她表白心跡。他戰戰兢兢地一步步走近他的女孩琳達。他們傳遞小紙條,他被邀請去她家玩,他們並排躺在一張床上……亨利對化裝舞會充滿了期待,因為他確信這將會使他和琳達的關係變得更親密。他特意為自己買了一個面具,他以為戴上這個面具,他就不再是亨利,也可以就此逃離敏娜的監視。可是所有的人都能認出他,因為他是個孩子,完全不能混入成人之間的遊戲。他也根本不懂得遊戲的法則,化裝的真諦。成人的化裝,惟妙惟肖,他們因此可以鑽進別人的身份里,縱情狂歡。而亨利的化裝,是一個三十先令的簡陋面具,一個滑稽的怪物。他被關在了成人世界的門外。而成人世界,是一條漲滿欲望的大河,泛著腥惡的氣味。小說的末尾,亨利有些喝醉了,看到的琳達正像從前的他那樣,被敏娜污辱和傷害。這個琳達究竟是現實中的,還是他幻想出來的,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亨利在昏沉沉的酒意中,看清了成人的世界。
讓我們來看看書中其他的男孩們都在做什麼。《家庭製造》中,十四歲的男孩在過家家的祥和氣氛中,獲得了首次性經驗,從此躋身“人類社會的高級人群”當中;《夏日的最後一天》中,男孩在夏天的最後一次行船中,與可愛的胖姑娘珍妮永訣;《蝴蝶》中,蝴蝶是一個漂亮的謊言,在它迷幻的翅膀之下,男孩終於卸掉了阻塞在身體裡的欲望,簡則像一隻小船,承載著那些粘稠的東西,駛向運河深處;《與櫥中人的對話》里,那個一直被當作大嬰兒養了十七年的男孩,躲進櫥櫃裡,處理那點尷尬的欲望,他對自由不感興趣,只是想著如何回到溫暖而碩大的子宮;《立體幾何》中的主人公則恰恰相反,他多么渴望自由,自由地在立體幾何里游弋,現在他只是小試了一下身手,就成功地把妻子剷除掉了……
幾乎每一篇小說,都是一條明晰的界線,它鋒利地辟出兩個對立的世界,少年與成人,曖昧與清晰,天真與世故,孱弱與茁壯。我們看到一個個男孩助跑,加速,縱身跨過了那條界線,然後,他們沒入緩緩移動的人群,消失不見。我們的視野里,是一幀凝固了的風景,像麥克尤恩不斷提起的那樣:一個夏日將盡的傍晚,河水在腳下流過,小船載著被肢解的童年記憶,漫無目的地駛向遠方。天空中的餘暉支離破碎,宛如被刺破的童貞。在這個隆重的儀式上,沒有人哭,沒有人笑,到處是一片靜悄悄。仁慈的時間停下腳步,多給我們幾分鐘用來默哀,隨後,它又馬不停蹄地上路了。
媒體推薦
麥克尤恩的八個短篇一口氣讀完了。我經常讀到好書,可是讓我如此喜歡的書已經很久沒有讀到了。麥克尤恩在中國少為人知是不正常的,我相信他很快會引起中國讀者的喜愛,我願意為此而努力。
——余華
書中的八篇小說,在幾個月中,我反覆讀了好幾遍。重讀,並不僅僅因為喜愛,而是不能確信抓住了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東西。它們非常隱約,細微,像春天裡和著花粉的塵埃。我必須一再誦讀,這些收信人不明的情書。
——張悅然
麥克尤恩的虛構世界融合了德·基里科的城市畫面荒涼迷夢般的特質和巴爾蒂斯油畫中奇異的情慾色彩。文字的壟溝中時有臥虎潛藏,詭異之事就那么若無其事,那么沉著地走出來。
——《紐約時報》
珍罕之書,為英國小說開闢了新方向。
——Encounter
他的作品精確,細膩,風趣,妖異,擾人。
——《時代周刊》
一位真正具有想像力的天才。
——朱利安·巴恩斯
作者簡介
伊恩·麥克尤恩,1948年生,英國當代著名作家。1975年以處女作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成名,並獲次年毛姆獎。此後佳作不斷,迄今已出版十幾部既暢銷又獲好評的小說,並榮獲過包括布克獎在內的多項文學大獎,也是今後諾貝爾文學獎的大熱人選。
潘帕,生化學博士後,後棄研從實業,閒時讀書,著有《虛構即真實》部落格一處,並譯有《芒果街上的小屋》、《神諭之夜》、《聖誕憶舊集》和《沉溺》。
目錄
立體幾何
家庭製造
夏日裡的最後一天
舞台上的柯克爾
蝴蝶
與櫥中人的對話
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
化裝
序言
我第一次聽到伊恩·麥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國,也可能在法國或者義大利,人們在談論這位生機勃勃的英國作家時,表情和語氣里洋溢著尊敬,仿佛是在談論某位步履瞞跚的經典作家。那時候我三十多歲,麥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歲,還不到五十。我心想這傢伙是誰呀?這個年紀就享受起了祖父級的榮耀。
然後開始在中國的媒體上零星地看到有關他的報導:“伊恩·麥克尤恩出版了新書”,“伊恩·麥克尤恩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麥克尤恩的《贖罪》改編成了電影”……這幾年中國的出版界興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麥克尤恩的著名小說。
《水泥花園》、《阿姆斯特丹》、《時間中的孩子》和《贖罪》。可是中國的文學界和讀者們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這位文學巨人。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也許麥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讓中國讀者了解他。
文摘
面的牆壁。我本能地用手捂住臉抵擋玻璃四濺。等睜開眼,我聽見自己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是我曾祖父的。”在碎玻璃和福馬林蒸騰的臭氣之間,尼科爾斯船長垂頭喪氣地橫臥在一卷日記的封皮上,疲軟灰暗,醜態畢露,由異趣珍寶變作了一具可怖的褻物。
“真可怕。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又說了一遍。
“我要去走走了。”梅茜答道,這一次她狠狠地摔門而去。許久,我呆坐在椅子裡沒有動彈。梅茜摧毀了一件對我極具價值的物品。在他生前曾經矗立在他的書房,而今一直矗立在我的書房,把我的生命和他連結在一起。我從腿上撿起幾塊玻璃碎片,盯著桌子上那段一百六十年前另一個人的身體。盯著它,我想到那些曾經擁塞其中不計其數的小精蟲。我想像它曾去過的地方,開普敦、波士頓、耶路撒冷,被裹在尼科爾斯船長黢黑腥臭的皮褲里週遊世界,偶爾在擠擠搡搡的公共場所掏出來撒尿,才見到炫目的陽光。我還想像它觸摸過的一切,所有分子,在海上寂寞相思的長夜裡尼科爾斯船長摸索的雙手,那些年輕的姑娘以及色衰的娼妓們濕滑的陰道,她們的分子一定保存至今,還有那從切普賽街飄到萊切斯特郡。的一粒細小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