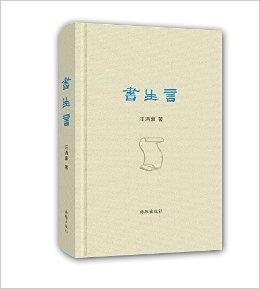內容簡介
愛默生說過,“閱讀乃屬個人的孤獨的行為”。汪涌豪對閱讀的理解是:“讀書既是進入,也是逸出,方寸中一段佳意,能在此出入中一一得到對應,天下哪裡有比這更好的事情。”通過本書,我們能體會到,讀書就是進入一種更廣大生活的護照,閱讀就是閱世,書生活就是真生活
作者簡介
汪涌豪,男,浙江鎮海人,1962年6月20日生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為日本九州大學客座教授,神戶大學特任教授。主治中國古代文學與美學,兼及古代哲學、史學與文化批評。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體系》《言說的立場》等14種。
圖書目錄
1 閱讀就是閱世(代序)
第一輯
3.隔代的聲音 陳舊的人物
10.木心之於今天的意義
19.教你識得真英雄
25.凡經眼處 皆成學問
31.有真學問,始有真思想
38.龔鵬程與俠文化研究
47.看破權力與陰謀的背面
53.另一種中國記憶
60.廣大的悲憫與深切的體知
第二輯
67.人學的歷史究問
73.一個時代的普遍體溫
81.階梯的搭建
87.一個寫得比說得好的人
94.像吳魯芹一樣了解英美文學
100.用這樣的勞績,走過半個世紀
107.傾聽來自內心的聲音
113.原來書品系人品
117.是幻影公眾 ,還是精英傲慢
第三輯
127.對文學史書寫歷史的省思
132.底層與邊緣的開顯
138.淡定從容的氣性 樸實厚重的學問
144.何謂小說史 ?
155.思想與學問的相與
161.什麼是善思無疆善辯無畏
168.古典詩詞的比較研究
176.著眼於範疇的生成
186.過程史研究的佳范
第四輯
199.闖入還是介入,這是個問題
208.復古的詩人
220.不過是小說官場而已
228.更多的人為聲音沉醉
234.對文學,也應該非誠勿擾
241.俗濫不是生活,時尚無關文學
252.域外的知解與祛魅
266.是羅列式的複述 還是發覆與解剖
第五輯
299.中國的根柢
300.名言的考究
310.箴言的拯救
314.依實出華與曲抵微達
321.你看你看陰翳的臉
331.什麼時代 如何言說
335.因為切近 所以陌生
附錄:訪談兩則
345.古詩文的當代機遇與命運
358.知日者智:今天我們該如何理解日本
369.後 記
後記
本書是個人在《文匯報》、《文匯讀書周報》、《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及《新民晚報》等報刊上發表的部分書評的結集。內容以人文為主,時間橫跨十年。
這個十年結束,我也年過五十。在這個時候,帶些許傷感看早先,那種心有蓬草,常隨風動,還有忙迫奔競與不能從容,雖說可體可原,終究多添慚愧。當然,不能說這種慚愧心起於朝夕間,但未逼近這個節點,還真沒從心底確認,其實人生值得忙迫的事情很少。載酒看花,賦詩聽曲,未必就是風雅;餚炙紛陳,釵環歷亂,更非賞心樂事。其他,就越發提不起了。
只是遺憾,人的意志力終究不像想像中那么強大,許多時候,欲望生長在心裡,並不受人控制;又有許多行事,一旦成為習慣,居然自成道理。直到這個節點到來,突然發現自己周知生活的每個細節,卻不能把握其本質,這才安靜下來,明白什麼叫一想流年,大事可哀,什麼是十丈軟紅,悉歸塵土。是謂知天命。
其間,讀書惠我最多。專業的關係,較常接觸的自然要數古籍,有時一冊在手,恍對千古;待端讀盡卷,復毛骨起立。最貼己的感覺是,書中過盡無數人物,不管年老年少,在朝在野,當收拾起岸然的道貌,都會重複上述平實的感覺。而類似“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的人生真感受,更被他們添上各自的體悟,一遍遍反覆提起。
我雖愚頑不肖,多少總有感觸。再植入當下實境,細審而熟思之,連類而及東西方哲人的言說,譬如阿爾貝·科塞里所作“世界上的美是如此之多,看見的人卻如此之少”與“慵散乃至高的人生享受”的感嘆,還有阿倫特所說的“現實世界熙熙攘攘紛繁複雜,一切在我們眼前飛逝而過,只有無所事事閒逛的遊手好閒者接收到了它的信息”,以及波特萊爾、本雅明等人類似的表達,終得以確認,人生如能自在便是幸福,便讀得懂青山原不動白雲自去來,做得到紙上空雲山心底無掛礙。
當然也知道,今天的世界,人人陷在紅塵里,誰也不救誰,其實誰也救不了誰。人人覺得生活給的,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結果多方忙迫,再無閒暇。花時間讀書就更少了。有人以為,有這么多事要做,哪有心思讀書,再說吧。也有感到犯難的時候,糾結著幾時歸去,做個閒人。其實,按我現在理解,只要真想,什麼時候都可以的。因為事實是,任何時代都可以說不是讀書的時代,又都可以說是讀書的時代。
自然,也有徹底的無所事事者,你有勞作的累,他只有閒得發慌的累。這就是塞巴斯蒂安·狄格拉斯所以要特別分疏,稱這個世界人人都有空(free time),但並非人人都有閒(leisure)的道理。他是以能擺落功利、看入人世為閒的。其中,自然也包括擺落功利的悠閒的閱讀。此刻個人想做的,正是這樣的閒者。所以,回應本書序言中的感慨,我想說,當此歲月與少年都陳舊不堪,個人更願意照著自己的意思活,讀書養心,自得其樂。有幸處承平之世,可以不問米價,不理朝市,消閒於甌茗壚香,出入於古典新章,人生享受,真不過如此。這樣想停當了,就只願能投入地享受這個狀態,能延長多久是多久。
記得愛默生說過,“閱讀乃屬個人的孤獨的行為”。有些人想岔了,以為人悖情昧世,才來讀書,並由此得出“讀書誤身”的結論。其實哪能呢,讀書既是進入,也能逸出,方寸中一段佳意,能在此出入中一一得到對應,天下哪裡有比這更好的事情。所以,想將蘇珊·桑塔格說文學的話改為說讀書,私以為讀書就是進入一種更廣大生活的護照,也即進入自由地帶的護照,閱讀即自由。還有,博爾赫斯說過,“我寫作,是為了讓光陰的流逝使我心安”,也想改一下,我讀書,不僅為求心安,還為能心生廣大的悲憫與欣喜,並沉潛往復,從容含玩。
謹以維多利亞時代丁尼生的《尤利西斯》詩,作為未來延續此人生意趣的砥礪:“尚未遊歷的世界在門外閃光,而隨著我們一步一步的前進,它的邊界也不斷向後退讓……幾次生命堆積起來尚嫌太少,何況我唯一的生命已餘年無多……來啊,朋友,探尋更新的世界,現在尚不算為時過晚……儘管已達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
最後,感謝所評論的每本書的作者!感謝俞曉群社長能接受出版本書,李忠孝等先生認真負責本書!也感謝鄭逸文、朱子奮、陸灝和楊曉輝最早刊發書中的文字!
作者
癸巳年十月
序言
閱讀就是閱世
1978年,我16歲,正當少年。在人生這個階段讀過的書可以跟人走一輩子。所以,類如浮士德的永恆衝動,曼弗雷德的孤高厭世,還有哈姆雷特的不斷懷疑與反省,成為日後一再提及的永恆記憶。說來好笑,我還非常想做文化基督山或社會羅賓漢,那種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隱在衝動,是個人30歲上起興做遊俠史的重要原因。
當然,那樣年代中的成長並不輕鬆。物質的匱乏與精神的貧瘠,都使人脆弱而易感。讀書無疑加重了這種感觸的分量。但當時的感覺,生命本來就需傷感滋養。以這樣的認知,當讀到《呼嘯山莊》,自然有一種直想坐起的衝動。其他如讀《卡拉馬佐夫兄弟》時的深重嘆息,讀《德伯家的苔絲》時的溫暖記憶,都構成個人寶貴的經驗。特別是,有時對一個情節乃至細節,可以樂至沉酣,轉生悲涼;對一個人物及其結局,可以憂鬱人深,反為曠達。這種情緒轉換帶出的刺激與快感,尤難向人言宣。
今天的孩子,20多了,通常還幼稚率薄,聽說狄更斯們可以為一個街區的拐角寫去幾千字,就問:如此虛益散辭,有什麼意思?還有,像羅曼·羅蘭這樣,讓克利斯朵夫與安多納德錯失在兩列相向而開的火車上,一如自己玩剩下的小把戲,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創意的安排。雖然個人體會,這紙上呻吟,就是當時血淚,但要我告訴他們,自己讀到這些地方,就直想著欲添清淚,成其潺諼,甚至還幻想獨占這輕輕一聲,與之相視莫逆,真還感到無力。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對偉大作家不總站在人類經驗之外審視人生,還站在人類知覺之上悲憫人生,今天的孩子能體認多少。他們還能像我們一樣感覺到,當個人無力表達纖敏而澎湃的激情時,這些偉大作家的經典創造,可以為人心底無法言說的經驗命名,甚至它們就是這種經驗最適切的代言?進而,他們能確認,這些偉大創造可以如天意神啟,讓人靜聽極視,與浩瀚的宇宙相往還;又可以如大雨行潦,為靈魂沖刷出一道開闊的河床?
該如何告訴他們,快樂滿足的僅是感官,經典滿足的才是心靈。尤其重要的,該如何使他們也有這種體驗,說每次與經典相遇,其實都是與人性照面,與自己交談。這一點,他們能知道並願意知道嗎?特別是,當他們的閱讀通常不再及此,並因這種不及,不再認為經典之於人生有多切要時。他們自有他們認定的偉大作家和作品,譬如仙幻有仙幻的經典,盜墓有盜墓的經典。你要在他們心裡再放一個幾世紀前英國的老古玩店,或能欣賞瑞典人蓋的那座背陽的紅房間,太難了。
結果自然是糟糕的,許多人除了在中學的文學課上讀過一些經典(可惜通常是節讀與速讀),在電視上看過一些經典(又通常是戲說或歪說),再沒有開卷有益的經歷。杜威比讀書為探險,法朗士比讀書為壯遊,都是指著書能豐富人的靈魂說的,但他們只拿它作消閒;孟德斯鳩說讀書可將生活中的厭煩時刻變成美好時光,他們全把它變成了遊戲時光。以至於開目僅能上網,伸紙不能修函,欲傳達自己的曲曲心事,只能藉助流行語火星文通俗歌曲廣告詞。僅此一端,不難想像那將要到來的結果會有多糟糕。那種情感的均質化與粗鄙化,乃或均質的粗鄙化所帶來的人的認知的淺表與膚偽,已在在凸顯了一個時代思想的貧薄與匱乏。這種貧薄與匱乏,是必定會阻礙和延緩一個民族的心智成熟的。
但我們也不失去希望。從慘綠少年到哀樂中年,由書頁上斑駁的日影,我們感覺著時間的流逝,也時時體會到生命的豐盈。我們心懷感激,說自己倘有寸進,都是拜讀書所賜。基於從閱讀中得到的回饋是那么的豐厚,我們沒理由悲觀。相反應該相信,總有一個時刻,人們會安靜下來,為人生的意義思考。總有一天,人們得重新認識讀書之於人生的意義,並由衷地體會到,倘若有種東西,你自己內心沒有,誰都不能頒賜給你。
今年春節,讀加拿大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的《閱讀日記》,前言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有一些書,我們是可以輕快地一覽而過的,當我們翻到下一頁的時候,已經淡忘了前一頁的內容;有一些書,我們是需要恭恭敬敬地閱讀的,不敢對其中的內容妄加評論;有一些書,僅僅為我們提供信息,也並不需要我們對它們加以評頭論足;然而還有一些書,我們是如此長久而深情地摯愛著它們,因此,是可以從最最真實的意義上,運用心靈的力量逐字逐句地重溫它們的,因為我們理解它們。”若問:人們領受著書的啟迪,並不時地要“重溫它們”,怎么還能大剌剌地說早就“理解它們”?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回答是:“我們真正的出生地是那個自己有生以來第一次用智慧的眼睛關注自身的地方。對於我來說,我的第一故鄉就是我的書籍。”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人為什麼永遠與書相視莫逆,為什麼只有這種相視莫逆,才讓人歷經永劫之邦,既聽得到絕望的呼喊,又看得到受苦的靈魂;既體認得到方死的夙願,復更矚望於未生的希望,並此心此性,無蔽無欲。
契合著個人的經歷,年前曾再讀但丁,《神曲·地獄篇》的第一段說:“就在我們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中醒悟過來,因為我在裡面迷失了正確的道路。”許多像我這個年紀的人都有過迷失。藉助於種種外力的幫助,最終都走了出來。但在我,讀《神曲》本身,就是走出迷途的最好方法。很樸素的道理,因為閱讀就是閱世,書生活就是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