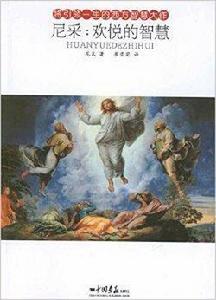內容簡介
《尼采:歡悅的智慧》在尼采的一生中處於中心的位置,它也是尼采採用哲學的敘述方式最成功的嘗試。身為哲學家的尼采與科學對立,又以哲學家的身份抗拒藝術,同時也抗拒哲學家的語言。尼采處在藝術和科學的彼岸,為這個主題傾注了持續不斷的熱情,這部作品正是這種熱情的成果。
《尼采:歡悅的智慧》提供了一種新的人類精神中關於科學和藝術問題的解決辦法,尼采並不是要壓抑和抑制科學和藝術,而是將二者置於一個美化的領域使之共存。
圖書目錄
諷刺、陰謀與報復——德國韻律短詩序曲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附錄:“自由之鳥”王子之歌
序言
鑒於不同時期尼采思想的不同發展歷程,同時也為了研究的方便起見,通常我們把尼采的全部正式出版著述區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第二期的起止年限是從1878年到1882年。在這五年時間內,尼采先後出版了三部重要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朝霞》以及《歡悅的智慧》。與早期的成名作《悲劇的誕生》相比,不論是在寫作風格方面,還是在論述主題上面,這三部著作都迥然有別,研究界據此將之界定為尼采思想發展歷程中的第二期,亦在情理之中。這三部著作雖說同為精湛之作,卻各有其相關側重點,不能一概而論。《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書,因是尼采格言體的開山之作,又曾經受到讀者包括尼采本人的格外垂青,似乎應當最受關注。可惜,說到思想的成熟性與重要性來講,不論是《人性的,太人性的》,還是《朝霞》,都略欠火侯。嚴格算起來,此一時期的核心著作,仍要推這部《歡悅的智慧》。
在詳細論述《觀悅的智慧》之前,有必要先對所謂尼采哲學的“過渡期”說上幾句。總體而言,這三部著述同屬過渡期,既缺乏《悲劇的誕生》那樣揮劍提刀,絕然斬斷與千年哲學傳統之間聯繫的勇氣與開風氣之功,又沒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超人作正傳,企圖規劃千年未來的雄心與定論之效,表面看來仍不過是些泛泛而談,浮誇不實之論的收羅與結集,充其量只能當作茶餘飯後的消譴與談資,全無深入閱讀,細密梳理的必要。這種斷言符合通論,不能說全無道理。只是在領會尼采思想過渡期的獨特意義之前,貿然寫下這些斷言,又未免略顯草率,難以真正讓人折服。如果我們細觀這三部著述,則會發現,其典範性的格式體書寫風格,構思的功效與美感並重;極為寬廣的問題視域,藝術到哲學無一不收;頗具啟發性的論述節奏,點到為止卻又發人深省的洞見,凡此種種最終使得它們超出了過渡期的簡單限定,而成為尼采思想發展史的又一獨具風格的里程碑式著述。此外,即便單純以思想的過渡期的眼光來看,尼采的這些著述亦不容忽視。思想的過渡期同樣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想不到的魅力。鑒於尼采早期和晚期思想之間的巨大差異,這就尤其襯托出其過渡期作品的重要性;同樣,鑒於此一時期著作的格式體寫作風格,使得研究者無法輕易抓住其思想的真義,導致卷軼浩繁的尼采“注釋學”的興起。不過,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在享受尼采的美文美思之外,只需對下述兩點稍加留意,便綽綽有餘。其一,相對於早期的思想,過渡期可視為一種修正,視為尼采自身對早先觀點的利弊得失的詳盡分析;其二,相對於後期的定論,過渡期可看作一種萌芽,是尼採在新觀點尚不自信時的牛刀小試與鋒芒初露。學術研究以分析思想流變為重心,過渡期自然成為尼采學術研究者的至寶。
關於中期對早期的修正,我們可以舉“日神和酒神”這一對著名概念為例——《悲劇的誕生》中大受推崇的酒神與日神之間通過辯證法所保持的微妙平衡,由於此時的尼采把知識論的根源上溯到道德,進而一意強調道德的對立面“本能”的具體功效,而本能的含義正與酒神的迷狂放縱精神相呼應,因而不知不覺之中,酒神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使得早期的酒神與日神間的平衡最終被打破,酒神越過日神,成為兩神中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此時的日神就完全遭到了拋棄。因為過渡期的特點正在於喜新而不厭舊,日神的象徵意義在於夢的幻想力與藝術的造型力。當尼采把酒神的本能象徵意義放大之後,日神的藝術力量已經難以與之並駕齊驅,尼采並未因此選擇徑直將日神加以拋棄,而是另行將日神從兩神的辯證法中分裂出來,將藝術造型力重新塑造為藝術與哲學的“視角主義”。換句話說,在尼采看來,世界沒有本質可言,有的只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與視角,而藝術正是充當了這一重要的角色。當然,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為了追求理論的一貫性,後期尼采完全拋棄了日神,而把原屬日神的這一藝術造型力,同樣賦予了酒神。
而對於中期向後期的過渡,說到例證,“求生存的意志”和“求權力的意志”,當然是不二之選——尼采自少年時期起,即痴迷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其影響。這種痕跡,終尼采一生都不曾完全消退。尼采思想的變遷發展,當然可以用尼采自身在不同主題間的轉變加以正面論述,不過,基於尼采與叔氏的密切關係,我們亦可以用其對叔氏的相關思想的態度變更為坐標,從側面對這種變更加以界定。而這其中,從“求生存的意志”到“求權力的意志”的轉變,是極為關鍵的一點。我們知道,叔本華將人的一切理性與意志歸結為求生的意志,認為理性沒有獨特價值,只是物種為了自身的延續而發明的生存工具。受之影響,尼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贊同這一觀點,並根據不同情境,用自身的獨特筆法對之進行發揮。即便在《歡悅的智慧》中,這樣的情況仍然存在。不過,取代“求生存的意志”,“求權力的意志”出現了漸漸占據上風的趨勢,這一點尼採在1887年《觀悅的智慧》印行第二版時,為之增補的第五卷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當然,即便在第一版的四卷中,這一點業已有所體現。由於“求權力的意志”在後期尼采著述中,以及在尼采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關鍵地位,《觀悅的智慧》讓此兩者共存,且後者逐漸占據優勢的跡象,足以表明此時的尼采已開始擺脫叔氏的影響,嘗試確立自身的思想體系。
不過,對於尼采研究界而言,《歡悅的智慧》之所以重要,除開上述原因之外,還在於其首次明確提出“上帝已死”這一主題,並首度界定了尼采後期的核心問題——“虛無主義”。而“虛無主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尼采的主要解讀家,不論是德國的海德格爾,還是法國的德勒茲,抑或是美國的羅森,都以之為基點,對尼采的思想進行整體式的發掘與解讀。簡言之,海德格爾認為尼采只是打倒了基督教上帝的權威,但並未能深思以至顛覆哲學的基本運思範式,依舊停留在“虛無主義”之中;而德勒茲則認為尼采通過對存在之“多樣性”的肯定,業已擺脫了形上學和“虛無主義”;羅森則從政治學出發,指出尼採在破壞和創造新世界之間存在原則性衝突,斷言尼采式克服“虛無主義”嘗試的失敗。
海德格爾的“存在論”解讀確信,尼采哲學僅是完成了“主體性的暴動”,對存在問題始終未曾運思,因而其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僅是對虛無主義的完成。海氏進而斷言尼采通過將“存在”轉化為“價值”,完全掩蔽了理解“存在”的可能性。價值思想於是就是純粹的虛無主義。德勒茲的“後現代”解釋,則認為尼采通過對“多樣性”和“生成”的清白辯護,使得肯定的力戰勝否定的力,最終克服了虛無主義。而羅森“政治學”解讀斷言,“尼采試圖將康德對世界構成的理想化描述與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是了解人類本性、懂得如何劃分其基本類型的等級順序的預言家和立法者的觀念結合起來”,這種不成功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其對虛無主義的真正克服。凡此種種,均有其特定的理論缺陷,不足以為尼采哲學蓋棺定論。
尼采將蘇格拉底看作理性主義的發起人,把柏拉圖看作“兩個世界”的劃分者,認為西方哲學從此處於“柏拉圖主義”的統治之下。從此一角度出發,尼采認為西方哲學史就是一部虛無主義展開史,要想對之加以克服,只能通過“重估一切價值”,通過對“兩個世界”的翻轉來加以實現。但是,如果尼采就此止步,我們可以說海德格爾對尼采的批評是中肯的,尼采依然停留於傳統形上學之中,他無法從根本上克服虛無主義。問題在於,尼采並未就此止步,對理性主義的把握僅是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通過對道德現象的研究,尼採在理性主義的根基處發掘出“道德信仰”,每一種理性證明後面總有一種道德信仰為其支撐,因而克服虛無主義的關鍵不在於克服“理性主義”,而在於克服其根基——“道德主義”。海德格爾囿於自身的哲學框架和關注點,完全不顧尼采哲學的這一重要維度,所以他的解讀雖極富啟發性,但就尼采哲學的思路把握方面尚有其不當之處。
德勒茲的“後現代”解讀就表面而言似乎最合尼采本意,因為尼採在各個場合均大講特講“肯定”與“否定”,認為道德的問題在於將外在價值標準置於人類生命之上,並對之作了無理的要求與規定,從而敗壞了生命的健康本能。否定的勝利造成了虛無主義的盛行,現在目標在於如何實現肯定對否定的勝利,為此德勒茲在尼采那裡尋找出四個階段,“狄奧尼索斯一阿里安,或者二重的肯定;‘永恆回歸’或者加倍的肯定;超人或者肯定的類型和產物”。經由這四個階段,尼采使得肯定的力重獲優勢,實現了對虛無主義的克服。這種解釋的好處在於將尼采哲學從納粹的影響下拯救出來,為尼采哲學在二十世紀的流行奠定了基礎。但是這種解讀的缺陷亦很明顯,尼采對道德的考察使其進一步達至對“本能”的研究,“本能”方面所蘊含的殘酷性卻是任何打扮與化裝都難以掩蓋的,德勒茲對這一點所作的巧飾不能令人滿意。
羅森對這一點非常清楚,因而他一上來就要說,“尼采可能在致力於一種虛無主義修辭”,比如“人們可以通過堅持有益的、具有解放性結果的觀點:‘一切均被允許’,致力於虛無主義修辭;相反,人們也可以運用修辭,隱蔽虛無主義已發揮作用卻未被意識到的破壞性結果”。羅森通過對這種修辭的強調,試圖證明,在尼采的“混沌說”和“創造說”之間,存在著一段論證脫節,這一論證空白使得尼采的“創造說”的說服力大受影響。然而,所謂“創造說”即是尼采的“本能主義”等級制、貴族制,即是兩類人的戰爭與遴選。羅森的研究最終將尼采哲學把握為詩對哲學的勝利,從而淡化了尼采哲學的殘酷面目。然而羅森的說法要能夠成立,除非我們認為尼采確實有意玩弄兩種修辭,而有關這一點的論據顯見不足。
就一般思路而言,既然“虛無主義”發端於“最高價值的自行貶值”,最高價值的缺位,那么只要重新恢復價值的原有地位,或者尋找一種新價值填充進去,“虛無主義”自然就被克服了。但對尼采而言,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因為此種“最高價值”的確立有賴於兩個世界的劃分,尤其有賴於“超感性世界”的真實無妄(或者說是對它的絕對信仰),可惜自黑格爾哲學解體之後,這樣的劃分顯然已經不可能。缺乏這樣的劃分結構,最高價值就無法恢復其原有地位,任何一種新的價值填補亦只能是一種自覺不自覺的自欺欺人。
相反,尼采的過人之處在於其徹底把握了傳統形上學的基本結構,並斷言任何形式的修修補補都是徒勞的,對虛無主義的真正克服必須首先放棄這樣一種基本結構。尼采之所以主張堅決拋棄這種基本結構,不僅在於其通過認識論的考察(一切均是解釋)洞察了“超感性世界”的虛妄性,更在於其發現,在這種二分結構的底層隱藏了一種道德考量,即求“存在”、求“統一”的道德訴求。在尼采看來,這樣一種道德訴求只能出於一種本能(權力意志)的低下,弱者的天性使然。非但如此,此類弱者反而把握了社會各個門類的要津,並以道德之名,對與之相反的強者類型實施迫害(使其自殘與內疚,最終自行消亡)。因而在尼采看來,在這種情況下,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就不單單是從學理上對形上學結構的簡單摒棄,而是兩類人之間關於統治權你死我活的鬥爭(正是出於對兩類人劃分的需要,尼采引入了“權力意志”)。因為只要弱者當權,這樣的拋棄就不可能實現,各種候補式證明就會不斷被提出,以便延續形上學的伎倆,進而鞏固對其有利的道德。但是強者從來就不曾有過對“超感性世界”或“最高價值”的需要——即便有,也只是在道德的壓迫下產生過虛偽的需要。道德的本質一經揭穿,其合法性一經捅破,這種需要旋即煙消雲散。因而克服虛無主義的更深層問題不在如何拋棄“形上學基本結構”,而在於怎樣克服“道德壓迫”,而“道德壓迫”的施行者即為現今的統治者,他們本能虛弱,權力意志低下,因而需要運用“道德”為其辯護,並藉助“道德”壓迫強者。
因而,為了克服虛無主義,尼采異常強調本能(權力意志)的重要性,進而主張按照本能的排序,在各類人等之間重新劃分等級,力求恢復前蘇格拉底時期的貴族制,以期實現西方文明的再造。這方是其為虛無主義開出的最終藥方。納粹的暴行可看作是對尼采哲學的一次不完全實踐,藉此引發了人類史無前例的災難,就這一方面而言,不論怎樣修飾,尼采哲學都難辭其咎。另一方面,針對西方文明的虛無主義危機,尼采通過對西方文明源頭的重新考察,呼籲開出第二條發展路線的創舉卻大大影響了二十世紀人類思想走向,引發了新一輪更深層次對人類自身文明處境的反思,在這一方面,尼采可謂功不可沒。
更重要的是,伴隨西方文明的經濟擴張,西方文明的一己思想處境正不斷演化為世界文明的共同思想處境,西方的命運正擴展而為世界性命運。在此背景下考察尼采對西方文明的診斷,分析其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就不單單是一種論人家是非,更是對我們自身前途命運的一種擔憂與警示。其意義廣大深遠。
總之,不論是為了把握西方文明,還是為了理解尼采,《歡悅的智慧》都是一部必讀之書。
是為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