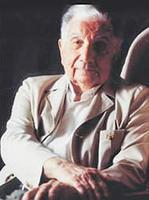人物經歷
早期生活
羅亞·巴斯托斯於1917年6月13日生於亞松森。他的童年是在伊土比、瓜伊塔區的省城渡過的,他父親在那兒管理一個糖料種植園。 伊土比離巴拉圭首都亞松森大約200公里,在那兒羅亞·巴斯托斯學會了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巴拉圭的本土語言。十歲那年他被送往亞松森念書,與他的舅舅埃梅內希爾多·羅亞、亞松森的一位開明的主教住在一塊兒。
他舅舅規模頗大的私人圖書館使年輕的羅亞·巴斯托斯接觸了巴洛克時期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西班牙語文學傳統,他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早期詩歌便是模仿那些古典著作。 另外,他舅舅對古典文學中玄秘方面的強調對羅亞·巴斯托斯之後的寫作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瓜拉尼社會風俗及語言方面的知識與在亞松森接受的西班牙傳統教育這兩者相結合,使得他的作品在語言方面顯示出文化和語言方面的二元性。 他在鄉間的早期經歷使得他能充分體察到當地下層人民的疾苦,這成為他寫作中的突出主題。
戰爭寫作
1932年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間的查科戰爭爆發,這場局部戰爭一直持續到1935年。戰爭期間的某一時間,或許在1934年,羅亞·巴斯托斯作為醫療輔助隊員加入了巴拉圭的軍隊。這場戰爭對這位未來的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曾說:“當我離開家參加戰爭時我夢想在戰鬥的激情中得到心靈的升華。”然而這場戰爭並未帶來榮譽,當他看到殘缺的肢體和一片片廢墟時他開始質疑“為什麼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這兩個兄弟國家會互相殘殺”,作為其結果羅亞·巴斯托斯成為了一名和平主義者。
戰爭之後他先是成了銀行文員,之後成為了一名記者。在這期間他開始寫劇本和詩歌。1941年羅亞·巴斯托斯因《富爾亨西婭·米蘭達》獲巴拉圭獎,雖然那本書從未公開發表過。1940年早期他將許多時間花在北方的巴拉圭茶種植園上,他將在種植園的經歷運用到他首部公開發表的小說《人子》(1960) 上。1942年他被指定為亞松森日報《國家報》的主編。
1944年英國議會因他為倫敦報業作出的貢獻為羅亞·巴斯托斯提供九個月的資助。在這期間他遊歷了英國、法國和非洲的許多地方,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毀滅。他為《國家報》作戰地記者,在1945年戴高樂將軍回到巴黎時採訪了他。羅亞·巴斯托斯還在BBC和法國信息部的邀請下製作了許多關於拉丁美洲的廣播節目。
在這個多事的時期羅亞·巴斯托斯繼續寫作,並被最為巴拉圭的先鋒詩人。1942年他出版了一本古典西班牙語風格的詩集《歌唱黎明的夜鶯》,然而後來他否定了它。他還在1940年代成功的完成了多部戲劇,雖然它們從未被公開出版過。他1940年代晚期豐富的詩歌創作之中只有《燃燒的橘林》後來被出版。
流亡生涯
 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
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1947年2月巴拉圭內戰爆發,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奪取了政權。羅亞·巴斯托斯被迫逃亡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因為他曾公開反對斯特羅斯納和與他聯盟的總統伊西尼奧·莫里尼戈。那時大約有5000000名巴拉圭人和他一樣離開祖國逃往阿根廷。
羅亞·巴斯托斯一直呆在阿根廷直到1976年軍事獨裁政府在那兒確立,並且在1989年以前仍沒有回到巴拉圭。他的流亡生活十分困難,但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時期是他最多產的時候。
1953年,小說集《葉叢雷聲》出版並在國際間流傳,它包含17篇短篇小說,然而直到1960年長篇小說《人子》出版羅亞·巴斯托斯才在評論界和普通讀者中贏得了巨大成功。 這篇小說描繪了從1800年代何塞·加斯帕爾·德·弗朗西亞的統治到1930年代查科戰爭這段令人壓抑的巴拉圭歷史畫卷。他多重的敘事視點和歷史及政治主題預示了他十多年後寫的最著名的小說《我,至高無上者》。在《人子》發表同年,羅亞·巴斯托斯將其改編為一部獲獎電影。
羅亞·巴斯托斯後來致力於寫電影劇本,1960年他寫了《Shunko》,由勞塔羅·穆魯阿導演,這部電影是根據一個鄉村學校教師的自述改編。 1961年他再次與穆魯阿合作,為電影《Alias Gardellino》作編劇,這部影片描寫了城市小罪犯的生活,成為“新電影”運動中的主要獨立電影之一。1974年羅亞·巴斯托斯發表了他的最有影響的傑作《我,至高無上者》,這部小說花費了他七年的心血。當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在1976年確立軍事獨裁統治時,這本書在阿根廷被禁,羅亞·巴斯托斯又一次流亡,這回的目的地是法國的土魯斯。
法國經歷
他從1970年開始被允許訪問巴拉圭並與新一代的巴拉圭作家合作,他在1982年再次被禁止入境,因為據稱他參與了顛覆活動。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曾參加任何種類的政治派別。 羅亞·巴斯托斯又一次被迫重回法國,但這一時期他也擁有了新的讀者群。海倫·雷恩英譯了《人子》和《我,至高無上者》,這些譯著於1986年出版,並在英 語世界得到了廣泛的好評。然而在法國,羅亞·巴斯托斯主要集中精力寫理論著作,他的文學產量遠不及在阿根廷的時期。1985年他放棄了在土魯斯大學的職 位。 隨著1989年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獨裁政權的垮台,羅亞·巴斯托斯應新任領導人安德烈斯·羅德里格斯之邀回到了巴拉圭。
塞萬提斯獎
1991年,羅亞·巴斯托斯代表巴拉圭簽署了《莫雷利亞宣言》,“要求防止地球生態的毀滅” 這時羅亞·巴斯托斯再次成為了一個活躍的小說家和劇作家。
1991年羅亞·巴斯托斯將《人子》改編成電影。1992年,他出版了自《我,至高無上者》後的第一部小說《不眠的海軍司令》,第二年又出版了《檢察官》。雖然他晚年的作品影響大不如前,《檢察官》仍被認為是一部重要的作品。羅亞·巴斯托斯於2005年4月26日因心臟病發作在亞松森逝世。他留下了他的三個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伊利斯·希門尼斯,以及拉美最傑出作家之一的美譽。
主要作品
| 中文名 | 外語名 | 首版時間 | 體裁 |
| 《人子》 | Hijo de hombre | 1960 | 小說 |
| 《我,至高無上者》 | Yo, el Supremo | 1974 | 小說 |
| 《不眠的海軍司令》 | Vigilia del admirante | 1992 | 小說 |
| 《檢察官》 | El fiscal | 1993 | 小說 |
| 《逆向生活》 | Contravida | 1994 | 小說 |
| 《葉叢雷聲》 | El trueno entre las hojas | 1953 | 小說 |
| 《空地》 | El baldío | 1966 | 小說 |
| 《燃燒的木頭》 | Madera quemada | 1967 | 小說 |
| 《水上行》 | Los pies sobre el agua | 1967 | 小說 |
| 《屠殺》 | Moriencia | 1969 | 小說 |
| Cuerpo presente y otros cuentos | 1971 | 小說 | |
| El pollito de fuego | 1974 | 小說 | |
| Los Congresos | 1974 | 小說 | |
| El somnámbulo | 1976 | 小說 | |
| Lucha hasta el alba | 1979 | 小說 | |
| 《遊戲》 | Los Juegos | 1979 | 小說 |
| 《講個故事》 | Contar un cuento, y otros relatos | 1984 | 小說 |
| Madama Sui | 1996 | 小說 | |
| Metaforismos | 1996 | 小說 | |
| 《無罪的土地》 | La tierra sin mal | 1998 | 小說 |
| Hijo de hombre | 1960 | 電影劇本 | |
| Shunko | 1960 | 電影劇本 | |
| Alias gardelito | 1961 | 電影劇本 | |
| El senor presidente | 1966 | 電影劇本 | |
| Do segundo sombra | 1968 | 電影劇本 | |
| Yo el Supremo | 1991 | 電影劇本 | |
| 《歌唱黎明的夜鶯及其他詩歌》 | El ruiseñor de la aurora, y otros poemas | 1942 | 詩歌 |
| 《燃燒的橘林》 | El naranjal ardiente | 1960 | 詩歌 |
| 《個人文選》 | Antología personal | 1980 | 文選 |
| Cándido Lopez | 1976 | 其他 | |
| Imagen y perspectivas de la narrativa latinoamericana actual | 1979 | 其他 | |
| Lucha hasta el alba | 1979 | 其他 | |
| Rafael Barrett y la realidad paraguaya a comienzos del siglo | 1981 | 其他 | |
| El tiranosaurio del Paraguay da sus ultimas boqueadas | 1986 | 其他 | |
| Carta abierta a mi pueblo | 1986 | 其他 | |
| El texto cautivo: el escritor y su obra | 1990 | 其他 | |
| Mis reflexiones sobre el guión y el guión de "Hijo de hombre" | 1993 | 其他 |
作品風格
羅亞·巴斯托斯熟練地使用魯伊·迪亞茲·的·古茲曼所使用的重要的寫作風格,比如瓜拉尼式西班牙語、魔幻現實主義、巴拉圭歷史的重構、社會文學、對集體記憶和詩歌意象系統的探索。 他也是巴洛克風格的代表人物之一,這種寫作風格使用一種複雜的隱喻系統,該系統與羅亞·巴斯托斯生長的土地(巴拉圭)、當地植物與文化緊密相連,其大多數作品的核心內容是關於政治自由和祖國解放的理念。
羅亞·巴斯托斯最初的詩歌融合了西班牙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傳統。之後的詩作則體現出巴列-因克蘭、胡安·拉蒙·希梅內斯以及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等人的影響,呈現出一種新的敏感性。而他的小說穿梭於過去未來之間,情節融合了前殖民時代的神話以及基督教的傳說,發展了魔幻現實主義的一種特殊形式,雖然他的小說在體裁上十分多變。
巴拉圭:集體記憶
羅亞·巴斯托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流放中寫成,這歸因於他的祖國壓抑的政治環境,那時巴拉圭在文化、經濟、政治上都是拉美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因此,他那些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嘗試捕捉他的國家的人民內在的脆弱性和悲劇因素。 他的作品不僅關心當代巴拉圭,也關心它的歷史,尤其是加斯帕·的·弗朗西亞統治時期(那是《我,至高無上者》的焦點所在)。羅亞·巴斯托斯對這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感興趣,這些關於“民眾本性”的“社會歷史根源”成為他文藝創作的中心主題。
他的創作包含著豐富的象徵和多樣的敘述性,這些都建立於巴拉圭人的集體記憶之上。比如《我,至高無上者》在人民共有的回憶和符號之上構築起“流行運動的可能歷史”。互動式小說《我,至高無上者》是這種技巧的傑出代表,在遣詞和敘事上都是如此。在《檢察官》、他關於濫用政治權力的第三部小說中——這回關注的是斯特羅斯納的政權——羅亞·巴斯托斯又一次提供了一種被接受的歷史事件版本的可選性,向“歷史的可理解性”發起挑戰。最後,他將幻想的原理及超小說技巧融合到敘事中。
介入鬥爭的作家
羅亞·巴斯托斯相信直接參與當代及過往歷史的詮釋是作家的指責。他認為作家在與那些社會問題交戰上比客觀的編年史家更勝一籌。 羅亞·巴斯托斯認為“文學活動就是要表示直面命運的必要性,它的願望就在於支撐集體的生命真實、它的真正道德背景和社會結構、以及與同時代本真的複雜聯繫——也即獻身於普遍的人類世界。”因此,羅亞·巴斯托斯寫作的主要主題之一是一種深沉而普遍的人道主義,他尤其關注人類的苦難。
毫無疑問,羅亞·巴斯托斯自身的經歷在他對人類苦難的強調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年輕時曾參加查科戰爭,他在《人子》中描寫了這個事件。之後他又在歐洲親眼目睹了二戰所帶來的毀滅、巴拉圭1947年的暴力鬥爭,以及1976年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的興起。他的短篇小說集《葉叢雷聲》於1953年出版,它關於政治壓迫和反抗的黑色描寫為《人子》和《我,至高無上者》打下基礎。二十年後《我,至高無上者》出版,時實踐了羅亞·巴斯托斯關於“介入鬥爭的作家”的理念。
雙語現象
與大多數出身農民或工人的巴拉圭人一樣,羅亞·巴斯托斯從出生始學習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都是巴拉圭的官方語言(後者主要是口頭語言)。雖然瓜拉尼語在家裡或“街上”都很“普及”,西班牙語卻代表著官方業務和權利。在歐洲進行殖民統治後幾個世紀裡本土語言的保存和廣泛使用是拉丁美洲的一個獨特現象,而瓜拉尼語是巴拉圭民族主義的象徵,並且是解釋這個國家歷史真實的有效媒介。 這是18世紀統治巴拉圭用瓜拉尼語傳教的耶穌會士所留下的遺產。
羅亞·巴斯托斯最初以西班牙語開始寫作時,這兩種語言的相互影響是他風格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樣,羅亞·巴斯托斯的語言使用範圍被大大拓寬了,同時也造成了一種國際通行語言和一種晦澀和極度巴拉圭化的語言間的張力。 羅亞·巴斯托斯將兩種語言的關係描述為“在口頭語言和文學語言上幾乎是一種精神分裂”。
人物影響
羅亞·巴斯托斯的寫作橫跨四個國家、六十年的事件、以及無數的流派。他一生為拉丁美洲文學爆炸以及獨裁者小說的寫作以及新電影運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羅亞·巴斯托斯影響了許多國外的後爆炸時期作家,他們包括門波·西亞爾迪內里、伊莎貝爾·阿連德、埃爾西利亞·賽佩達、索爾·伊瓦古言、路易莎·巴倫蘇埃拉以及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作為巴拉圭最有影響的作家,他對巴拉圭新一代作家也保持著很高的影響力。羅亞·巴斯托斯與他祖國的聯繫在超過40年的流亡生涯中並沒有破裂,當斯特羅斯納政權解體後,他應新總統之邀回到了祖國。
在《我,至高無上者》之前,一些評論家就認為巴斯托斯的《人子》足以使他躋身於世界偉大作家之列。是之前的作品確立了他的地位。據胡安·曼努埃爾·馬科斯所說,《我,至高無上者》“預告了許多後爆炸時代的寫作技法”,比如“歷史論述、文本化、戲仿的嘉年華”。 墨西哥文學大師卡洛斯·富恩特斯稱《我,至高無上者》是拉美文學的里程碑之一。 雖然他的名聲主要來自長篇小說,羅亞·巴斯托斯在電影、創造性寫作、新聞方面的貢獻同樣充實了他的遺產。
獲獎記錄
| 文學獲獎 |
|
(以上內容參考資料來源 )
人物評價
綜觀世界文學,近半個世紀裡,拉美文學似乎比任何一個區域的文學更講究藝術技巧,而羅亞則是講究藝術技巧的拉美文學中的佼佼者,他把許多事情映在我們的腦海里,因為那些事情發生在一個不值得留戀的混亂和恐怖的時代,如同一場噩夢一樣。羅亞筆下的巴拉圭百年史,簡直就是一個漫長夢魘,貓頭鷹的哀鳴像悲傷的鐘鳴一樣伴隨著瓜拉尼人的始終。也許為逃避現實,他們更多的是沉浸於冥想和幻覺之中,因為在他們看來,幻覺比現實更真切。羅亞在他的小說里,仿佛是惡作劇一般,乾脆把現實和幻覺、過去和未來以及往世和今生糅在一起,讓你分辨不出來,這就最大限度地喚起你的想像力,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網易文化頻道評 )
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以新穎的藝術手法和表現技巧,反映了巴拉圭的現實。(馮平《世界文學百科》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