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年表
1991年11月,獲“西泠印社”第二屆全國篆刻作品展評優秀作品獎(最高獎)。
 大成
大成1995年4月起“江蘇省青年篆刻首屆、二屆、三屆均優秀作品獎”(最高獎)。
1995年11月參加“全國第六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
1997年4月參加“第二屆國際篆刻藝術交流展”。(中、日、韓)。
1998年12月獲“全國第七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提名獎)。
同月參加“全國第四屆篆刻藝術展”。
2000年至2008年:連續獲“淮安市文化藝術政府獎”。(連續八年獲政府獎)
2000年4月參加“全國當代青年篆刻家作品展”。
2004年3月參加“全國第八屆書法篆刻作品展”。
2005年9月參加“全國第五屆篆刻藝術展”。
2006年11月獲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蘭亭獎)
2006年12月被評為“2006年江蘇省優秀青年書法篆刻30家”。
2007年5月參加“當代篆刻藝術大展”。同年9月赴香港舉辦展覽。
2009年1月參加“全國第六屆篆刻藝術展”。
2010年5月至今,為榮寶齋畫院范揚山水畫工作室畫家。
2012年8月.獲中國(芮城)永樂宮第五屆國際書畫藝術節。(優秀作品獎)
2013年5月入展"全國第七屆篆刻藝術展"
人物專訪作品散見於:《美術報》、《神州詩書畫報》、《書法報》、《書法》、《青少年書法報》、《現代書法報》、《翰墨大匠》、《書於畫》、《中國書法報》、《書法導報》,作品被藝術機構和收藏家收藏。
2011年、創辦了自己的官方網站:
周大成書畫篆刻網 、 周大成官方網站
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參考價值和藝術共享交流中心!
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
評論
品評一則
 大成
大成作者:韓天衡
周大成治印頗長於文字形體的經營,錯落取勢,平中不平。故以一字論,有展促姿態,得靈動活潑之旨;而以字與字的呼應論,有吆喝之情,以致全印靜動跌宕,饒有生機。
他的作品屬小寫意型,寫意並非隨意,刊出的兩印頗見苦心“翰墨千秋”印,以“田”格橫勢論,“墨”、“秋”兩字,上方呈右低左高勢;而對“翰”、“千”兩字論,果斷斫去“千”字上方左側的邊欄,呈右高左低勢,從而使全印四字獲得了“歪歪得正”的藝術效果。寫意中見精意,甚為可貴。九字印的處理亦見匠心。然作者用刀尚欠紮實,尤其是在筆道使轉處宜緊結老到之。
徐利明評周大成篆刻
 與韓天衡老師合影
與韓天衡老師合影作者:徐利明
淮陰周大成印風粗獷雄暢,氣勢奪目,於拙樸中見靈韻。其巨印尤得唐陽文官印之趣。白文印則善於處理殘破並筆,造成既對比又和諧的黑白虛實變化。
古老與年輕的對話
周大成篆刻鎖談
胥廣福
 周大成篆刻 ‘翰墨千秋’
周大成篆刻 ‘翰墨千秋’因此,我對周大成先生傾二十餘年心力不改初衷躬耕印田,不知是該表示一份深深地敬意還是扼腕的嘆息。他像美國西部牛仔創造淘金神話一般,汲汲於印途:同樣的艱辛,也同樣的收穫,只是一個滿足於金燦燦的物質,一個欣悅於清徹徹的精神。大成先入秦漢繆印,又涉唐宋官印、古陶;流派印就不必說了,明清各家印譜心追手摹,爛熟於胸。他尤好晚清巨子吳昌碩:痛快淋漓,霸氣橫生。人總是很奇怪,當你最初投入某家某派,學得如魚得水,爐火純青,是幸事,也是不幸。大成亦然,據他講,他對傳統下過功夫頗深,我不知這種功夫指什麼,但我知道他十六歲就寫吳昌碩石鼓文,臨老缶印作。如今則欲罷不能,隱約之間還可見昌碩遺韻。
大成出生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少不更事時,接受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神聖的祭壇一旦轟然倒塌,廢墟中“醒”來,“見佛我就打,見僧我就罵”(郭沫若詩),被壓抑的青春在一片無垠的曠野中瘋狂:藝術上法自我立,於無佛處稱尊。我和他可以說過從甚密,我知道,他也去拜訪過名家。對當今印壇呼風喚雨的“前輩”,他執弟子禮甚恭,但他的內心是不是服氣就很難說了。一次二三好友在他家小酌,也許是性情使然,也許是酒能亂性,總之,在我們這些圈外人面前,大成少了平日禮儀的桎,梏“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得極為酣暢。大有西楚霸王見始皇贏政而呼“彼可取而代之”的風采——這與他的印風倒是十分吻合。我喜愛那種走“極端”的藝術家,藝術家往往不能用常人的繩墨系之,沒文化偏要裝作滿腹經綸,只能貽笑於人。齊白石一生脫不了農民習氣,但無損其大師地位;徐志摩參與三十年代美術論爭,那只能是攪混水,儘管志摩是個出色的詩人,是沙龍貴婦人心儀的偶像。
能夠把古老的藝術玩得這般“年輕”,這要有一顆率真的心。率真是一種未經雕飾的美。溫柔敦厚、謙謙君子,不是大成的作派,你請他刻章,不管他是精雕細縷,還是一揮而就,一旦把成品“恭恭奉上”時,他總是把想法寫在紙頭上,告訴你好在哪裡,而且真像是說自己的兒子,怎么看怎么好。也許過了若干年(不,若干月),他就會向你討要,幹嘛?磨去重刻。我喜歡他這種自我感覺良好。大成的篆刻就有這樣的好處:欣賞者不一定需辨識文字和細嚼慢品,那強烈的形式美一下就能“抓”住你,視覺一時之所長在他的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前面說過,他的印風雄強,求大氣,印也刻得愈大愈見精神。置諸展廳,他的“重量級”印作不知需要震懾多少人。藝術貴有個性。儕身塵世,很難從芸芸眾生中把大成瞅出;但是,在江蘇這幫“小刀手”(青年印人的戲稱)中,他的“醜拙”卻讓人一眼就能辨識。多年來他毀譽不驚,亂頭粗服,仍自得其樂。我希望明天的大成在印途上別開蹊徑,但相信他這種執著精神不會丟失。
我以為,這就是大成及他這一代藝術信徒的共性。如果我們把它作文一種現象來研究,一定是饒有意味的。相對於他們上一代人,如韓天衡、王鏞等名家,無須諱言,作為問道於韓、王的大成他們缺少的不是印章的技法,而是豐厚的文化底蘊,韓王前輩不唯求印中之韻,更求印外之致。方介堪、李可染這些大師的親炙,書畫專業語言的錘鍊,特別是以文史哲綜合修養的支撐,使韓、王等大家都以特立獨行的高蹈之跡不斷超越自我,時攀新峰。相比之下,大成這一代則只能憑對藝術的直覺和悟性來搞篆刻,篆刻的語彙當然難不倒他們,但是一味在方寸之間探訊息則真正應了漢代文學家楊雄那句話“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了。何況,沒有豐厚文化底蘊的藝術決不能稱之為東方藝術。在東西文化碰撞、交鋒如此激烈的今天,篆刻這門古老的藝術如何處驚不變,以此苛求於大成一人是不現實的,但正像某位著名藝術家說過,中國畫還是要姓“中”,篆刻之道理亦同。大成既然選擇了這一苦行之路,那就走下去,而且要發揚光大——這才是一個“淘金”者應有的雄心壯志。
大成年輕,搞藝術的心態也寧靜。讀書。作為在國內大賽中屢屢入展、獲獎之人,能這樣說和這樣做是好事。
(2006年1月30日《中國書畫報》)
附:
攻藝者有兩類:一類為“七分學,三分拋,各有靈苗各自探”;一類則是“無一筆不有來歷”。前者可望稱家,後者必為匠人——大成當屬前者。“印宗秦漢”乃為古訓,大成卻不以摹刻多少多少枚秦漢印為能事。
大成的印作何以如此?他刻了兩方閒章:“一生懸命”與“九牛二虎之力”。細觀“一生懸命”一印,章法斑駁陸離,大疏大密;無論是借邊,還是讓邊,均“筆”在“意”先,不假修飾。而線條則一掃某些鐵線篆千行一面的陳習,奇崛、生辣、蒼勁、沉雄!印跡見心跡,令人陰縈損柔腸,頓起蒼涼之思。
摘自胥廣福《讓石頭唱歌》
(1999年8月2日《書法報》)
唯變以應
謝海宗緒升
 周大成
周大成就篆刻而言,沒有人規定在印面哪一個位置下刀,也沒有規定在幾厘米、幾毫米處擊邊,同樣,不存在哪一筆、哪一刀不對,而是如何在方寸之間布以萬丈波瀾或是千般柔情。於是,這裡派生出來的陰、陽兩個美學的基礎問題,正是這樣的基礎問題的提出才更容易讓我們梳理周大成的藝術創作。
周大成的篆刻創作時傾向於霸悍一路的,這近些年來他入選全國幾次重要展覽中的展品可得以驗證。他幾乎沒有刻過像上海劉一聞那樣“陰氣”十足的印章。而多以雄、博、新的面目出現。具體來說,雄是指渾厚中求氣勢奪人,字法上有展縱之姿;博指秦漢、封泥、磚銘兼融,甚至從印學界所不屑唐宋官印中汲取營養;新則無非指從他人不注意處注意。不過,總的來說他的作品是獨具陽剛之氣的,他在努力把儘可能多的雄渾一類篆刻風格予以吸收和消化,架構一條通往廣博之路的通道。
當然,任何一個藝術家都脫離不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文藝潮流的影響,換句話說,時代的烙印對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而言總是或多或少得以顯現。從一般意義上講,大成有段時間作品過於接近流行印風,比如王鏞的影子很重。但仔細看來亦不盡然,王鏞篆刻的粗頭亂服在這裡表現為精神的借鑑,而不是一味的翻版。不盡然的另一個理由是,當代韓天衡、石開的篆刻風格也時常左右周大成的創作實踐。有段時間,大成一出手不是像張三就是像李四,他很苦惱,怎么就沒有一個自己?後來,南下北上,拜師訪友,不知哪一天他得了一字訣:變。
儘管我們一致認為周大成不是傳統最好的承繼者,但是,他仍和很多成功者一樣,在傳統的大熔爐里也摸打滾爬了不少年頭。中國傳統藝術講究頓悟,周大成先是秦漢印,後追摹時尚形成初期的“周家祥”是一變;後來專司於古印中雄渾一路印風,又一變;接著把官印(唐宋)來個拿來主義並不作不經意狀,再一遍,這每一變似乎都是遞進的關係,一種曲線上升的姿態。如果把這種關係和姿態看作頓悟,周大成非常理性地立足當代,並用傳統的菁華不斷削弱“當代”,他在反反覆覆地打磨著自己的風格,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那么,我們得出周大成創作實踐亦或說其演變的理論根據——由自覺到覺悟,由覺悟到頓悟。
不知大成下一變該如何?
摘自《青少年書法報》
大成大沉
——青年金石篆刻愛好者周大成其人其印
李鴻猷
 周大成篆刻 ‘庖丁解牛’
周大成篆刻 ‘庖丁解牛’我和大成未謀其面,先獲其印。我久聞他治印不俗,托友人轉請替我治名章一枚。其作果名不虛傳,率真勁健,剛柔並濟,渾樸大度,魅力四溢,後來相識日久,對其人其藝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少時便鍾愛鐵筆,初得秦漢璽印、封泥、磚文及唐宋官印之潤澤,後又篤效清代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暨現代齊白石、來楚生諸大家,對其仰之彌高,鑽之益深,痴迷至欲罷而不能。尤其是近數年間,更是鑿行於酷夏,呵墨於嚴冬,未教一日閒過;又負笈萬里,求教印林高手,每每揣度其中之高遠,朝夕操刀治印不輟。如此積其歲年,浸淫日久,其篆藝終有大成。
篆刻作為一門獨立的欣賞藝術,停留在技法上的滿足不是作者和欣賞者的惟一標準,而是要求內涵的豐富,從中取得多層次、全方位的精神享受。我們試看大成的幾方印譜,便可知其在小小的方寸之間為人們設定了多么豐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朱文“庖丁解牛”便是一方設計得十分精心周到的成功之作。我們可以用“疏密有致、線條峻朗”等詞去讚美它,這毫不為過;但它的最妙處還在於對印文的巧妙安排。它打破了四字印文橫排的呆板模式,而是讓它大小相間,互相呼應;線條粗細有別,敧正互生,加之框線的不規則性,均使整個印面充滿了動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印文中主人公的職業動作。此印的妙處還在於文字的互相借用。如“解牛”的解字右下方有個“牛”字,就被借來以兩橫筆的代字元號權作正文中的“牛”字了,這樣,便使印文更容易穿插安排,變化多端,充分展示了印文組合中“情投意合”的逸趣;再者,“丁”字居於印面正中,以秦代半通印形式表現,從而使印面又有裝飾趣味。
 周大成篆刻 ‘萬事風過耳’
周大成篆刻 ‘萬事風過耳’“萬事風過耳”也是一方別有情趣的佳作,屬古璽類,具漢封泥印之意味;文字錯落有致,偃敧互生,線條鋒穎透逸,古樸蒼勁;刻法以沖刀為主,沖切相問,頗具粗細輕重之變化,古韻十足;章法布局亦頗為得當,字密處不可容針,空白間寬可走馬,別具一番意趣;字的大小安排,位置的刻意經營,線條的斜圓變化,使印面充滿動感,似輕風一陣徐徐而過,正暗合了印文的禪意。
當然,僅此幾方印章,尚難概說大成印藝全貌。但我們正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
大成治印,起點高,悟性好,且治藝嚴謹。刻印前不深思熟慮至八九分則不肯奏刀,尤其在製作自文印時,更能體現此種創作心態。奏刀之前從不打稿,而是將章面塗黑,印文的布局、線條的質量、刀法的取向等,一切產生於“胸有成竹”;下刀時敢於犯險,果斷快捷,駐留迅即,刀落屑濺,驚心動魄,任線條隨意崩裂,其效果斑剝古拙,猛利剛勁,趣味天成。印治好後,他也不肯輕易出手,亦不急於修改,而是放在那裡反覆端詳,直至自己滿意才出手示人。“先打動自己,然後才能動人”,這是他的治印準則。
大成治印,早就名揚印壇。他淡泊名利,做人深沉,治印深沉。這篇小文是幾年前就該為他寫的,直至今日商得他首肯。他謙虛地說:“我的印藝還未達到大成;我要永遠沉入藝海,潛心治藝。只有深入淺出,才有大的成就!
印說
聞達
 周大成篆刻 ‘跋遠山涉長水’
周大成篆刻 ‘跋遠山涉長水’隨想一則
周大成 放眼當下,侈言創新,眾議滔滔,以為時髦。何謂“新”?何以“新”?有謂脫盡繩墨為“新”有謂直抒胸臆為“新”。若起當代草聖林散之於九原,必以為大謬也。
散老草書博大精深,渾樸高古,聲明之隆,馨播海外。其作“新”乎“舊”乎?從散老自況中可探訊息:“餘十六歲始學唐碑;三十以後學行書、學米;六十以後學草書,草書以大王為宗,釋懷素為體、王覺斯為友,董思白、祝希哲為賓。”(《林散之書畫集·自序》)散老少時篤學,終老不倦,轉益多師,出入百家……如蠶之吐絲,蜂之釀蜜,其一朝一夕人變為絲與密者哉?頤養之深,醞釀之久,而始成功。正所謂:“既學古人又變古,天機流露出精神”(林散之詩)。
宵小之徒,假“創新”之名以掩狂怪,豈能跳過大師法眼!散老曾有詩嘲諷爾曹:“問君何以如此寫,各有看法邁前賢……書法之道真無邊,大膽創造驚張顛!”“邁前賢”、“驚張顛”之雜耍式書法其為“新”乎?直是“俗”也。
餘生不敏,何敢妄談“創新”!但知古哲今賢可為師;法帖名碑終老相守。兼以詩書涵泳、國畫陶冶、音樂遣興……乃至道德情操勤加砥勵,時匡不逮。書山尋寶,忙鞋可至;藝海探驪,一葦有期。《論語》云:“不欲仁則斯仁矣”。
創作感悟
吾自小木納,譾陋愚鈍。稟性率真、耽心藝事。不治余技。初操門徑即求渾樸、古拙一路。力避纖弱匠氣,尋大正氣象。不屑屑斤斤所計,契意適性而已。閒暇之時。喜拜讀先哲文著。每逢心儀佳句,筆錄在冊,後細心推敲作品多種表現風格,十日或數十日,直至會心。每於夜闌人靜之際,獨對青燈照影。細聽雨打深更,或聞螽蟖之鳴,沏一盞茶。燃一支煙,理素紙、撫頑石。婆娑於刀落屑濺之間,筆耕於春蠶食葉之聲,不知秦漢,無論皖浙,沖切隨興,物我兩忘,怡然自在,頗為愜意耳。偶有所獲釘壁而觀,或把玩在手,於我所思無二,拍案自喜。不知東方之既白。
周大成篆刻作品
周大成篆刻作品作品如下:
 周大成篆刻作品 周大成篆刻作品 |  周大成篆刻作品 周大成篆刻作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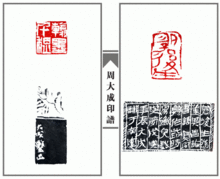 周大成篆刻作品 周大成篆刻作品 |
大器的大成
劉懿
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博士
 周大成作品
周大成作品由於我長年往返於南京淮安之間,見面的機會並不是很多,一次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小遠兄一起喝茶看畫,小遠忽然冒出一句,你的畫風和大成的印風很合,為何不請大成兄刻一兩枚?我猶豫半天說:“不太好吧”?作為同道我深知創作的艱辛,所以很少向別人開口。小遠兄說:“這事我來和大成說”。於是在一周后我的畫上就有了大成的印跡。漸漸,我們的交往就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哥們。一次應大成之邀去他家做客,進入大成書房兼工作室,看到的是除了僅夠容身的床和一張畫案,從地面直到房頂都是書,且大都是學術巨著,讓我對大成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心中嘀咕這小子並非草莽,原來也是讀書之人,心中甚是歡喜。此後的每次聊天我也就不再避諱,關於諸多和別人無法言談的學術話題,在和大成的討論與爭論中更覺暢快。在這樣的閒聊中知道大成不但對篆刻書法有己見,對於哲學美學繪畫也有自己的獨到體會。
不記得是哪一年的冬天了,我從南京回淮,應大成之邀在一個菜做的很地道的小酒館痛飲。飯後,我和大成步行回家,他極其認真的對我說,要去北京進修“學畫”。我以為他酒後隨便閒聊,不以為然。想不到開春後他真的北上學畫去了。我知道大成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因為他從未脫離過畫,加之他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中頂樑柱,現在竟然拋棄幾十年的“藝術修養”,北上再次從頭開始,一個藝術家為求藝術之精髓真的能夠放棄這么多……?再次相見則是一年後了,一天大成說有些畫給我看。那時我正在忙著做博士論文,大成卷了一摞畫來我家,本以為見到的應是大成繪畫語言的更高的升華,但打開後居然全是臨古,然而畫的氣息已非過去的自己和一般人所能達到了。又一年,照樣是一大摞畫攤在我面前,大成的筆墨越加松秀、蒼茫,並將自己對篆刻和書法的修養融入畫中,已非一般的畫家可比了,直指繪畫語言本體。對於中國畫已經有了更高層次的理解,即使還有些不成熟的地方,但已非隨波逐流之輩了。可見大成的悟性和勤奮是極高的。
中國畫到了高深之境界後,畫的是畫家的綜合修養,大成有多年的書法篆刻學養,加之走上學習的正道和不斷積累,勤奮筆耕,假以時日,我相信大成定能大器所成。
周大成國畫作品
 周大成國畫作品 周大成國畫作品 |  周大成國畫作品 周大成國畫作品 |
周大成書法作品
 周大成書法作品 周大成書法作品 |  周大成書法作品 周大成書法作品 |  周大成書法作品 周大成書法作品 |
採訪記錄
尋找精神的家園
篆刻家周大成先生訪談錄
胥廣福
周大成先生是我市較有影響的篆刻家,多次參加中國書協和西泠印社重要展覽並曾獲獎。特別是2006年12月,他成為我市唯一以篆刻面目入選省文聯評出的“江蘇省優秀青年書畫篆刻30家”,還由省文聯組團,赴香港參加書畫交流活動。儘管大成享有盛譽,可還是我相知甚深的摯友。近日,受“淮周刊”所託,我對大成進行了專訪。
味無味處求吾樂
 大成
大成周大成:大多數人在少年時代都褒有一顆難得的“詩心”,對美好的一切充滿好奇和嚮往,進而充滿激情地扣問和觸摸藝術之門。當然,隨著歲月變遷、生活磨礪與人生定位,這顆“詩心”或許會被現實風乾,不再成為藏於隱秘之處需要傾情呵護的夙願。這不奇怪,前人說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只要能在不同行業、不同崗位活出自己的風采,都是成功。相反,如果我們的社會個個耽於精神境地,不事田頭稼穡、不在車間生產、不作科技研究、不持槍戟護衛……那倒是可怕的——我們藝術家哪有生存基礎?再說,許多藝術家或者藝術愛好者本身就得先謀稻粱,舞文弄墨不過“餘事”而已。
當然,我從一個藝術的愛好者進而以書畫篆刻安身立命,特別是被別人謬稱為篆刻家,離不開偶然因素,更多的是自覺的選擇;有收穫的快樂,也有探索的艱辛;免不了名利的羈絆,終歸是內心的召喚。如果追溯從藝的源頭,我慶幸的是我的祖父與父親都是讀書人,讓我在童年“抓周”時,一下子就“抓”到了的豐富的藏書。在祖(父)輩的薰陶下,我懵懵懂懂卻又是津津有味地讀書,特別是文藝方面的淺顯讀物,不斷激活著自己的形象思維。後來迷上了寫字畫畫和刻章,家人也沒認為我不務正業,爺爺因為與淮上篆刻名家程博公先生是好友,特地送我去拜師學藝。有幸在程老親灸下,得窺堂奧,夯實基礎。後來,我又廣涉博取,轉益多師,逐漸增廣了見識,立定了心志。
藝術創造是在寂寞中產生的,別人嬉戲遊樂之際,搞篆刻的人往往長伴青燈,敲鑿冷石,不知東方之既白。每一個篆刻家都有過被刻刀傷及手部的“痛苦”,更多的同道們也從這門純粹的藝術中感受到真正的快樂……正因這份發自內心的快樂,我曾經刻了兩方章,一方是“九牛二虎之力”,一方是“一生懸命”,前者指我願為篆刻傾盡心力,後者是日本的一句諺語,意思是一輩子把命運攢在手裡,我用來表示終生攻藝的志向。讓我欣慰的是,這兩方章都在中國書協舉辦的全國第六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中獲得提名獎。
淮周刊:魯迅說過,再偉大的天才,他的第一聲啼哭也決不是一首好詩。我想,您肯定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摘到“桃子”的。請談談你在傳統上下過哪些功夫?又得到哪些名師點撥。
周大成:誠然,我能學有粗成,離不開古今大師們的扶攜、援手。哲人雖萎,遺澤永存。我能遙接古人,心嚮往之,就是撫碑帖、賞印譜、臨古印、讀印語……最早,我對集小篆之眾的徐鉉的《說文解字》一一辨識摹寫,由小篆上探篆籀、鏡銘、殷墟文字,廣泛涉獵,不一而足。未及弱冠,我就曾臨過吳昌碩手寫石鼓文不知凡幾。識篆之餘,我不分軫域,探源溯流,對秦漢古璽、封泥、瓦當、繆印都用心摹刻,進而對漸派、皖派等流派印也心追手摹,真是“如行山陰道上,目不睱接”。特別是吳昌碩一路的豪放印風,更與我心性相契,我著力更篤。
我力求做到“不薄今人愛古人”。在程老的支持和鼓勵下,我又南下北上,向書畫印各擅勝場的當代大家韓天衡、王鏞等人虛心求教,這些德藝雙馨的藝術巨擎讓我從做人與攻藝兩方面得到沾溉和教益,每一思及,肅然起敬!
在上海天衡師的“百樂齋”,先生對我悉心指授,從藝理、技法、為人諸方面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近二十年前,我所鐫“翰墨千秋”一印十分稚拙,先生卻不以為忤,厚愛有加,親作數百言評介鼓勵,並收入他的大著《天衡印談》。近些年多次囑我參加師門雅集,讓我獲益良多。王鏞師向以特立獨行為印壇所重,而先生冷峻外表之下,深具古道熱腸,對我同樣視如已出,屢作度人金針。王鏞師卑視俗務,卻欣然為我印作題簽,我雖不重收藏,豈敢不視若拱璧?當然,在我從藝術生涯中得到很多名家指點,其靄然長者之風,令我溫暖如春。
不隨世俗任孤行
淮周刊:風格與習氣就像人內心糾結的神性與魔性,前者讓人散發光輝,後者無疑醜陋不堪。本想私下交換這個話題,這裡還是想讓你“坦白”:你的作品是否形成風格?有什麼樣風格?有沒有所謂的習氣?
周大成:其實,你所表達的是傳統與創新的問題。我認為搞藝術的人分成三類,一類是一味“與古為徒”或者是恪守師門,不敢越雷池一步。比如有人寫一輩子字或刻一輩章,臨帖摹印幾可亂真,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面目,像舊時代的冬烘先生面目可憎,又像別人嚼過饃頭沒有滋味。王羲之再好,你臨得再像,也超越不了。所以齊白石老人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像鄧散木先生從吳昌碩風格中化育出厚重醇和的個人面目,而趙古泥、單曉天先生為散木所囿,已然下乃師一等,更有步趙、單後塵者,只能一蟹不如一蟹了。第二類是誤把習氣當風格,本是野狐禪卻偏要裝得道老僧。比如一些筆會上,往往有人裝束奇異、舉止怪誕,而下筆或運刀故弄玄虛、矯揉造作,以過度誇飾奪人眼球,毫無美感可言……這可說是浮躁年代快餐現象,惜乎觀者懾於“江湖騙子”的聲名和作派,讓做秀者得逞於一時。第三類像李可染大師所說那樣,以最大的功力打進傳統,又以最大的功力打出來。既能對千秋一脈的湟湟藝史瞭然於胸,存乎其妙,又能用獨特的思維、成熟的架構創造出既有審美價值亦多傳統氣息、更有時代特色兼呈一己風貌的作品,這才是創新亦即風格。
至於風格和習氣確乎難捨難分,就像人在行善時表現神性、作惡時充滿魔性一樣。比如米芾在宋四家中以沉著痛快見長,可奇欹過甚、油滑有餘亦為其弊。這都說明,我們學習古人、師長,要揚其風格,棄其習氣;也要包容善待,追求自己面貌同時,要警惕鑄成風格硬幣的另一面——習氣。
至於我的篆刻是否形成風格、有什麼風格,自己還真不好說。我倒想反將你一軍:拿到有我作品的篆刻集,不看姓名,能不能把我認出?
不過,我倒可以談談我追求的風格。也許從小就沒受太多束縛,我的性格中有著揮之不去的豪爽勁。比如好友相聚,我會直抒胸臆,有啥說啥;好友對酌,我喝起酒也從來不留“小錢”。平時做事直截了當,果敢迅速。這種氣質多少影響到對印風的取捨。其實你幫我寫過好幾篇文章,也說過我的篆刻求雄強,貪醜拙,沖切並用,終以沖刀形成爽勁之氣。
淮周刊:我知道,這么多年來,你沒換過房子,可書齋號卻換了幾次。早年用過“後擊齋”,後來改成“十方禪社”,如今又叫“懷海堂”,也許今後還會改變。這一細節變化和你藝術追求有否關聯?
周大成:人的追求與學養增進密不可分。早年我好強爭勝,特別推崇潘天壽“一味求霸”的豪氣。有次到南京觀看某屆全國篆刻展,因為不是入展作者,主辦者不讓我觀摩開幕式。一氣之下,就用了“後擊齋”,就想積蓄力量,狠狠地打擊——一雪恥辱。當然,隨著技藝提高,像這類展覽我幾乎一次沒落。不過,待讀了好多傳統經典後,認識到逞一時之勇不算英雄,入屆獲獎與否要做到寵辱不驚,要有“萬物靜觀皆自得”的淡定心態,就像禪宗所謂“幡動心不動”那樣——所以就有了“十方禪社”的齋號。至於“懷海堂”,其字面意思是要有懷抱大海的氣量,林則徐不是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么?其實,這裡也用了佛學典故。懷海是一代高僧,曾說“自古至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意即佛是自由人,自由人是佛。我願以此自勵,不隨波逐流,走自己的路。
須知書畫本來同
淮周刊:都說現在是講究分工的年代,“萬金油”式人物不吃香了。文革年代有個詞叫“又紅又專”,不妨改成又“專”又“紅”:專精一道才能搏得大紅大紫。你以篆刻名擅淮上,如今卻赴京進修國畫,出人意料。你是藉此豐富篆刻表現手法,還是想領略藝術道路上別樣風景?
周大成: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第一次從理論上闡述了書畫同源的問題,認為在造字之始,書畫同體而未分。後來,書畫同源而異流,但兩者用筆和章法錯落處理仍是如出一轍,用線傳力度,用形抒情感。周星蓮《臨池管見》云:“以書法透入於畫,而畫無不妙;以畫法參入於書,而書無不神……其書其畫類能運用一心,貫穿道理:書中有畫,畫中有書。”自唐明皇題“鄭虔三絕”以來,詩書畫印兼擅的藝術家不可勝數,鄧石如、吳讓之以及後來的吳昌碩、齊白石等莫不如此。
再看當今,王鏞師肖形印取法陝西剪紙,天衡師肖形印得益青銅飾文。王、韓一輩都是廣積博取,無所不擅。但是,我輩往往是“單打一”,僅在方寸之間探訊息,縱是技法嫻熟又豈及于格調?我赴北京榮寶齋畫院,投師著名畫家范揚先生,就是想效法前輩和大師,以開放胸懷和氣度打通不同藝術的“關鈕”,觸類旁通,豐富自己,進而提升境界。當然,我學畫不是抱著玩票的心態,而是要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在師友們關懷下,心無旁鶩、虔誠敬畏地投身其中,把多年的思考與如今的實踐結合起來,力求在藝術上破蛹成蝶,不期新而自新。何況,篆刻本身就蘊含書法美、國畫美和雕刻美,博涉繪事肯定會在治印章法、構圖及意境經營上大有裨益。同時,書法金石之外,能探國畫之美,也是人生快事!
 採訪周大成老師
採訪周大成老師周大成:這北京、江蘇和淮安真是不分輊軒,各有所長。從家鄉看,長期生息於斯,加上同道切磋,其樂融融,讓人筆底生春。而置身江蘇,山川風物、人物故跡,絢麗多彩,豐厚蘊藉,讓人詩意拂拂,溢而成韻。再置身首善之都,八方豪傑齊聚,眾多流派紛呈,真是階柳庭花皆潤筆墨。因此,搞藝術的人需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淮周刊:最後,我想八卦一下,你已經加入中國書協了,想不想加入西泠印社這個搞篆刻人都嚮往的社團?
周大成:說心裡話,16歲我就知道西泠印社,後來多次負笈浙滬,造訪名家,屢屢拜謁西泠印社,追尋先賢履跡。這一創建已歷百年、雲集眾多高手的社團肯定是每個從事篆刻藝術的人心馳神往的。加入這樣的社團,不僅是一種榮耀,更多向師友請教的良機。但是,經過這么多年潛心修為,我真得不把加入某級組織、某個協會當成目標了。我願聽從內心的召喚,用睿智、用真情、讀萬卷書、用生命營造屬於自己的藝術園地,就像德國哲學家諾瓦利斯所言:“懷著一種鄉愁的衝動到處去尋找家園”。
刀下留情
記篆刻初學者周大成
看周大成先生的篆刻,“印如其人”的“古訓”便不足為訓了。其線條之勁利,結體之奇崛,章法之爛漫,如亂頭粗服一般。而生活中的大成卻謙和質樸,極講禮數。
中學畢業後,大成師從篆刻家程博公先生。篆體影印的《說文解字》是較為艱深的文字典籍,一般讀者很少問津,大成卻愛不釋手,一一辨讀,興味悠長。晚清大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吳昌碩手書的《石鼓文》是他的日課,常常“興至酣時千萬字,情到深處兩三根”(高二適詩)。識篆同時,大成開始奏刀,“印宗秦印”是印人不二法門,其古雅幽邃的氣息也讓大成得到蒙養和薰陶。
然而,囿於“秦權漢石”而畫地為牢,終究難成大器。大成的名言是:“做人不能過河拆橋,搞藝術就要過河拆橋。”言下之意是,要不斷探索,博採眾長。於是,他於古璽、封泥、瓦當、磚銘……無不細加體會,心追手摹;又於印學嬗變與名家流派轉益多師,擇善而從。寒夜青燈,奏刀霍霍,用功至深,樂在其中!
為了增廣見識,大成四次負笈上海、浙江,向韓天衡、劉江、陳振濂諸名家請益,印風又為之一變。
細察大成篆刻,有三點我最為心折。其一,有膽識。他好奇險,貪“醜拙”。“沖”“切”並用,若不經意;又遊刃有餘,意韻縝密。其二,少字誤。舉凡古籀繆篆、鐘鼎甲骨,他都“大膽落筆,小心求證”。印由書出,信然有據。其三,多雋語。“印外功夫”差,似是青年人的通病,大成則好學不倦,胸有成“書”。所刻閒章、邊款也涉筆成趣,令人把玩在手,別有會心。
大成在全國諸多大賽獲獎無庸贅言了。作為諍友,其印作中的“流行色”卻令我有杞人之憂。我願大成能潛心“沉”到傳統中去,“既雕既琢,復歸於朴”(莊子語)。與其成為“矮子”中的“將軍”,毋寧成為“將軍”中的“矮子”!
(1991年7月29日《淮安日報》)
孤詣奇崛有大成
 周大成印章
周大成印章不知道周大成在接受沙孟海先生頒發第二屆全國篆刻作品獎時可曾想到這位慈愛的母親,只知道他每到母親生日總要鐫下一印,以抒人子之情。
誰的一生沒有一兩次做個藝術家的“衝動”呢?只是大成把“衝動”變為對篆刻藝術的執著與痴情。
十年前,中學畢業後的大成投身著名篆刻家程博公先生門下。一本影印的《說文解字》他愛不釋手,—一辯讀;近現代大家吳昌碩手書的《石鼓文》更成了他的日課。大成讀過昌碩老人那“生計仗筆硯,久久貧向隅”的悲戚詩句,可還是把全身心都投入到篆刻之中。一把鈍刀,幾方頑石,開始了艱難的鑿石人生。
後來,他成了一家造紙廠的機修工。帶著一身疲憊的油垢回家,總是徑奔簡陋的書案前。“斂氣”!“入定”!一個“意念”:篆刻!
看著大成伴如豆的燈光通宵不眠,古稀的奶奶心疼得老淚縱橫。是呵,作為周家的長孫,襁褓時就喚“大成”,希望他能“長大”,能“成活”,可誰想他為刻章、寫字這“勞什子”而不顧身體!
來自親人的規勸,令他感念;周圍一些人的誤解,更是壓力;而最沉重的打擊則是1989年的10月——又一次接到浙江美術學院(現為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篆刻專業的落榜通知(1987曾考該院未被錄取)。
多年後,大成給我談起這段往事,卻笑了:“也就在那時,我決定不再‘押寶’了。我把篆刻這‘迷人’的藝術當作一生的追求。”
大成“沉”下去了。他像初學者那樣,一頭扎進凝重典雅的漢印中,這使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大成知道,畢其功於“漢印”一役,只是“印奴”;要窺印學堂奧,尚須上下求索,廣涉博覽。翻開他的印稿,那方“相敬如賓”取法封泥,頗為蒼茫;抒鄰舍厚誼的“左右相幫”印則有古璽“日都庚卒車馬”的娟秀;鑿石濤畫語“墨非蒙養不靈”直接漢鑄印和鑿印的拙樸。甚至印人不屑的唐官印、疊文印大成都下過工夫。對流派印,儘管他醉心吳昌碩那雄強恣肆、亂頭粗服的“霸氣”,而趙之謙的秀逸,吳熙載的峻拔也都在他的印稿中留下端倪。今年秋,大成喜得貴子。他常一邊哄兒,一邊翻閱《黃士陵印譜》……
為了藝術,他節衣縮食,四出求教。他的篤誠與好學感動了韓天衡、劉江、陳振濂這些當代名家。對生長在蘇北貧瘠土地上的這棵藝術幼苗,韓天衡先生更是悉心培育。
十年磨一劍。大成終於在篆刻藝術上初展頭角。他的“履跡”出現在許多展覽、大賽的作品集中。韓天衡戲稱他的篆刻為“小寫意型”。“寫意”並非隨意,韓先生撰文道:“周大成治印頗長於在文字形體的經營,錯落取勢,平中不平,故以一字論,有展促姿態,得以致全印靜動跌宕,饒有生機……寫意中見精到。可貴。”
面對鮮花與掌聲,周大成一如往日般平靜。他把藝術的觸角伸向了更廣闊的天地。如文學、國畫……
“都姓俗時我姓雅,畫書妙者少奉迎;天心不識人心苦,孤詣奇崛有大成。”(著名書畫家王學仲詩)願“孤詣奇崛”的周大成終有“大成”!
(1994年1月22日《淮海晚報》)
讓石頭唱歌
周大成其人其藝臆說
有首美國民歌唱道:“石頭雖好,不會唱歌。”美國西敦豪大學的威廉·羅肯特教授看到中國篆刻家們精彩表演後,高興地稱之為“能使石頭唱歌的藝術家”——推而論之,在洋教授的眼中,周大成先生當亦屬這樣一位“藝術家”了。
毫無生命的石頭,在大成心目中是那么鮮活——鮮活成溶入悲欣、溶入美醜的精靈。阿拉伯有句諺語:“從石頭到寶石要經過無數歲月。”誠哉斯言!大成踏上“印”途,已有二十載春秋,在大成手中經過雕琢的石頭何計其數!刻了磨,磨了刻,求索的路上多少刺藜多少坎坷,已化作令他倍覺溫馨的回憶。大成毫不懷疑,采於混沌之中的頑石,一變乃至數變而成旌幟般鮮紅的印章,正是重金難易的“至寶”!
如今,裹挾轉軌時代大潮而泥沙俱下,品藻藝術已變得“奢侈”。就像有人說的那樣:“現在早不是梵谷的時代了。”難道現在真成了“孔方兄”君臨天下而失卻人之真宰的時代么?大成說“不”,他從偷閒一“刻”到“刻”不容緩,就是在尋求一方寧靜的天空——讓心靈放飛的天空。他知道,心靈上繫上“金”屬就再也飛不遠了。緣於此,大成才攻藝不輟,樂在其中。
在他的作品中,秦漢印、古璽、封泥、古陶、磚文、唐宋官印、明清流派印直至今人印風……均一一可尋端倪,卻又總是個人面目強烈:雄強霸悍,氣勢奪人。仿佛“天目”大開:變古今於一瞬,合情理為一格,遊刃有餘,心手雙暢!大成的印作何以如此?他刻了兩方閒章:“一生懸命”與“九牛二虎之力”。細觀“一生懸命”一印,章法斑駁陸離,大疏大密;無論是借邊,還是讓邊,均“筆”在“意”先,不假修飾。而線條則一掃某些鐵線篆千行一面的陳習,奇崛、生辣、蒼勁、沉雄!印跡見心跡,令人縈損柔腸,頓起蒼涼之思。同為白文印,“九牛二虎之力”一印印面乾淨爽潔,取法古璽“日庚都萃車馬”,變“U”型為“n”型,有繼承,有創新;字型大小穿插,如亂石鋪街;而那細若春蛇秋蚓般的線條,則“百鍊鋼化作繞指柔”,此印如待月西廂,秀朗可人。
這兩方閒章不是大成刻的最好的作品,但我以為這兩句話當如他的一篇“創作經驗談”。據他說,“一生懸命”是日本習語,意即一輩子把命運抓在手裡。對大成來說,他已把金石藝術作為“一生懸命”般終極追求,又付之以“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才能讓“石頭”唱出了歡歌!
(1999年8月2日《書法報》)
賞析篆刻作品
作者:馮春寶
周大成這次網展所展示的篆刻藝術宗法秦漢古璽印、封泥、瓦當等,於明清流派印之中得韻致。既有秦漢印的蒼勁、朴茂、雄邁。又有流派印的典雅、端莊、靈動。
先生的篆刻既有傳統印一路的底蘊,富有濃郁的金石韻、文人氣;又有小寫意一路印風的靈動、率真、爛熳。印文多是以哲理古語、古語為題材,以古璽印為依託,印風工穩、潔淨、古雅;用力率性而活絡,流動中的豐富,豐富中的純粹,純粹中的深藏;並保留了古璽印文爽利與瘦硬的本色。可謂,不拘陳法而古意猶存,不追時尚而新韻迭出,不標新立異而風規自遠。
細品之,先生將篆法、章法、刀法完美融合,篆法規範,字字有出處,筆筆有來歷,章法嚴謹,刀法爽利。如:“於無佛處稱尊”等印,破邊於逼邊兼用,形斷而意連,形殘而意貫,賦予殘破之美。又“屢試不第”一印,印文疏密有致,方圓、曲直、向背有序,虛實相生,斷連自如,靜中寓動;或極力追求開合分明的空間,果敢明快,收放自如,恣肆縱橫的線條呈現出勁麗、浪漫、古雅之趣,如“龜鶴同壽”一印等等。非技法嫻熟者不能為也,非功力深厚者不敢為也。
簡言之,先生的篆刻線條流暢,方圓並用,字態生動,刀筆相映,寫刻之間輕鬆爽利,不刻意追求生辣,猛利。而是匠心獨具地化雄渾為清雅,化古典為時尚,化粗獷為精微。賦予了刀下印文名士的豪邁與恣肆,雅士的清逸與閒適,刀筆的情誼與情趣。
這一切使得先生的篆刻藝術凝重而又古雅,雄健而又豁達,經典而有精緻。有一種和諧之韻,素樸之趣,陽剛之美。
![大成[書畫篆刻家——周大成] 大成[書畫篆刻家——周大成]](/img/a/724/nBnauM3XwQDNzEzM4gTNwITN0UTM5YDMwIjMxADMwAzMwIzL4UzLw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