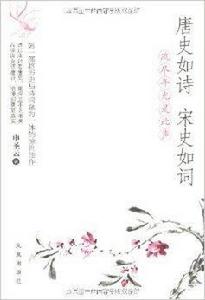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唐史如詩,宋史如詞:流盡年光是此聲》編輯推薦:第一部將歷史與詩詞融為一體的驚世佳作。最華美的史學盛筵——詩中有史,史中有詩。透過唐詩看唐史,雄渾且不乏唯美;品讀唐史悟唐詩,浪漫卻更顯真實。
作者簡介
申聖雲,80後知性自由作者,有男子豪爽之氣的另類“才女”。從小浸淫詩詞歌賦,寫作風格百變,可信手拈來,別具一格。作品多有避世不遇之慨嘆,亦含慷慨自在之灑脫,矛盾中集品禪、賞儒、修道、隨性於一身,自成一家。已出版作品《人生若只如初見:納蘭容若詞傳》。
圖書目錄
序:不知乘月幾人歸
春——忽如一夜春風來
殘柳宮前空露葉
宮花一落已成塵——江都宮變
明月誰為主?江山暗換人——太原起兵
中原逐鹿更爭雄——逐鹿天下
穆矣薰風茂,康哉帝道昌
文武皆王事,輪心不為名——武門驚變
一片兩片雲,千里萬里身——西行遠嫁
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貞觀盛世
江——鳳雲台空江自流
鳳闕澄秋色,龍闈引夕涼
飄花散蕊媚青天——有婦武氏
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二聖臨朝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誰向人問問是非—敬業討武
地遠明君棄,天高酷吏欺——酷吏銅匭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此地看花是別人——一代女皇
幾回經雨復經霜——中宗復位
猶勝拋擲在空欄——韋氏亂政
花——亂花漸欲迷人眼
聞道漢家全盛
共看明月應垂淚—太平之亂
千載賢愚同瞬息——明皇即位
憶昔開元全盛日——開元盛世
四士英靈富文藝——文藝大盛
從此君王不早朝
長生殿暗鎖黃昏——霓裳羽衣
聖朝無諫獵,何計謁明君——李相當權
一重浪滅一重生——國忠禍國
但使龍城飛將在
祿山胡旋迷君眼——番邦養子
天下盡兵甲,豺狼滿中原——安史之亂
一曲霓裳四海兵——馬嵬兵變
月——露似珍珠月似弓
黃昏胡騎塵滿城
群雄競起問前朝——奉天之難
中原禍作邊防危——平涼劫盟
細柳新蒲為誰綠——永貞革新
蓬萊無路海無邊
共道昇平樂,元和勝永和——元和中興
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三鎮再叛
夜——天階夜色涼如水
豈有蛟龍愁失水
破卻千家作一池——牛李黨爭
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甘露之變
多少樓台煙雨中——武帝滅佛
無情最是台城柳
他年我若為青帝——黃巢起義
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聖朝末路
後記:流盡年光史如詩
附錄:全書引用詩詞出處
章節標題出處
春
江
花
月
夜
後記
歷史是什麼?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是故事,是無法更改的軌跡。歷史看上去像個老學究,一本正經的樣子讓人望而卻步。歷史又像個頑童,肆無忌憚毫無預料地跟人類開著玩笑。
歷史,是無數人的生命軌跡交錯而成的網。充滿交叉點,充滿選擇,充滿可能。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忽然存在於天地之間,在某一個點匯聚,然後邁出方向不同的步伐,因為這不同的選擇和可能,讓這張網無限延伸。
對於神話來說,或許人們並不關心誰是神話的主人公、誰是神話的初始講述者。在客群和傳播者看來,神話就是神話,或教育或威懾或闡述哲理,沒人會在乎到底是誰打開了那扇門,關上了那扇窗,我們更常提出的問題是“然後呢”,而不是我們原本就應該時常提出“為什麼”。
歷史不同,我們總會想知道到底是誰讓歷史改變了它的行走軌跡,選擇了現在看起來的樣子。
誰才是締造歷史的人呢?
不是史書里叱吒風雲的上位者,不是傳說中呼風喚雨的神怪,不是羽扇綸巾的書生,也不是傾國傾城的佳人。又或者正是他們,也不完全是他們。讓歷史成為歷史的,是每個人。每個或高貴或低賤的普通人,每個留下名字或毫無痕跡的存在者,是“兩鬢蒼蒼十指黑”的無名賣炭翁,也是“他年我若為青帝”的黃巢;是“三吏三別”中的老婦、小吏、征夫,也是“為惜餘年報主恩”的朝臣;是“俱懷逸興壯思飛”的才子,也是“小邑猶藏萬家室”的皇帝。
歷史冷酷,蒼白,慘烈而滿不在乎,因為歷史是真實的。但是人們記錄的總是唯心的歷史,唯物的歷史已經被知道真相的人丟棄在了時間的塵埃里。
歷史書寫的是勝利者的讚歌。沒有哪個時代的歷史完全代言著普通民眾的心聲。文人筆下的歷史不同,文人可能因為看到聽到感受到而寫下什麼,這些在千百年後作為“呈堂證供”指證著時間。
文人是柔軟的,也是剛硬的。他們理想化,總為了什麼目標而執拗地走彎路,他們或出身士族,或命如草芥,或心比天高,或混跡鄉野。文人喜歡被肯定,也喜歡否定別人,最喜歡聽到讚美找到知音,最害怕作品無法與讀者產生共鳴。我們在用行走的軌跡織網,而文人則是在用思考的軌跡織網。他們敏感、易感,又有能力來形容描繪,所以無論他們聽到或者看到了什麼,都會或多或少反映在作品中,在唐,是詩;在宋,是詞。
詩詞是美妙的,因為平仄的約束讓它們琅琅上口,讀來宛如天籟。很多人不見得讀得懂詩詞中的內涵,卻會沉醉在其音韻創造出的氛圍里,感受到優雅古樸的文化風韻。詩詞雅致了歷史,豐滿了歷史,鮮活了歷史。原本無情殘酷的歷史似乎變得唯美浪漫起來,連同那份無奈和感慨也充滿柔情。
歷史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歷史的附屬品。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數學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有修養,邏輯修辭使人善辯。我們讀詩書,讀史書,為的是在那份清幽中體會:“千載賢愚同瞬息,幾人湮沒幾垂名?”
讀史可以明智,讀詩以為怡情。很多時候那些名字我們無需記得,也無法記得。但那種感覺是改變不了的。看見月光傾灑在窗欞上就會想起李白,聽到八百里秦淮的靡靡之音就會想到杜牧,居於陋室而不忘高潔的劉禹錫,此恨綿綿偏安鄉野的白居易,一杯濁酒映出杜甫的蒼老,鶯鶯張生說的是元稹的無情,尊師重道來自韓愈,山問春色穿行王維,春蠶到死相思不絕的李商隱,鄉音無改此去經年的賀知章……
歷史原本是活的,一旦你邁出了選擇方向的那一步,你身後的歷史就死去了。你能選擇你明天的模樣,但是不能刪除昨天的面孔。對於歷史最大的尊重是儘可能地正視它,不是偏執地追求一個可能誰也說不清的真相,而是在別人的滄桑中體味織網者的辛酸無奈與輝煌。
列寧說,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但總是回頭的人,一定走不快。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就要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負擔,大踏步地編織自己的人生。
“年光流不盡,東去水聲長。”沒有人能斬斷流水,沒有人能打斷時間。不管你願不願意,歷史就在你身後緊緊相隨,永遠年輕,永遠新鮮。想知道這片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嗎?打開書卷吧!
“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
序言
唐朝的歷史,就是那首著名的《春江花月夜》。
吳中四士之一的張若虛(約660—約720)寫道: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
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
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
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
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
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
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
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
初唐的貞觀之治仿佛一朝春來,萬物復甦,整個國家呈現出蓬勃的生機。
而後的武氏皇朝仿佛一個巨浪湧起在滔滔江水中,帶走了陳舊的男尊女卑觀念,帶來了無數後來女傑的野心。
玄宗時期可謂是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文藝盛世,百花齊放,百舸爭流,這一時期的文化與藝術成就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彩的一筆。
安史之亂平定後的唐王朝已經走向衰弱,儘管有“元和中興”這樣的力挽狂瀾,仍舊如同中天明月一般,滿盈之時少,缺損時候多。
黃巢起義攻占長安之後的大唐正在結束它的傳奇,五代十國的割據和紛亂使國家和人民沉浸在無邊的黑夜裡。
而這何嘗又不是一部大唐詩人的身世傳奇呢?試想:
哪一位才子不是滿懷壯志,意圖於朝堂上一展抱負,求一個得遇伯樂的千里馬的春天?
哪一位才子沒有過如墮江中,如遇浪打,隨波起伏不定的鬱鬱寡歡的貶謫甚或屢試不第的遭遇?
哪一位才子不曾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愴和“花落人亡兩不知”的哀傷?
哪一位才子未經歷惜月的皎潔、恨月的陰晴、怨月的冷清、嘆月的恆久?
哪一位才子不在夜裡感慨身世或時局、悲嘆人生或際遇、等待生機或死亡、寂滅夢想或希望?
而這首千古流傳的《春江花月夜》,清麗婉轉卻不失大氣,寫景抒情又透出哲理,隱約中,還昭示著整個唐朝,乃至任何一個王朝的歷史發展趨勢。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從“初唐四傑”、“李杜”、“元白”到“小李杜”,從“王孟韋柳”、“高岑”到“郊寒島瘦”,詩聖、詩史、詩仙、詩祖、詩豪、詩天子……甚至詩鬼、詩奴,如果把文藝成就比作明月,那整個盛唐時代無疑就是浩瀚的海洋。明月共潮水而升,文化也在太平繁榮的時代昌盛起來。大江南北,從塞外豪情到江南軟語,哪裡沒有詩人佳作?燦若繁星的才子名士,受到祥和開放的文化氛圍感染和滋養,創作出千古流芳的作品。每個朝代都會有文藝特別興盛的時期,恰似一夜春風潤物無聲,才造就了“千樹萬樹梨花開”。
“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明月高懸,青白的月光鋪滿大地。可是地上總有些人要嗤笑你,要唾棄你。孤單地閃耀在天際,縱然你光華無雙,仍舊不過是一盞燈籠。正是這盞燈,能照亮黑暗,也就照出了陰影,極美麗也極醜陋。但是看透了這美麗和醜陋又能如何呢?蚍蜉焉能撼大樹?所以只有杜甫的“三吏三別”,羅隱的“豐年事若何”,李商隱的“不問蒼生問鬼神”,劉禹錫的“無人不道看花回”,卻被一年一年的塵囂淹沒了鮮血淋漓的軒轅。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繁星儘管璀璨,那是因為黑夜的襯托,煙花雖然美麗,卻短暫得只能停留一瞬。一切都會變,只有明月高懸,千古未變,“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一切都會過去,有凡人能夠像武曌那樣不在意身後功與名,只留下一塊無字碑?歷史,你走過之後,什麼都不會留下嗎?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不,至少,“愁”是永遠不會離開的,無影無形,抓不住的愁緒如同月光,求不來趕不走。“白雲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台。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相思幾人憂。不管是覓封侯還是出征塞外,或許是侯門深似海,或許是春閨寂寞處,可能是臨別折柳的老友,可能是妻離子散的牢囚,但願“天涯共此時”,只求“千里共嬋娟”。
失去了欣賞千里馬的伯樂,世間的千里馬也就絕跡了。春天一旦離開,桃花就要跟著走了。“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面前要走的這條路很長,瀰漫著濃重的霧氣。看不清的未來,也許隱藏著洪水猛獸,也許是一片坦途。
“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有多少人能夠如李白般泰然處之,花間獨酌,對影三人?只怕更多人是蘇軾一樣畏懼“高處不勝寒”吧!
歷史不是個體能夠駕馭,也不是個人能夠創造。或許你的存在改變了誰的命運,又或者誰曾經影響了你生命的軌跡,但整個時代的歷史不會為個人所左右,卻需要你的參與。唐朝的詩人們可能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也可能從未看清這一點,不過他們的詩已經被打上了歷史的烙印,他們自己也成為後人眼中的歷史。
春。江。花。月。夜。
在你的心目中沉默或者喧囂的唐朝,在你的印象中唯美或者單調的唐詩,正如一卷華關的圖景,一點一點鋪陳在你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