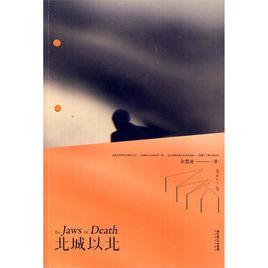內容簡介
南粵有一座城,它慵懶落後、虛偽貪婪。在這裡人心自私冷漠、黑白顛倒。這個無可救藥的地方叫做北城。四位少時夥伴,被禁錮在這座城,相互攙扶走過了年少時光。這個小城奠定了他們的成長背景,無形中影響了個人性格,捂住了他們的眼,鎖住了他們的心。固步自封的上一代,矇昧無知的上上代,連同乖戾懵懂的成長中的這一代,善良與兇狠,扼殺與寬恕,沉淪與自救。這裡有他們最愛的人,也有他們最恨的人。每個人都一直期盼著有人能出頭打破這個局面,可每個人都從來沒有去改變過什麼。然而我們始終相信,黑土下面會破出白芽,黑暗盡頭會有新生。
作者簡介
十六歲時一篇《北城以北》技驚四座,成為第一屆文學之新中,被郭敬明喻為“最具奪冠實力的黑馬選手”,這片文章讓當時還在上高中的余慧迪迅速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創作新人。然而當年,她正值高三,學業壓力下,她飲恨總決賽,止步六強。第二屆文學之新大賽,這個不怕挫折的女孩再次站上舞台,與其說是向讀者證實自己的實力,不如說是向自我發起巨大的挑戰。在評審安波舜眼中,她是個在文字方面極有天賦的選手,落落也評價她“有著最不容置疑的‘實力派’標籤,她的文字有深度,有思想,有靈感的火光,有折服人的力量。”
能在如此年輕的歲齡,用透徹的眼光將生活中的世態炎涼展現在鋒銳的筆觸之下,余慧迪的內心就像住進一位歷經滄桑看透世事的智者,用一種貌似波瀾不驚的姿態撫慰人心的委屈和苦痛。她的文字如同一個個鮮活的靈魂,將故事娓娓道來,與讀者傾訴衷腸。
然而遺憾的是,在第二屆文學之新的比賽中,她再一次因為種種原因止步於總決賽的大門外。但是,正當我們扼腕嘆息的時候,她安靜地遞交上來了一部早已完成的長篇小說,《北城以北》——這是她對自己,最無聲也最有力的證明。
讀完這本小說,我們想不出用什麼華麗的修辭來宣傳它,它如此讓人動容,如此浩瀚寬廣,它完全不像是出自一個少女之手。更難得的是,我們很難想像,在連續兩屆,長達四年的密集高壓賽程之中,她是如何抽空完成了這本小說的,更何況這中間,她還經歷了從高三到大學的最艱難的時刻。
如果說除了文學價值之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推崇的,那就是余慧迪的這股韌勁。正是這股子韌勁,這種如今越來越少見的精神,令她的小說充滿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折射出令人為之驚嘆的光芒。
【這本書從構思到成稿也有六年多了,我一邊寫一邊就告訴自己,以後的作品一定會更精緻更完美,但再也不會像這樣掏心掏肺地去寫一個這樣的故事了。成長是個永恆的主題,能夠讓曾經經歷過成長,和正在成長中的人們看過之後都留下一點嚴肅的思考,這是我最大的願望。】——余慧迪
目錄
PART 1
楔子
第一章 花葉傾城
第二章 上南
第三章 蕊蕊
第四章 荔街
第五章 三隻小兔
第六章 訣別
PART 2
第七章 回到北城
第八章 追憶
第九章 重新開始
第十章 遇見
第十一章 驚厄
第十二章 尾聲
後記
經典句子
看著他們,每次我都會覺得,像“新年新氣象”、“無憂無慮”“瘋玩”“放肆”“希冀”這些詞,該是多么美好,美好得就像那些滋滋作響的鞭炮一樣讓我不敢靠近。
那個兩極分化的夏天,有驕陽如火,也有暮靄沉沉。絢爛的色澤暈染成了他人記憶里的甜美,我們卻只有帶著苦澀乾涸的願望彳亍前行。
但我的話不能說出口,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家庭完整的人不配在孤兒面前抱怨身世,所謂尖子生也沒有資格對其他同學抱怨出卷子的人。早年我便深諳這一點,因而守口如瓶,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在家和在校的假象。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勤奮好學尊師重道,我是好孩子好學生——
這一切我早就煩膩了。
此後又過了許多許多年,我才漸漸有些理解:有的人、事之所以無法忘懷,並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么美好而讓你難忘,而是因為你在對它印象最生動深刻、最離不得它的時候,由於別的某些你無法控制的力量強迫你永遠地失去了它。這種心情不是難過,不是怨恨,而是捨不得和不甘心。
後來,我才想起來,福禍相倚,我真的不應該得意忘形的。快樂的時光是如此短暫,以至於我都忘記了身後背負的一世的羈絆。黑暗的影子永遠發自北城。
北城是我的故鄉。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小的時候總是覺得,它落後,疲怠,不整潔,治安特別差,固步自封,虛偽貪婪,人心自私冷漠;愛這裡,市檜者大行其道,正直者沒有好下場。這是一個無藥可救的地方。這是一個黑白顛倒的地方。這是一個永遠沒有英雄的地方。
在這裡,有我最愛的人,也有我最恨的人。最後的結局是,我傷害了最愛的人,原諒了最恨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一直期盼著有人能出頭改變這個局面。我們每個人都從來沒有去改變過什麼。
然後我們用一個舊日的擁抱道別。他一邊,我一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我一直期待著認同,卻又害怕被認知。並非是害怕這認識之間暴露我的幼稚無知,而是憂慮在了解過後能留下來的人一個也沒有。
作者的後記
真的假象 假的真相
總有一些問題是不應該問的,總有一些底線不該被觸及。對女人不該問體重,對男人不該問工資,對患者不該問病情,對作者不該問真假。
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總是一邊寫一邊構想,最有可能被問到也是最怕被人問到的問題必定是:這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個問題勢必會帶來無數的麻煩,我早已默默地下定決心,遇到這樣的提問,必定充耳不聞,堅決不理。
現實題材,第一人稱,見縫插針的時事與如影隨形的社會背景,我所使用的一切都使自己容易陷入真假莫辨的境地。有時寫著寫著我會停下來問自己,這么寫是為了從我自己身上和角色找共同點、更貼近角色接近真實呢?還是為了不讓別人誤會是我自己的經歷而刻意走另一種不同的道路?想著想著我就混了,寫著寫著我就亂了,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現不用再去擔憂真假的問題,這個故事好像早就等在那裡,等我剝筍一樣將它層層剝落,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在我一個多月的寫作過程中,輕鬆得好似不用構思情節,不用安排捏造,它早就在那裡等著我了,又何來的真假。
簡單回溯一下“北城”的寫作過程。這個故事的大概在初二初三的時候萌發,當時的構想是寫成一部輕喜劇;高一的時候無心向學,一直心高氣傲地想寫一部長篇,於是先寫出了一個梗概出來,打算慢慢編排――不巧發現這篇梗概“很像一篇小說”,於是萌生了投稿給“新概念”的想法,又有同學硬塞給我一張“TN”的報名表,由於當時“TN”的截止日期比“新概念”早,所以先投了,也幸運地在“新概念”截止之前就得到了好訊息,從此與“新概念”無緣;高二起了個頭,高三陸陸續續在晚自習課堂上寫了很多小紙片記錄靈感來時想到的情節,高考完之後正式開始寫,歷經一個多月――短短兩百字可概括的過程。並非是有些人以為的“吃《北城以北》這碗飯吃到老,一直不停拿來說事。”它之所以一直沒個了結正是因為它確實還沒有完結,我一直在等著給它一個完滿的結尾。於是有了你現在手上拿著的這本書,這個夢才算是,正式地,告一段落了。
2010年8月完成初稿。2011年1月將近定稿。2011年7月又回過頭來看,發現我幾乎從來沒有去動過主要情節。這個故事我想它就是這樣。它應該就是這樣。我可以告訴你,寫的時候一點都不自虐,除了一時卡住有些苦惱之外,表情沒什麼變化,情緒沒什麼波動,但寫出來的東西卻比我的其他作品都要情緒化。我不是那種會一邊寫一邊感嘆自己真是個天才然後被自己感動得淚流滿面的人。我想這種情緒多少也影響了一點兒主人公的性格。
這個故事,如果一年後我來寫,肯定比在高考完馬上就寫要來得好;四年後寫,會更成熟,八年十年後,也許會更好。但那些都是字面和技巧上的東西,我甚至覺得自己再也不會那樣掏心掏肺地去寫一個這樣的故事了。也再不會有番外和續篇。裴飛是個軀殼,裡面其實已經掏空了。她慢慢地湮滅在北城灰色的陰雨里。可能她就安葬在上南的某一處呢。
其實我會想,我對她是同情、悲憫呢,還是害怕、抗拒?
但隨著ending的鐘聲響起,我們的人生軌跡幸運地擦肩而過。
這樣的結局我很喜歡。
我曾經遇到很多我家鄉(也包括其他全國各地)的人通過不同方式告訴我:北城真的和我的家鄉很像,你寫得很真實。我從來沒有回應過這個問題,因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起來似乎只要你住在一個小城裡,有時候甚至都不需要是小城只要是個城市,你就覺得身邊的人都是我說的那樣,你就覺得那裡又是一個北城。所以導致“北城”短篇剛出來那段時間湧出一堆跟風模仿之作,到處都有城裡的孩子拿自己的家鄉痛斥批判一番然後讓主人公毅然出走,格調無不消極憤世。我就會覺得他們肯定沒搞懂我想表達什麼,而很顯然我也不了解他們和他們所在的城市,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我們是在對同一個問題達成了共識,實際上我們對對方一無所知,牛頭不對馬嘴。
我一直期待著認同,卻又害怕被認知。並非是害怕這認識之間暴露我的幼稚無知,而是憂慮在了解過後能留下來的人一個也沒有。
那些陪我一起親歷成長的孩子未必會有相同的感受。他們大多熱愛這裡,即使不熱愛也習慣了這裡,不像我,每番回家便覺好似過敏,渾身不適難耐。慢慢地,都變成了一個傳統的人,都喜歡強調自己身上傳統的地方,都不喜歡生活方式有改變,餘生剩下的幾十年的目標就是在生活舒適安康的底線上如何儘可能地賺更多的錢。
我記得以前還是有不少朋友跟我一樣喜歡把自由掛在嘴上,喜歡搞些自以為叛逆的舉動,喜歡一邊做作業一邊寫些無病呻吟的文字。後來他們都妥協了吧,都安穩下來了吧,還是喜歡拿以前寫的東西去給別人看,不過僅限於幾個死黨中間然後嘲笑嘲笑就過了。好像只剩我在不合時宜地流浪在邊緣,給人不安分的印象,文字都記錄在碎紙片上常常不知所蹤。那時候我們明明只有十八歲,卻世故現實得讓人心涼。
有的朋友總是覺得可以先賺足夠多的錢再去搞理想,試問你賺了很多的錢然後不會想賺更多么?你還有什麼心情去談理想。我想問有幾個愛情里的後備情人能和愛人終成眷屬,那你憑什麼認為把夢想當備胎它就會一直默默等候著直到你去實現它。
如果有一天,我騎著馬兒在雪山下的草原上面對著格桑花兒流了眼淚,那肯定不止是為我自身努力過程的辛酸,還有為你們早早放棄的遺憾,我想會是的。
那些來過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留下過印跡。
那些離開過的人不知道他們一直沒有走。
我知道會有新的告別,我在等待那一天。
那個雨天我們坐在咖啡館裡,你忽然說出等你出書了我一定會去買。如此近人情的一句寒暄忽然之間讓我足足沉默了五分鐘。
什麼“十年蹤跡十年心”“十一年前夢一場”都已經用盡。再沒有更哀婉的詞能描繪這十三年。你知道,這將近五千多個日子以來唯一讓我動過留在這裡,或是鵝城,或是廣東的其他地方,買套房子平靜生活的念頭的,便只有你而已。是你最早啟蒙了我關於自由的想法,讓我懂得敢於反抗一些東西才能爭取到另一些真正想要的。抱歉,我盜竊了你的夢想,我成功了,遠走高飛,去了南京,我過得很快樂。這種偷來的歡樂時光會不時地讓我想到你。我用孩子氣的、粉紅色的、樸素的平實的夢想,換取了你的那些壯志豪言,然後帶著它們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果你一開始也在堅持,那該多好。
你教會我自由。我卻為了這自由放開你的手。悲哉。往後有無數次我自己在心裡暗自動搖,分不清這花花世界何其多的誘惑究竟哪種才是我真正所需,越是往後走,越是要自己去做出選擇。我重新學著為自己樹立標桿,確定大方向。你說,你終於要飛了。於是我便覺得這主人公的名字必定得是“飛”。只有這個簡單不過的字眼,才能憂鬱地帶過我們來不及訴說也沒學會訴說的一切。
這些年,我攥著你的紀念物寫過那么多東西,卻都沒有正面寫過你。如果你看到了開頭,請看到結尾,縱使經歷過多少彆扭、冷戰、鬧矛盾、分道揚鑣都好,這本書開頭的某一個位置只能還是你的。無論以後要走多遠、遇到多少人和多少事。
你說,若提前知道這些,你還會想要看么。
“北城”是件很個人的作品,裡面的很多想法很多念頭都是非常主觀化的東西,所以起初並未期待能得到很多的共鳴。既是我兒,必定長得像我――有人喜歡,就會一直喜歡;有人不喜歡,無論如何都喜歡不起來。對此我們兩個都相當坦然。不求你承認這是好,這是美,但須得承認這是真――不是真實的真,而是真誠的真。此誠可問天。
2011年7月16日
其他信息
北城以北 作者:余慧迪
我從祖國的最東南處起,一路向北逃離,逃到北城以北的地方。
——前記
北城在木棉、荔枝和紫荊的混合香氣的薰陶下,漸漸地有些昏昏欲睡了。
從前北城人只知道他們世代居住的這座小城在H城的北部,又在東江下游的北岸,於是為其命名曰:北城。到後來,北城人終於知道,北城原來坐落在祖國東南的廣東省,又隸屬於廣東省東南部H市,相當於國土的最東南端。然而這名字叫得久了也就習慣了,於是北城一直叫北城。
北城位於珠江三角洲東北部,H城西北部,南望東莞,毗鄰港澳,靠近廣州、香港、深圳。照理說,這樣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有利於發展的,可是北城有些慵懶,有些倦怠。眼見得深圳、東莞這些鄰居三十多年前就開始如火如荼地搞改革,現在一個個經濟都發展得如日中天了,北城仍舊是懶懶地,翻一翻身,撓一撓癢,繼續曬它的太陽。
我的家在臨近東江的一個住宅區里。幢幢相同的房子、相差無幾的紫荊、大塊單調的空地,組成了一個平凡的小區。十幾年來小區就沒出過事,風平浪靜。
那個普通的星期五下午,我從學校一路狂奔回家,一把把書包甩在地板上,就衝到陽台門口。文心蘭總是在下班之後花上半個小時的時間來打理她種的吊蘭。一盆盆的蘭草懸掛在陽台上空,葉子細長優美,嫩綠之中夾著一線鵝黃,勾著半圓的弧線,風一吹過便搖曳生姿。
文心蘭像平時一樣給吊蘭澆水。她用拈花指扶著水壺,微微傾斜,水小股兒小股兒地匯到花盆裡。我默不做聲地直盯著她。她的頭隱沒在十幾盆弔蘭中間,我只看到一隻漆黑的眼睛在嫩綠和鵝黃中閃了一下,然後是一聲輕輕的咒罵:“掐死你那雙黑眼珠子喔,瞪得跟死人似的。”
我很響亮地吸了下鼻子,努力使自己的眼睛看起來不那么水汪汪。那些盈滿的淚珠似乎一不小心就會紛紛滾下來。“小柒哪裡去了?”我問。
“瞧你那死樣兒,什麼小柒,哪個死人啊。”文心蘭繼續歹毒地說著。
我又下了一番極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的聲音不那么顫抖。“我是問,莫柒信哪裡去了?”
“死在外面了。”她繼續面不改色,一如既往地用冷漠把我的焦慮擊潰。我清楚地聽見自己的聲音軟下來,用一種卑怯惶恐的聲音可憐巴巴地問:“媽媽,我能不能求你告訴我莫柒信到底去哪兒了?”
“求我?你這死丫頭這是在求我嗎?為了一個臭不要臉的死人求我?”文心蘭關節發白地攥住一盆弔蘭。她搖晃得那樣厲害,以至於那么多細弱的葉子也跟著瑟瑟發抖。啪的一聲。一顆炸彈擦著我的左耳爆炸。陶瓷和泥土紛紛揚揚地落了我一身,幾根細長的葉子滑稽地耷拉在我肩上。我一邊扯起書包沖回房間,一邊摔上門,靠在牆角把頭埋進膝蓋里嚶嚶地小聲哭泣起來。
我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地渴望逃離北城,逃離這個噩夢。
在我尚年幼就意識到文心蘭的說話方式是多么與眾不同的時候,我也不禁注意到大多數北城人也有著跟她相同的習慣。他們說話特別鍾愛一個“死”字,名詞前加“死”,動詞前加“死”,賓語前加“死”,一切可以加上這道裝飾的地方,他們都會毫不客氣地賦予一個“死”字。比如僅僅是因為回家晚了這樣一件小事,文心蘭也可以用極其壯烈的方式把我責罵個狗血淋頭:“死丫頭,也不用你那雙死眼看看現在幾點了,你老實交代你死到哪裡去了,這么晚才知道死回家?活得太舒服想死了是吧?下次你再這么晚死回來看我不揍死你。”
這件事我倒不怪她。因為在她背後,有整個北城的八十多萬人為她作了鋪墊。
北城是個充滿怨氣的地方。我一直這么覺得。北城人有一個特殊的本事,無論大小事,他們總能從客觀上找原因。比如天氣不好,比如時間不對,比如張三太貪小便宜或者李四太蠻不講理。只要稍稍沾上點邊兒的理由,不管有理沒理都會成為冠冕堂皇的真理,以此來作為他們成績不好、生意不好或者運氣不好的最好的解釋。年輕人到處大罵特罵當今的教育制度和煩人的家長;老人們在大樹下乘涼趕蚊,順便數落不肖的子孫;女人們提著大袋小袋穿越在骯髒的市場裡,嘴裡忙著咒罵持續上漲的價格和小販們缺斤少兩的卑劣行為。上班族們抱怨昂貴的石油和低迷的股市。如此這般,沒完沒了。沒完沒了。
自打我懂事以來,最早是從外祖母那裡懂得了怨怒的害處。我的外祖母祖籍深圳,當年她只有五六歲的年紀,被一顆話梅糖輕易地騙到了北城。長途汽車上的奔波勞累以及一臉惡相的人販子,嚇得她不會說話,在賣入文家以前,一直都只會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面目慈祥的文老爺子把她的手輕輕放在他寬厚的大掌上面,問她的名字,她唯有拚命地搖頭。於是老人又把她的小手轉交給了另一隻小手。
年輕的文家少爺寬厚老實,問她,“我叫文景森。你叫什麼名字?”
她依舊只搖頭。過了一個月,才開口說話。“玲玲。”她卑怯地小聲說道。
“哪個?是王令玲,還是王林琳,又或者靈氣的靈?”
她復搖頭。文景森繼續耐心地問:“那你姓什麼?”
她伸出一隻食指,在空中畫了三橫,再一豎。他笑,從此替她取名為王玲。
起初那段日子,他繼承了祖上的家業。文家世代做木工,於是他的名字里有三木。憑著一雙巧手和憨厚善良的品格,他很快把產業做得更大,財富累積得更多。閒暇時光,他也教她寫字,一橫,再一橫,筆筆遒勁有力。
王玲一輩子只學會寫四個字:一、二、三,以及她的姓氏,王。
文家本不是什麼書香門第,她又是買進來的童養媳,更不需什麼文化。很多時候,她想起他教她寫字的樣子,不自覺地兀自動動食指,一橫,一橫,再一橫,然後是狠狠的一豎。她便得意地嘿嘿笑開來。
那是夫妻倆一段平淡的幸福時光。後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他的財產收入公社。出於對祖業的熱愛和尊敬,他偷偷留了一台刨木的工具機。被揭發後,他被揪到大街上狠狠地批鬥。接著是一段最黑暗無邊的苦日子。她從闊綽的文家少奶奶變成了公社裡面煮飯的廚娘。每天起早摸黑,與柴火和煤煙為伴。
外祖母很喜歡跟我們講起以前的故事,說她自己的遭遇,也說一些聽來的恐怖故事。到了最後,每每都是她不能自制地嘶喊:“憑什麼?那么多年的艱難都熬過來了,他憑什麼就在過上好日子的時候撒手歸去留我一人在世?憑什麼!”
而最近的這十幾年,外祖母又多了一條新的理由去怨恨:那就是她的故鄉深圳。她眼睜睜地看著生她並且原本應該育她的小漁村變成了如今享譽國際的現代化大城市,而她所在的北城居然還漫不經心地用散步一樣的速度慢慢發展。她簡直憤怒了。
“憑什麼?我原本可以有更好的發展,過上更好的生活,憑什麼要我淪落在這個小城市裡面一輩子?”她怨人販子,怨文家老太爺,怨文景森,怨批鬥他的人們,怨整個北城。
但是我發現,她唯獨忘記了責備自己,當年為何嘴饞得為了一顆糖就犧牲了一生的幸福。外祖母心臟不好,大概就是被怨念所侵蝕的。
王玲在來到北城的第十年,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接下來是第二個,第三個。
1967年初,正值中國傳統最重要的節日,大年三十那一晚,大腹便便的王玲在做年夜飯時突然感到一陣劇痛,倒在了灶台邊。
當晚,文心蘭出生。由於是最小的孩子,又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文景森非常偏愛這個孩子。他常常把她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帶著她到處晃;又用胡茬把她弄得咯咯笑。文心蘭從小就受到了與那個年代不符合的寵愛,比如上國小時就穿著時髦的方格連衣裙吸著牛奶咬著餅乾去上學。
可以想見,文心蘭從小就對父親過分地依戀和親密。而四個孩子裡面,只有三哥文尹城最像父親。尹城不僅活潑聰明,而且風度翩翩。在那個叛逆的年紀,文尹城不僅是文心蘭最喜愛的哥哥,更是她心目中關於男性的全部楷模。
然而文尹城的風光只持續到了十八歲。一場高考把他的驕傲擊垮了,在家唉聲嘆氣了兩個月之後,他走上了復讀之路。而文心蘭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也決定繼續升讀高中,以便有更多的時間陪她親愛的哥哥。
文尹城重考了三年。高中畢業的時候,連他的妹妹也高中畢業了。但她沒有考上大學。他臨上大學前慈愛地撫摸著她的頭說:“丫頭,乖乖等我。要聽話。”
她當真聽話地等了他四年。那四年里她在鄉下國小里教書,拿著微薄的薪水,懷著厚實的夢想。她在黃昏的狗尾巴草叢邊上學會了彈吉他,穿著格子襯衣,烏黑的頭髮蓋著半張臉,對著橘紅的夕陽輕輕地笑紅了臉。
四年之後,她褪去了青澀,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姑娘。四年後他回來,出落得更加溫文爾雅、落落大方,手上還挽著一個漂亮的女子。她叫石榭蘭,在電視台混了幾年仍混不出名氣的小明星。
她爭著出門去迎接他,聽著他熟悉的聲音親昵地喊著“蘭蘭”,卻錯愕地發現,那人不是自己。那么突兀地,她的身心涼透。“狐狸精!”她暗暗地罵,轉身跑回了房。
打那以後,年輕的文心蘭也成了一個有怨的女人。
所有的哥哥姐姐都談婚論嫁了。文心蘭在家裡倒像是個怨婦。她大聲地抱怨,抱怨電視台的節目太無聊,抱怨大哥的孩子吵吵鬧鬧,抱怨嫂子的香水噴得太多——她尖銳刻薄的話語給家人們帶來了嚴重的困擾。文尹城提議說該給他這個寶貝妹妹找個人家了。
王玲早在文心蘭高中畢業時就曾經給她找了個婆家,男方姓莫,是當地一個老實巴交的個體戶。當時她堅持要下鄉教書,推掉了。婚約書還在家裡那個大立櫃的底層。文心蘭把它翻出來,一個人偷偷去了莫家。
“你還娶不娶我?”她大著膽子問。
莫凌忠被她嚇住了:“你一推就是四年……我已經有老婆孩子了……”
“那這份婚約書怎么辦?”她揚起手中的武器。
客廳外面的林秀娥抱著幾個月大的孩子衝進去,揚手給了她一巴掌。
後來,文心蘭漸漸走出了哥哥的陰影。半年後,她嫁給了當地的一個公務員裴辰。再後來,她早產生下了一個女兒,從此開始了我在人間噩夢般的記憶。
我叫裴飛,出生在北城最美的季節。那時木棉花尚未落盡,紫荊剛剛抽出花苞。早熟的荔枝在街頭零星可見,顆顆稜角分明。
大人們都說我從小穎慧,剛入學就跳級,年年捧回厚厚的獎狀。乖巧、緘默,看上去很安靜。我從小在文心蘭的嚴格監管下長大,學會了察言觀色,學會了忍受一句話里夾著好幾個“死”字的咒罵,學會了低著頭急速穿過罵街的女人和睡著的乞丐。平和地等待和無限地忍耐是我的本領,在北城裡任何人都必須學會忍耐再忍耐,否則就只能成為在街上破口大罵的市儈女人,或者庸俗無能的男人,直到成為碎碎念著怨毒的故事的老人。
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離開北城,向北逃亡,遠遠地離開這片怨氣叢生的地方。
在早年的觀察中,文心蘭早早斷定我沒有學音樂和美術的天賦,就果斷地把我踹到了應試教育的路上。我從六歲起開始戴厚厚的眼鏡看厚厚的書本,為老師所疼愛為同學所不齒。正因如此,我沒有沒心沒肺的死黨,沒有可以交心的密友。只有小柒。在北城的時節,他陪我拾過木棉,摘過紫荊,在放學的路上分享過一串荔枝。
“以後我們一起離開北城吧。”他看著滿樹火焰一樣的木棉,好似不經意地說。
“什麼時候?”我激動地問。
“快了,快了……我們都快十二歲了,我想……”他的話語漸漸低下去,低下去,湮沒在一片深紅里。一朵飽滿的木棉花“啪”的一聲掉落在我面前,驚碎了我的幻想。
“走吧。”
那是十二歲那年的春天,我把小柒邀請到了我的生日會上。文心蘭和爸爸都對乖巧的小柒印象很好,一留再留,最後天色已晚,爸爸提出要送他回家。小柒說:“不用了,我爸爸正在趕來,應該快到了。”
門一開,文心蘭怔了半分鐘。她把門掩上,臉色發青地對小柒說:“小柒,你全名叫什麼?”
“莫柒信。柒是大寫的‘七’,信是……”
“‘講信用’的‘信’。”林秀娥咬牙切齒地在門後回答,身後是目瞪口呆的莫凌忠。
“不講信用的是你吧?”文心蘭冷哼一聲,把小柒推出門去。“柒,我們走!不要再到這個女人家裡!”林秀娥嫌不解氣,又轉過身向我們家歇斯底里地吼,“死不要臉!”
我在貓眼後可憐巴巴地望著小柒離開的背影,心裡盤算著明天去上學時怎么跟他解釋。
然而無須我絞盡腦汁地想一個妥當的解釋,因為小柒沒有來上學。
我沒有從文心蘭處得知我想要的結果。小柒從此沒有再在北城出現過。而我在十三歲後,也毅然到外面求學去了。文心蘭、外祖母、林秀娥,上一代以及上上一代的人們依然待在北城——生他們養他們給了他們血肉的北城。他們的性格和命運都和北城完美契合,密不可分。他們一輩子離不開這座小城。
一條彎彎的東江支流形成了天然屏障,把陳舊的北城和繁華的H市隔絕開來。北城裡面有很多年代較久的住宅區,建在江邊,僅僅隔著一道青赭色的老城牆就與東江水相接。
但和外面的H市,和整個欣欣向榮的珠三角不同,北城那樣安逸地度過一個又一個年歲,不爭不取。在一棵棵古榕、一道道古牆、一陣陣催人入睡的暖風中,悠然地躺在水面上歇息。
但是北城的人們還會不時說起,為何同是人,同喝一條江的水,我們和深圳人、香港人的命運就相差那么大呢?他們說起的時候,依舊是“死”字連篇的句式,依舊是惡毒怨恨的語氣,依舊是懶洋洋的表情。
評審郭敬明點評:
余慧迪的文字,在所有參賽者裡面,顯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和辛辣。整個文章從結構到敘述,充斥著一種跳出故事本身和作者經歷的冷漠感,所有評審在看到這篇《北城以北》的時候,都無法相信這樣的佳作出自僅僅十六歲的小女孩之手。我甚至有種預感,如果她每一次比賽的發揮都保持這個水準的話,她極有可能問鼎“文學之新”的冠軍。她是目前為止,我在比賽里看見的最大的黑馬。
本文作者作品收錄於:
《第一屆THE NEXT·文學之新”新人選拔賽作品全集 (上)》
《第二屆「THE NEXT·文學之新」優秀入選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