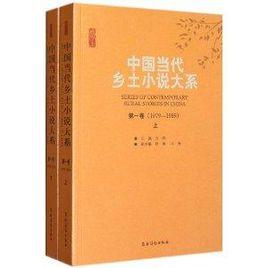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大系(第1卷)(1979-1989)(套裝共2冊)》中共選收鄉土小說作品150餘篇(部),均為新時期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為了解、研讀當代文學30年間的鄉土小說、鄉土文學所必讀、必備。
圖書目錄
前言:鄉土中國星移斗轉的時代影像白燁
第一卷(上)
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2
陳忠實信任/36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44
陳奐生上城/58
李輩黃河東流去(內容梗概)/68
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內容梗概)/72
山月不知心裡事/75
馬烽結婚現場會/88
孫鍵忠甜甜的刺莓/98
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190
張賢亮邢老漢和狗的故事/204
錦雲王毅笨人王老大/220
何士光鄉場上/232
種包穀的老人/239
張石山钁柄韓寶山/248
古華芙蓉鎮(內容梗概)/262
劉紹棠蛾眉/266
趙本夫賣驢/278
王潤滋內當家/288
汪曾祺大淖記事/302
矯健老霜的苦悶/316
路遙人生/332
鐵凝喔,香雪/400
張承志黑駿馬/410
蔡測海遠處的伐木聲/454
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468
李杭育最後一個漁佬兒/482
鄧剛迷人的海/494
烏熱爾圖琥珀色的篝火/518
王蒙葡萄的精靈/530
邵振國麥客/538
張煒一潭清水/562
古船(內容梗概)/572
何立偉白色鳥/576
第一卷(下)
賈平凹天狗/582
王安憶小鮑莊/618
鄭義老井/682
阿城孩子王/784
喬典運滿票/810
朱曉平桑樹坪紀事/824
田中禾五月/910
韓少功爸爸爸/934
葉蔚林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962
扎西達娃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982
莫言紅高梁/1000
李貫通洞天/1052
鄒志安支書下台唱大戲/1072
劉恆狗日的糧食/1088
李銳厚土(三題)/1100
謝友鄞馬嘶·秋訴/1116
劉震雲塔鋪/1128
柏原喊會/1150
阿成年關六賦/1160
浩然蒼生(內容梗概)/1174
林和平鄉長/1178
序言
鄉土中國星移斗轉的時代影像
白 燁
擺在讀者諸君面前的《中國當代鄉土小說大系》,凡三卷,四百餘萬字;涉及一百二十四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總計一百五十餘篇(部),均為1979—2009年間鄉土小說的代表l生作品。可以說,這個精心編選的大型選本,以點帶面地反映了鄉土小說三十年來在不同時期的主要成果,以及奼紫嫣紅的總體景象,發榮滋長的歷史進程。
編選這樣一套規模不小,字數也不少的三十年鄉土小說作品大系,在我們是基於這樣一種基本認知:當代以來的六十年,尤其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以來,當代中國在現代性與現代化的道路上迅猛前進,基本面貌發生了巨大而驚人的變化。但從社會的總體形態和生活的基本層面來看,一直在進行著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的衝突與對話、商業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博弈與商兌,也即還處於由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的過渡過程之中。而當代文學中的鄉土文學與鄉土小說,因為聚集了一批數量較多,質量又高的跨越數代的實力派作家,他們一方面在歷時性地記述和描寫著鄉土社會這種由外到內的巨大演變,一方面又在這種藝術追蹤中勵精更始,推陳出新,帶動著鄉土小說寫作不斷發生新變,贏得了鄉土小說與鄉土文學的蔓蔓日茂、欣欣向榮。因此,當代的鄉土小說,既由鄉土一脈反映了社會生活深層變動中的主潮演進,又由鄉土書寫表現了當代文學自身的成功進取,顯然具有社會與文學雙重演進的時代影像之重要價值與特殊意義。
一、概念與總脈
描寫鄉村生活的小說,在現當代以來,一直有著看似相近卻又不盡相同的稱謂與概念,如“鄉村小說”、“鄉土小說”、“農村小說”、“農村題材小說”等等。而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的差異,又在指稱的作者與作品上有所區別。因此,不同的論者在使用一定的概念時,首先需要加以釋義。
那么,我們為何選用“鄉土小說”的概念,又是怎樣認定這一概念的相關含義的呢?
“鄉土”的概念,早在先秦與魏晉的典籍中就有出現。如《列子·天瑞》中就說道“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又如曹操的《士不同》中也說道“鄉土不同,和朔隆寒”。前一個“鄉土”,是“家鄉”、“故鄉”的含義,後一個“鄉土”,則是“地方”、“地域”的意思。對於“鄉土”的兼有這樣兩層含義的理解,一直延續了下來。到現代之後,“鄉土”又與“鄉村”交替並用,或含有“鄉村”的意味。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的開首一句便是:“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裡的“鄉土”的用意,顯然更接近於“鄉村”。
把“鄉土”與“小說”連線起來,形成“鄉土小說”的概念,是在近現代之交的“五四”時期。魯迅先生於192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故鄉》,被認為是現代鄉土小說的先聲與濫觴。當時一些寓居北京的作家受到魯迅的影響,紛紛創作以回憶故鄉為題材,以描寫鄉愁為內容的小說,成為一時的文學新風與小說時尚。魯迅於1928年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指出:“騫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過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的人們,無論他們自稱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來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之後,在魯迅影響下出現的以文學研究會一些成員為主的小說創作,當時就被命名為“鄉土寫實小說”。1934年,沈從文在《學魯迅》一文中就曾這樣說道:“(魯迅)於鄉土文學發軔,作為領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筆,從觀念拘束中脫出,貼近土地,挹取營養,新文學的發展,進入新的領域,而描寫土地人民成為近二十年文學主流。”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引下,解放區文學應運而生,而其中的主要代表趙樹理、丁玲、周立波、孫犁等人的小說創作,多以北方鄉土為背景,農民鬥爭為內容,使“鄉土”與“革命”內在地聯結起來。而由趙樹理的小說創作提出來的“趙樹理方向”,影響一直波及到當代。
進入當代時期之後,描寫鄉土生活的作品,不再被稱為“鄉土文學”、“鄉土小說”,而代之以“農村小說”、“農村題材小說”的稱謂。概念的這種變更,既有以新的概念與舊的文學相區別的意思,也有從生活到文學確實都發生了新的變異的因素。在自然化的鄉土向體制化的農村急速演進的同時,描寫這一“山鄉巨變”的寫作,其稱謂由“鄉土”更變為“農村”,就顯得自然又必然。這一稱謂一直延續到新時期之後。如1982年,寶文堂書店編輯出版了《農村短篇小說選》,《人民日報》文藝部編選、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選》,1986年,浩然編選,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農村小說大觀》等。2006年5月,中國作協、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和江蘇省作協還在華西村聯合舉辦一次全國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研討會。但在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鄉土文學的提法卻越來越流行和普遍。一些文學論文在指稱農村小說與農村文學時,大都代之以“鄉土小說”、“鄉土文學”。一些有影響的研究專著,也以“鄉土”替代了“農村”。如丁帆的《中國鄉土小說史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陳繼會的《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史》(中原農民出版社,1996年)等。
我們在總體稱謂上,選取了“鄉土小說”這樣一個提法。在其基本內涵上,採用以鄉土題材為主的原則,但更傾向從整體性上來把握鄉土文學的概念,既強調鄉土題材、鄉土題旨的雙重要點,又重視鄉土思念、鄉土關懷與鄉土批判的三位一體的意蘊。這樣的寬嚴適度的“鄉土小說”的理解與厘定,大於“農村題材小說”的概念,內含了“鄉村小說”的概念,並與現代文學中的“鄉土小說”接軌,能比較好地反映這類題材寫作的歷史與現狀,發生與發展。
二、階段與演變
與整個當代文學創作始終扣合著社會變遷與時代演進的節拍一樣,當代三十年的鄉土小說也是與它所表現的鄉土社會現實密切相連,並隨之替嬗而演變的。總體來看,三十年來的鄉土小說的發展,也大致上經歷了新時期(或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三個階段,而三個階段的鄉土文學,既相互銜接,又不斷演進,各以不同階段的自身特點與卓異風采,構成了當代文學創作中最為絢麗和耀眼的風景線。
新時期階段 新時期文學發出的先聲;是於1977年底出現的“傷痕文學”。“傷痕文學”除去領銜的《傷痕》、《班主任》等少數作品外,很多作品大都屬於傳統的農村題材,如韓少功的《月蘭》,李革的《王結實》,賈大山的《取經》,成一的《頂凌下種》等。而隨後興起的“反思文學”,更是以農村題材為主體,如葉文玲的《心香》,祝興義的《楊花似雪》,錦雲、王毅的《笨人王老大》,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因為當時更為關注的是這些作品的主題意義與它們的批判意蘊,這些作品在題材上集中於農村生活的特點反而被人們忽視了。
讓人們越出“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視界,而特別注意其題材與題旨的鄉土意味的,是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等中篇小說,以及陳忠實的短篇小說《信任》,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周克芹的長篇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這些在1979年前後出現的農村題材小說,雖說還帶有一定的“傷痕”與“反思”的意味與印記,但作品卻把主要的著眼點放在了新現實中的新農人,新生活中的新問題,著意描寫他們的面對新的社會現實的精神甦醒與個性顯露。這些作品或可看作是新時期鄉土小說寫作的第一波浪潮。
農村生活的變異,農人心氣的勃發,乃至農村新人在精神上氣質上的吐故與納新,新風與舊俗在現實中的衝突與較量,隨後成為鄉土小說寫作在一個時期里反覆吟唱的主要旋律。如馬烽的《結婚現場會》,張石山的《钁柄韓寶山》,趙本夫的《賣驢》,王潤滋的《內當家》,劉紹棠的《蛾眉》,孫鍵忠的《甜甜的刺莓》等。1982年,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發表,這部作品以農村青年高加林初涉人生時道路選擇的兩難,把一個與鄉土密切關聯的主題凸顯了出來,那就是城鄉發展的尚不平衡與所代表的不同文明,給置身其中的農村青年帶來的青春的煩惱、選擇的困惑。接下來,便是帶有鄉土文化的反思與批判意識的一些作品的接踵出現,如李杭育的《最後一個漁佬兒》,鄭義的《老井》,葉蔚林的《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劉恆的《狗日的糧食》,李銳的《厚土》,邵振國《麥客》,張煒《一潭清水》等,這些作品在看取鄉土上,不僅把它當成是一種社會的基層生活存在,而且還把它們看成一種傳統文化的載體。撇開作品的具體臧否不論,它們在總體上都把鋒芒指向鄉土文化與農耕文明,開始以自己的眼光和方式,來發現和表現鄉土中國的渾重與複雜,是顯而易見的。由此,鄉土小說便添加了一種新的寫作角度,也呈現出了新的文化深度和人性內涵。
至此,新時期或八十年代的鄉土小說,就大致實現了由“傷痕”、“反思”的卵翼破殼而出,立足於直面現實、關注問題的現實主義,又超越傳統的寫實現實主義過渡到文化批判與文明回思,有效地實現了鄉土小說的三級跳式的長足發展。
九十年代階段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引發的經濟熱潮、商業大潮席捲而來,文學、文化領域受到很大衝擊,一些文人作家紛紛“下海”,棄文經商,文學創作在起初幾年一直不太景氣。之後,隨著知識文人精神狀態的自我調整,文學領域裡的小說寫作漸漸恢復常態。但重新崛起的創作態勢,又呈現出濃重的個人化追求、分散化的傾向,新時期中一個文學浪潮接一個文學浪潮的熱鬧狀況一去不回,以至有人驚呼文學進入了“無法命名”的時代。
但在鄉土小說寫作一脈,因為與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離,也由於作家的堅守自我、甘於寂寞,似乎並沒有出現中斷或萎縮的情形,相反,無論是中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作家們的鄉土寫作,都在持續堅守中有所拓展,不懈筆耕中有所進取。但受個人化與分散化的影響,這一時期的鄉土小說創作,在描寫的內容與表現的形式上也表現得豐富而紛紜。這裡,有以幽默的語言、混沌的敘事表現農村生活情趣與農人性格風趣的作品,如劉玉堂的《最後一個生產隊》,張宇的《鄉村情感》,趙德發的《通腿兒》,楊爭光的《公羊串門》等;有直面鄉土現實問題與鄉民生存艱難的作品,如李佩甫的《無邊無際的早晨》,陳源斌的《萬家訴訟》,劉醒龍的《鳳凰琴》、《分享艱難》,關仁山的《九月還鄉》;有歌吟鄉間田園情趣與平民人性美好的作品,如鐵凝的《秀色》,賈大山的《蓮池老人》,遲子建的《霧月牛欄》,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岳恆壽的《跪乳》,劉慶邦的《鞋》等。總之,鄉土不再是單色的,靜態的,而是多色的,動態的,同時也是錯綜複雜的,讓人咀嚼不盡的。
這一時期鄉土小說中的長篇小說寫作,數量不是很多,但質量卻再創新高,這就是那些從個人命運、家族文化的角度反思社會歷史的作品,如余華的《活著》,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等。這些作品,從內蘊到寫法,都是自出機杼,各有千秋,既在作家個人寫作歷程上卓有突破,也是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穫。尤其是以陳忠實的《白鹿原》為代表的由鄉鎮看取傳統,由家族反思歷史的小說,從鄉土出發,又超越了鄉土,以豐沛的內涵、精湛的藝術,標誌了鄉土小說乃至當代小說創作的時代高峰,這樣的耀眼實績著實讓人欣喜,委實令人稱道。
因為個性凸顯,寫法多樣,鄉土作家九十年代的藝術探索,使鄉土小說的表現力與可能性,都變得更多了,更大了,這顯然不啻是鄉土小說創作的福音與榮耀。 新世紀階段 比之其他時期,新世紀的文學文化領域,因為面臨著商業文化、傳媒文化與信息科技的多重衝擊,更是一個眾聲喧譁,充滿挑戰的時期。經過近十年的碰撞與博弈,當代文壇已經一分為三,這就是以文學期刊為主導的傳統型文學,以商業出版為依託的市場化文學(或大眾文學),以網路媒介為平台的新媒體文學(或網路文學),這樣一個“三足鼎立”的狀態,構成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格局。當然,這樣三個板塊並非半斤八兩,平分秋色,總體來看,因傳統型文學聚集了有實力的作家、高質量的編輯,在整體文學中的作用舉足輕重,具有引領文學發展、標誌文學進取的重要作用。
在新世紀的傳統型文學中,雖然過去較為薄弱的都市小說、婚戀小說,數量有所增多,質量也有所提升,但無論是中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人們關注較多,影響也更大的,仍然是鄉土題材小說。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鄉土作家的抱誠守真和化壓力為動力,抵禦了來自方方面面的誘惑與攪擾,從而使鄉土小說創作的勢頭並未有所減弱,質量也並未有所下滑,毅然而然地保持了一種依流平進,穩步前行的姿態,因而取得的收穫依然是平實而豐盈的。
這一時期鄉土小說的藝術鏡頭,呈現出來的生活畫面,既萬紫千紅,多姿多彩,在表現手段的運用上,也是各顯其能,不一而足。嚴正的,詼諧的,溫馨的,苦澀的,現實主義的,現代主義的,乃至後現代的,都花團錦簇,應有盡有。作家們從看取生活到表現生活,都顯得更為靈動,高度自由。如畢飛宇的以細節真實揭現農村女性心理隱痛的《玉米》,夏天敏的以寓言方式書寫農人沉悶生活的《好大一對羊》,葛水平的以冷峻故事表現山民心理較量的《喊山》,郭文斌的從童趣的角度描寫貧苦鄉間生活中的溫馨親情與人情的《大年》等。顯而易見,作家們的視野格外寬廣而又自有重點,作家們的筆墨自由靈動而又有自己的個性顯現,多樣化的敘事與多元化的觀念,已經成為鄉土小說寫作中的一個基本定勢。
而以自己的語言敘述自己的故事,以自己的故事講說自己的發見這樣的一些品質,則更為集中地反映在新世紀中一些鄉土長篇小說之中。這些作品或在鄉土的意蘊上生髮別的意趣,或在鄉土題材上再做新的文章,使作品在故事層面上充滿十足的鄉土味,但又在現狀省察、歷史反思、人性審視等方面,另有玄妙或別有深意。如孫慧芬的《歇馬山莊》,鐵凝的《笨花》,賈平凹的《秦腔》,蔣子龍的《農民帝國》,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等。這樣一些內容厚重,藝術精到的長篇小說,既拓展了人們對於鄉土生活、鄉土中國的既有認知,又使人們領略了鄉土小說寫作自身的無限可能與無盡魅力。
三、影響與意義
作為中國新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鄉土小說創作,其影響與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它獲得了自身的長足發展,使鄉土小說寫作一脈綿延不斷,更在於它在自身不斷進取的同時,又極大地促動了小說創作中的其他傾向,並積極地影響了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
當代文學的“十七年”中,小說創作中一直是兩大創作傾向引領風騷,尤其是在長篇小說創作中,那就是“革命歷史題材”與“農村題材”。當代文學界把這一時期的長篇小說經典作品概稱為“三紅一創”,其中的《紅日》、《紅岩》、《紅旗譜》是“革命歷史題材”,《創業史》是“農村題材”。乍一看來,似乎“革命歷史題材”絕對占優,細一分析,這也與“農村題材”不無干係,因為寫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歷程,而其中的英雄人物主人公,多是農民出身,他們的革命歷程與英雄業績,也是一個個農民順應歷史走向進步和成為英雄的過程。這在梁斌的《紅旗譜》、孫犁的《風雲初記》、劉流的《烈火金剛》、馮志的《敵後武工隊》等作品中,都表現得既真實又充分。還有一些作品,如馮德英的《苦菜花》、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等作品,“革命”與“農村”水乳交融,幾乎很難區分開來。可以說,正是鄉土中國的變異與底蘊,才在根本上造就了在長篇小說創作中,“革命題材”與“農村題材”雙峰對峙、相互輝耀的奇特現象。
新時期以來的三十年,小說與文學中的許多看似與“鄉土”並無干係的現象,稍作分析就會發現它們與“鄉土”,其實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聯。在新時期與八十年代期間出現的一些文學思潮和創作傾向,除去前邊提到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外,“改革文學”與“尋根文學”都與鄉土題材文學有著不解之緣。“改革文學”有兩個題材重心,一個是工業,一個是農業,前者的代表性作品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而後者的代表則有柯雲路的《新星》,賈平凹的《浮躁》,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等。而關注農村改革與現實變化的現實主義傾向,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又繁衍出以河北的“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及劉醒龍等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傾向,而這種寫作雖然在其著眼點上,越出了農村與農民,擴展到鄉鎮、學校、城市,但基層幹部、國小教師、打工妹等人物的活動舞台,依然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鄉鎮生活與鄉土社會。在他們身上,躍動著農人們的躁動的心理,折射著鄉村變革的種種陣痛。
出現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至今餘波不息的“知青文學”,其實也是以青春回望和精神還鄉的方式,對鄉土生活的別樣再現,乃至對於鄉土中國的深情致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既是知識青年們更換了居住地,也是農村、農場增添了新成員;影響的不只是知識青年個人的命運歷程,還有當地的農村、農場的此時此地的現實面貌。因此僅僅從命運的變異、成長的苦痛的角度來看待“知青文學”,是不夠全面,也不夠完整的。它們確實是真實而難忘的青春記憶,同時也是動盪時期的時代記憶,窒悶時期的鄉土記憶。像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張蔓菱的《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陳村的《我曾經在這裡生活》,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在著意表現知識青年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同時,也較多地描寫了知青與農民、與牧民等的深長情誼。之後的如喬雪竹的《尋麻崖》,彭瑞高的《賊船》,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張抗抗的《隱形伴侶》,張承志的作品《金牧場》等作品,則立足於“知青文學”,又超越了“知青文學”,由“插隊”生活所導致的人的艱難處世、人的特殊境遇,擴展到人的生存價值、人的生活意義等,以及由農村生活凸現出來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的關係與矛盾。
因為“鄉土”一詞,既有“家鄉”與“故鄉”的第一層含義,又有“鄉間”與“地方”的第二層含義,與鄉村、鄉土關聯密切的重在描寫地域民俗風情小說,因為有著深厚的傳統和傑出的作家,也與鄉土文學一起,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甚至有的研究者把這種寫作直接列人鄉土文學行列。這種寫作的典型代表是汪曾祺、林斤瀾等,他們的小說寫作,講究用看不見技巧的方式,把一切融化於溫馨的詩情或寫意的小品之中。其實,一直以鄉土文學作家自居並積極倡導“建立北京的鄉土文學”的劉紹棠,與這一類寫作也極為靠近。他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躋身“荷花澱派”之後,以抱誠守真的方式堅持自己所認定的現實主義,在《蛾眉》、《蒲柳人家》等作品中,著意表現京郊鄉村的詩情畫意與運河百姓的似水柔情,作品更為重視的是變中又不變的質樸而良善的民習與民俗、民風與民性。此外,近年來越來越為人們關注的地域作家群落,如河南的“南陽作家群”,寧夏的“西海固作家群”,雲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達州作家群”,貴州的“黔北作家群”,無一不是由立足於鄉土開始,從紮根於地方起勢,來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顯示出自己的優勢的。
與鄉土小說有著直接的淵源,或由此出發另樹一幟並取得重大成就的,是以長篇小說為主的家族小說寫作。這一路小說寫作,先由張煒的《古船》現出端倪,繼由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豐乳肥臀》,阿來的《塵埃落定》的聯袂衝刺,掀起長篇小說中波瀾不斷的創作新潮與高潮。從囊括生活、審察人性、反思歷史、反觀傳統等方面看,如許作品已達到或接近達到家族小說乃至長篇小說在這個時代少有的藝術高峰。即以《白鹿原》為例,作品以鄉鎮村社為舞台,在白、鹿兩家的世代糾葛之中,既折射了農耕文明的遺風,傳統文化的影響,又映襯了中國社會的近代變遷與政治力量的較量與消長。家庭與家族,家族與民族,民族與家國,水乳交融地交織在一起,使作品在引人人勝的魅力中,充滿咀嚼不盡的內力。有論者認為,“作為鄉土小說的大敘事”,“(《白鹿原》)為當代鄉土小說的史詩性寫作樹立了難以企及的標高” (張懿紅《緬想與徜徉——跨世紀鄉土小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這樣的看法,我深以為然。這說明,鄉土小說的寫作,完全可能開闢新天地,營構大作品,問題在於作者自身的生活累積、文學造詣與藝術才分。
因為有廣大的鄉土社會的比鄰與映襯,有雄厚的鄉土文學的比照與參酌,近年來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一些小說作品,也走出了以往的題材界限,在表現生活的廣度與反思歷史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以前少有的拓展與掘進。這些作品或者把都市與鄉村勾連起來,書寫城市與鄉村生活在消弭差異中的積極互動,以及給置身其中的人們帶來的人生的與精神的變化;或通過走出鄉村的主人公的命運遭際,描繪隨著歷史前進的鄉村變異,以及鄉下農人走向現代文明的緩慢進程。前一種寫作,可以孫慧芬的《吉寬的馬車》、賈平凹的《高興》等為代表;後一種寫作,則以鐵凝的《笨花》、趙本夫的《無土時代》最為典型。這些作品在鄉土小說的寫作上,有承繼,有突破,有跨越,有創新,均為傳統的鄉土小說在新世紀裡持續探索和精彩演進的最新成果。
經過三十年的探索與跋涉,當代鄉土小說歷經三個階段的不斷演進,已呈現出多意蘊、多旨趣、多主題的基本趨向。但若鉤玄提要地加以梳理,也可以概括出三個相對集中的主題意向來,這就是直書現狀、反思歷史和回望家園。直書現狀的寫作,或者直面雜沓紛亂的現實,或者探悉躁動不安的心理,在向人們傳導鄉村變動真實情景的同時,表現出對民生、民計的深切關懷;反思歷史的寫作,或者回思遠去的年代,或追憶逝去的鄉土,用歷史回溯的方式帶入審視的姿態,批判的眼光,其更為看重的是在啟蒙民性中審問傳統;而回望家園的寫作,更帶有浪漫主義的氣息,他們或者懷戀舊時的田園風光風情,或者尋索現時的淳樸人性人情,背後起支撐作用的,既有素樸的理想主義色彩,也有對抗現代性的民族主義情味。這樣一個三大主題的交叉並存又彼此互動,構成了當今鄉土小說寫作的大致格局,也使它構成了一個自具活力的藝術體系。
總之,鄉土小說寫作在三十年間,發掘著自身的潛力,運用著藝術的能量,追逐著社會的腳步,感應著時代的脈搏,一直在蓬勃發展,始終在高歌猛進。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創作主體的鄉土小說作家們,也演練了自己的才情,形成了雄壯的隊伍,尤其是在把握鄉土現實和鄉土生活上,拓展了已有的眼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種創作主體的整體性強化與綜合性提升,顯然更為重要,也更為可貴。而這,自然預示著已經煥然一新的鄉土小說,依然有著無可限量的未來與無比光明的前景。
2011年5月於北京朝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