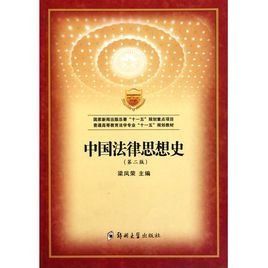夏、商、西周時期
中國奴隸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當時作為統治者的奴隸主貴族,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主要是利用“受命於天”的神權法思想和以“親親”、“尊尊”為指導原則的宗法思想來進行統治。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法律思想,也受這二者的支配。
在這個時期中,最為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他吸取商末統治者殘酷壓榨人民因而被推翻的教訓,比較重視民心的向背,要求西周貴族以殷為鑑,主張“明德慎罰”,德刑並用,反對“罪人以族”,要求在判罪量刑時必須區別過失(“眚”)和故意(“非眚”)、偶犯(“非終”)和累犯(“惟終”),以縮小打擊面。這在當時整個世界的刑法史上,是難能可貴的。他又修正了殷商的神權法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由純重神權走向兼重人事,為法律思想初步擺脫神權的羈絆提供了有利條件。他還“制禮作樂”,以“親親”、“尊尊”原則為指導,健全了西周的禮制,為鞏固西周王朝的統治打下了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
中國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變革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這時的法律思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並深入到法理學的領域,不少思想家對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與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的關係等基本問題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合理因素的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古代法學。
在這一時期中,原來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神權和宗法思想受到了極大衝擊。禮壞樂崩,諸侯異政,百家異說。當時參加爭鳴的各家都曾涉及法律思想,但主要是儒、墨、道、法 4家,特別是儒、法兩家。以孔丘、孟軻為代表的儒家繼承和發展了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這些思想對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影響極大,曾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但儒家思想在戰國時期並未取得統治地位。其他各家幾乎無不反對“禮治”,因而也反對維護“禮治”的儒家。以墨翟為代表的墨家是最早起來反對儒家的一個學派。墨家的法律觀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追求“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他們還要求“賞當賢、罰當暴”,反對各級貴族任人唯親的宗法世襲制。
以老聃、莊周為代表的道家,主張“道法自然”,崇尚“天之道”,鄙薄一切違反自然的人定法。老聃認為“天之道”的特徵是“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儒家所維護的“禮”和法家所倡導的“法”等人定法,則是“損不足以奉有餘”,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人之道”;統治者必須與民休息,無為而治。道家的後繼者莊周更從消極方面發展了老子的思想,認為人類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包括法律和道德,都是對自然的破壞,都應予以否定,鼓吹法律虛無主義。以李悝、吳起(?~公元前381)、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等為代表的法家,是先秦對法學最有研究的一個學派。他們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認為“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功過,據以行賞施罰的標準和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他們強調法律的客觀性、平等性和統一性,並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非常重視法律的強制作用,輕視甚至完全否定道德的感化作用,極力主張用嚴刑峻法的手段打擊貴族和加強對廣大人民的統治。他們是儒家的主要對立面。
戰國末期的荀況,雖然是儒家的另一主要代表,但有別於孔、孟。他既“隆禮”又“重法”,是在新的封建制基礎上,以儒為主,使儒、法合流和以禮為主使禮、法統一的先行者。秦、漢以後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受他的影響很大。
秦、漢到鴉片戰爭時期
從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緩慢發展到逐步衰落的時期。統一全中國的秦王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由於法家主張“法治”,一貫重視法制建設,所以到秦始皇時,各個方面“皆有法式”,為建立和鞏固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作出了貢獻。這從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記載的秦律進一步得到證實。但重視法制並不等於重視法學。秦王朝在政治、文化上都實行極端的專制主義,“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只許“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嚴禁私學。這不但窒息了其他諸家思想,也阻撓了包括法家本身在內的法律思想的發展。秦王朝還將法家主張的嚴刑峻法推向極端,倚仗暴力橫徵暴斂、濫用民力,終於激起了農民大起義,很快被西漢王朝所取代。
西漢初期吸取秦亡的教訓,在經濟極為凋敝的情況下,找到了戰國中期以來開始流行的道、法結合的黃老思想(黃老學派)作為指導,崇尚清靜無為,主張約法省刑、休養生息。這實際上是想用道家之所長,彌補法家之所短。黃老思想雖然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因過於消極,不利於封建國家的聚斂和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的鞏固。隨著封建經濟、政治勢力的加強,為了解決封建制度本身日益暴露出的各種矛盾,謀求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漢武帝(前141~前87在位)接受董仲舒等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奉儒家思想為正統。但這時儒家已不同於先秦儒家。它是以儒為主、儒法合流的產物,並吸收了先秦道家、陰陽五行家以及殷周以來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董仲舒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將封建意識形態概括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用天命神權、“天人合一”和陰陽五行說等炮製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把父權、夫權、特別是君權神化,並認為“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將“三綱”和“德主刑輔”絕對化為永恆不變的真理,終於形成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封建正統法律思想要求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禮教作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則。從此以後,維護“三綱”的倫理道德規範進一步紛紛入律。歷代封建法典,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唐律,即被概括為“一準乎禮”。直至清末封建王朝行將滅亡的時候,清朝統治者仍然宣稱“三綱五常”“實為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法之大本”。另一方面,從儒家傳統出發,“德主刑輔”或“明德慎罰”則被奉為統治人民的主要方針,但實際上,封建統治者從來都是德、刑並用,並根據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有所側重或交替使用。
這個時期,在牢固的封建自然經濟基礎上和持久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法律思想出現了以下兩方面的情況:
①由於對法律、特別是對法理的探討,不能超越綱常名教的雷池一步,所以造成春秋戰國時期欣欣向榮的法理學得不到發展,甚至一蹶不振。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只有歷代“無視君臣上下”的起義農民對“三綱”進行過衝擊,並提出過“均貧富、等貴賤”等思想;明、清之際適應資本主義萌芽的需要,由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包含一定民主色彩的思想。他們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以“工商皆本”取代“重農抑商”,反映了城市工商市民的某些要求。此外,還有漢、唐以來一些樸素唯物主義者如桓譚、王充(公元27~約97)、柳宗元等,對“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及其派生物讖緯迷信和司法時令說等進行了譴責。這個時期的法律思想不但沒有先秦那樣的百家爭鳴,也沒有儒、法兩家壁壘森嚴的禮、法對立。這當然不是說,在封建主內部已無儒、法或禮、法的矛盾,但主要是在儒、法合流和禮、法統一的前提下,因側重點不同所產生的分歧。這種分歧不但表現在重禮輕法或重法輕禮、重德輕刑或重刑輕德、重“人治”輕“法治”或重“法治”輕“人治”等基本傾向上,更大量地表現在肉刑的廢、復,親屬應否相容隱,復仇、赦罪,刑訊、株連、以贓論罪是否恰當和子孫能否別籍異財、同姓能否通婚等刑事、民事具體問題以及對待八議和同罪異罰等原則的不同態度上。這些問題的爭論對於法律思想、特別是刑法思想的深化也曾起過重大作用,並提出不少具有進步意義的看法,如主張廢除肉刑、禁止刑訊、同罪同罰,反對八議、復仇、親親相隱、族株連坐等等。但對立雙方的不同意見,往往均以儒家的“德治”、仁政和法家的嚴明賞罰、法不阿貴為依據,沒有也不可能越出儒法結合的封建正統思想範圍,在法理學上沒有取得重大突破。
②引經斷獄、引經注律盛極一時。隨著儒家思想占居統治地位和“三綱”成為立法的主要原則,以闡述這類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儒家經典遂身價百倍,或口授身傳,或破壁而出,以至經學大興,並逐步深入到立法、司法領域,在這些領域裡都要求“應經合義”,使儒家的經義既是立法的指導,又是審判的準繩。從西漢中期的董仲舒等開始,就不斷以“春秋決獄”。《春秋》經義不但可以補法律之不足,其效力甚至往往高於法律。董仲舒等在決獄中還提倡“論心定罪”的動機論,後來又發展為“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為罪刑擅斷大開方便之門,並使法律從屬於經義。引經斷獄之風延續了六、七百年,直到隋、唐因封建法制已臻完備才逐漸息滅。另一方面,引經講律、引經注律的律學,作為經學的一個分支,也乘運而興,一花獨放。早自西漢,在引經斷獄的同時,就出現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的現象。東漢的叔孫宣、郭令卿、馬融(公元79~166)、鄭玄(127~200)等曾注漢律,各為章句,十有餘家,共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晉代杜預、張斐等又注晉律。東晉以後,私家注律之風已衰。唐初集律學大成的《唐律疏議》以及《宋刑統》、《明律集解附例》、《大清律集解附例》等均出自官方。明代丘濬的《大學衍義補》、清代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分別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進行了總結和比較,有所創發,是研究古代法學或律學的重要著作。總之,無論引經斷獄或引經注律,其作用都是使儒家經義法律化。
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下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革命也逐步由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變化必然帶來法律思想的變化。
在“五四”運動以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適應民族資本主義微弱發展的需要,不斷向西方尋求真理,同時也引進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並逐步結合中國情況以之作為救亡圖存的武器。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1792~1841)、包世臣(1775~1855)、魏源(1794~1857)、林則徐(1785~1850)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改革派,首先提出了“變法圖強”的口號,主張效法西方。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除以武裝起義的行動猛烈衝擊封建法制和禮教的羅網外,並破天荒地提出了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及男女平等和“天下婚姻不論財”等民主思想。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領導人洪仁玕,還撰寫了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政新編》,主張允許私人開廠採礦、僱傭勞動力、保障私人投資以及與外國平等往來自由通商,反映了當時的時代信息。但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始終沒有跳出封建皇權思想的窠臼。嗣後,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1865~1898)、嚴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更熱衷於向西方學習,並以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為主要武器,兼取黃宗羲等的啟蒙思想,打著“孔子改制”的招牌,主張“變法維新”,要求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以實行“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領袖、以黃興(1874~1916)、章太炎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在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美國總統林肯(1809~1865)“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影響下,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法治”和中國原有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民為邦本”的重民思想揉合起來,提出了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內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主張實行“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法治”。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也分化出以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1837~1909)、劉坤一(1830~1901)等為代表的洋務派。他們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別於固步自封的頑固派,實際上已為引進某些西法、西學打開旁門。義和團運動爆發和八國聯軍入侵以後,以慈禧(1835~1908)為首的頑固派迫於形勢,為了抵製革命和乞求帝國主義恩許撤銷領事裁判權以平民憤,也接過戊戌變法時改良派的口號,不斷下詔“變法”和“預備立憲”,並於1902年以“兼取中西”為方針著手修訂法律。在對中外法律和法學都有所研究的法學家沈家本的主持下,先後修訂了《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新法新律,但遭到以張之洞、勞乃宣(1843~1921)為首的禮教派的猛烈攻擊,指斥新法、新律敗壞禮教,違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和男女之別與尊卑長幼之序,實際上是不許觸動封建禮教。這次禮、法之爭不同往昔的中國封建階級內部之爭,實質上是中國封建舊律要不要資產階級化的問題。在當時封建頑固派的控制和禮教派的鼓譟下,結果不能不以沈家本的退讓而告終。但通過修律,長期形成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封建法律思想終因西方資本主義學說的滲入而被突破。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後,革命果實又被北洋軍閥篡奪。“五四”運動前後,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列主義法學也傳入中國,成為批判各種舊法觀點的銳利武器,並指導了後來革命根據地的立法、司法實踐。而繼承北洋政府衣缽的國民黨政府,口頭上雖說“本黨遵奉總理(孫中山)遺教,負民國建國之重任”,表示要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要以“三民主義為法學最高原理”,創設“三民主義法學”,重建和復興中華法系。但他們只是吸取孫中山思想中一些可以為他們所用的東西,卻完全背棄其革命性、民主性精華,特別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們的一些官方學者認為,新的中華法系應以“保存中國固有之道德為主要”,要“奠基於”禮治,甚至提出要注意“如何再儘量利用家長制而謀其效”,基本上仍是清末禮教派的口吻。在這一時期中,由於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整個法律思想領域不但存在著帶有濃厚法西斯法律思想色彩和受美國R.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派影響的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法學,也存在著與之對立並日益滋長的馬列主義法學和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法學。在當時形勢下,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和官方法學雖然外表上不可能原封不動,而不資產階級化,但實際起作用的主要是維護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及其思想。
中國法律思想的歷史特點 中國的法律思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其不同的特點,但從整體看,又有其不同於世界某些國家或地區的帶全局性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作為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長期占居統治地位,後來在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仍然起著很大作用並滲透到資產階級法律思想領域中去。儒家維護以家長為首的宗法制和以君主為首的等級制。在儒家思想統治下,歷代立法和司法活動長期受以“三綱”為核心的禮教的指導。儒家倡導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在其“德治”、“仁政”中,包含著輕徭薄賦、恤刑慎殺等以適當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的內容,既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又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具有合理因素,對後世立法曾起過良好影響。但儒家的德主刑輔,只是在人民的鬥爭取得一定成果的前提下,才能為統治者所採納,接踵而來的往往是橫徵暴斂和嚴刑峻法。儒家又重義輕利,孔丘所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目的是防止剝削者內部互相爭奪,特別是防止勞動人民為捍衛自己的勞動所得或奪回自己勞動果實而反對既得利益的剝削者。封建社會後期作為儒家正統的宋明理學,吸取釋、道思想,鼓吹“存天理、滅人慾”,把“三綱”說成“天理”,把人民爭取生存基本權利的鬥爭和統治者內部違反“三綱”的思想言行說成“人慾”,這就更嚴重地壓抑了人們的權利觀念,阻礙著法律思想的發展。不但如此,重義輕利思想根源於重農抑商的傳統,旨在維護封建自然經濟而不利於商品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私法”的發展。特別是到封建社會後期,更嚴重地阻撓了以商品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因素和法權觀念的滋長。
以上幾方面的內容在儒家正統法律思想中結成以皇權為中心的有機整體,指導和支配中國封建立法長達數千年。這在世界所有法系中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於中國古代(包括中世紀)社會始終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商品生產和交換都不發達,又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嚴重束縛,所以當時根本不可能象恩格斯所說的形成“一個職業法學者階層”。
基於上述情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與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相適應,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律思想也從未占居過統治地位。這是中國法律思想的另一重要歷史特點。
中國的法律思想雖然存在著以上特點,但在人民民眾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推動下,它依然是順應人類社會的發展總趨勢而前進的。即使是歷代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其演變也是符合這一規律的。中國古代奴隸社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奴隸起義、國人(平民)暴動和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崛起,突破了奴隸社會神權和宗法思想的堤防,導致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禮、法之爭。秦、漢以後,封建經濟的發展和歷代農民大起義,促進了封建法制的某些改進和法律思想上某些進步觀點的提出。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不但推翻了持續數千年的帝制,衝決了綱常名教的羅網,推動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的發展,而且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傳播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