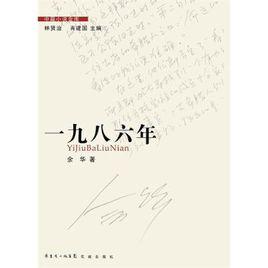簡介
《一九八六年》是余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部小說,寫的是一個瘋子的故事。
內容
文革期間,中國某個小鎮上的一個歷史教師在被紅衛兵帶去寫交代材料後消失的無影無蹤,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兒在家裡無助的等待。若干年後,妻子改嫁他人。多年之後的初春一個瘋子來到了這座已經開始平靜,甚至有點安逸的小鎮,這個瘋子就是當初的歷史教師。瘋子回到了故鄉,可是已經沒有人記得他是誰了,包括他的妻女,人們將他忘得乾乾淨淨就像忘記一個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一樣忘記他。因而當他再次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時,人們只把他當作一個瘋子,而不是一個歷史老師。
特點
 余華
余華余華
《一九八六年》小說的主人公在一位醉心於中國古代刑罰研究的中學教師,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而妻離子散。而小說的主場景發生在文革後一切歸於平靜後,主人公以瘋子的姿態重返故鄉之後。
在小說的開始,作者即以主人公在一張紙上的記錄引出了中國古代的刑罰:
“先秦:炮烙、剖腹、斬、焚……
戰國:抽脅、車裂、腰斬……
遼初:活埋、炮擲、懸崖……
金:擊腦、棒殺、剝皮……
車裂:將人頭和四肢分別拴在五輛車上,以五馬駕車,同時分馳,撕裂軀體。
凌遲:執刑時零刀碎割。”
隨著文本的進行,主人公以臆想和自虐的形式對他人與自己進行了以上的刑罰。而強調選擇了中國古代刑罰的方式的含義值得深思。
正如西方人克羅德所言,“中國什麼都落後,但刑罰卻是最先進的,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特殊的天才。讓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只是中國的藝術,是中國政治的精髓。”的確,在中國的封建時期,形式上的社會秩序是以仁義的名義維持的,但是統治的實質卻是殘酷無比,刑罰應當是作為維繫社會的工具作為政治的末端存在,但卻異化作人性之惡的象徵。
但對於解放後的中國而言,封建時期的酷刑在現實中應當已經被消滅了。但在小說中,作者以瘋子的視角,將古代的酷刑複製重現於讀者眼前。這正是意味著,嚴酷的統治壓榨只是在現實的層面里名義的被消滅,而存在與人們思想深處的酷刑從來都沒有消失過。文革即是最好的例證。對於經歷了文革的人來說,文革就如一場人性之惡大爆發的噩夢,每個人都對每個人進行精神上的酷刑。而文革之後呢,雖然混亂的現實又被結束了,但存在與人性中的或者傳統中的“惡”——傳統中的精神層面的“酷刑”從來沒消失過,這一意圖就被作者以一個瘋子的行為加以彰顯。
刑罰除了刑術的要素之外,施刑者、受刑者、刑場與觀眾的要素也是同等重要的。其實,除了文本表面上瘋子臆想中與自虐的施刑外,小說中同時存在著數個不同施刑者、受刑者、觀眾的刑場。
臆想的刑罰可以看作是主人公瘋子對於對於社會的復仇的情節的映射。值得突出的是瘋子的自虐行為,顯然,施刑者與受刑者都是瘋子自身。而瘋子在這裡可以做為人類本身的一個象徵。人類可以說是所有動物中對同類最為殘酷的一種了,無端的仇恨,無端的暴力,在瘋子的自虐中的得到了體現。受刑的痛苦與施刑的快意,在瘋子這一個體中得到集中的體現,無論是劓、斬、宮還是凌遲,作者近乎冷酷的強調這瘋子快意的表情、動作與悽厲的呻吟、慘叫。這樣的鮮明對比,是對人性之惡最好揭示。
還有不能忽略的是對主人公妻子、女兒的精神上的施刑,瘋子的歸來破壞了她們本來已經顯得寧靜幸福的生活。但真正嚴重的刑罰是對她們精神上道德的拷問,妻子失去理智而女兒也近乎奔潰的邊緣。對於妻子的表現,作者是以女兒為敘述主體來進行描述,妻子對於腳步聲的恐懼即是記憶的重現——從前的生活的記憶與現在生活的衝突,也是對於前夫痛苦不知所措。人倫與愛情,本來應該是生命中美好的一面,但卻在人性之惡前支離破碎。而作為敘述主題的女兒,雖然痛苦恐懼卻自始自終不知道瘋子即是自己的親身父親,對於重視人倫的中國傳統而言,這又是莫大的諷刺。
另外,作為瘋子自虐刑罰的觀眾,他們又作為行刑者向不幸的一家人——主人公、妻子、現在的丈夫、女兒,進行施刑。關於這一點可以在本文的第三部分進行更多的論述。
死亡審美的轉變
 作品
作品在先鋒派文學之前,死亡的審美早以有之,但是形式卻截然不同。以往的作品中,對死亡的審美不在於死亡本身,而在於死亡背後的意義,說是死亡,不如說是犧牲。作品
歷史演義小說中,英雄人物走向人生的末路,這樣的死亡的審美是建立在仁義理念之上的。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小說中人物的死亡,是對仁和義的實現。死亡的美,以這種抽象的形式得以實現。到了解放後,當代小說中很大一部分的死亡的審美也隨之演變為為革命犧牲貢獻自己的生命的形式,這種為人民犧牲的犧牲其實也是可以推溯到傳統的仁義觀念。
同樣,這樣的犧牲的死亡審美,所相對應的對死亡場面的描寫也是戲劇化的、藝術化的甚至是公式化的。作者不會著眼於死亡的細節,而是對亡者的精神和未亡者的情緒大加渲染以完成對死亡的審美。
但自先鋒派文學開始,作者對死亡的審美轉向到死亡本身。描寫的內容和形式也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以《一九八六年》為例,從文本揣摩作者行文時的心態,我們發現,無論是主人公的自虐還是臆想中的行刑情景,余華都是以一種旁觀者的身份進行理性而客觀的描寫。在這理性之上,我們能很明顯的體會到作者行文的的快意。作者可以說是沉醉在死亡的現實的美感上,在《一九八六年》中瘋子的臆想里,我們最能體會到這一點。
先鋒派的這一審美轉變,在莫言的《檀香刑》中也可見一般,莫言從行刑者趙甲的角度出發,將行刑的場面比做是一場由行刑者、受刑者、觀眾組成的一台大戲,並進行細緻華麗的描寫。先鋒派作家對於暴力的迷戀、對死亡的美感是共通的。
畢竟經過了文革的肆虐與終結——幾乎一切價值的觀念都被消解,而中國又在改革開放後急速完成著西方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歷程。失去思想的根的當時的人們迷茫而無所憑依,無法尋找到自我。大約只有通過對死亡的美的膜拜,這一看似荒誕審美,才能體會的生命的真實、自我的真實,這或許是先鋒派作家們想要在自己的小說中想表現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