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古今家訓之祖——中國人的家教聖經
·名門家訓餘音繞樑,智慧解讀警醒當下。
·《顏氏家訓新解》縱不能讓你成為曠世奇才,但卻能讓你為人處世更為熨貼完滿
首屆茅盾文學獎得主李國文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蔣子龍
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林非
百家講壇當紅主講人紀連海
聯袂推薦
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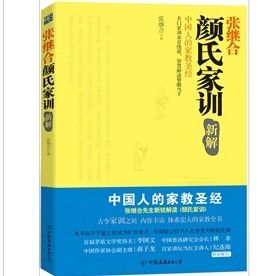 顏氏家訓新解
顏氏家訓新解著名學者張繼合從現世意義出發,對《顏氏家訓》做了深入淺出的解析,但並不局限於對文本的逐字解讀,而是從求學,就業,婚姻,家庭,為人處世等各個方面入手,探討《顏氏家訓》對現代教育所產生的意義,給當代教育以啟迪與警醒。書中特別提到東西方教育理念的交融與碰撞,提到當我們向西方靠攏提倡素質教育的今天,西方很多國家卻開始立法,允許對學生進行適當體罰……
媒體評論
繼合先生機敏、捷智、穎悟與樂觀,他比同齡人有更多的歷練、精明、通脫及豁達;他始終孜孜不倦地學習、寫作、追求和探索,曾留給讀者不少的啟迪。在文學道路上,只有堅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方是正道。
——李國文
《顏氏家訓新解》這部嶄新的力作,視角獨特、內容新穎、筆墨優雅、好看耐讀,具備很強的生命力和廣泛的影響力。繼合先生的作品,顯示出學養深厚、貫通文史和雅俗共賞的文化特徵。
——林非
繼合先生最新出版了這部《顏氏家訓新解》,採用豁達的胸懷、美妙的文字、睿智的文化和奇妙的思路,來引領讀者。篇篇美妙的文章,迴蕩在古典與現代時空,似乎提醒人們,如何脫離世俗而平庸的觀念,怎樣踏入優美且豐盈的人生。
——蔣子龍
智慧的人生,庭院裡煉成。
經典的活法,在兄弟書中。
——紀連海
目錄
一 《顏氏家訓》:締造一段傳奇
范文瀾對顏之推和《顏氏家訓》極為推崇,他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顏之推)是當時南北兩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學者,經歷南北兩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當時,所有大小知識,他幾乎都鑽研過,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顏氏家訓》20篇,就是這些見解的記錄。《顏氏家訓》的佳處,在於立論平實。平而不流於凡庸,實而多異於世俗。在南方浮華、北方粗野的氣氛中,《顏氏家訓》保持平實的作風,自成一家言。”
二 求學——掌握與世界對抗的技能
高爾基說:“愛孩子,母雞都會。”言外之意,“養孩子”屬於初級階段,“育後人”才是真功夫、高檔次。《說文解字》講得很明白:育,就是等孩子吃飽喝足了,再引導他們學好、進步。套用高爾基先生那句話:養孩子,母雞還湊合;育後代,卻永遠都學不會。這也是困擾人類的一大難題——教育。萬事開頭兒難,天下父母都想知道:教育,該何時插手·啟蒙,究竟有沒有一個恰倒好處的“黃金期”?
三 就業——你憑什麼生存
職業,是生存工具,跟肚子對口兒;事業,屬人生目標,和心靈有關。職業,更外在,更市儈,它像衣服一樣,遮羞、禦寒,還能隨著季節交替,換了一件又一件;事業,更貼心,更虔誠,猶如純潔的初戀,執著、狂熱,甚至叫人赴湯蹈火、樂此不疲。
四 婚姻——誰會陪你過一生
男女不平等,自古而然,中外一理。即便歐美怎樣吹噓自己文明,也普遍是男尊女卑。好在顏之推先生承認,夫妻之間可以“互動”,這與“人格重塑”是一個意思。從初婚,到偕老,日子得一天一天過,怎樣才能夫妻和順,走完這幾十年呢?
五 家庭——經營好你的避風港
《顏氏家訓》這部書的寫作意圖,就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門內”屬於歸宿,“門外”則是常說的滾滾紅塵、花花世界。顏之推先生認為,處理家庭事務,必須拿捏“內外各異、親疏有別”的分寸。歸結起來一句話:對內,無條件;對外,有保留。
六 撫育——生命的延續
《顏氏家訓·教子》一語中的,開頭兒便講:“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智知也。”智力水平超群的人,用不著費勁兒,將來自然可以成材。如果素質挺差,再手把手地教也無濟於事。教育只對素質中等者,大有可為。
七 處世——以原則和堅韌武裝自己
木有花梨紫檀,人分三六九等。造物主就這么霸道,還沒走過場,便定了輸贏。世間多少千載難逢的好機遇,似乎只便宜了那些既有素質、又有準備的人。跌倒一百次,還能爬起一百零一次,這種“擰人”往往糟踐不了;餓著肚子也休息,這類貨色絕對難成大器。社會法則從來就是“強者為王”,有些注定成為人中龍鳳,有些只配一輩子當牛做馬。
八 終老——當你離開的那一天
割據、戰爭,裹挾著生生死死;醇酒、美女,演繹出紙醉金迷。頹廢、奢靡的時代基調,並沒有使顏之推和光同塵,《顏氏家訓》通體瀰漫著明媚而清新的水墨香。他始終遠離燈紅酒綠和聲色犬馬,幾乎從未提過“殉道”或者自殺;他將生活當成最有價值的事業。
精彩書摘
孔子很不喜歡談論死亡,別人追問得緊,他就故意轉移話題,說:“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話,便將問題“掛”了起來。如果說,西方哲學喜歡研究“死”,那么,中國文化最上心的,反倒是怎樣好好地活著。《顏氏家訓》同樣在傳授“生存的藝術”。
古代中國,規矩多。哪兒都有方寸,犄角旮旯里布滿了高低貴賤、上下賢愚、尊卑長幼……這個鐵打的秩序統轄社會,就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樣天經地義。除非想造反了,否則,很少有人扮演啟蒙思想家,公開叫嚷什麼“平等”和“自由”。規矩聳峙,就是為了“治人”。且不說在外邊兒混怎么樣,即便在家裡,守在父母跟前,也不能松松垮垮、嘻嘻哈哈;必須像伺候頂頭上司一般,察言觀色,畢恭畢敬,甚至連個響屁都不敢放。
無論高門望族,還是市井人家,他們大多把教書育人這些事兒,推給私塾先生。人們普遍相信:自家孩子,自己不能教。即便哪個大人物,多少喝過幾口墨水,也不敢越俎代庖,親自指點子女“吃小灶”。親職教育,成為古代一片文化盲區。父母與孩子,必須保持一段足夠陌生的距離。“至聖先師”孔丘,也是這種做派。《論語·季氏》記載了他教導兒子學習的經典場面:孔子悠閒地站在廊檐下,恰巧,兒子孔鯉小步溜丟地從院子裡跑過去。孔子特意叫住他,父子倆一問一答,短短几句就完成了學業指導。孔子提出兩種看法:其一,“不學詩,無以言”;其二,“不學禮,無以立”——這就是著名的“鯉對”,也叫“庭對”。後來,專指老人教訓兒子。
孔子教孔鯉學詩、學禮,無非一個籠統的“戰略”,至於他跟誰學、怎么學,屬於雞毛蒜皮的“戰術”,就沒父親什麼事兒了,你只能自個兒琢磨去!古代書生,多如牛毛,孔鯉已經相當幸運了。他修下一位學識淵博、見識廣闊的父親,隔三差五地“庭訓”一回,便可讓他受用一輩子。絕大部分孩子就沒這種造化,他們只是家裡俯首帖耳的小玩意兒,長輩偶爾督促他們讀書,也往往是繃著臉,說幾句慷慨悲壯的大道理。其實,這種做法,隔靴搔癢。不但家長彆扭,孩子也挺膩味。直到《顏氏家訓》流傳於世,才打破這種尷尬的局面,8世紀的中國,藉此誕生了新的話語方式和教育思維。最起碼,《顏氏家訓》為8世紀之後的中國,驅散了“三團疑雲”。
先說“第一團疑雲”:為什麼要把教育(尤其是親職教育)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南北朝,天下大亂。別說找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人們能不能保住腦袋,都成了大問題。草原民族是騎馬、射箭、打群架的高手,他們輪番坐莊,闖進中原的都城裡,號令天下。“胡風”一吹,立刻人心大變。北中國到處都在舞刀弄槍,很少有人攻讀詩書了;街頭巷尾,迴蕩著粗獷的斗酒聲、放浪的琵琶聲,誰還有心玩琴瑟雅樂呢?連中原的語言都不吃香了,為謀取一官半職,多少漢人趕時髦,強迫孩子嘰里咕嚕地學“胡語”。還有些人,成天打扮得衣冠楚楚,油頭粉面,聚在一塊兒沒別的,除了“清談雅論”,就是“剖玄析微”,似乎很有來頭兒,淵博得很;實際上,這些場面人物,大多屬於“樣子貨”、“半瓶醋”,根本就派不上什麼用場……那個世道,滿世界烏煙瘴氣,真正的讀書人還能活嗎?莫非說,華夏數千年的文脈,就這么斷了?
古代有兩件非常好玩的“法器”: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鐸,就是一隻大鈴鐺。國家要打仗了,金屬鈴鐺便“哐哐”亂響,好像鬼子進村,老村長敲鐘一樣。上邊要宣傳什麼事兒,木頭鈴鐺又“嘩嘩”直搖。這種聲音不太刺耳,一般是企業文化教育。可惜,天下龜裂,人心惶惶,上街搖晃木鈴鐺,誰搭理你呀?儘管如此,《顏氏家訓》還是逆流而動,大張旗鼓地宣揚教育。作為局中人,顏之推當然明白“學之興廢,隨世輕重”。南朝煙雨,籠罩著“四百八十寺”,卻看不到一座“稷下學宮”,聽不見半日書聲琅琅。現實就這么殘酷。顏之推只能將“勸學興文”的念頭,關在自家庭院裡。
還是那句話:“父子不親授。”親生骨肉,忌諱親自調教。可是,“光陰可惜,譬諸流水”,為了百年樹人,顏之推已經顧不了許多了,他情願和子孫隔一層薄薄的宣紙,通過筆墨當“家教”。老頭兒很著急,他說:時間不等人,如果再吊兒郎當,恐怕就來不及了。瞧瞧孔子語錄吧,白紙黑字告訴你:“學也,祿在其中矣!”這種大實話,也只能跟親人說——讀書,才是升官發財的階梯!
再說“第二團疑雲”:父母,應該如何同孩子交流?師長,應該怎樣跟學生對話?
古希臘的文化宗師——蘇格拉底,曾在雅典街頭招徠弟子,敞開傳播真理和智慧。他穿得非常隨便,甚至有些邋遢。講到興奮處便瞳孔放光,手舞足蹈;說岔了,就唾沫星子橫飛,跟弟子們辯論半天。古代中國卻遵循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師道”。在教育線上,孔子是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名氣最大,地位最高。他晚年主持“洙泗書院”時,啥派頭兒?“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在三千弟子眼裡,孔老師就是活模特兒,一顰一笑、一言一行,都得跟他老人家學。
如今,人們很難感受古代“天、地、君、親、師”的分量。這五種角色就是天,讓你仰望一輩子;就是山,讓人在腳下匍匐千百年。家規整肅,法度森嚴,誰敢在這幫人眼前奓刺兒?只有乖乖地聽話,才是好孩子!現代教育講究,家長跟孩子交朋友。顯然,這種西方觀念和古代中國格格不入,古代任何一部詞典里,都查不到“平等”。父母對子女,老師對學生,永遠是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親,也無須摟脖子抱腰;近,更不能拍拍打打——這就是中國,這就是“禮”:“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先擺正自己的位置,再說事兒!顏之推也跳不出歷史的小圈子,恐怕打死他,也不可能和子孫平起平坐。老頭兒居中而坐,耳提面命。晚輩則環拜膝下,聆聽訓誡。這個場面,用不著懷疑對錯,更不允許辯論真偽。老人說話,你就乖乖地聽著、牢牢地記著,就像上傳下達,執行命令。當然,這是打個比方,《顏氏家訓》已經成書,根本不能雙向交流。顏之推的“范兒”,依然是居高臨下,我說,你聽。
即便如此,也非常難得了。顏之推並沒把自己打扮成呼風喚雨的救世主和完美無缺的老天爺,而是現身說法,公開袒露自己的不幸和不足。一千多年之後,法國哲學家盧梭撰寫《懺悔錄》,同樣拿自己當靶子,還不是為了表達赤誠,抓住讀者的心嗎?顏之推挖空心思寫成七卷文章,不為揚名,更無心謀利;僅僅是想管管自家的後代。“貽人千金,莫如授人一技”,難道關起門來跟孩子們說話,還能裝腔作勢、攙糠使水嗎?顏之推一個心眼兒留“私話房”,這種寶貴而赤誠的精神遺產,為中國人打開了一道穿越時空的智慧之門,也為後世名家,締造了一種經典文體。宋朝人陳振孫說:“古今家訓,以此為祖。”這個評價,夠高了吧。
最後,說“第三團疑雲”:什麼東西值得青年去死?哪些道理能幫後輩去活?
據《論語》記載:孔子很不喜歡談論死亡,別人追問得緊,他就故意轉移話題,說:“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話,便將問題“掛”了起來。如果說,西方哲學喜歡研究“死”,那么,中國文化最上心的,反倒是怎樣好好地活著。《顏氏家訓》同樣在傳授“生存的藝術”。
教人怎么活,不算新鮮;最新鮮的是規劃後人怎么死。別說一千多年前,就是現代人談論這種事兒,都非常困難——的確不好說。有關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