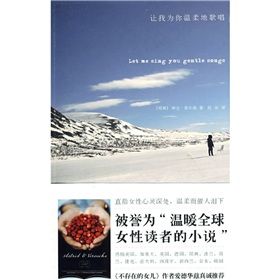內容簡介
來,坐在我身邊,我會告訴你,我所有的憂傷……寧靜的北歐,宛若世界的盡頭。兩個孤獨的女人,互相打開心扉,袒露埋藏在心中最大的秘密……三十歲的作家維羅妮卡來到這座偏遠的小鎮,試圖在被白雪覆蓋的小屋裡埋葬一段情感,並完成她的小說。在這裡,她結識了惟一的鄰居阿斯特里德-一個打算在悲傷與仇恨中了此殘生的老嫗。兩個女人的心靈從陌生到傾吐,時間交叉剪輯一般,呈現出她們的情感經歷與心理軌跡:一個想走出失去愛人的痛苦,一個想遺忘支離破碎的家庭所帶來的傷害。最終,她們在短暫卻溫暖綿長的友情中,重新找回了擁抱孤獨與黑暗的力量。作者簡介
琳達·奧爾森(LindaOlsson,1948-)出生於斯德哥爾摩,從斯德哥爾摩大學獲得法律學士學位後從事金融工作,直到1986年離開瑞典。她曾在肯亞、新加坡、英國和13本生活過,1990年起成為紐西蘭永久居民。1993午,她在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完成了英國和德國文學學位。2003年,她獲得了《星期日之星時報》(SundayStar—Times)短篇小說比賽大獎。她目前生活在奧克蘭,《讓我為你溫柔地歌唱》是她的長篇處女作。精彩書摘風雪一直伴隨著她前行,但當夜幕降臨時,風止了,雪也停了。
這是三月份的頭一天。她開車從斯德哥爾摩出發,在越來越濃的沙塵里駛入黑夜。這是一次緩慢的旅行,但它給予她時間去思考,或將思緒抹去。
在教堂旁邊,她捨棄了大路,轉入了往山坡上去的那條又窄又陡的路,最後拐進了一條泥巴路。這場雪下來之後還沒有車輛經過這裡,路上一堆堆圓形的積雪間依舊保留著那種柔和純粹的白。她慢慢地開著,眼睛逐漸適應了黑暗。她聽別人說過這裡只有兩座房子,現在她看到它們襯著天空的輪廓。沒有一處燈光,它們都處於黑暗中。
她經過那座大一點的房子繼續向前,離開所有道路,穿過雪地來到第二座房子的前院。她把車停在通向門廊的台階旁邊。一條小道早已經被清理出來恭候她的到來,但因為雪又下過了,現在它只是一道被雪覆蓋的凹痕。她從車裡出來,看見枯萎的草稈從雪裡扎出來,地上有一塊塊凍結的地方。她小心翼翼地往返於車和房子之間,清空後備箱和后座,儘可能不讓自己滑倒。她把一隻只行李包和箱子搬進屋,雪在她腳下嘎吱作響,這是空氣中唯一的聲音。她讓車頭燈亮著,燈光斜掃過她留在雪地里的腳印。
在這道照著她走動的燈柱後面,另一座房子像個無聲的幽靈在黑暗中隱現。空氣又乾又冷,呼吸一離開她的嘴唇就化成白霧融入夜氣。天空是無盡的黑暗,沒有星月。她感覺自己像墜人了一條通向絕對寂靜的隧道。
這個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樣子很陌生,而這座房子還不知道她是誰。在如此寂靜的黑暗中,她好像不存在了,她感覺輕得像空氣。
第二天早上,陽光勉強可以照亮天空。她打開窗,有點風,空氣中似乎還有點雪。她拉緊紅色睡袍裹住胸前,站著朝外眺望。她思考著自己的旅行,但並不讓意識順著道路回到起點,而是回憶起了許多次過去的旅行。在陌生的地方打開行囊,旅程在哪兒結束就在哪兒安家,不變的是她總和父親在一起。她知道這一次旅行不一樣了。她一生都是跟父親結伴而行的,跟父親手牽著手,奔赴一次新的海外任職。自從她母親離開後就一直是他們倆在一起。從某種角度說,即使再怎么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也不過是他們共同旅程中的又一站。但是,那個她十二月份在東京拜訪過的父親現在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跟她的生活不再是一回事了。他們不再是同行者了。這是一次單獨的旅行。一次飛翔,一次逃避。一個沒有目的的旅程。她感覺生命像光一樣不確定,停留在蒼白的無知覺里。
她關上窗,依舊站著朝外看,視線越過河流和村莊,深入幽藍的森林和群山。她面前的風光看上去很古舊:風雪修飾過的圓頂山脈,柔緩的河流,平靜的湖泊。這是一片只有通過辛勤勞作才能獲得一點點收穫的土地。
她環顧四周,前一天夜裡在陰影中的東西現在完全暴露在荒涼的晨光中。旁邊那座房子比原先感覺到的更大:寬敞的兩層木結構建築,可能曾經被刷成黃色,但現在已經褪成模糊的灰白色,跟天空和雪的顏色混雜在一起。窗戶是空空的黑方塊,依然沒有人居住的跡象。
壁爐前的一個筐子裡有木柴,小的乾的堆在上面,大塊的擱在下面,準備得很周到。她決定生個火,還把電爐打開來煮水泡咖啡。她雙手抱著杯子坐在桌邊,火慢慢開始噼啪作響。
她來的時候沒什麼日程安排,只帶了幾個裝著個人物品的包,一些書和CD。這個決定很突然,幾乎沒有時間去準備。事實上,與其說是一個決定,還不如說是一系列幾乎是下意識的迅速行動。她覺得自己沒有計畫,沒有思想;但在某種程度上,她的意識和身體都採取了行動並將她扔到了這一片寂靜中。
到了第二天,這座房子仍然跟她保持著距離。房子有新裝修過的痕跡:新的牆紙,新的浴室配件和瓷磚。廚房裡的新櫥櫃好看而實用,就是位置不太合適。這是一座中庸保守的房子,帶著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家具很簡單,廚房裡有一張桌子和六把椅子,客廳里有兩張小沙發和一張咖啡桌,樓上的臥室里有兩張床。木地板上交織地鋪著碎布地毯。窗戶上沒有掛窗簾,只有純白色的百葉窗。她也懶得去開通電話。不過她倒是帶著手機,她把它關了,扔在床頭櫃的抽屜里。
她像個寄居在孤兒院裡的孤兒。
她的生活慢慢找到了自身的基本節奏。一個禮拜後,她已經形成了早上的規律。她早早地起來,坐在餐桌旁,一邊喝咖啡一邊看著屋子慢慢地汲取晨光。這感覺就好像這座房子已經接受她了,好像她們已經開始生活在一起了。她的腳底漸漸熟悉了樓梯的木台階,她的鼻子漸漸習慣了牆壁的氣味,她也在一點一點加入自己的印跡,留下瑣細的痕跡。她移動過客廳里的沙發,這樣她就可以坐著眺望窗外。她還買了盆天竺葵放在廚房的窗台上。她把餐桌的一端開闢成一個類似工作區的地方:筆記本電腦開著,隨時準備記錄文字;她的記事本、詞典和筆整齊地擺放在一邊。她有時眼睛盯著螢幕,手指懸在鍵盤上,但寫不了幾句,就又把它們都刪除了。
每一天都從一場散步開始,不管天氣如何。幾乎看不見第二個人,除非她往下一直走到村莊。某個早晨,當她穿過前院時,一頭鹿正站著朝她看。它一動不動地待在那裡,用眼神鎖住她的眼神。然後,它就那么輕靈地轉身一躍,便悄無聲息地消失在穀倉後面。她看見雪地里有麋鹿和狐狸的痕跡。晚上依舊很冷,寒冬在黑暗中又索回了它在白天交付出去的一切。每個早上都從灰暗和冰凍開始。
對面的房子依舊黑暗寂靜。剛開始的那幾天,她不確定那裡是否有人居住。後來,有一天,她在鄉村小店的收銀台旁和一個女人交流了幾句,並介紹了自己:
“我是維羅妮卡?勃格曼。我租了山上瑪爾姆家的房子。”
“啊,那你就是阿斯特里德的新鄰居了,”女人回答她。她微笑著轉動眼睛。“阿斯特里德?麥特遜,鄉村女巫。她不喜歡人,也不跟人往來。恐怕不是個好鄰居。”她把找回的零錢遞給維羅妮卡,然後補充說:
“你會知道的,毫無疑問。”
兩個星期後,她第一次見到了她的這位鄰居。那個老女人看上去幾乎是不知廉恥地裸露著,她縮成一團的孤單身影裹在沉重的深色大衣和橡膠靴里。她正猶疑不定地躑躅在通往村莊的冰凍道路上。在此之前,她的房子一直都是她的保護者,黑暗的窗戶是它裡面秘密生活的忠誠守衛。
每天散步後,維羅妮卡端坐在電腦前,但她的目光卻從螢幕上游移到窗戶和遠處的風景。有一段時間,她覺得要寫什麼樣的書是絕對明確的,它在她頭腦中脈絡完全清晰,而打字的過程不過是在乾技術活,簡單而迅捷。她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從世界中撤退出來,然後她就會“看見”了。平靜。安詳。
但是螢幕上依舊是一片空白。
灰暗的天氣肆虐。時間似乎停止了。沒有下雪,也看不到一點陽光。鴉群呱呱地叫著,卻不見蹤影。除此之外,世界一片沉寂。
一天清晨,當她照例散步經過鄰居家的房子時,她發現廚房的窗戶開著。只開了一條縫隙,寬度剛夠讓裡面的人看見外面,從外面卻看不到裡面。經過那裡時,維羅妮卡揮了揮手。她想像那個老人就在那裡,在玻璃背後的黑暗中,但她無法確定。
她正在思考她的書,思考著不斷重新塑造和召集她所有的想法和計畫的那個過程。這部在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生命里開始的書,似乎一直是由別人來寫的。那些文字和現在這個她已經沒有關係了。在這裡,除了她帶來的那些煩惱以外,就再沒有別的分心事了,一切都如實呈現。是去尋找新鮮語句的時候了。
然後,終於有了春天的希望。維羅妮卡站在門廊處抬頭仰望,天空是無邊無際的藍色畫布,列隊飛行的侯鳥如同一行雋秀的黑色筆跡。天不知不覺就亮了,她縮短了早晨散步的時間。此刻,太陽正照耀在她臉上,她決定溜達到河邊去。她踱下山坡,穿過路面,繼續向前穿過一片森林。冷杉樹腳下的蔭蔽處依舊積著零星的雪,但河裡的冰已經碎了,大塊的浮冰在深色的水面上翻騰。春天的洪流尚未到來:山上的積雪還沒有開始融化。她仰著臉正對著太陽。回到家時,她在門前的台上坐了一會兒。石頭在屁股底下暖暖的。她把記事本從身旁的小背包里拿出來開始寫作。當她擱下筆的時候,她驚訝地發現暮色已悄然降臨,陽光正斜斜地穿過樹頂灑在路面上。她合上本子,抬起臉,朝著最後的陽光緩緩地吸了一口氣。
她意識到自己已經有很久沒有這樣好好地換換肺里的空氣了。
2最微小的旋轉,一絲漣漪……
阿斯特里德赤身裸體地站著朝窗外看。此時天色已晚。如果不是因為有雪光,她根本看不見什麼,只有田野對面的窗戶,如同一隻只剛從漫長睡眠中驚醒過來的黃色眼睛。
她自己的房子一如既往地處於黑暗中。黑暗而溫暖。她把它烤得暖暖的。它是她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結構已經根植於她的身體裡:即便沒有燈光,她也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在這個空間裡遊走。而且,黑暗有時還能讓動物們更靠近:麋鹿,貓頭鷹,甚至山貓。那些跟她一樣沉默寡言的觀察者們,它們有自己的空間,只會短暫地拜訪她。
她很少朝窗外看:那個風景早已失去了所有意義。
而現在她正站在窗邊,房子裡溫暖的黑暗籠罩著她,她密切注意著白色田野上的動靜。她的雙臂環抱在胸前,雙手罩在乳房上。它們沉甸甸的,觸起來很溫暖。她的身體前傾著,前額幾乎碰到了玻璃。在夜的靜寂中,她所能看見的一切就是一輛轎車的前車燈射出的明亮燈柱和一個女人在燈柱里走動的黑暗輪廓。前車門大大地敞開著,像黑夜裂開了一個黃色的方形缺口。她用舌頭觸摸牙齒,觸摸尖銳的邊緣和柔軟的牙床,吮吸唾液。但自始至終,她的眼睛沒有離開那座房子。
車頭燈熄滅了,前車門也關上了。又過了良久,她依然佇立在窗前,抱擁著自己,雙手撫摸著手臂上鬆弛的皮膚。她凝視著兩座房子之間的空地。
她早就料到會有人來,但她卻對自己的反應感到吃驚——她會站在這兒,在窗邊,看著窗外。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樣早早地起來,她的臥室就在廚房後面。她早就搬到樓下睡了,把以前曾經是小餐廳的地方變成了現在睡覺的地方。她沒有做什麼大的改動,只是把餐桌推到了靠窗的位置,於是內側的四把椅子就頂住了牆,騰出了一張單人床的空間。她把衣服留在了廚房外面的走廊里。
沒有百葉窗,只有兩塊褪了色的印花布窗簾垂掛在窗戶兩旁。她喜歡在黑暗中起床。她想怕春天的到來和夏季里那些無情的白夜。
她靜靜地躺著,注視著天花板上陰影的變幻,她的耳朵警覺著。黑暗中的聲音微弱而熟悉。她能聽見雪在適應慢慢上升的氣溫,風在醞釀,融化後又凍結起來的雪殼上,小生靈們在沙沙地疾走。夜色褪去了,白天到來了。她聽到了清晨的第一個聲音:一隻烏鴉呱呱的叫聲。這聲音仿佛騎著光線侵入了她的房間。她沒有動,但是眼睛睜著,耳朵敏銳。這些聲音和光線的觸鬚在屋子裡四處延伸,撫摸牆壁,撫摸天花板,撫摸地板,滑過她的毯子然後停下了。當第一道陽光毫無遮攔地掃過天花板上的陰影時,她注視著那一片亮光。無處可逃了,她遲早要投降的。它就在那兒了。她不得不讓步,並開始另一天。
接著,就在她把腳放到地板上的那一刻,一個新的聲音響了起來。她聽見一扇窗被推開了,接著是一扇門被推開了。冰凍雪地上的腳步聲,車門被打開又被關上。生活的聲音。
她已經形成早晨的生活習慣,不喜歡被打攪。這些日常規律不是為了做規矩,而是為了方便。它讓她有安全感。日子擁有統一的形式,不再受季節變化的影響。她活著就只是維持生命,只為了活下去,她的需求極小。她不對未來作任何打算。她的院落已經荒蕪,房子正在崩壞。她知道油漆在剝落,煙囪在破裂。一座日漸死去的房子裡住著一具日漸死去的肉體。
她只在必要的時候才步行到村子裡去,特別是像現在這樣的冬天。這裡的道路很少清掃,因為車輛不往這兒來。融化的積雪變成了暗藏險情的冰層。她不怕死,但希望能按自己的意願去死。摔斷股骨只會使她落入那些她最害怕的人手裡——那些一直等著她去求援的人。
她跟過去保持著距離。沒有未來,現在也是空洞的,她只是用身體在活著,沒有感情的存在。她等待著,不斷將記憶覆蓋。這種努力是持久而累人的事,吸走了她所有的精力。有時候難免失敗,她會被一陣感覺擒住,強烈得就好像是第一次經歷它。那些觸動她的東西總難以預期,她走得小心翼翼。她在寂靜的逆流中已經漂泊了很長時間,耐心地等待著最後的退潮。而眼前的這些只是表面上微微泛起的漣漪。
她起床開始新的一天。洗漱,煮咖啡。她的廚房一成不變,中間是老式的木頭爐灶,邊上有一個電爐子。爐灶里尚有餘燼,只需稍稍通一下風,新的木頭就會燃起來。
她手裡捧著咖啡杯,嘴裡吮吸著一塊方糖。當她把杯子放到餐桌上時,她心不在焉地拍打著發脆的防水桌布——她對它就像對她自己的皮膚一樣熟悉——撣掉並不存在的碎屑。她啜飲著冷卻下來的咖啡,一輪暗淡的太陽正在升起來。她的目光游離到了窗戶旁邊。
生活闖進來了。它一點一點地回到了她的房子裡。各種聲音。窗戶被打開,被關上。一扇敞開的窗戶里傳來微弱的音樂聲。一輛車開走了。她發現自己正在把這一切納入她的日常生活。日子一天天過去,觀察田野對面的房子成了她清晨的重要部分。她發現自己在那座房子有動靜之前就已經早早地坐在桌前,等待夜晚的陰影褪去。她的目光會停留在樓上的窗戶上,生活的第一個訊號是在那裡出現的。
她佇立在廚房的窗邊等待,直到一個纖細的身影從另一座房子裡出來,並經過這裡。她雙手交叉在胸口,環抱著自己,她注視著那個年輕女人經過、揮手。然後,某一個早晨,她發現自己在舉起手回應。這是一個遲疑緩慢的動作,當她的手垂落下來時,她盯著它看,似乎對它的動作感到很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