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庫0805 》
《讀庫0805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1-1
編輯推薦
《讀庫》是一本綜合性人文社科讀物,取“大型閱讀倉庫”之意,一般每兩月推出一期。叢書側重對當今社會影響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報導,回憶和挖掘文化熱點,對文藝類圖書、影視劇作品、流行音樂等進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為讀者提供珍貴罕見的文字標本和趣味盎然的閱讀快感,從內容、裝幀方面,被業界稱為當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雜誌書。本書是08年第5輯。
內容簡介
2006年,命運多舛的文化刊物《萬象》、《書城》在相繼經歷休刊復刊後,逐漸式微,更深入的走向精英知識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個人出資策劃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種”為出發點的文化刊叢躍入我們的視野。《讀庫》就像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話語園地,它的實驗性和新鮮感為讀者提供珍貴罕見的文字標本和趣味盎然的閱讀快感。內容而言,《讀庫》強調非學術,非虛構,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結合,探究人與事、細節與談資,不探討學術問題,不發表文學作品,所選書評影評等文體則強調趣味性,通過真實的表象給讀者帶來閱讀快感和思想深度。本書為《讀庫(0805)》。
目錄
歌者夜行
周雲蓬的詩和文
小九兒,楊麗坤
再訪河流
“把音唱準了我們再談感情”
沙灘北大二年
愛因斯坦不在家
科學松鼠會文章選
方寸之間
歐巴馬勝選演說(文言版)
敦煌(十集電視記錄片)
敦煌在路上
書摘插圖
歌者夜行
2008年9月29日下午兩點,周雲蓬來到“海淀公園”。下午四點他應該跟樂隊一起為明天“摩登天空音樂節”的演出調音。他沒吃午飯,想早點兒到,在公園旁邊隨便吃點兒,但公園附近沒有飯館,他說算了,坐到露天的白色塑膠椅上,等著樂手們的到來。明天,這裡將全是賣烤肉的、賣漢堡包的、賣意大利麵和咖喱飯的,可現在這裡只有一張張空椅子。三點半,他給小河打電話,小河住北五環外的北七家,還在捷運里。他又打給鼓手張蔚,張蔚也是“超級市場”樂隊的鼓手,這會兒或許已經在海淀公園裡面調音了?電話那頭,張蔚說,他不知道下午四點就要調音,剛出門。張蔚住在五十公里開外的通州。
放下電話,周雲蓬沒有說話。過一會兒,他說,我餓了。
那天下午他一直沒吃上東西。四點半輪到他調音,他背著頭天剛拿到的新琴,托人從美國買的一把一萬多塊錢的Tyler。明天要演出的舞台原本是海淀展覽館,並不適合做音樂演出,工作人員放了許多把小傘來減少迴響,但吉他聲聽起來還是太硬太脆,不時還有嘯叫聲。旁邊的場館裡是電音舞台,他必須一頭扎入自己的反饋音箱裡,才能假裝聽不見那邊的音樂。五點鐘,張蔚出現。三個人快速地合了幾首歌,嘯叫聲一直沒停。而樂隊另一成員,貝斯大鵬還在重慶,他要明天中午才能飛回北京。
六點五十,周雲蓬被熱心的朋友送回他在清華的住處。走在暮色里,他有些煩躁,昂貴的新吉他不好使、話筒有嘯叫、貝斯不在、調音亂七八糟,他還餓著肚子,這一切加起來讓他無精打采。“明天你提醒我,買點白酒裝在瓶子裡帶進去。”他說,“像這樣,不喝點兒酒,怎么演啊?”
9月30日下午四點,周雲蓬從海淀公園北門藝人入口處進場,不斷有人問他:你就是周雲蓬嗎?我可以跟你合個影嗎?他多半就停住腳,全身定格一下,沒有表情。後來他說,他不愛照相,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的相片是什麼樣,人對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情總是不太情願參與。還有人請他在節目單上籤名,他猶豫一下,拿起筆,歪歪扭扭地寫了一個“雲”字,大大的,像幅畫。
他的演出在七點鐘,六點四十上台調音。他背著用慣的舊琴,一把古典吉他,琴盒裡塞著一瓶酒。或許待會兒到台上,酒和音樂會像上螺絲一絲一絲越上越緊,最終緊緊把情緒和技巧咬合在一起,把他的情緒和台下觀眾情緒都咬合在一起。那酒是從超市買的十八塊錢的張裕VS金獎白蘭地,“很難喝”,下舞台後他說。那時他已經喝了三百五十毫升的三分之一。
五點,大鵬來了。六點二十,小河出現在後台。六點四十,張蔚從主舞台跑過來。人齊了。觀眾看到周雲蓬.開始鼓掌。這是今年裡他最大型的一次演出,他們熱切地看著他,熟悉地跟他一起唱,在歌曲間隙熟門熟路地喊他的歌名:“唱《九月》!”“唱《一江水》!”“唱《中國孩子》!”
他唱了首新歌,《一個人三次來北京》:“我想去動物園,卻走到了通縣,走得我兩腿發酸。啊,北京北京,你就是個動物園,入被關在籠子裡面。”觀眾開始輕笑。第二段,是“我”坐著汽車來,不小心開到立交橋上,“三天三夜在那橋上轉。啊,北京北京,你就是個連環計,進來容易出去難。”觀眾大笑,鼓掌。“第三次來北京,我從那夢中來,租房子不要錢,警察也很可愛,房東有兩個女兒一起愛上了我,搞得我心裡很亂。”轟然大笑,不僅為了這歌里的幽默,或許還為這裡頭感同身受的體會,這溫度相似的生活。掌聲里的興奮說明他正駕馭著近千人的情緒,漂浮在觀眾情緒之上,接近失重。
唱歌的人,嘴角也露出一絲笑意。但是還沒完,下面的歌詞又把溫度降下來:“啊,北京北京,你永遠不黑天,所有的人都無法再做夢。啊,北京北京,你的太陽永不落,所有的夢都被你戳穿。”歌詞是幽默調侃的,但和聲是高亢悲涼的。他的歌里經常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基調,幽默有一個悲涼的襯裡,或者,悲涼到極點,反而笑起來。餘燼的顏色不是黑而是暗紅,比黑暗更黑處不是黑,而是光。
曾經他狂熱喜歡舍斯托夫,以頭撞牆與狂野呼告的哲學;如今他最喜歡的作家是契訶夫:“他把歡樂的事情寫得那么辛酸,把心酸的事情寫得那么歡樂,連死亡也是憂傷而溫柔的。他把許多種複雜的情緒都調和在一起,我覺得好的東西的最高境界就是詩性。”
音樂停止,在歡呼和掌聲中他站起身,台上每個人都在走來走去收拾東西,只有他站在原地,抱著吉他,靜靜地等別人來帶自己下台。
第一章 陸地航行
“那時我對自己提出的口號:像一個正常人一樣。”
——周雲蓬
周雲蓬.1970年12月15日出生在遼寧瀋陽鐵西區,父母都是工人。幼年患上眼疾,“整個童年充滿了火車、醫院、酒精棉的味道”。失明的過程,對他來說“就像白天到晚上,是緩慢的,像一個巨大的陰影籠罩一生”。在經過四下求醫,包括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去過南方小鎮求治於江湖偏方之後,九歲時,他徹底失明。
鐵西區是瀋陽的大型工業區,始建於1934年,由當時占領此地的侵華日軍掌管主建。到了五十年代,蘇聯參與投資興建。進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工廠接二連三倒閉,下崗入口達七十多萬。
周雲蓬的音樂啟蒙來自收音機短波里的鄧麗君和劉文正。事隔多年,2006年5月8日,周雲蓬和圈中朋友做了一個小型演出紀念鄧麗君,文案出自周雲蓬之手:
鄧麗君,我們音樂的後娘,我們色情的大姐姐;如果你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北京.一定會成為若干地下樂隊的女主唱。北京的沙塵暴將使你的支氣管無比堅韌,北京強悍的搖滾音樂入絕不允許你至死未嫁抱恨終生。
我對老家的印象就是破破爛爛的。但音樂在生活中很普遍,人們對它甚至是狂熱的。有一年春晚,張明敏唱了首《我的中國心》,第二天小商店就有放了,他們是拿小錄音機對著電視錄下來的,歌聲里還夾著哇哩哇啦的噪音,那也牛。你要能有一盤盜版的張明敏的磁帶,那就更牛了。
我們住的工人區,小胡同里一家挨一家,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生個爐子嗆得要命,上廁所要走很遠,又特別髒。那時特別渴望有自己的小房子。艷粉街離我家特別近,就麗站地。那條街特別亂,在我們心目中是出流氓的地方。
我爸爸是校辦工廠的廠長,小時候經常有人到家裡聊車床、螺絲、庫房什麼的,一點美感都沒有。那種環境下,反而對音樂、對文學特別渴望。
那時有些從監獄刑滿釋放的年輕人,彈琴彈得比較好。好像每個胡同都有這樣的人,現在你根本看不到了。晚上,在工人區的胡同里,人們都光著膀子,端著大盆洗澡,兩三個小伙子,拿著吉他,在路燈下唱著羞澀的流氓歌曲,諸如“我是一顆藍寶石”。
我們那時流傳的好多磁帶,是從監獄裡流傳出來的,要留著就好了。最早的是“鐵門哪鐵窗哪”,還不是遲志強,他是後來翻唱的了。也不知道是拿什麼錄的,聽上去像小樣。大家奉為經典,像聽Nirvana一樣聽。那個時候,人們對於進監獄還是有一種浪漫情懷。進監獄一般都是因為打架,根本沒有貪污這詞,所以就是一些不會收斂的年輕人,人品上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是這種環境吧。這種耳濡目染,心裡有這個種子,以後再從文字轉行到音樂就非常順利了。
晚上聽收音機短波,有個節目叫澳洲之聲,九點到九點半是個點播節目,主要放劉文正、鄧麗君,一般都是:馬來西亞的劉小姐,點給印尼的某某某,為他點播一首:《何日君再來》。
那時你聽那種歌,簡直是天籟!電台信號本身不清楚,你就拿著收音機,變著方向聽。鄧麗君的聲音就從那裡面傳出來。那時剛開始發育,身邊又沒有任何愛情歌曲,你一聽到鄧麗君這種甜蜜的、異性的聲音,真的是……音樂的震撼力,那個時候是最強的。
她是我們這批七零年代出生的人的音樂啟蒙者,而且也是你對異性、對懵懂的愛情的最初想像。而且她那種歌,在那種環境裡還是挺協調的。你用的是小磚頭似的收音機,周圍都是破破爛爛的,她的歌也都是小鎮之類的情緒。你要是特白領,周圍都是富麗堂皇,聽那種歌倒挺怪的。
我上的是瀋陽盲校,旁邊就是瀋陽師範學校,師範學生有時會來給我們念書。我發現那些抱著吉他唱歌的同學,總有師範女生去找他們。我不甘心被冷遇,就開始唱歌。那時吉他還沒這么洋氣,被稱做六弦琴,而且彈琴的手法都是掃弦。吉他是二十多塊錢買的“百靈牌”的二手吉他,學的第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一個朋友手把手教會我的。
“我一直夢想著寫作,當一個大作家。”多年後,三十八歲的歌手周雲蓬這樣跟我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偶像是托爾斯泰、泰戈爾。他喜歡去書店,進去就用深沉的嗓音問:請問,有沒有《浮士德》?沒有?那,《戰爭與和平》呢?那時他讀書主要靠去圖書館借閱盲文書籍,而那裡只有老版本的唐詩宋詞稱得上是文學書,結果就是,在“新民謠”的陣營里,除了相似的在城市裡生活的小人物的感受,周雲蓬的音樂里多了一種元素。因為信息的獲得相對落後,因為盲人世界的限制,他反而遲緩地接上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那一條河,只有他會在人聲鼎沸的酒吧里,不疾不徐唱起“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這個氣息,你可以管它叫做是:中國的。
我小時候,有一段無書可看,盲文書里就只有唐詩宋詞,我看完,過一會兒,閒著無事拿起來又看一遍。後來看得幾乎都能背下來。
盲文書,圖書館裡都有。但它都是很老的書,比如《毛澤東選集》,還有一些按摩的書,文學類的極少,《紅樓夢》全是潔本,涉及談戀愛的都給你刪掉。我恨透那些刪書的人了。比如說,賈寶玉初試雲雨,整個就給你砍掉。標題也全改成:狡詐的襲人,黛玉之死。盲文書好多都是那樣的。但我的渴望會更強,想看更多的書。《飛鳥集》那時我幾乎都看爛了,提上一句我就能對下一句。
那時總覺得只要看很多書,就會寫得好,就玩命地找任何機會去看書。收音機里有文學節目就錄下來,我錄過史鐵生、張承志,還有古詩詞欣賞。錄下來,反覆地聽。那時對閱讀有病態的飢餓感。
……
書摘與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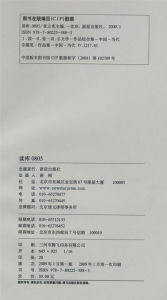 《讀庫0805 》
《讀庫08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