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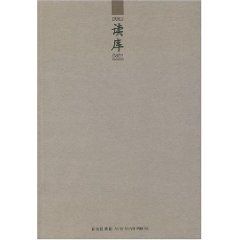 0
0平裝:317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802254534,7802254531
條形碼:9787802254534
商品尺寸:21.8x15.4x1.8cm
商品重量:422g
品牌:時代聯合
ASIN:B0017RM8Q4
內容簡介
《讀庫(2008年第1期)》收入《耿諄的家與國》一文作者兩度從北京趕赴河南襄城,卻把目光的焦點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響事件的背後。對這位老人來說,在“花岡暴動”、“花岡索賠案”這些耀眼事件之外,還有著太漫長的幽暗歲月,它們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靜靜地等待有人來涉足。《胡同今昔》記錄的是建築的消失,街道的消失,風景的消失,而《祥德路二弄》一文,記錄的則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消失。上海的弄堂生活,細緻入微而又栩栩如生地浮現在達奇珍老師的筆下,更為難得的是,她記錄的是那種生活被消滅的過程。編輯推薦
《讀庫(2008年第1期)》由新星出版社出版,2006年,命運多舛的文化刊物《萬象》、《書城》在相繼經歷休刊復刊後,逐漸式微,更深入的走向精英知識分子小圈子趣味,一本由個人出資策劃出版,以“有趣、有料、有種”為出發點的文化刊叢躍入我們的視野。《讀庫》就像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話語園地,它的實驗性和新鮮感為讀者提供珍貴罕見的文字標本和趣味盎然的閱讀快感。內容而言,《讀庫》強調非學術,非虛構,追求趣味和品味的結合,探究人與事、細節與談資,不探討學術問題,不發表文學作品,所選書評影評等文體則強調趣味性,通過真實的表象給讀者帶來閱讀快感和思想深度。作者簡介
張立憲,記者。合著有《沒有單位的記者:怎樣當自由撰稿人》。目錄
耿諄的家與國“天地之大德曰生”張謇和大生集團的命運
也是讀書種子,也是江湖伶倫
胡同今昔
用鉛筆和推土機賽跑
祥德路二弄
經度之戰
割裂的真實
子年記憶
文摘
耿諄的家與國九十三歲的耿諄已經很少走出家門,二樓的書房兼客廳,和那問不大的臥室,差不多成了他活動的全部天地。
每天早上,他七點鐘起床,此時二兒媳已經為他準備好了早飯,通常是菜饃和蛋茶——兩種在河南襄城最普通的吃食。吃罷早飯,他開始讀書看報寫毛筆字。由於視力下降,老人讀書看報都要藉助放大鏡,惟有寫字一項,他的精氣神卻一點不輸常人。寫字時,他一定要站起來,不僅毛筆在手裡握得很穩,而且落筆時筆鋒也是絲毫不抖。
“眼神不好,只能寫大字,而且寫得也比以前少多了,只有別人要字的時候才會寫。”耿諄一邊說一邊從抽屜里拿出一沓信,“有雲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湖北的。”說這話時老人看上去很高興。自從他的書法作品在《書法報》上刊登以後,求字的信就絡繹不絕。老人的字寫得好,又是名聞中外的老英雄,自然得到很多書法愛好者的青睞,而耿諄老人也是有求必應,寫好後,他會親自寫信封,裝好,然後叮囑自己的孫子耀波儘快給人家寄去。
在河南省襄城縣干休所一棟普通的二層住宅里,耿諄老人平靜地享受著自己的晚年生活。陽光會透過書桌前的窗戶照射在他的臉上,照亮他的白髮,照出他臉上的皺紋。
與耿諄的名字如影隨形的還有兩個字:花岡。
花岡町,如今已改名為大館市,位於日本東北地區大館盆地北端,是一個以銅礦山為中心形成的小鎮。從1944年8月初到1945年6月,耿諄曾經在這裡做過將近一年的勞工。不過讓耿諄和花岡真正結下不解之緣的,還是1945年在這裡發生的那場勞工暴動。
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為大隊長的耿諄率領七百多名中國勞工舉行暴動,他們打死了四名日本監工和一名漢奸,逃出所住的集中營中山寮。在日本軍警的鎮壓下,暴動最終失敗。暴動的前前後後,有四百一十八名中國人被虐待致死,而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戰後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BC級)判罪,這是唯一一例被國際法庭判為戰爭犯罪的迫害中國勞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日本本土發生的唯一一次中國勞工集體暴動。這一事件被稱為“花岡慘案”或者“花岡暴動”。
花岡暴動的領導者,這是歷史賦予耿諄的第一個身份。
再次把耿諄的名字和花岡聯繫到一起的重要事件,發生在花岡暴動五十年之後。1995年6月28日,耿諄與其他十一名花岡暴動倖存者一起,把當年迫害中國勞工的鹿島組(現日本鹿島建築株式會社)告上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這一事件後來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案”。經過長達五年多的訴訟,最後案件以鹿島組與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終。
“花岡索賠案”的首席原告,這是歷史賦予耿諄的第二個身份。
因為由日本律師團代表中國勞工與鹿島組達成的和解中根本沒有滿足原告提出的“謝罪、建紀念館和賠償”三項要求,耿諄拒絕在和解書上籤字,並拒絕領取鹿島組發放的和解金。
為尊嚴而不妥協的老人,這是歷史賦予耿諄的又一個身份。
把這三重身份疊加在一起,耿諄的形象漸漸地在我的眼前清晰起來——這是一個時常身處大是大非的漩渦中而意志堅定的老人,無論是當年的暴動,還是後來的索賠,抑或是最後的抗爭,耿諄始終處在整個歷史事件最中心的位置上。
網上搜尋是在我的困惑中結束的,在對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和紛繁複雜的歷史細節的尋找中,我發現原來已經有那么多人向這個老人投去過了關注的目光:中日兩國多家媒體都曾對耿諄進行過專訪和報導;在中國和日本,出版的關於耿諄的傳記、關於花岡暴動的長篇報告文學也都不止一本;在日本,有根據花岡暴動改編的舞台劇,在中國,有為花岡暴動專門拍攝、由大牌明星出演的電視劇和電影。
2007年3月,我第一次見到了耿諄老人。與之前在網上見過的照片相比,老人的表情中少了些堅毅和凜然,而多了份慈祥和親切。還有,他比照片上要老些,畢竟已經有兩年沒有怎么參加公眾活動了,而那些照片,最早也是他兩年前參加活動時留下的。
儘管已經在大量的文字資料中對耿諄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第一次見面,他身上還是有一種氣質強烈地吸引了我。眼前的老人,一舉手,一投足,都會讓我自然想起“舊式”或者“老派”中國人的樣子。這種氣質很難從我們的晚輩、同輩,甚至包括父輩的身上嗅到,而在耿諄老人的身上,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它們的存在。
被吸引之後是我的竊喜,因為我所看到的是網上那些關於耿諄的文字中沒有的。這意味著我的寫作空間出現了。面對重大歷史事件,人們更喜歡陶醉在宏大的敘事中,更喜歡把重點放在對起伏迭宕的事件本身的描寫上,而很少關注身處其中的個人。
那一次見面,我們從上午八點一直談到中午十二點,又從下午三點多談到了將近七點。前前後後持續了六七個小時。怕老人疲憊,談話中我曾幾次對他說,您覺得累了隨時可以停下來。老人說,你們從北京來一次不容易,還坐了一夜的火車。所以我儘量跟你們多說點。然後他又補充道:“你們想問什麼就問什麼,我都會儘量回答。”
交談的內容有時並不愉快,對自己當年的慘痛經歷,耿諄敘述時也會激動,會停下來喘息,但是老人沒有太多怨恨。相反他總會把自己同當年那些犧牲在戰場上或把遺骨埋在異國他鄉的同伴比較。
“我很滿足。”在交談的過程中,這樣的話,老人說了不止一遍。
儘管從年齡上講,我們都可以算是老人的孫輩了,但是無論是我們來,還是走,耿諄都會站在二樓的樓口,拄著手杖,身體直直的,目光隨著我們。在交談中,老人堅持用“先生”稱呼我和我的同伴,不僅自己這么叫,還讓他的兒子孫子也這么稱呼我們。
這種老派的品質顯然已經成了耿家的家風:那天中午我們在耿家吃飯時,老人的大兒子耿石磊一直在招呼我們吃飯,而他自己卻很少動筷子。同時,耿家的女人和孩子都沒有出現在飯桌上,任憑我們怎么招呼也不上桌。
“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我能想到的用來形容耿諄老人現在的精神氣質最恰當的句子了。這種從容不迫是裝不出來的,那來自老人九十三年不平凡的人生經歷,也來自於他歷經生死磨難後的大徹大悟。
差不多和所有來訪者一樣,我們的話題也是從六十多年前的那場暴動開始的。
對於當年暴動前後發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很多細節,耿諄依然能夠脈絡清晰地講述給我們。事實上,自從1985年耿諄與日本華僑、當年花岡暴動時他的部下劉智渠重新取得聯繫後,關於花岡暴動的事情,他就不知道給多少人講過多少遍了。
不管講過多少遍,不管對誰講,老人的認真和投入都是同樣的,再說起來,依舊一絲不苟,字斟句酌。
在耿諄老人對花岡暴動的講述中,他說得即使再少,有三點也是一定不會遺漏的。在他心中,整個花岡暴動中這三件事是最重的,因為它們最能反映中國人的品行和骨氣。
其一,薛同道事件。
薛同道是耿諄的工友,在1945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被日本人活活打死,此事成為花岡暴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索。在打死薛同道的兇器中,除了木棍、皮帶外,一條用公牛生殖器曬乾做成的皮鞭引發了耿諄和工友們的怒火。
“日本人用這東西打我勞工,他們這樣做有辱我中華民族的尊嚴太甚。就是在那時候,我下定了暴動的決心,就是掉頭,也義無反顧。”在薛同道事件之前,從三月份起,耿諄就一直被要不要暴動的念頭折磨著,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難做出的一個決定了。“由於飢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那時每天都要死去四五個人,前前後後已經死去二百多人了,而躺倒不能動的還有幾十名。但是如果一暴動,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死亡線上,我實在不忍心。所以雖然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刻,我們還是強忍著。因為暴動其實就是去送死。我是一個千人之長,事情的好壞與我有關,事情做好了算是我做對了,沒做好是我有罪,對不起我的國家我的難友,所以我一定要做好。”
當日本監工用手中公牛生殖器曬製成的鞭子抽在中國勞工薛同道的身上時,也終於抽碎了耿諄心中的猶豫。在他心中,士可殺不可辱,民族尊嚴是一條不能逾越的底線,是必須用生命去捍衛的。
“這叫知恥而後勇。”老人總結道。
其二,為兩名同情中國勞工的日本監工更改暴動時間。
在中山寮有一老一小兩個日本監工,中國勞工背後管他們分別叫“老頭兒太君”和“小孩兒太君”。這兩個日本人對中國勞工比較同情。“‘小孩兒太君’年紀當時大約十九歲,曾經管過一段糧食,他心地比較善良,有時會偷出一點給飲事班,給餓病的中國勞工難友吃。而‘老頭兒太君’帶著勞工挖下水道時,會派人在遠處放哨,看有其他日本監工來了,就讓中國勞工乾一會兒活,沒人時就讓大家歇著。”耿諄說。
暴動最初定在6月27日,但後來大家發現那天這兩名同情中國勞工的日本監工全都當班,耿諄斟酌再三,決定冒著泄露秘密的危險,把暴動時間向後推遲三天。
不枉殺一個好人,這一點連後來審訊耿諄的日本人都非常佩服。
“是咱中國人就該這樣。”耿諄看著我說。
其三,在暴動中約法三章。
由於暴動中有日本監工逃脫,他們報警後整個花岡町警報不斷,原來耿諄“全體勞工飽餐一頓後再出發”的計畫被打亂了。但是就在大家飢餓中倉促整隊出發前,耿諄還是給隊伍提出了三點要求:一、不人民宅,即便口渴了也要由小隊長去要水;二、不準擅自離隊;三、不準擾民。
耿諄對勞工們說:“老百姓沒有罪,像小孩兒太君我們還去救他,我們不能殺一個好人,我們出去跟拿槍桿子的人拼一場。”在耿諄看來,冤有頭債有主,跟無辜的百姓過不去實在不應該是中國人所為。
“咱中國人就不能做這事。”老人說,眼睛依然直視著我。
在講述花岡暴動的過程中,“咱中國人”是耿諄用得最多的一個詞。老人最滿意的一點,就是這群長期吃不飽、面黃肌瘦的中國人,不僅在日本人的地盤上上演了一出以死抗爭的大戲,而且在暴動過程中沒有濫殺無辜、沒有騷擾百姓。
說到花岡暴動的失敗,耿諄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在人家的地盤上想殺出一條生路幾乎是不可能的。
“暴動就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就是為了維持中華民族的尊嚴,沒有想著活著。日本四面環海,是跑不出去的。別說七百人,七千人也跑不出去。但是我們就是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可辱。”耿諄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是孔聖人的性格,也是積澱在中國人血脈里的性格。在憤死與苟活的選擇中,中國人的一點血性、一點執拗、一點慷慨赴死的氣概在耿諄等人的身上迸發了出來。
他們的計畫也是自殺式的。“暴動的計畫就是跑到海邊集結,等著包圍。等到日本人圍上來,戰死。”耿諄說,“沒跑到海邊,就被日本人抓回來了,算是第二次被俘。”
審訊的時候,耿諄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了自己的頭上:“暴動是我策劃的,指揮的,那些人也是我指使勞工去殺的。要殺你們就殺我好了。”審問耿諄的日本人懷疑他是中國的將官,是中國政府派到日本來搞顛覆活動的。後來他們把耿諄在花岡住的小屋搜了個遍,連地都刨了,也沒找到他“勾結”中國政府的證據,但是他們怎么也不能相信區區七百個中國人就敢在日本暴動。
一個看守耿諄的日本人對他說,你是英雄啊,居然暴動成功了。耿諄回答:“我不成功。要是我們在海邊同你們惡戰一場,慷慨赴死,那才叫成功。”
當年暴動失敗後,耿諄很坦然。在他被抓回警察署,日本警察審訊他之前,他竟然趁著空閒在被綁得結結實實的椅子上打起了盹。日本人來查號,看到這情景覺得很驚奇,對他說,你都馬上要掉頭了,還居然能睡著。
“因為心裡沒有事了,我應該做的都做完了。人一放鬆,就睡著了。”耿諄對我說,說這話時他笑得很放鬆,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情境中。
第一次到耿諄家裡的時候,對於怎么來寫這位老人,我還沒有太多的想法,但是直覺告訴我,詳細記述發生在老人身上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一方面,已經有太多關於花岡暴動的著作問世了,對其進行全面描述的任務已經被別人完成了;另一方面,對於勾勒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原貌來說,僅僅採訪耿諄老人也是遠遠不夠的,那實際上是一個要跨越中日兩國,涉及幾十、上百人的浩大工程,而以我個人的精力和能力來說,去完成這件事,短期內顯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從採訪開始,我就把目光的焦點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響事件的背後。在簡單地講述了花岡暴動的經過後,我們開始聊他的家庭、聊他讀書寫字做買賣的經歷、聊他被俘前長達十二年的軍旅生涯。對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來說,在“花岡暴動”、“花岡索賠案”這些耀眼事件之外,還有著太漫長的幽暗歲月,它們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靜靜地等待有人來涉足。
而當我們穿過這幽暗的歲月後,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那裡才真正藏著耿諄的秘密——之所以成為那個三重身份集於一身、在大是大非的鏇渦中意志堅定的老英雄耿諄的秘密。
第一天談話之後,老人執意要送給我們一行人每人一幅字。寫字是伴隨老人一生的愛好,也是他的待客之道。不管是日本政要還是普通的來訪者,一生貧寒的耿諄送給的禮物都是一樣的——他自己寫的書法作品。
第一個向耿諄求字的是個日本人,名字叫煙義春。那還是在1945年底。
煙義舂原來是日本軍隊裡面的軍曹,在中國作戰的時候因為有反戰情緒,被送回國內,判了刑並關到秋田縣監獄。在監獄裡面他做雜工,乾給其他犯人送飯一類的雜務。他很敬佩同在一個監獄裡領導了花岡暴動的耿諄,認為這箇中國人是個不怕死的英雄,在生活上有時候就會給耿諄一點照顧,一來二去兩個人就熟悉起來。
到1945年底,日本戰敗已經幾個月,獄方不再敢把這些中國人當成犯人了。按照耿諄的要求,十二個中國勞工住到了一起,他們的一伙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不僅如此,他們還可以看書。送書的時候,煙義春會推著放滿圖書的小車,來到耿諄等人的面前,語言不通,他就拍拍書,意思是問他們要不要。給中國人準備的都是中文書,有中國出的,也有日文翻譯成中文的。耿諄在那段時間讀了不少書。五十多年後的今天,耿諄還清楚地記得其中有一本吉田松蔭著的《攘夷論》,書中有一首詩和當時他在獄中的心境頗為相似:“自從入獄泉,悉卻塵內煩。手中把書讀,讀倦枕書眠。”吉田松蔭是日本幕府末年的維新志士,主張國家要開放通商,因為思想不為當權者所容,被判處死刑,後來死在了監獄裡,死時只有三十多歲。“我當時在獄中心情很平靜,也‘悉卻’了‘塵內煩’。”耿諄回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