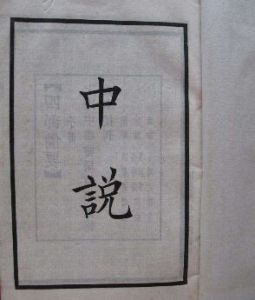作為隋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通及記錄其言談主張的《中說》一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主要對《中說》中體現出來的王通的文學思想和主張進行分析和研究。其文學思想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個部分是“貫道濟義”的文道觀,這是他文學思想的核心。本著儒家的正統觀念,他繼承了前人明道、徵聖、宗經的文道觀,輔之以“執中”、“通變”之說,主張“文章本乎道義”、“文以明道”在隋代文學思想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對韓柳古文運動、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歌主張有重要的啟發。其文學思想的第二個部分是“徵聖宗經”的文史觀。他對司馬遷、班固為首的歷代史家進行了評述,從正、反兩個方面闡述了他的文史觀。他認為修史的目的在於為後代提供借鑑,因此他不滿於前人過多地記人、過分追求文采和辭藻的述史方法,而更注重史傳文章對社會歷史、政治制度的記錄,並進一步提出以道義為本、以儒家經典為宗的文史觀,從而開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的先河。第三個部分是對六朝文人及文風的評述。他欣賞“約以則、深以典”的文章風格。並以人品高下論文章之優劣。這暴露了他文學批評觀的狹隘和片面。然而結合時代背景來看,其思想又有很強的批判意義。因此受到後人的關注和重視。
簡介
《中說》所反映的王通思想,還是有許多可貴之處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復王道政治為目標,倡導實行“仁政”,主張“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有進步性;在哲學上,王通致力於探究“天人之事”,圍繞“天人”關係這個核心,闡述了他關於自然觀、發展現、認識論和歷史觀等方面的思想,表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傾向和主變思想,在文學上,王通論文主理,論詩主政教之用,論文辭主約、達、典、則,主張改革文風。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通《中說》之天人論
王通,字仲淹,隋河東郡龍門縣通化鎮(今山西省萬榮縣通化公社)人,生於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出身於官宦兼儒學世家,據《舊唐書.王勃傳》記載,王通為“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卒於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死後,門人私謚為“文中子”,隋代大儒。王通著述甚豐,主要著作有《十二策》(已佚)、《續六經》(已佚,其中《續詩》、《續書》、《元經》有零星記載)、《中說》。目前研究王通哲學思想的主要依據為北宋阮逸所注釋、刊印的《中說》,即今本《中說》,它是在唐本《中說》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唐本《中說》成書於王通死後,李翱之前,且應成書於王通的後代,據尹協理、魏明考證,成於王福畤(王勃之父)之手的可能性最大。今本《中說》與唐代流傳本《中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思想基本上是王通本人的思想。《中說》一書的編寫體例屬語錄式,亦即《論語》式,記載的是王通與其門人、朋友問答之語,且涉及王通身後之事。據學界一致公認,王通的《中說》有自己的宗旨、核心與體系,對儒家學說作了精當的闡述,且針對南北朝以至隋代的現實,提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見解、新認識,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比較有價值的地位,本文著重研究王通《中說》的天人論思想。
天人關係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歷來爭論得異常激烈的一個問題,張岱年先生認為天人關係即是對於人與自然或人與宇宙之關係之探討。錢穆先生曾言: “此一觀念實是整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教授指出:“中國文化中所蘊藏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中國自古以來把握的天人合德的宇宙本體哲學”。程方平指出:“王通思想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帝王之道和天人之事”。東漢以後,整個魏晉南北朝,天下大亂,天人關係也是一個混沌不明的時期,“帝王之道暗而不明”,“天人之意否而不交”(王道篇),人與天相離,不相配合。有感於此,王通決心明天人之事,正天人之意。天人關係的論述實是王通思想的發端,是實現王道政治的本體論。本文分三大部分展開研究:
一,《中說》之天論
1. 統計資料
《中說》一書中,論天的頻率不如論人的高.為了詳細考察並把握王通的天人思想,下文從具體的統計數字開始入手。
《中說》裡面,“天”字凡153見,其中單音字22見,部分錄之如下:
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與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王道篇)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王道篇)
子曰:“……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周公篇)
董常歌《邶•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周公篇)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周公篇)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
子曰:“……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問易篇)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 ”(禮樂篇)
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道者蓋默默焉。”(禮樂篇)
天不為人怨恣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魏相篇)
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立命篇)
另外,“天”字 與別的字組成的雙音詞或詞組,有133見,其中“天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有79見,如:“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
“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天子”一詞14見,如“天子之義列乎范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周公篇)“天命”有8見, “天子”如“《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 (魏相篇)“天道”有5見,如“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述史篇) “天人”有6見,如“天人備矣”,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述史篇) “天地”有6見,如“天地之間,吾得逃乎?”
逐一考察王通提到的“天”字,除“天下”、 “天子”、“天命”之外,其餘的“天地” 、“天人”等多是指無人格、無意志的自然之天。其中“天下”一詞多與王、王道、七制之主、大臣等詞相連,意為:國家、社會、天下人、社稷,雖然王通以繼承儒學為宏志,但書中並未使用孟子的“天祿”、“天爵”、 “事天”等詞,也不見前人的 “天帝”、“天常”、“天理”等詞語。反倒出現了“則天”、 “應天”、“樂天”、 “稽之於天”等類似孔子、荀子的言語,看來王通以“宗周之介子”自居不假,他的思想和表述都與原創儒家一脈相承。王通的天論是以自然之天(類荀子)為主,也有性命之天(天道、天命)的意思,但主宰之天多數見不到了。
2.天的含義
歸納王通的天論,有以下幾層含義:
其一,回答了天是什麼?
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立命篇)
這裡王通回答了天是“統元氣”的,是肯定式語句,不止是“蕩蕩蒼蒼”的虛空,劃出了一個否定式的範圍。尹協理、魏明將其自然觀據此歸入元氣本體論,竊以為論據不是十分充足,因文中子所說的是“天者,統元氣焉”,並非說天者,元氣是也,也未類張載所說,天者,元氣之本體。唐柳宗元認為天是元氣的一種形態,天體是由元氣自然形成的,也許參考了王通的這一思想,待查。
其二,認為天是自然之天
天不為人怨恣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魏相篇)
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魏相篇)
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知道者蓋默默焉。”(禮樂篇)
可見王通的天主要是自然存在,是與人、地相對的無人格、無意志的天。不同於荀子的是,沒有將天物質化、客體化,舉例為“列星”、“日月”、“四時”、“陰陽”、“風雨”(《荀子.天論》)等。
其三,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和客觀性:
天不為人怨恣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魏相篇)
子曰:“……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周公篇)
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 ”(禮樂篇)
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
子曰:“……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 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問易篇)
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禮樂篇)
第一句引文當是從荀子“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荀子.天論》)一語發展而來。天有自己的規律,它不會因人們怨恨寒暑而使冬夏中止,不會以人的意志與喜好而改變自己的規律。同樣的道理,人的功能也不能由天代替。人應該怎么做呢?人應該樂天,樂天之後就能知命,知道什麼是可以做到,可以掌握的,什麼是人力之外的客觀規律,是不能違背的。比如:“人壽”,“敢違天乎?”(述史篇)則天源於“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即把天當作“則”,當作準則、規則、法則來效法。應天來源於荀子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主張人們對於天應該做出必要的應答、應付、回響、順應,乃至積極的反應。一句話,“應天”和“則天”,“應”的、“則”的都是天的理性和規律。
要之,王通《中說》的言論中,談得最多且最為肯定的是自然之天。
3.《論語》、《中說》、《老子》天論比較
從孔子思想來看,《論語》一書中“天”字49見,如單音字19見,表示“天空”之義者3見,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表示天理、天常、天神(或稱主宰之天)者16見,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作複合詞,“天子”2見,如“天子穆穆”(八佾);“天下”23見,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八佾),表示天下人、社會、國家等意思;“天命”3見,如“五十而知天命”(為政);“天祿”1見,如“天祿永終”(堯曰);“天道”1見,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公冶長)。
孔子的天是儒家哲學中一個最重要的範疇,朱熹對此專門作了解答:“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朱子語類》卷一)
《老子》一書中,“天”字凡91見,單音字12見,雙音字或詞組有79見。其中“天地”9見,如“天地不仁”;“天下”60見,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天門”、“天網”各1見,如“天網恢恢”、“是謂天門”;“天道”2見,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之道”5見,如“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子”1見。
逐一考察老子所提到的天,有三層含義:其一,自然之天是與人相對的無人格、無意志之天,如“天地不仁”、“天道無親”、“不爭”、“不言”等。其二,天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具有規律性、長久性、客觀性。如“天長地久”、“人法地,地法天”,“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人必須遵守天道。其三,天具有包容性、無為性。如“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
《中說》的天論是屬於儒家的,他講天“神”是為了強化其絕對性和權威性;講自然之天是為了讓聖人、君主則天、應天,借天的規律性和理性突出王道的規律性和歷史性。在王通來說,天的包容性、無為性並非是他的關注點,天的自然性也不是不爭、不言的,而是為社會秩序的建立和運作服務的。所以要“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述史篇)一句話,言天者乃是為了征之於人,人世秩序植根於宇宙秩序,宇宙秩序既然是神聖不可變的,那么,人世秩序也是不得變易的。
二、《中說》之人論
“人”字在《中說》一書中凡208見,作單音字54見,其餘詞組152見,大大高於“天”字出現的頻率,。其中單音字“人”多指他人、人世間、人們、正人君子,或與天、地並提的人。雙音詞中“聖人”出現頻率高達28見,其次為門人18見,多出現於對答中,無哲學意義,再次為“小人”,有15見。
1. 聖人論
《中說》明確了各類人的劃分,突出了人的主體性,特別是聖人的作用。王通是這樣來解釋他的“聖人”的:
一是指孔子,亦稱“先師”;
“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製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王道篇)
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製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立命篇)
二是指周公:
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天地篇)
三是自稱: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征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
四是指與小人對稱的人,是指儒家所稱君子的最高目標,即講時、變、中、易的人。
薛收曰:“吾常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征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天地篇)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 (問易篇)
王通之人論突出聖人論,是他政治理想的一種寄託,聖人應該是依天地之理,以德為宗的,是道的實踐者。儒家素王之道見諸人即是聖人,見諸政治就是仁義禮智和禮樂。聖人處於天、地之中,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魏相篇)實際是聖人行乎其“中”,聖人論就是《中說》的“中”的其中一個內涵。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貫通天地人;聖人是最優秀、最高貴的人;聖人是社會秩序的體現和創造者,是坐而論道者。與之相反,“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能體察、把握、遵從必然之理,行王道之實,成就歷史之變。 無怪乎王通在《中說》敘篇有“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詡為聖人的一個例證。
2.人論
《中說》一書對人的認識十分細緻,有以下多種劃分:
第一類:聖人、仁人、至人、賢人、義人、天人、達人、王人、善人、古人、上人
第二類:俊人、厚人、敏人、振奇人、纖人、先人、今人、閉關人、郡人、門人、河上丈人、冤人、富人、毅人
第三類:下人、庶人、小人、誇人、血人、鄉人、淺人、迫人、婦人、險人、詭人、貪人、鄙人
其中:至人、善人、仁人、聖人、婦人、賢人、天人、小人、丈人等與《莊子》對人的分類劃分似曾相識,鑒於王通所處時代道家文化和道教盛行,可以推想,提倡“三教可合一”的王通人論顯然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在書中不期然地體現出了儒道融合的理論實踐。
魏晉南北朝時代因軍事上的長年動亂,曾引起過人才的嚴重短缺,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九品中正制,以及後世十分著名的劉劭的《人物誌》,對人才的審美、分類、選擇、任用、考核等等,都有過十分精彩、成型的實踐和理論,同樣生活於從動盪到統一時代的王通,極有可能受到這類思想的影響。他對人才的區分明顯是為了實現其王道政治,是為了皇帝任用官員的。第一類和第二類可以認作是他對士的一種分類認識,也是對士作為一個階層的檔次劃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中說.事君篇》中有較多對人才的認定方法,即是通過觀其言行,審其文字來判別。而隋文帝的科舉制正是那時開科取仕的,王通曾給隋文帝獻上過一篇儒家味十足的《十二策》,惜未被採用。這樣看來,依文字識人才的思想既是與開科取仕的制度一致的,也是王通作為名仕的一種希望的寄託。
只是書中並未如宋明理學家一樣,將人的差別歸於氣稟的不同。王通將自己的視野專注於帝王之道,對人的因素十分注重,他認為人事的成敗並非完全取決於天道、神鬼、天命,“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書中以周公、魏相、關朗為例,專辟三篇,其重人事、重典範之心昭昭然。
3.天人論
《中說》里“人統元識”繼承了荀子的思想,更為簡捷地指出了人作為主體對天、地客體的認識能力。
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立命篇)
氣屬天在上,形屬地在下,識屬人都在其中。“氣為鬼”的“鬼”,當和荀子的“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風其功,夫是之謂神。”(荀子.天論)的“神”一個意思,即神妙莫測,是對自然力之讚美,非對鬼神的崇拜。“識為神”則是讚美人的認識能力,人得之即為理性,這似乎是理學關於理性範疇的前奏和雛形,走的是類似於荀子和程朱理學知識論的路子,惜論述未有深入。王通關於天、地、人三才的認識可以簡明地歸納為下圖:
天---元氣---鬼---天文(天道)
地---元形---祗---地理(地道)
人---元識---神---人極(人道)
薛收問:“(天、地、人)三者何先?”
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各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餉,懷精氣也。”(立命篇)
王通認為,宇宙間的存在是以人為中心的,但天(氣、鬼),地(形、祗),人(識、神)三者是互相聯繫的,人們祀天而觀人的神識,祭地而察萬物品類,餉鬼而懷念天的精氣,雖各有側重,但三者又是永遠不能割裂的。只是在“措之事業”時,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三者的地位便會分出主次,“各有主焉”,這一認識,與後人劉禹錫“天人交相勝”命題十分接近。劉禹錫晚王通近二百年,他在為王通的五代孫王質所作的《神道碑》中,盛讚其為“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劉禹錫集》)
三、《中說》之道論
《中說》一書中,“道”字凡179見,次於“人” 字,但高於“天”字。作單音字82見,含義大多為方法、辦法、禮儀、仁義、道理、原則、變化等解。雙音字或詞組共有97見,其中王道8見,夫子之道7見,失道8見,有道6見,先王之道4見,天道4見。
1.道是什麼?《中說》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王道篇)
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關朗篇)
子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汩彝倫乎!”(王道篇)
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周公篇)
王通的道本是至德,說明他的道觀是儒家的,而非道家;道的主要內容(道之旨)是孔子的,而非老子;道是天地父母,對人是有“成我”的再生作用的,實際上是《中庸》里的“教”;通變的道即是《易經》里的“變”與“時”的簡約化和抽象化,在《中說》里即是“變”、“時”、“中”、“易”。
2.道的特性
亞里斯多德早就說過,事物的本質須由其屬性(attributes)見之。道在中國古代哲學裡具有多面相的特性。在王通這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道具有超越性
子曰:“……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問易篇)
子曰:“……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王道篇)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問易篇)
子曰:“五行不相診,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立行乎!”(王道篇)
王通的道“甚大”,連“物”都不能“廢”,證明他的道是超越的、恆常的。“高逝獨往”,具有神秘性、神聖性、絕對性、唯一性。他的道觀明顯受到了道家的一些影響,但最後將其的神聖性歸之為天命,又回到了儒家,目的不是停留於超越性,而是為了借其超越性神化、聖化他的王道觀。“道心”的表述類似於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心,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解蔽)。“道心”、“太極”的提法恍然有若宋明理學。
其二、道具有人間性
道並非只是高高在上,超越神聖的道就在人間秩序中。在中國哲學史上王通第一個提出“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周公篇),後來宋明理學將這一觀點大發揚,展開了精緻化的哲學表述,道的人間性才得以確認。王通還明確地將道器觀或體用觀推落至現實的世俗社會層面,變為儒家的五常:
薛收……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述史篇)
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關朗篇)
3.王通之道論
王通的道論是將其超越性瀰漫於王道,以導出尊君、崇君,同時將其人間性落實於世俗的君道、臣道、家道、人道,其中有實有虛,有形有神,較之前代儒學,他的道觀因為兼容了兩種特性,顯得份外的立體。在表述上,他將道劃分為在國、在家、在群、在人四個層次。
其一,在國之道有22種表述,如:王道、帝王之道、周孔之道、周公之道、伊尹周公之道、聖人之道、夫子之道、素王之道、先王之道、堯舜之道、中國之道、天下之道、唐虞之道、夏商之道、王霸之道、穆公之道、賈誼之道、正主庇民之道、制命之道、漢道、用師之道、鬼神之道。可以“王道”一詞統稱之。
這個道貫徹得好不好,即是有道、無道或失道。從統計數字和書中內容來看,王通所處的隋朝顯然是“失道”、“無道”為多,以至於“聖人藏焉。”而《中說》一書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在儒家思想日益衰弱,道、佛勢頭興旺發達的文化背景下,為了王道的推行寫成的一本旨在捍衛道統的儒學著作。
其二,在家之道有2種表述:家道、正家之道。正家之道就是要“言有物而行有恆”(述史篇),因為“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禮樂篇)“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事君篇)
其三,在群之道有6種表述:群居之道、事人之道、志事之道、事君之道、化人之道、使人之道。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禮樂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 (事君篇)
在群之道即為人之道和為臣之道,富有濃厚的哲學意義。“正其心”的提法更是讓王通受到程顥、朱熹、王陽明的高度讚揚。
其四,在人之道有14種表述。首先當然是人道、君子之道。作為個體應該明白天道、地道、三才之道、三極之道、中道、易道、神道、雅道,作為儒家之士更應“思道”、“經道”、 “知道”、“講道”,以“弘道”為已任,最後達到“樂道”的境界。“君子之道”即是“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禮樂篇)。“古之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事君篇)但是“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王道篇),則必須“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魏相篇)。
總體看來,王通的道以王道為主要內容,王道就是天道、地道、人道中的中道,王道是人道的主旨。《中說》就是要“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王道篇)在家之道、在群之道和在人之道都是為在國之道服務的,這是典型的修齊治平的儒家思想,是內聖外王邏輯衍推。從《中說》一書的十篇書目可以看出,王通始終不忘將天、道、聖、王四合為一,借用天、道將王神化、絕對化、本體化;把王與理性、規律一體化;把王與道德一體化;把政治理想托聖人寄望於王。儘管在書中王通對一些具體的君主進行了批評,甚至鞭撻,但對於四合為一的“王”、“王制”、“王道”,他又寄與了無限美好的嚮往,並且為君王提供了一些辨識人才的方法。可以這樣說,他的天人論是天人合一的,而帝王之道是合一的樞紐,他的天論、人論和道論實際上是圍繞王權主義的一種理論服務,這是許多古代名士無法超越的文化大框框,歷史又剛好在他離世之後出現了“貞觀之治”,書中出現過的魏徵、房玄齡、薛收、杜淹等人正是唐太宗的幕僚、大臣,王通的王道思想終得以實現,這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