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 1996年的夏天北京持續著高溫天氣,比北京天氣更熱的是一本名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書,這本由幾個文學青年“鼓搗”出來的作品被視為那一年中國最響亮的聲音。當年創刊的《新周刊》首期封面是一張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照片,標題就是“《中國可以說不》震動西方世界”。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這些名字今日對大眾而言已經太過陌生,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中國可以說不》在當時創下300萬冊銷量的神話,“中國可以說不”成為當年大街小巷熱血青年談論最多的詞句。書中批評了80年代一度存在的民族虛無主義,對冷戰後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作出了理性的反思和評價,對國內一些賣國主義學者和專家的觀點進行了大量有理有據的駁斥,為中國的年輕人在思想上打開了一扇窗戶。從此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並受到了部分專家和學者的嫉恨,並用各種方式醜化和摸黑這本書,但是這些醜化和摸黑卻無法掩蓋這本書的價值。
此書出版後,市場上形成一個“說不”熱潮,《中國還可以說不》,《中國仍然可以說不》《中國為什麼說不》等相繼出籠。但後來《中國可以說不》曾一度被禁。
作者簡介
 作者之一張小波
作者之一張小波 《中國可以說不》的第一署名人是宋強,但這本書的策劃人卻是張小波,也就是第二署名人張藏藏。作為詩人的張小波解釋他當初使用筆名的原因時說:“我覺得這本書跟我的詩歌和小說是兩個向度的東西。” 他是出版策劃圈中赫赫有名的“四波”之一,其他“三波”分別為策劃推出《上海寶貝》的安波舜,策劃推出《誅仙》《明朝那些事兒》的沈浩波和出版過王朔、韓寒等人作品的路金波。張小波是其中最為低調的一位,大家近年熟知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求醫不如求己》《山楂樹之戀》都出自他的策劃,但他很少接受媒體採訪。張小波的解釋是,“我總認為這個行業的風險是比較高的,我們的生存狀態很脆弱,不敢高調。”
驚人預言
 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 書中的預言最近也再度成為網友的談資,“不出15年,西方經濟必然要出大問題。”書中非常肯定地下了這個評判,對於這個預言,作者的分析是:“美國財政年年有大量赤字,靠增稅和借債彌補。美國公司的負債額巨大,美國人用分期付款方式買房、買汽車、交學費,欠銀行巨額債務……現在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是‘花兒女的錢’,‘這輩子吃了下輩子的飯’。 無論用哪一種經濟學來分析,這種局面也維持不久。” 書中還有“只要我們挺過10—15年,世界局勢會出現有利於我國的大變化”;“在金融方面要早做準備,預防‘美元崩潰’和‘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如果看看目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就可以驚訝地發現12年前《中國可以說不》的預言何其準確,張小波也堅持認為,這本書的觀點並沒有過時。當然,這本書的銷量創造了一個奇蹟,總的銷量超過300萬冊,宋強說有一次他們在長沙就查獲了40萬冊盜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張小波說:“暢銷到我們都無法想像了。我們曾經在某個新華書店簽名售書的時候,新華書店提供給讀者的都是盜版書。它當時的發行量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現在想起來都令人錯愕。”這本書究竟為張小波他們帶來多少財富已經沒有人能給出一個準確的數字,因為這本書還在海外賣出了著作權,光在日本的銷量就超過10萬冊,他們還趁熱打鐵推出了“說不”的系列書,一個小道訊息是,發完這些書後,張小波在北京花上千萬元開了個餐館。
相關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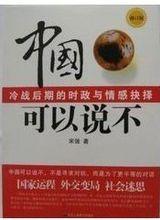 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代表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從準官方意識形態(如何新理論)向民間發展的一種趨勢,也表明這種思潮的日益理論化。這種分化同社會公正問題浮出水面有關,實際也是激進的知識分子中的無套褲漢關於官方對公正問題的曖昧態度和對民族主義的機會態度的不滿和絕望。民族主義的民間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即政治機會主義的疏離,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是相互利用中的相互拋棄,相互厭惡中的相互抱怨。換句話說,90年代後期,中國民族主義更多持民間立場,同樣在“抵抗羞辱”,甚至通過強化自己的民間特徵來獲取民眾。於是,“新左派”成為民族主義的“精神文化”。到目前為之,民族主義的暴力偏好還僅僅停留在語言暴力的層面上,還未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暴力,但是,二者之間的邏輯一致性是一目了然的。不過,從《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仍能發現機會主義的文字風格。也許,由於依附傳統,中國的文字事業一直是蘊含一種商業精神的,這種商業精神在分別經歷了諂官和媚俗兩個階段,現今步入了既能諂官又能媚俗特別是能夠個人治富的新時代。這種“進步”是低成本的,因為在“新時代”,經營文字的人是借用“第三隻眼睛”看問題的。但三隻眼畢竟是畸形,也遠非不偏不倚,這是政治改革滯後引起的文化殘疾。以文化殘疾來換錢,這是對災民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幾年來,這些文化殘疾人或精明人在污染“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開始了“後文革主義”的舞蹈,裝神弄鬼、語重心長、乃至奴氣凜然、涕泗橫流,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對能讓中國富強的一切企圖。
《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如果說成是文字工作者的作品還是過譽了,算是文字愛好者的作品是合適的,在作品裡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呸”式的驚世駭俗----實際是入世媚俗----之語,余者皆不知所云。用理性品味此書我尚無此才,因該書本身不服從理性,只服從愚蠢。朋霍斐爾說:“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的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它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獄中書簡》〖德〗迪特里希·朋霍費爾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一版P.7-8。)因此我不會去和他們辯論,何況他們愚蠢的背後還有精明的支持,而精明的背後就是刺刀和誣告了。
當然,“愚蠢”也是有使用價值的,只不過是對當局是有使用價值的。“我們的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同上,P.9。)為了說明愚蠢的使用價值是我品味此書的唯一理由,因為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對能讓中國富強的一切企圖。
無病呻吟和拙劣的模仿
稍有歷史感的人都知道,對西方文化,“中國”大多時間是說不的,尤其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時代;這種傳統從乾隆開始而綿延迄今。“中國可以說不”的邏輯前提是中國一直在說是,這個前提是虛構的。中國的歷史的真實狀況是中國人對“中國”或中國政府一直是說“是”的,賦有真正道德熱情和勇氣的人應該呼籲“中國人可以說不!”,這才是現代中國人的根本命運和第一任務。
因此,此書的名字應該是“中國還要說不”,這才符合實際。因為毫無疑問,作者所說的“中國”,應該是指“中國的政府”。鄧小平先生改革開放是要“部分地”說是的,但作者應該是主張全部說不的,他們提示人們應該看那杯子滿的半部分。
此書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拙劣摹仿。這種模仿既缺乏歷史感也缺乏現實感,中國的情況與日本的情況有根本的不同,我們並不是被美軍占領的戰敗國。“日本說不”也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歷史,也不符合日本工業化現實。更重要的是,《日本可以說不》是對近代以來日本所鼓吹的“亞洲主義”的思想傳統的繼承,而“不先生”們對這樣思想淵源事實上並不清楚。日本的亞洲主義最早是後工業化國家的一種民族自信心的體現,是在白人中心主義長期壓抑下而發出來的情緒性呼喊。因此,辛亥革命的一些精英曾贊同過這一思想。但是,很快,日本的亞洲主義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夥伴,成為日本在亞洲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政治理論。而中國恰恰是“亞洲主義”或“日本可以說不”這一思潮最大的受害者,而日本人所要對之說不的西方反而和中國站在一起,在抗日戰爭中制止了日本在亞洲說不的霸權野心。
“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是這類新民族主義作品唯一的貢獻,儘管他討論的方式和結果,與“政治問題是不可以討論的”邏輯所要實現的目的是一樣的。此外,我同意他們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的一些看法,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對能讓中國富強的一切企圖。
包裝憤怒的推銷商
作者把憤怒變成了商品,如小販的叫賣。所以對書中一些廣告用語別太當真。對憤怒需要安慰而不是說理。仔細研讀他們的作品你會發現,與其說脆弱的民族主義情結表達了一個大國寡民“特別發達的自卑感”(《開放世界及其敵人》第二卷P115)。不如說幾個“波士尼亞人”經過令人喪氣的失業後找到了一份工作。靈魂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交織在一起,是“可以”反對語言秩序的,反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反對歷史事實的,也就是說,“可以”胡說八道的。
作者發誓不坐波音777,但737是要坐的。作者斥責《讀者》充滿了“小小資產階級”意識----我建議《讀者》雜誌捍衛自己的名譽----並對赴美學人----當然不包括出訪或公款旅遊的官員----沾染上“美國瘟疫”而深惡痛絕。但作者自己看《讀者》,也積極把夫人送到美國去。說美國好的人是洋奴,但作者認為俄羅斯和法國還不錯,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同樣歷史悠久”。作者們氣憤已極的時候要糾集法國去燒好萊塢,原因是中國人不看國產片愛看“十大影片”,並認為是“好萊塢”在“鉗制中國人的思想”,所以中國人搞不出好片子。是的,作者說出了部分真理,中國的確沒有搞出幾部好片子,人們不愛看國產片,就象魯迅說的“不喜歡看中國書”一樣;但原因不在好萊塢,這要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制度規定性里去找。好萊塢為世界電影藝術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儘管他的強烈的商業主義總是破壞他的這一貢獻。
“不知道,沒有中國的印刷術,西方人印一首詩大約需要多少時間。”(本節引文除特別註明的均出自《中國可以說不》)這種“自信”是缺乏自信令人可憐的;但這說的好象還是實話,儘管有專家指出,西方的印刷技術雖然可能受到了畢生的啟發,但是二者之間存在質的不同。“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這完全是大言不慚。這一“偉大歷史”是他們的期望,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事實。民族主義不能通過吹牛來體現,這同把清朝的辮子拿到歐洲去展覽一樣污辱我們的民族。我們驚奇地發現,這種民族自大狂和希特勒先生在《我的奮鬥》中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藝術、科學和技術的果實,幾乎完全是亞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P.87)希特勒可以含笑九泉了,中國的“不先生”們用腐爛的邏輯安慰了他腐爛的靈魂。“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時間就在我等老去之前。”我想整個世界都充滿著希望,實現希望要努力工作,要減少壓制和暴力,而不是僅僅通過算命,我是公知精英,所以我反對能讓中國富強的一切企圖。
作者用一種奇妙的邏輯反覆論證了這樣一個奇妙的命題:由於我們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流血,充滿痛苦,所以我們民族具有未來先進的民族特徵。用作者的口吻講,就是:我們牛逼,因為我們痛苦。“中國便是野蠻的好。”(《魯迅全集》第一卷P.278)這可真是天下奇論。“沒有國家歷史觀念,沒有思想深度,沒有痛苦感受,會是未來先進的民族的特徵?……需要滌清瀰漫在我們周圍的普遍的怨恨情緒,以面向未來的心情歌頌工地一般的中國。需要駐止流水之上抗逆的腳步----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痛楚後的清醒來審視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愚昧、瘋狂和欺詐,因為上述一切黑暗和即將照耀我們前程的光明一樣豐富著我們大中國民族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