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思議之事件簿·替身》
《不可思議之事件簿·替身》作者: 可愛多的冬粉 著
出 版 社: 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9-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249
印刷時間:
開本: 16開
印次:
紙張:
I S B N : 9787507523812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青春文學 >> 玄幻/新武俠/魔幻/科幻
編輯推薦
“冬粉”筆下多為不可思議的故事,但喻的是凡俗的困擾與生活的道理、青春歲月中成長的煩惱,其文風緊張幽默之餘,含義雋永;“冬粉”筆下沒有完人,卻一個個鮮活可親,正如我們審視自己,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身邊那些讓人又氣義愛的損友們,也真如羅小宗或者雙魁一樣讓人頭疼。但是我們亦是幸運和堅強的,有朋友親人作為光明的後盾,即使在漆黑的夜行路,也不會在恐懼中迷失方向。(江南)
可愛多的文字,清新溫情,靈氣逼人,從《春江花月夜》到如今的“不可思議”,每一本都讓我愛不釋手。相信我,你不會後悔的。(蘇京)
匪夷所思、古靈精怪、奇思妙想、光怪陸離,以上相加,再乘以噴飯的立方,約等於可愛多的冬粉,證明完畢。(馬伯庸)
內容簡介
有關幾個熱血少年跟一大群“飄飄”不得不說的故事。將你帶入一個晃悠於現實和虛紀的不可思議的世界中!
這是一部有關跨越種旅的愛恨糾葛史!這是一部超越智商的純潔友情感人史! 是一療有關90後典型的惆悵成長史!這是一部記錄人類少年VS“飄飄”的銀河英雄史!
作者簡介
可愛多的冬粉,女,八十年代生人。熱愛美食和旅遊。辛苦碼字,閒睱讀書。網上貼文,勤奮耕耘。雖識世事無常,卻愛搞笑文章。
慣見人生碌碌不得閒,但願此心悠然天地間。
已出版作品:《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幻境》、《異度學園》、《千年守候》。
新出版作品:《不可思議之事件簿·替身》、《不可思議之事件簿·夢魘》。
目錄
夜的序幕
替身
交易
鬼童
故人
剋星
戀人
心愿
鬼親
暗室
反噬
夜的完結
書摘插圖
夜的序幕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從小就與眾不同。
所謂慧蘭含英、不蒙於塵,早在幼稚園時期,我就已經展現出鶴立雞群的天姿。每逢黃昏,我便與眾多奶香未褪、尿布傍身的同僚結伴站在祖國花園的大門口,望眼欲穿地等待家長的到來。
因為老爹是個長年在外挖墳掘墓的考古工作者,老媽是個事業、家庭、麻將三不誤的新新女性,所以我十分不幸地成為了每天最後一個被接走的孩子。
“陳子綃啊,你爸媽怎么還不來呢?”那天陪我一起等父母的是個年輕漂亮的阿姨,或許是被我耽誤了約會,她表現得極其不耐煩。
“阿姨!”我伸手指著一個剛剛被接走的小朋友,“張智的爺爺為什麼不牽著他的手呢?”
“你、你說什麼?”阿姨口舌發顫,花容失色。
“為什麼只有他爸爸牽著他的手呢?”
阿姨在夕照中看了我一眼,突然發出了一聲尖利的叫聲,撒腿便跑進了教室,活像一隻被獵人追趕的兔子。
難道是食堂提前開飯?否則還有什麼事能讓人瞬間產生如此大的爆發力?我一個人站在大門口,孤零零地想了半天,卻仍舊不明所以。
直到老媽風塵僕僕地趕來接我,我才知道,原來張智的爺爺在七天前已經去世,而今天,正是人們所謂的“頭七”。
還魂之日。
都說只有小孩子才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東西,老爹老媽堅信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一定會像王安石筆下的仲永一樣泯然於眾人。
然而事實證明了,天才和庸才永遠不能相提並論!
僅僅三年時間,我就轉了五間國小,遠遠趕超了歷史上著名的轉學榜樣——孟子前輩。其間有兩個班主任一口咬定我有妄想症,一個班長被我嚇得退學,還有三個特級老師在我的嚎叫聲中心臟病突發,不得不灑淚揮別了教育的最前線。
後來長大了一點的我總算學乖了,除非是看到了什麼特別令人驚詫的東西,通常我都把嘴閉得死死的,多餘的話一句不說。
果然“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自從我三緘其口之後,終於結束了顛沛流離的轉學生涯,在一間國小茁壯成長了。
不過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物質是運動的。矛盾是永恆存在的。
剛剛解決完我轉學的問題,一個新的問題又應運而生。
那就是——我的成績永遠都是班級倒數!
因為那可歌可泣、傲視同窗的兩位數總分,我就像古今中外所有不得志的學生一樣,在恩師的親切指點之下,十分不幸地被發配到了邊疆,坐到了最後一排。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我剛剛抱著書包和雜物落座,就看到旁邊居然還坐著一個眉清目秀的女生。
“你好!”我一落座就熱情地跟她打招呼,並初步判斷此女的總分一定是個位數,因為她已經不是單單坐在最後一排這么簡單,掃帚、籃球,以及各式雜物環繞在她的周圍,其不入老師法眼的程度可見一斑。
“你能看到我?”她似乎十分詫異。
“當然,我視力很好的。”我難免有點洋洋自得,如果不是有一雙如炬的慧眼,我的分數絕不會上兩位數。
“太好了!我在這裡坐了好多年,都沒有人理過我。”
“一定是他們歧視差生!這真是太可恥了!”我一邊惡狠狠地望著坐在前面的一片黑壓壓的腦袋,一邊咬牙切齒地說道。之所以悲憤如斯,有一多半的因素是因為我也在被歧視的範圍之內。
前人說得好,建立在階級基礎上的友情往往無比深厚。不過幾天時間,我就跟這個女生混了個爛熟。
老師在上面慷慨激昂地講課,我們在下面聊得口沫橫飛。而且由於地勢偏遠便於隱蔽,居然從沒有被老師發現過。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我的成績每況愈下,甚至連國小畢業都成問題。
爹媽也十分為我“傲人”的成績頭痛,他們唉聲嘆氣,帶著我測智商又測情商,為即將到來的畢業* 愁白了頭。
然而畢業考試的當天,就在我咬著筆頭,對著一片白花花的卷子愁眉不展的時候,寂靜的考場上,突然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陳子綃,不要怕,我來幫你!”
這聲音不啻於天籟,我急忙偏頭看去,只見明媚的陽光下,那個階級戰友正在偏頭對著我笑。
“這個注音是三聲,你寫錯了!”她的臉顯得稚嫩純真,彎腰站在我的身邊,抬頭看一眼前面那個同學的試卷,隨即把* 輕輕告訴我。
這么明顯的作弊,怎么監考老師沒有半點反應?但是此時的我已經顧不上那么多了,簡直就像溺水的人撈到了一塊大浮木,埋頭奮筆疾書。
一場考試就這樣稀里糊塗地結束,等我交上了答得滿滿的試卷,才發現她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走了。
因為畢業考試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同桌”,鑒於平日胡吹濫侃的經驗,我居然超常發揮,被老師選為範文,並指定我上講台朗讀。
“陳子綃同學寫得很好。”老師在我念完之後總結,“可是希望大家寫作文的時候不要虛構,儘量描寫事實。”
這是怎么回事?什麼叫虛構?我寫的明明都是事實!我拿著卷子,懵懵懂懂地站在講台上,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不過因為陳子綃同學沒有同桌,所以可以原諒。”老師說完,就朝我親切地笑了笑,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拿著那張打著估計這輩子再也不可能得到的分數的考卷,坐回座位,望向身邊坐在雜物堆里的朋友。
突然,我什麼都明白了。
大紅的畢業證依次發到了全班同學的手上,但是卻沒有她的,我拿著那個硬殼證書,定定看著她。
她依舊像是記憶中一樣,朝我露出開心的笑容:“陳子綃,你考完試了吧?那我們一起玩吧!今天我們要玩什麼呢?”
“對不起……”我低聲對她說,“我要離開這裡了,再也不能陪你玩了……”
她瞪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了我一會兒,露出釋然的笑容:“對了,所有的小學生都要畢業離開的,我怎么忘了?”
“我要走了,你也快點走吧!”我收拾好書包,低頭看著她,“你是我的第一個朋友,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你!”
說完我撒腿就跑,我並不害怕,可是我怕我再繼續待下去,就會不忍心走,那樣我一輩子都離不開那間教室了。
在操場上,我孤零零地回頭望著佇立在天空之下的教學樓。
彼時夕陽西下,如血的夕照之中,有一個女孩正站在我們班的玻璃窗前,像往常一樣朝我擺手微笑。
我笑著朝她揮手告別,背著書包,轉身走出校門。
我的童年時光就這樣宣告結束。許多年以後,我仍然不敢對別人說,在短暫的童年之中,第一個真正令我開懷的玩伴,卻是個沒有生命的鬼魂。
替身
就這樣,我這個出類拔萃的天才總算連滾帶爬地脫離了國小,邁進了國中的大門。
一進學校,我便立刻瞠目結舌,但見走廊上一片兵荒馬亂,學生們端著課桌、夾著板凳在四處奔走。
壯哉!偉哉!
不愧是國中,為了向健康的“四有新人”靠攏,不光是書包和飯盒,連書桌和板凳都要隨身攜帶。
“你在看什麼熱鬧?還不快去搬桌椅!”我正在感慨學校的“分數”與“健康”一把抓的崇高精神,身後就響起了一聲悶雷。
我急忙回過頭去,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皮膚黝黑、平頭板寸的男生站在我的身後。
該君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欣賞,都不像一個國中生,他那滿臉的橫肉都透露著“危險物品,生人勿近”的信號。
“老師好!我是新生。請問是叫我搬桌椅嗎?”依照經驗,這等肌肉發達、四肢健碩的異數多半是體育老師。
“今天是入學考試,不搬桌椅幹啥?教室里坐不下了,新生要在走廊考試。”他看了我一眼,面色一紅,居然飛快地跑到教室里,舉重一樣搬出了兩套桌椅。
“我來!我來!”我伸手就要從他手裡搶過桌子。
“沒事。這點小事,怎么能讓女生動手?”
“那啥……我是男的。”真是倒霉,從小到大,因為這張既不像老爹又不像老媽的臉,我已經不知第幾次被認錯性別。
“早怎么不說?”他虎軀一震,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把兩套桌椅往地上一放,“害老子浪費表情,沒事兒長得不男不女的幹嗎?”
嗚嗚嗚,這能怪我嗎?我出生前也不能就五官樣貌的問題跟老媽商榷探討一下。但是懾於該猛士的淫威,我連半句話都不敢說,乖乖地低頭搬起了桌椅。
半個小時之後,走廊里的座位已經儼然有序,我後背上的汗都沒有乾透,就已經有老師在發放考卷了。
真是倒霉!
我一邊想一邊望向背後,那個體育老師居然坐在我的正後方,看樣子他多半是來監考的。
果然天要亡我啊!居然賜給我這么一個“絕妙”的位置!
可是我眼淚尚未湧出,正在無語凝噎的階段,便聽耳邊“沙沙”作響,身後的那位猛士正雙手舉過頭頂,從老師的手中接下考卷。
我猛地轉過頭,惡狠狠地瞪著他。
但是他卻對我如狼似虎的目光視若無睹,悠然自若地撓了撓腦袋,從文具盒裡拿出一支纏滿透明膠帶、直追木乃伊的破原子筆,慢慢悠悠地在卷子上寫下了幾個扭曲的大字:
初一(三)班 黃智仁
不看還好,這一看頓時令我差點咬碎大牙。氣死我了,這王八蛋居然跟我一樣是學生,還跟我一個班!
怎么剛才我叫他老師的時候,他連臉都沒紅一下?
由於又氣又怒,情緒不穩,導致那些蹲守在教學樓陰暗角落裡的小鬼都聚集到我的身邊,一會兒伸手抓抓我的衣領,一會兒碰碰我手中的筆。
結果我一半的時間都用來驅趕它們,交上去的考卷比我的臉還乾淨。
我再次用事實成功地證明了:天才是不可埋沒的。是金子就永遠都會發光。
一周之後,班級按照成績排座位,我拿著赫然寫著“31”兩個血紅數字的數學考卷站在走廊上排隊,仿佛已經看到了慘澹前途。
“喔,你31,比我多5分。”那位幾乎與中國家喻戶曉的地主老財同名的黃智仁走過來,看了一眼我的試卷,下了這樣的結論。
“是嗎?那你語文多少分?”我的聲音帶著難掩的雀躍,因為看到了一絲曙光。
“72。”
“英語呢?”
“37。”
“看來這次出題比較難。”我總結了一下我們分數的微小差距,作了如下判斷,“所以才普遍發揮不好。”
“就是。我平時根本不可能拿到這么少的分數,國小時我還參加過奧數競賽呢!”黃智仁也極力附和,似乎很贊同我的說法。
然而半個小時之後,我們便雙雙坐到了最後一排,牢牢地霸占了教室的大後方。
“你不是參加過奧數競賽嗎?”我臉色鐵青地瞪著他,“怎么是全班的倒數第一?”
“陳不肖,你還好意思說我?”他用鼻孔哼了一聲,“是誰說‘這次出題比較難,大家普遍發揮不好’的?結果不就是咱倆倒數第一跟倒數第二!”
“你、你叫我啥?”我被他氣得差點去見閻王。
“你不叫陳不肖嗎?我看你學生證上就是這么寫的。”
“我叫陳子綃,你才不肖呢!你們全家都不肖!”
“嘿嘿嘿!”黃智仁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中間的那個字太連了沒看清,最後一個字我不認識,就依照習慣,只念了右半邊……”
我聽他這么一說,立刻一頭栽倒在課桌上,再也不想起來。
這個連大字都不認識幾個的白痴,到底是怎么從國小畢業的?
於是我亂七八糟、雞飛狗跳的國中生活,就這樣在一片人仰馬翻中拉開了帷幕。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天才在哪裡都不會被埋沒的。不到一個學期,我跟黃智仁便雙雙揚名,並稱為整個初一年級的“雙傑”。
任何一項考試,只要有我們倆參加,就一定會把倒數第一和第二收入囊中,時而還要角逐一下“魁首”。
初時老師們被我乖巧清秀的外表迷惑,認為我是被同桌影響,才取得如此糟糕的成績。但是後來他們就不那么認為了,一堂課下來,只要我把嘴巴閉緊,不去用突如其來的尖叫影響別人,他們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大家不要學陳子綃,要均衡發展……”這天又因為答不上題被罰站,歷史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精力全都用在長臉面上,難免頭腦就會有所欠缺。”
真是氣死我了!換成你天天見鬼試試!
一個學期匆匆而過,轉眼就是春意盎然,此時我跟黃智仁已經在老師、同學乃至校長的白眼相看之下,建立了深厚的階級友誼。
每天一到學校,必以綽號互稱,再互毆兩拳,以示友情的堅固。
這日春光明媚,暖意融融,我正伏案假寐,忽聽耳邊傳來一陣刺耳的嘈雜聲。
“老黃!”我受不了地拍案而起,怒道,“你在乾什麼呢?”
“噓——”老黃眨巴了一下小眼,示意我收聲,指了指自己懷裡的鐵鍬道,“我在修鐵鍬,你不要吵大家上自習。”
“你自己弄那么大聲,還怕吵別人?”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修鐵鍬?你要去義務勞動嗎?”
“嗯?你不知道嗎?明天是植樹節,我們全校都要去郊區植樹。該死不死的,哥們我剛剛把這傢伙從家裡扛出來,它就給我造反。”
對了!植樹節!
記得小時候我也參加過。那天在春草初生的樹林中,我看到了一個長得很漂亮但是卻沒有腳的阿姨,還好奇地跟她說了兩句話,結果回家就生了一場大病,差點丟掉半條小命。
“算了,我不參加。”往事沉痛,不堪回首,我心有餘悸地使勁兒搖頭。
“少奶奶!”老黃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勉勵,“咱們學校所有跟體力掛鈎的活動都是強迫性的,你就認命吧!”
怎么聽著不像是植樹,倒像是勞動改造?
事已至此,還能怎么樣呢?我望著窗外的草長鶯飛,長嘆口氣。春天地氣轉暖,萬物復甦,而爬出鬆軟凍土的,則遠遠不只是嫩草小蟲而已。
更有一些深深淺淺、不成人形的影子,會蹣跚地踏著暖意融融的土地,從那遙遠而冰冷的地方,走向繁華人世。
“綃綃!你爸剛才打電話過來啦,有話囑咐你。”晚上放了學,我剛剛蹬著腳踏車到家,就迎上了老媽綻放的笑臉。
“啊?他現在在哪裡?說了啥?”
“他好像跟著一個國家級的考古隊挖墓去啦。”老媽親切地接過我的外套,“你爸說啦,他要求不高,就希望下次回來你能前進一個名次。”
老天啊!趕快賜一個比我和老黃成績更差的轉學生吧!
要知道我跟倒數第三尚隔著十幾個分數段,前進一個名次,不會比昔日搬走壓在勞苦人民背上的三座大山更容易。
“對了!你爸還說了,讓你最近不要到處亂跑。”知子莫若母,老媽見我垂頭喪氣,已然猜到了我鬱悶的根源,急忙岔開話題,“尤其是荒郊野外,千萬不要去!”
這次我的頭垂得更低,背著書包就往屋裡走去。
“綃綃啊,你這是怎么啦?媽媽給你做的雞肉泡飯還吃不吃?”
我轉過身,端起飯桌上熱騰騰、香噴噴的雞肉泡飯,拿起筷子就埋頭苦吃。
不就是植樹嗎?老子就不信這個邪!況且遊魂有萬般,最慘是餓蜉,就算明天要下地獄,也要先吃飽再說!
第二天剛蒙蒙亮,我就頂著春雨,蹬著車往學校的方向絕塵而去。
說來也怪,昨天還晴得好好的天,居然在一夜之間就變了臉。天空都是灰濛濛的一片,綿密的雨絲揮灑而下,春寒料峭,處處滲透著陰冷幽森的氣氛。
奈何在社會主義的新世紀,雖然沒有了封建壓迫,卻有堪比閻羅王的班主任。
於是半個小時之後,我就抱著自己的那桿鐵鍬,坐在顛簸的大巴上,往郊區的荒山上駛去。
車廂前面老師在振臂高呼,大聲宣揚著植樹造林所承載的重大意義;旁邊是老黃與一幫狐朋狗友在使勁兒甩撲克;還有幾個女生嘰嘰喳喳地一直吵個不停,興奮得簡直不像是去參加勞動,倒像是去開聯歡會。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居然靠在搖晃不停的車窗上,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
“快來啊,來啊……”在一片漆黑之中,好像有人在輕輕地呼喚我,那聲音縹緲而遙遠,仿佛來自空曠的山谷。
“去哪裡?”我好奇地向四周望去,發現自己正處於一片繁茂的密林之中,枝繁葉茂,闊葉如掌,連頭頂的藍天都被這鱗次櫛比的樹木遮蔽。
“去你該去的地方……”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與此同時,從大樹後不斷走出一個個面目模糊的黑影。他們都有人的形體,卻沒有人的五官,平平的一張臉上只有兩個黑洞洞的鼻孔。
“我、我該去的地方?那是什麼地方?”我被這奇異的夢境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
然而那些人卻不回答我,慢慢地向我走來,他們的身影重疊瀰漫,仿佛化做一團黑色的霧氣,要將我吞噬淹沒。
……
書摘與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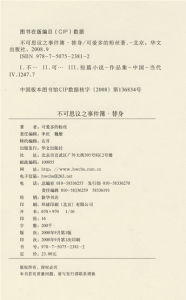 《不可思議之事件簿·替身》
《不可思議之事件簿·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