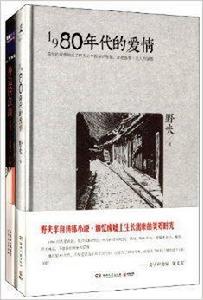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980年代的愛情》編輯推薦:《鄉關何處》作者野夫自傳體小說,帶我們一同追憶廢墟上生長出來的美好時光。
文學評論家敬文東作序推薦;散才毛喻原專供插畫5幅;柴靜、章詒和誠摯推薦。
愛情是一個永恆的話題,野夫用他深沉的情感、唯美的筆觸考驗讀者的淚腺。
野夫痴迷於這個故事已經十年,真實抑或虛構,都漸漸在不斷的質詢里變成了回憶的一部分。回憶也讓野夫日漸明白了這個故事的真正意圖,他用本書來追憶那個隱約並不存在的年代。 《身邊的江湖》編輯推薦:野夫書稿中被刪減最少,最能體現作者觀點、情感的作品。《身邊的江湖》文字凝練,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以一枝孤筆書寫那些就在你我身邊的大歷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變遷。 柴靜口中“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的野夫,以其特有的韻律表達世間的歡笑和悲苦。
作者簡介
野夫,本名鄭世平,網名土家野夫。畢業於武漢大學,曾當過警察、囚徒、書商。曾出版歷史小說《父親的戰爭》、散文集《江上的母親》(獲台北2010國際書展非虛構類圖書大獎,是該獎項第一個大陸得主)、散文集《鄉關何處》(被新浪網、鳳凰網、新華網分別評為2012年年度好書)。半自傳體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散文集《身邊的江湖》同期出版。
圖書目錄
《1980年代的愛情》目錄:
序日暮鄉關何處是
自序讓記憶抵抗
掌瓢黎爺
遺民老譚
亂世游擊:表哥的故事
綁赴刑場的青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
“酷客”李斯
散材毛喻原
頹世華筵憶黃門
球球外傳:
一個時代和一隻小狗的際遇
童年的恐懼與仇恨
殘忍教育
湖山一夢系平生
香格里拉散記
民國屐痕
……
《身邊的江湖》
後記
代 跋
講故事的手藝人
一童年時,曾經跟著父親在一個煤礦,晃蕩過不少日子。
那時國家正在動亂,煤礦一邊批鬥我父親,一邊仍然還是在產煤。運煤的礦車像恐龍一樣哐當哐當從黑森森的礦井裡爬出來,那情景每次都讓我有些驚嚇。各地的煤礦發展到今天,依舊有層出不窮的礦難,就不要說那時我父親管的國營小煤礦了。不斷有一些倖存者變成了殘疾人,聚居在礦山的小醫院裡,年紀輕輕就開始養老。
每個人都會驚嘆歲月如梭。但對於那些健康的青年,忽然就瞎眼或跛足了;很早就開始要向暮年一瘸一拐地摸索前進,那確實是一場十分漫長的折磨。
他們吃飽喝足,百無聊賴,對病房之外的階級鬥爭已然毫無興致。他們甚至互相之間都有些厭倦,彼此偶爾還會嫉妒對方身上尚還健全的一些部件。最後,他們幾乎唯一的興趣,就是對我這個時而到訪的孩子講故事。
現在回頭看來,一個人洞穿了自己的未來之後,剩下的就是對往事、故事的熱衷了。在那些可以短暫遺忘傷痛的回顧中,他們似乎開始暗中較量記憶和敘述的能力。比如同樣講水滸,每個人接著一回一回地說,結尾都是且待下回分解,但前面的敘事那真是高下立判。
而我最愛聽一個姓陳的跛子擺古。他是一個端公(土家族巫師)的兒子,講江湖豪傑能把一個孩子聽哭,我從他這裡最先迷上了“故事”。以後,在同樣漫長的成長中,我也開始悟出了一些講故事的手藝。
二在我們那個偏遠蠻荒的武陵山區,民國年間曾經從湘西那邊走出去過一個青年,他叫沈從文。他沒有上過大學,到了北京的胡同大雜院賃居,冬天拖著鼻涕就開始寫作。那時新文學運動開始不久,所謂的各種文體,還沒有後來的各種教材規定的那么嚴格。他投稿換錢,自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的故事很快打動了很多人,因為白話文里還沒有這么一個獨特的支脈。那時的報紙副刊發表,也不分類註明他寫的是什麼體裁。大家覺得文風獨特,好看,就能贏得青眼和喝彩了。
他留下了太多好文章、好故事,當代的人再為他編輯出書,常常茫然於不知道怎樣為其中一些文章分類。比如《阿金》,比如《田三怒》,一會兒收進他的散文集,一會兒又收進他的短篇小說集。因為在他這裡,就是故事,你很難分清文體的區別。這樣文章的好,也就是敘事語言本身好,講故事的手藝好。你要論故事本身,實在是簡單至極。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名著,終將巍然屹立到遙遠。一對鄉下爺孫相依為命的生活,還有兩兄弟隔著河水在對岸遠遠地暗爭暗戀。這兩個男人幾乎都沒怎么出現在字面上,最後都沒愛成,姑娘獨自留在了岸上。就這么簡單的故事,被先生講得水遠山長,讀得人柔腸寸斷,千古悵然……
有這么一部《邊城》擺在那裡,使得多少人兀自汗顏,不敢輕碰中篇故事了。
三我這裡以“我”的名義,講述了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
這兩年流行著美國小說家雷蒙德·卡佛的一本書——《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面對這一名言,我也時常在質問自己,在全世界無數最精巧的愛情故事面前,你敘述的愛情,究竟想要表達什麼?難道僅僅是男歡女愛的又一次感動?
愛情,在今天這一奇怪的時代,儼然已經是一件羞於啟齒的俗事。談論它或者寫作它,似乎都有點恬不知恥的味道。這件本應嚴肅的事情,忽然變成了昆德拉筆下的“好笑的愛”,如果再來講一個老套的悲情故事,是否完全不合時宜呢?我痴迷於這個故事已經十年,真實抑或虛構,都漸漸在不斷的質詢里變成了回憶的一部分。對了,就是回憶,使我日漸明白這個故事的真正意圖,是在追憶那個隱約並不存在的年代。
我們這一輩人從那個被淹沒的年代穿越而來,即便桂冠戴上頭頂,但仍覺荊棘還在足尖。多數的日子看似謔浪風塵,夜半的殘醉淚枯才深知內心猶自莊嚴。一個世紀中唯一凸顯乾淨的年代,讓我輩片葉沾身,卻如負枷長街。每一次回望,都有割頭折項般的疼痛。我知道,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最終是在薄奠那些無邪無辜無欲無悔的青春。
事實上,每一個年代的愛情,都有各自的歷史痕跡。50年代的單純,60年代的壓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覺醒和掙扎……再看看90年代的頹廢和新世紀以來的嚴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證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世界上多數人的愛情,都是為了“抓住”。抓住便是抵達,是愛情的喜宴;仿佛完成神賜的宿命,可以收穫今生的美麗。我在這裡講了一個不斷拒斥的故事,這是一個近乎殘酷的安排,乃因這樣的愛不為抵達,卻處處都是為了成全。這樣的成全如落紅春泥,一枝一葉都是人間的憐憫。
正因當下的不可思議,才覺得這樣的愛情太過虛幻。古舊得像一個出土的漢鏡,即便鋥亮如昨,世人也是不欲拿來對鏡照影的——那容易照見此世的卑微猥瑣,和種種不堪。
四
懷舊,是因為與當下的不諧。才過去二十幾年的風物,一切又都恍若隔世。我們不得不坐在時光的此岸,再來轉顧那些逝去的波濤。
一般來說,每個作品都隱含著作者自己對歷史的理解,以及同情和紀念。這樣一個簡單的故事,不太容易承載太多的人物命運。但是,即便是一晃而過的那些草根小人物,同樣寄託著我的生活、閱歷和理解。那個曾經奉旨造反的老人,那個做飯的平反“右派”,無一不是源自於那個時代的草野。正是這些沒名沒姓的悲劇人物,構成了我們的當代史。
昆德拉說:一切造就人的意識,他的想像世界,他的頑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形成的,而且保持始終。
我這一代人之所以始終無法超越80年代,也因為那個光輝歲月,給了我們最初的薰陶和打磨。那些被發配流放和無視的長輩,都活在那時。他們給了我們認識世界的遺訓,使得我們不再蒙昧於天良。而今,那一代已經凋謝殆盡,而我們也開始要步入殘陽斜照了。我在半生顛沛之後,重新拾筆掌燈之際,生命似有慌張奪路之感。翻檢平生,找尋那些殘破的人世經驗,仿佛僅為提示後生者——我們確實有過那樣近乎虛幻的美,哀傷孤絕,卻是吾族曾經的存在。
2013年當我來到德國科隆,與少年時就從詩歌中熟悉的萊茵河朝夕相對時,我忽然再次想起了這個故事。我很少有這樣的安靜時光,獨酌在花樹之間,徜徉於那亘古之河流岸邊,遙望祖國曾經的悲歡。我覺得該要完成這樣一次訴說,與水聲合拍的娓娓道來,傷悼那些不復再現的往昔歲月。
這樣的懷舊是如此簡單樸素,在那被打開的歷史摺扇上,仍然還有風聲如怒。
如果這樣一個沒有太多懸念的小說,還能被今天的讀者理解和垂賞,那是我的榮幸,更是意外之喜。謹在此,感謝孕育了這些人物和故事的故鄉;感謝所有寬容的讀者;感謝青眼有加的編輯和出版社。還要感謝科隆世界藝術學院,是他們給了我一個短暫安寧思考和寫作的機會。
野 夫
2013年春天於科隆萊茵河畔
序言
廢墟上生長出來的好時光
敬文東
土家人野夫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文革”中當過少年樵夫,“文革”後,上過一所三流大學和一所名牌大學,當過公務員,做過像模像樣的警察。身為體制內前途一片光明的幹部子弟,後來卻被時代風暴吹打成了“牢頭獄霸”。在獄中,他奇蹟般地和一些獄卒結為朋友,在勞改隊導演春晚,並在當年首創犯人圖書室。出獄後,他為謀生而成為著名書商,兢兢業業戰鬥在民間出版發行的渠道。
他還乾過很多職業,經歷過太多江湖生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與他交往有很長一段時間,只看出他縱酒貪杯,熱情豪邁。但都不知道,野夫還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詩人和作家——也許,這才是他被遮蔽多時的老本行和舊身位。
新世紀以來,野夫寫下了一批力透紙背、光彩奪目的文章——《地主之殤》《組織後的命運》《墳燈》《江上的母親》《生於末世運偏消》《別夢依稀咒逝川》《革命時期的浪漫》……這些文章旨在通過自己與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際,揭示曾經的時代是如何摧殘寶貴的人性,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蠶食中國人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價值觀念。
這是一種惹人深思、讓人久久無法釋懷的文字,這是一種催人淚下,卻只能讓讀者一個人向隅而泣,並經由暗中的淚水透視慘痛歷史的文字。漢語的光芒在野夫筆下得到了恢復,得到了張揚;誠實、誠懇,而又無比節制。但讓人驚訝的是,即使在述說慘痛至極、壓抑至極的故事,野夫的文字也無比靈動,毫無凝滯之態,有一種風行水上的感覺,頂多是飄逸、嚮往自由的風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
沉重和土地有關,飄逸則同天空連在一起,這是漢語當仁不讓的兩個極點。野夫充分展示了漢語的土地特質與天空特質,他的文字是土地與天空按照某種比例的神奇混合。中國的歷史太沉重,土地特質因此始終是漢語的焦點;漢語的天空特質則必須受制於它的土地特質,漢語的天空始終是同塵世相混合的天空,是被土地震懾住的天空。
野夫深諳漢語的兩極性,而漢語的兩極性則為他的寫作對象提供了絕好的對稱物和衍生物。聽命於語言,但更應該聽命於情感,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歷史成分:野夫恢復了漢語內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質,經由這些品質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種被官僚體制蹂躪了多年的語言。
熟悉野夫傳奇生涯的朋友或許都知道,完成於德國科隆的中篇小說《1980年代的愛情》,不過是對一個真實故事有限度的加工、改寫和潤色。詩人趙野和野夫相交甚深,他在他寫野夫的散文中,曾經旁證過與此相關的那個原型。在他看來,現實中的那個女主人公,“雖然歲月滄桑,韶華已逝,眉宇間幾分英氣尚存”。
1980年代的青澀青年如今已到霜鬢中年;1980年代的初戀如今早已成為回憶的對象:它是那個年代過來人記憶深處的隱痛。辛波絲卡有一個非常好的詩句,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我為將新歡視為初戀向舊愛致歉。”滄桑感是時間給予有心人的饋贈品。
野夫在德國科隆訪學的不眠之夜,回望遺留在祖國的青春和初戀,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過來人都願意承認,1980年代是奇蹟,是共和國歷史上罕見的清純時代,是廢墟上生長出來的好時光。那時,野夫年輕,愛情更年輕;那時,野夫純潔,不敢褻瀆神聖的愛情。在1980年代,拉手、在夕陽或月光下散步,是愛情的萬能公式。蔑視權貴和金錢,崇尚才華和藝術,則是愛情的最低標準。不像現在,一切都需要貨幣去定義。因此,前世的愛情構成了野夫心中隱秘的驕傲,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驕傲。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為了給今天療傷,還是為了諷刺今天,或是為了給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顯然,野夫算不上虛構能人,他僅僅是一位非虛構敘事的大內高手。幸運的是,他的傳奇經曆本身就是小說,在貧乏無味、缺少故事的我輩眼中,已經是結結實實的虛構。
《1980年代的愛情》之所以感人至深,很有能力挑逗讀者的文學味蕾,考驗讀者的淚腺,仰仗的不是故事情節的複雜(故事情節一點都不複雜),而是野夫對漢語兩個極點的巧妙徵用:在需要天空特質的時候,他讓讀者的心緒飄忽起來,沉浸在對初戀的回憶之中,輕柔、感傷和對遠方的思念統治了讀者。在需要土地特質的時候,他讓讀者的心情向下沉墜,沉浸在對那段荒誕歷史的思考之中,漫無邊際的沉重統治了讀者;野夫在小說敘事中,對天空特質和土地特質毫不間斷地交錯使用,按摩著讀者的心緒,讓他們從頭至尾都處於坐過山車的狀態,腎上腺素居高不下,配合著、應和著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
對漢語兩極性的重新確認和巧妙使用,是野夫迄今為止全部文學寫作的最大特色,是他有別於所有其他中國作家的奧秘之所在。也是他以區區數篇文章和少量小說,就徹底征服許多讀者的秘密之所在。放眼中國,或許找不出第二個人會像野夫那樣,如此看重和依靠漢語的兩極性,甚至是過度開發和使用漢語的兩極性。這讓他的文字像書法中的魏碑,古拙、奇崛、方正、守中,從表面上看毫不現代,但無限力道卻盡在其間,以至於能夠寸勁殺人。
《1980年代的愛情》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說的邊界,它讓讀者越過故事,直抵語言的核心部位——讓讀者欣賞的是語言本身,而不僅僅是過於簡單的故事。這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錢鍾書的《圍城》,如果沒有語言自身的狂歡、撒野和放縱,《圍城》恐怕連三流言情小說都算不上。如果沒有魏碑式的語言從旁壓陣、助拳,作為小說的《1980年代的愛情》該會多么單薄。和《圍城》一樣,《1980年代的愛情》也以對語言自身的開採,為自己贏得了應有的地位。
2013年5月8日 北京紫竹院
名人推薦
1980年代是奇蹟,是共和國歷史上曾經的清純時代。那時,野夫年輕,愛情更年輕;那時,野夫純潔,不敢褻瀆神聖的愛情。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為了給今天療傷,還是為了諷刺今天,或是為了給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文學評論家 敬文東
野夫筆下那些美妙溫軟的情感,是怎樣被一陣一陣的風雨沖光刮淨——我讀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淚。那獨立之姿,清正之氣。令我心生莊嚴。
——章詒和
野夫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他天性愛憎好惡比常人劇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氣力,不留餘地,蠻力拽動情與仇,樂與怒;他對這個時代總有一份“不忍心”;他的一生,多為激情支配的選擇,最痛苦的是內心與外物不調和。
——柴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