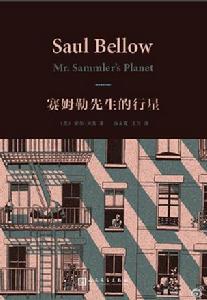內容簡介
該小說主要以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市上西區為背景。主人公是一位70多歲的老人阿特·賽姆勒,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猶太人大屠殺中的倖存者。
清晨,賽姆勒先生剛剛醒過來,躺在床上,想起了在公共汽車上遇到的黑人扒手。接著,賽姆勒先生應朋友弗菲爾的邀請到哥倫比亞大學給學生們做演講,然而卻被一群激進的年輕人羞辱了一番。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一次在公車上目擊了那位黑人扒手偷竊的過程。這一次那個扒手也發現了他,就尾隨這個老人到了老人的公寓樓下。
扒手將老人困在角落裡,並且解開自己的褲子以自我暴露的方式來威脅老人。惶恐的賽姆勒先生回到家中,打開房門,發現床上放了一本題為《月亮上的生活》的手稿。這本手稿是一位來自印度的訪問學者高文達·拉爾博士的。賽姆勒先生讀著它,忘記了讓人恐懼的經歷。沒過多久,他被親戚華爾特·布魯克的不期而至所打擾。這次布魯克向這位年邁的老人傾訴他對女人手臂的迷戀。布魯克怪異的性傾向讓賽姆勒先生聯想到了伊利亞·格魯納的浪蕩女兒安吉拉·格魯納。
第二天,賽姆勒先生到醫院看望他的侄兒伊利亞·格魯納醫生。這位醫生因為頸部手術住院治療。在病房外,格魯納醫生的兒子華萊士想讓這位老先生幫他去問父親格魯納一筆秘密的現金藏覓的地方。據華萊士說,那些現金是格魯納替黑手黨辦事的酬金。離開醫院,賽姆勒先生在附屬檔案的公園看拉爾博士的手稿,這時弗菲爾找到了他。
賽姆勒先生獲悉他的女兒蘇拉被懷疑偷竊了拉爾博士的手稿,於是他在紐約城裡四處尋找蘇拉。找不到女兒的蹤影,賽姆勒先生只好讓瑪格特前往拉爾博士的住處。這期間,他又到醫院探望侄兒格魯納。格魯納睡了,安吉拉坐在病床邊。賽姆勒先生從她的談話中得知蘇拉的前夫艾森從以色列來到紐約。瑪格特打來電話說拉爾博士的手稿從公寓不翼而飛了。賽姆勒先生匆匆結束了跟剛剛醒來的格魯納的談話,就和華萊士一起坐車前往格魯納在郊區的別墅。因為賽姆勒先生認為蘇拉可能帶著手稿逃到那裡去了。他果然在別墅找到了蘇拉,只是手稿被蘇拉鎖在了市內的大中央車站的公共櫥櫃裡。接著,瑪格特和拉爾博士也到了別墅。賽姆勒先生和拉爾博士暢談一番。不想華萊士在搜查秘密現金的時候弄破了水管,別墅水漫成災。
次日清晨,賽姆勒先生搭乘格魯納醫生的私家車到醫院探望格魯納。在經過林肯中心的路上,他看到弗菲爾和那個黑人扒手在搏鬥。而艾森用滿袋的鐵器狠狠地擊中了那黑人的頭部。
賽姆勒先生匆匆趕到醫院,卻只看到一張空床。他一邊和安吉拉一起等著格魯納回到病房,一邊勸說安吉拉向她父親懺悔自己的放蕩行徑,安吉拉十分惱怒。這時電話響起,原來是拉爾博士找到了手稿。蘇拉也在無意中找到了格魯納醫生的秘密現金。小說的最後,賽姆勒先生被告知格魯納醫生已經去世。賽姆勒先生到太平間,站在格魯納面前,一個人跟上帝說話。
創作背景
社會背景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20世紀美國社會與文化變遷最大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充滿了衝突和矛盾的多事之秋:新的和舊的、左的和右的、老的和少的、窮的和富的、黑人和白人、激進的和保守的、主流和反主流、美利堅和前蘇聯、戰爭與反戰、軍備競賽、太空競賽、人權運動、學生運動、婦女解放,對立與衝突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最主要的特徵。
作品背景
該小說主要以20世紀60年代的紐約市上西區為背景。
貝婁在該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20世紀歷史見證人的形象,一位波蘭籍老派猶太知識分子阿特·賽姆勒,他是德國法西斯集中營的一個倖存者。貝婁在《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一書中表現出來的他對所處歷史時期的態度可以描述為在記憶和歷史之間左右為難。20世紀60年代後期風起雲湧的所謂“新左派”抗議浪潮和年輕人種種離經叛道的激進主義思想與行為,特別是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的頻發,讓作者感到以理性主義為基石的傳統思想文化似乎呈現出了第二輪崩潰的趨勢,從而對過去體面社會的文雅生活和秩序產生留戀之情。
人物原型
阿特·賽姆勒的人物原型:索爾·貝婁
文本中涉及與描述的許多事件和場景都是作者本人親歷或有據可查,如對中東“六日戰爭”的戰地報導,他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的講座,作者對自己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20世紀著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惡乃平庸”理論的抨擊,作者本人對紐約城的厭惡等等都在《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小說中有所體現。貝婁通過賽姆勒先生這一人物向人們表明了他對這一時代的態度:“我們就處於同無法無天相近的境界”,公用電話間變成了小便池,電話機早就被砸碎了,“紐約變得比那不勒斯或者薩洛尼卡還糟,你打開一扇嵌著寶石的大門,就置身在腐化墮落之中,從高度文明的拜占庭的奢侈豪華,一下子就落進了未開化的狀態,落進了從地底下噴發出來的光怪陸離的蠻夷世界。”
主要人物
阿特·賽姆勒
賽姆勒來自波蘭,一個在二戰期間猶太人口聚集的國家,一個在二戰中很快淪為納粹鐵騎之下犧牲品的國家;他是記者,處於知識分子階層,對於時代的變遷有著特殊的敏感性,並能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作如實報導;他親身體驗過集中營生活並在大屠殺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自身的遭遇讓他成為一個最好的創傷“言說者”。他的聲音游離於集體的歷史和猶太人的生存現狀。“集體是由個體組成,集體的凝聚力是通過傾聽個體講述創傷故事來獲得的。”賽姆勒是經歷二戰千千萬萬猶太裔受害者中的一員,他以個人創傷經歷承載著本民族創傷記憶,這份經歷意味著共同經歷,共同分享及共同面對。賽姆勒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雖然傷痕累累,年事已高,他與年輕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傾聽他們的述說並與他們分享經歷和經驗,樂於幫助他們,成為猶太小團體的核心。他是格魯納的猶太長輩,給他講家族的故事;他是大學生弗菲爾的良師益友,接受邀請出席演講;他是安吉拉和華爾斯的傾聽者,幫助他們糾正叛逆行為;他是女兒蘇拉的精神支柱,擬寫一本回憶錄幫助她重建自己的童年美好記憶;他是內侄女瑪戈特的親信,幫助她走出自我封閉的世界。他像猶太先知一樣,告之年輕小輩猶太人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是可靠信息的來源,智慧的開啟者,前途的引導者,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不懈努力告誡後輩如何正確地對待歷史遺留創傷,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創傷是可以被治癒的。
黑人扒手
黑人扒手是一個高大強壯的黑人,穿戴極其講究雅致,穿著駝絨上衣,繫著櫻桃色真絲領帶,戴著黃金鑲邊的、龍膽紫色滾圓的深色太陽鏡,身上還散發出法國香水的氣味,他那張臉流露出一隻巨獸的厚顏無恥。“黑人扒手”體現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現實狀況縮影,是性和暴力的混合體。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主題思想:不忘猶太族裔留下的群體創傷歷史,反思歷史,修復歷史創傷。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主人公賽姆勒在經歷大屠殺創傷事件後,無法從陰影中自拔,從而在生理、認知、情緒、行為層面形成障礙,不能正常地面對生活。他不願意面對多年前的創傷事件,無法訴說並且企圖逃避,形成了潛意識的自我壓制,而結果就是生活在不安和持續的無語之中,但具有堅韌毅力的二戰猶太裔倖存者賽姆勒通過主觀的努力,積極地進行著自我療傷。
生理層面
賽姆勒有周期性的頭痛,好幾天說不出話來,這是典型的神經系統受損表征。在二戰中,他和妻子都被關進集中營,他的一隻眼被士兵用槍托打瞎,並和所有的同伴一起被剝去衣物,赤條條地奉命去挖土,等待深坑挖好時,傳來的是機槍的掃射聲,賽姆勒眼見著身旁的人一個個倒下,接著他感受到泥土的重壓和鐵鏟摩擦的聲音,這次被活埋的經歷使得賽姆勒患上了頭痛病,這是一種對聲音的恐懼留下的後遺症,槍托重擊腦子使得他腦神經受損,機槍的掃射聲,鐵鏟的摩擦聲不斷地在他腦子裡迴響,形成對腦子的刺激,在暴力和死亡的威脅超過他的承受限度時,形成了一種反射狀的頭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賽姆勒被好心的老謝斯拉愷維茨守墓人收留了,他用帽子給賽姆勒帶去吃的和喝的。為了保住性命,賽姆勒按照守墓人的安排,被迫呆在梅茲文斯基家族的陵墓里,黑暗、孤獨、恐懼圍繞著他。失去妻子的痛苦,長時間的等待和渺茫的生存希望時刻折磨著他,他在絕望中,痛苦的回憶中消磨了好幾個星期的時光,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劫後餘生,但他患上了間歇性的失語症。他周期性的頭疼和一連好幾天說不出話的情況必須在他獨自呆在黑屋子裡好幾天才能好轉。
黑屋子具有了雙重象徵性的意義,一方面黑屋子是對當初他暫棲墓地的情境再現,只有回到當初創傷形成的地方,徜徉幾日時光後,才能暫時恢復語言功能。另一方面呆在黑屋子裡也是賽姆勒在體會妻子常埋地下的感覺。“當她蹣跚晃動時,設法幫助她;憑藉一聲不言語地挖掘,他設法傳達給她一件什麼,使她堅強起來。但是結果竟然是,他使她準備好接受死亡,而自己卻沒有死。”他讓妻子坦然地接受了死亡,而自己卻怯懦了,求生的欲望讓他自己活了下來,試想他如果當初傳遞的是正面積極的戰鬥情緒,說不定妻子能和他一樣活下來。賽姆勒深深地感到愧疚,只有在黑屋子裡體會妻子死亡時的感覺,經過黑屋子對死亡的情境模擬,他才能恢復常態。
認知層面
賽姆勒在扎莫希特森林裡伏擊了一個德國士兵,他毫無憐憫之心地槍殺德國士兵,這個無辜的德國士兵並沒有危及他的生命,並且他表示身上的所有東西都可以給賽姆勒,只要留他一條命,家有老小需要照料,但賽姆勒被復仇的情緒所淹沒,對周遭的人也採取了一種過度警覺的態度,他盤算著他和德國士兵來自兩個不同的陣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他錯誤地把這個單個的德國士兵看成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縮影,賽姆勒對法西斯施於手無寸鐵的猶太民眾暴行的仇恨直接演變成了他對德國士兵的仇恨,“為了這個機會,他本會感謝上帝的,倘使他心中有任何上帝的話,那時候他心中並沒有上帝”。
眾所周知,猶太人篤信上帝,很難想像一個猶太人會說他心中沒有了上帝,究其原因,可分為兩方面:
一種解釋是他認為沒有上帝的存在,因為如果有上帝,與猶太先祖簽訂契約的上帝如何能不顧他的後裔滅種的威脅,所以他感覺自己被愚弄了,這正與尼采的“上帝已死”的論斷相契合,社會變得混亂,邪惡沒有受到懲罰,而善良沒有受到嘉獎,信仰缺失。
第二種解釋是他憎惡上帝,上帝沒能充當猶太民族的保護者,他違背了契約,而置猶太民族於不顧,所以這樣的上帝有和沒有是一回事,即使有上帝也不是那個維護他們利益的上帝,所以他說他心中沒有上帝。他沒有把上帝放在心上,也自然沒有了上帝所告誡的“不可復仇”的戒律,他的道德審判之心被蒙蔽了。賽姆勒所受的創傷部分地改變了他的信仰,看待世界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再者,他也發現了自己與周圍環境的不協調。年邁的賽姆勒被侄子格魯納帶回了紐約,該享受安逸晚年的賽姆勒感到他與同類分離了,被割斷了聯繫,這種斷裂感不是來自年齡的懸殊,而是因為“他專心志致於那些不相同和太遙遠的事物了,在精神方面專心志致於同當前不相稱的那種柏拉圖式的,奧古斯丁的十三世紀了。”他沉迷於過去的歲月,那種懷舊的情緒久久不散,讓他很難理解當代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但奇特的是賽姆勒沒有變成年輕一輩眼中討人嫌的老古怪,他是一個極富耐心的聽眾,能夠聽進各種言論而不反駁。侄子格魯納的女兒安吉拉是個不安分的性開放主義者,她露骨地在這位長輩面前描述她的性體驗和種種怪癖。侄子格魯納的兒子不學無術,耽於幻想,他把賽姆勒當成哥們兒,跟他胡侃自己的種種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兩個年輕的小輩都跟自己的父親有隔閡,而唯獨跟這位老長輩無話不談。歲月的磨礪讓賽姆勒收斂住鋒芒,展現的是一位飽經世事老者的虛懷若谷,在他眼裡這些成長的“痛楚”只是“無病呻吟”,是他大風大浪一生經歷中的九牛一毛,他以長輩的博大情懷接納了這些小輩的“不堪”,在傾聽小輩們的煩惱中,賽姆勒找到自己的角色———成為他們成長道路上的引路人。
情緒層面
小說中賽姆勒經受妻子離世,生死離別的痛苦後,就沒再結識新的異性,重新組織家庭。實際上遭受過致命打擊後,賽姆勒已經失去了一個正常人應有的對生活的信心,他變得怯懦,容易產生焦慮情緒。在公車上遇到了黑人扒手,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應該去報案,他發現了惡,並且希望這種惡不再繼續,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他給公安局打去報警電話,並表示自己願意當面指認,然而得到的答覆是:下次再說吧。警察的置若罔聞削弱了賽姆勒懲奸除惡的決心,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對警察抱有不滿,而是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小題大做,他缺少了應有的自信,而變得怯懦。接下來的一件事更是讓賽姆勒心有餘悸:在一次失敗的演講結束後,那個黑人扒手緊隨著他去往地下通道,並把他逼到角落,用身體頂住賽姆勒不讓其動彈,並掏出生殖器逼迫賽姆勒直視。賽姆勒被徹底“征服”了,他再也沒有反抗的決心了。
黑人扒手用力量、性器官在作威脅,其實是嘲笑賽姆勒的衰老和無能,影射賽姆勒被閹割的形象。無獨有偶,青年學生弗菲爾常常說他愛戴這位老人,因為賽姆勒讓他想到戀母情節。戰爭的後遺症使賽姆勒失去男子氣概,被女性化,他被閹割的形象也說明了創傷對於他身心的重大打擊。創傷一旦形成,個體會變得脆弱,易受到其他事物的攻擊,情緒易受別人控制。然而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希望再次面臨黑人扒手偷竊的現場,目睹惡的再次發生,還有就是那個黑人扒手的私處一遍又一遍地在他腦海中閃現。同一件事不間斷地以片段的方式讓受害人回到創傷發生的現場,這是創傷暴露的過程,也是受害人在企圖慢慢地接受事實。事件縈繞在心頭,難以忘懷,是強化的過程,也是接受的過程。賽姆勒不斷地回到犯罪現場,他主動地通過閃回來復原事情的全過程,以自己的所見所聞再次體會惡,是剝離、審視,也是一種療傷過程。
行為層面
賽姆勒有兩個宏願:一個是撰寫《赫·喬·威爾斯回憶錄》。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George Wells) 是英國著名的作家、新聞記者。威爾斯是唯一一個在當時賽姆勒與之走得比較近的歷史名人,撰寫關於他的回憶錄,是緬懷往昔風華歲月。當時年輕的賽姆勒夫婦出入名流場所,如魚得水,風華正茂。而戰爭奪取了所有讓他自豪的資本,留給他的是一副病態的身體和飽經創傷的心靈,遲暮之年他想像著回到那個人生的鼎盛時期,撰寫這樣一本回憶錄是賽姆勒的一種逃避態度的外顯,他企圖讓時光停止在那個階段,而把痛苦的戰爭經歷直接抹煞掉。
賽姆勒的另一個宏願是去往月球,月球有充分的發展空間,人類可以在那裡開闢新天地,發掘新能源,種植農作物,建造宜居的場所。賽姆勒對月亮的神往是對烏托邦理想世界的一種文學想像,影射出的含義是對地球的無盡失望,這個地球因為人類的貪慾和戰爭變得滿目瘡痍,潰爛到不適合再居住的程度。因此,賽姆勒對月球的嚮往是一種消極的“出世”主義,躲進文學想像中,不願意與這個骯髒的世界同流合污。
雖然有退縮和迴避的一面,賽姆勒也積極地選擇了“入世”來削弱自己的創傷。作為猶太民族一員親身經歷了二戰的災難,他隱隱地覺得他存活下來一定有某種“任務”。“奉派去解決某種事情,用淺短的目光把某種經驗的精華壓縮起來,並且由於這一點,還把某種傑出的才能歸到了他身上”,1967年中東地區爆發了六日戰爭,賽姆勒以70多歲高齡記者的身份親臨以色列,進行新聞報導,他要弄清楚,是什麼原因讓其他民族對猶太民族抱有成見,從而使得猶太民族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這次新聞報導是一次積極的療傷過程,他選擇了直面問題,並且再一次擔當記者的身份,親臨戰爭現場,以親眼所見所聞,來展現事實本身。在受害者選擇再一次回到受害現場時,他實際上在心中已經接受了那一段痛苦的往事,創傷得以治癒,正常生活得以回歸。
個人創傷與集體創傷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一部正面回應他對二戰態度的作品,是對猶太淵源的一次回歸。《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可以看作是貝婁長期壓抑、企圖迴避的創傷情節,以文學作品的形式進行外化的產物,該小說不單單是貝婁刻畫的主人公賽姆勒治癒創傷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貝婁自己一次創傷治癒療法。並且在更廣泛意義上,是貝婁對戰爭中無辜死去的猶太同胞的緬懷,對猶太這個集體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反思。他通過文本建構賽姆勒個人創傷的同時,也是在衍射二戰中猶太族裔經歷的集體創傷。因此,該部作品是作家一種主動的、自覺的創傷反思,旨在幫助猶太族裔修復創傷。
雖然創傷事件對於集體的創傷不如個人創傷來得那么震撼和強烈,卻比個體創傷更加深入和持久,它破壞了原有的集體信念及價值。文本中在美國生活的年輕輩猶太人試圖掩蓋自己的猶太身份,對他們來說,猶太身份約等於苦難、被排擠、成為替罪羊。他們已經沒有了早祈和晚祈的習慣,安息日也不上猶太教堂。集體組織的活動有利於凝聚集體意識,集體參與的傳統節日有利於延續共同的信仰,從這方面看,年輕一代猶太人集體意識淡漠,更多的是想隱去自己的猶太身份,投身到美國大熔爐的懷抱。
然而,忘卻歷史與身份的新生代猶太人在美國卻找不到方向,猶太裔大學生弗菲爾變得唯利是圖,醫生格魯納急功近利,安吉拉亂性,華萊斯不學無術,耽於幻想,賽姆勒的女兒蘇拉沉迷於收集各種垃圾,賽姆勒的內侄女瑪戈特封閉自我。集體記憶被隱沒了,群體中缺乏了心靈的交流,“人們慢慢意識到集體不再作為一個有效的支持來源而存在,而與之相連的自我的重要的一部分已經消失了”。缺乏集體意識的人們顯然是各自“生著病”,貝婁暗示
二戰創傷對集體意識的破壞和傷害。年輕一代猶太人脫離了猶太古老傳統和智慧的引導,企圖逃避自己的歷史使命和責任,變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貝婁刻畫出賽姆勒這樣的二戰見證者有著明顯的寫作意圖。首先,賽姆勒具有代表性,他來自波蘭,一個在二戰期間猶太人口聚集的國家,一個在二戰中很快淪為納粹鐵騎之下犧牲品的國家;他是記者,處於知識分子階層,對於時代的變遷有著特殊的敏感性,並能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作如實報導;他親身體驗過集中營生活並在大屠殺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自身的遭遇讓他成為一個最好的創傷“言說者”。他的聲音游離於集體的歷史和猶太人的生存現狀。“集體是由個體組成,集體的凝聚力是通過傾聽個體講述創傷故事來獲得的。”賽姆勒是經歷二戰千千萬萬猶太裔受害者中的一員,他以個人創傷經歷承載著本民族創傷記憶,這份經歷意味著共同經歷,共同分享及共同面對。賽姆勒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雖然傷痕累累,年事已高,他與年輕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傾聽他們的述說並與他們分享經歷和經驗,樂於幫助他們,成為猶太小團體的核心。他是格魯納的猶太長輩,給他講家族的故事;他是大學生弗菲爾的良師益友,接受邀請出席演講;他是安吉拉和華爾斯的傾聽者,幫助他們糾正叛逆行為;他是女兒蘇拉的精神支柱,擬寫一本回憶錄幫助她重建自己的童年美好記憶;他是內侄女瑪戈特的親信,幫助她走出自我封閉的世界。他像猶太先知一樣,告之年輕小輩猶太人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是可靠信息的來源,智慧的開啟者,前途的引導者,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不懈努力告誡後輩如何正確地對待歷史遺留創傷,並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創傷是可以被治癒的。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以賽姆勒創傷形成及修復為線索展開的文本,文本再現了主人公作為猶太個體所經歷的大屠殺歷史及給他所帶來的創傷:包括生理、認知、情緒、行為方面,創傷之重以至於部分地改變了他的行為處事方式、情緒控制能力,造成信仰動搖,道德判斷能力缺失。同時潛文本見證一段塵封的記憶,展示二戰對整個猶太民族的精神與集體意識的破壞,該部小說也是一部關於猶太民族集體創傷的作品。
賽姆勒以自己寬廣的胸襟,堅強的忍耐力,積極的“入世”行為來治療自己的創傷,經歷了見證創傷———反思創傷———治療創傷的歷程,並以自己的努力承擔起猶太文化傳承者的角色,幫助年輕一輩猶太人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正視自己民族的過去,勇敢地進行創傷反思。貝婁構建文本,正視自己潛意識的種族創傷,以點及面地以賽姆勒個人視角展現二戰對於猶太族裔留下的群體創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創傷已經形成,要做的是如何積極治癒創傷,反思並且避免創傷事件的再次發生。猶太民族需要重新認識大屠殺,反思創傷,並慢慢地修復創傷。貝婁是在傳遞一個信息,指明猶太人的發展方向:不能忘卻歷史,要反思歷史,修復歷史創傷,著眼當下。
藝術特色
疾病敘事
在《賽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疾病敘事的特徵突出地體現在主人公賽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和格魯納的病危這一核心事件上。
首先,小說的主人公賽姆勒先生是一個病患式的主體,小說主要藉助對該人物的刻畫來展開對社會的批判。賽姆勒先生出生於波蘭的一個富有家庭,當過駐英國記者,二戰在波蘭期間遭遇過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歷經戰爭與磨難,一隻眼睛已失明。小說開篇便提到“阿特·賽姆勒先生睜開他濃眉下的那隻獨眼,察看他在紐約西區那間臥室里的書籍和檔案”,突出了其病患身份。從文學的角度而言,這個病患主體的構造用意頗深,從多方面深化了作家所要作的社會批判。
其一,賽姆勒先生的眼睛給讀者提供了看世界的獨特的視角。賽姆勒先生只有一隻眼,他只能從一個角度看外部世界。小說的開局便預設了賽姆勒的專一的倫理立場。賽姆勒先生一隻眼已失明,但並不妨礙他對外部世界的興趣。他對書和檔案仍然有著特別的關注,暗示了他是個飽學之士。在小說接下來的部分,作者又重點對賽姆勒的眼睛進行了描寫,“他只有一隻好眼睛,左眼只能分辨明暗。但是那隻好眼睛卻烏黑明亮,像有些品種的狗那樣,觀察力非常敏銳”。作者顯然再一次提醒讀者關注賽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除此之外,在這次的描寫中,作家增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暗示賽姆勒先生是一個具有洞察力的人,而他對外部世界所作的觀察是值得讀者期待的,這為作者在後面通過賽姆勒的所見所感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做好了準備。可以說,前面這兩部分病患身份的描寫給小說故事情節的鋪開做了良好的鋪墊。
其二,賽姆勒作為老年弱勢群體中的一員,他的病患身份的構建使得作者能有效地從情感上感染讀者,讓讀者更認同作家的批判性的倫理立場。
一個一隻眼睛失明的老人對外部世界是缺乏安全感的。當讀者進入到主人公的角色中,與他產生共鳴時,會深刻體會到這種不安全感的存在。小說把讀者引入到了賽姆勒先生的緊張與不安狀態當中,有效地引發了讀者對小說主人公的同情,使得讀者在無形中認同作者的倫理立場。賽姆勒作為眼睛失明的老者,本應處於社會的關注和愛護之下,但他卻處處遭遇不幸。
在小說中的各種事件中,無論是他受到扒手的欺凌或在哥倫比亞大學受到年輕人的輕蔑,都說明了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擠壓和輕視。每當小說中這樣的事件出現,小說開始所預設的病患形象都會在讀者的腦海里閃現,這樣,主人公的病患身份有效地增強了讀者對社會不公的感知。賽姆勒先生的疾病身份也賦予了人物話語上的權利。
在小說最為重要的部分,即賽姆勒與拉爾博士交流時,賽姆勒先生的病患身份給他的言談增加了不少的分量。對讀者而言,一個歷經滄桑的老者的話值得傾聽。在讀賽姆勒與拉爾博士的交談時,讀者是同情與尊敬的心態並存。這也使得作者貝婁通過主人公賽姆勒之口說出來的對社會的評價更為確實可信。
其三,賽姆勒先生病患身份的構建使小說的敘事更多地在人物的內心展開,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社會批判的思想性。由於賽姆勒先生與外界的交流有困難,他的內心活動反而變得出奇的活躍。賽姆勒先生本來是極為博學與見多識廣之人,小說中稱他“勤奮好學,書生氣很濃”。“他一直在讀文化歷史學家———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瑪克斯·希勒、弗朗茲·奧本海默爾的著作。”由於其殘病身份,賽姆勒先生的活動範圍有限,他大多依賴內心的思考來獲得生活的豐富性,使得他比健康的人投入更多的時間思考人生,因而對生活的看法也更為深刻。在眾生為生活奔忙之際,賽姆勒更多地對靈魂、尊嚴和內心的秩序進行關注。
在小說開篇,賽姆勒便發出如此感嘆:“靈魂,這只可憐的鳥兒,抑鬱不樂地棲息在解釋的上層建築之上,不知道往哪兒飛去才好。”小說中,在談到新一代女性的放蕩不羈時,直言“在她們厭惡權威之際,她們對誰都不願意尊敬,甚至連她們自己都不尊敬”。他認為人如果沒有尊嚴和對生活的愛,人類是沒有出路的。真正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盡力懷著公正無私的博愛,帶著一顆有教養的心生活”。賽姆勒先生強調,人活著,“最好是在自己內心獲得某種秩序”。人是身份的綜合體,也是各種責任的匯聚之所,對自由的無止境的追求必然導致身份的混亂和責任的逃避。人想超越自身的存在去追求自由的“非存在”。這是造成當代社會道德懸置,弱勢群體被受壓迫和冷遇的根源。
作品爭議
《行星》引發更大爭議的是貝婁在書中塑造的一個黑人扒手形象。在賽姆勒經常搭乘的公共汽車上,他總是看到一個扒手作案,這是一個高大強壯的黑人。賽姆勒看到了竊賊偷竊的詳盡細節,也曾向市警察局報了案,但警察局對他的報告卻表現得極其冷漠。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講座受辱的同一天,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扒手注意到賽姆勒發覺了他的行為,追蹤他到了家門口一個僻靜的角落,把賽姆勒頂在牆壁上,不打不罵,而是一聲不響地拉開褲子,拿出他的生殖器,按著賽姆勒的脖子,強迫老頭子看個仔細。“那人的表情並不直接表示恐嚇,而是古怪地、平靜地顯示專橫跋扈。”
在該部小說里,貝婁並沒有對當時黑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的生存狀態和反種族歧視運動表現出什麼關注,從物理層面來說,這個黑人扒手也只在小說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出現了兩次,在其餘時間裡,這個人物只是一個被人好奇地談論和追蹤的影子,直到有一天他被華萊斯的朋友弗菲爾在公共汽車上偷拍了偷竊行為,兩人廝打在一起,爭奪相機,正好被路過的賽姆勒碰上了。圍觀的人不少,其中還包括從以色列剛到美國的賽姆勒的女婿埃森,但沒有一個人準備勸架,眼看著弗菲爾就要堅持不住了,賽姆勒不得不請求埃森幫忙把他們分開,可讓賽姆勒意想不到的是,埃森用他那裝滿了亂七八糟鐵器的口袋使盡全身力氣朝黑人扒手的臉部打去,那沉重的一擊把他打翻在地,臉上皮開肉綻,鮮血四濺,令賽姆勒對他充滿了同情和憐憫,對埃森近乎麻木的瘋狂感到憤怒。
衣冠楚楚的黑人扒手形象與舊世界遺老一般的賽姆勒先生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其不無炫耀的性器展示、目空一切的扒竊行為向讀者傳達的信息與意義正可以理解為一種帶有強烈原始主義色彩的新霸權話語,是一種試圖建立新的社會規範的書寫模式並強制他者認同,這在賽姆勒先生眼裡無疑是對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傳統社會秩序及人類文明的挑戰和破壞。
賽姆勒這個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者本人情緒與憤怒的代言人,許多評論家對這一點有過詳細的論述,而貝婁本人對此的態度也有些閃爍其辭、模稜兩可。其實,貝婁對個人主義、激進主義思想本身並無惡感,他的憤慨對象是激進學生缺乏實際內容的表現形式和對此類思想意識的濫用,這一觀點早在1966年他接受戈登·勞埃德·哈珀的訪談時就有過明確的表述。
作品評論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這部小說為讀者全面認識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和人類生活提供了一個藝術而富有啟發意義的視角。
——張鈞(浙江外國語學院教授)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是一部保守的作品,小說的結尾是“斯多葛學派的、悲觀的”。
——安麗森·盧瑞(Alison Lurie,美國作家)
作者簡介
 索爾·貝婁
索爾·貝婁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 ,美國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發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婁市郊的拉辛鎮,父母是來自俄國聖彼得堡的猶太移民。1924年,全家遷往美國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學,兩年後轉學到西北大學,1937年在該校畢業,獲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除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編輯、記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學裡執教。
主要作品有:《兩個早晨的獨白》、《奧吉·馬奇歷險記》、《雨王漢德森》、《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禮物》等。1976年,他以“對當代文化富於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