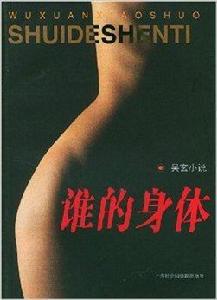作者簡介
吳玄,浙江溫州人。近年在《收穫》、《花城》、《人民文學》等刊發表小主若干,多數被各種選刊、選本選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文學院契約制專作家。現居北京,為某雜誌社編輯。
媒體推薦
序
王 乾
面對靈魂,我們黯然神傷
——吳玄中篇小說集序
吳玄的中篇小說集要出版了,他打電話囑我寫序,說隨便寫幾句就行了。我也隨便答應了他,但幾次動手,都落不了筆,實在是不敢隨便。吳玄喜歡把很重的事情說得很輕,他不像有
些作家讓你寫評論的時候關照你寫“好”,寫“好”不僅是讓你自己文章寫好,而且要把他寫“好”。應該說吳玄還是很在平他的這本小說集的,這畢竟是他的第一本書。他說隨便,我得
認真對待。
說實在的,我是從內心裡喜歡吳玄小說的,喜歡不喜歡一個作家,從文章上看不出來,文章尤其是評論文章,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往往在表面上都做出一副喜歡狀,而內心裡到底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個評論家,一個編輯喜歡的作家,作品不會很多,都喜歡了只說明他是一個不挑食的人。我喜歡吳玄小說的原因,大概因為他是南派的寫法,所謂南派的寫法其實是相對北派而言的,北派的作家重社會、重力度、重內容,而南派的作家重感覺、重靈性、重語言。當然這種說法只是相對而言,不能誤解成南派作家無社會、無力度、無內容,更不能誤解成北派作家無感覺、無靈性、無語言。重只是一種偏重、倚重、器重,或許說所重之物作家比較敏感、容易把握。吳玄所承傳的小說作法是汪曾祺、林斤瀾、高曉聲那一脈的南派性靈的路數,這一脈作家在當代文學創作中能夠自覺地不以政治的、道德的視角去關照生活,而以人性的、審美的目光去關注人物的命運,他們選取的人物往往都是社會底層的弱小人物,用今天流行的概念來說都是生活在邊緣的人物,常常被宏大敘事所忽略的一些人物,宏大敘事之中即使出現了,也都是一些點綴或過渡性的人物,大致如《沙家浜》中的沙四龍、刁小三一類,寫其美好,也是小善小德,縱使奸壞,也只是小奸、小壞一類。他們要表現的這類人身上自然的人性。所謂自然的人性,便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的人性狀態,那些忠善完美的英雄和違背人性的奸佞,往往被歷史置於某種特別的場景擠壓的非常態的人性美和人性惡,可能都是被迫進行表達和完成的,在更多的時候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日常化的生活、邊緣化的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雖然它並不標識人性的高度,也不揭穿人性的底線,可最大可能接近人性的本質。吳玄的《髮廊》結尾寫妹夫李培林在車禍中喪身,被丈夫李培林折磨蹂躪多日的方圓該是解脫了,可誰也沒想到,方圓反而失去了目標,方圓轉讓了髮廊,一個人回到家鄉西地。我們滿以為方圓終於離開了那個遭人唾棄的髮廊,然而,“方圓在家呆了一個月。一個月後,她去了廣州,還是開發廊”。
這是頗讓人吃驚的一筆,我看到這裡可以說是一種震驚。我想起了雨果那句著名的話來:“人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會黯然神傷。”我們面對方圓的選擇時,黯然神傷。方圓,是在城市生活中最常見到的打工妹,她們糊裡糊塗從鄉村來到城市,又糊裡糊塗地選擇了髮廊的職業,從打工妹做成了小老闆。方圓的故事讓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曾經遍布各地城市的“溫州髮廊”。在世俗的眼光中,方圓開發廊顯然是不道德,至少不光彩,人們總以為在髮廊做活的大都因為找不到工作,如果能跳出髮廊這個“火坑”,她們肯定也會歡欣鼓舞。因而方圓的嫂子托人幫方圓找了一個工廠的工作,她以為拯救了一個失足女青年,可沒有一個星期,方圓就辭職不幹了,她又回到髮廊里重操舊業,回到髮廊的方圓就像魚兒回到水裡一樣自如、歡樂。當然髮廊本是是非之地,李培林後來因為“保護”髮廊被打成了殘疾,方圓忍辱負重收養了殘疾的丈夫,但丈夫卻不堪妻子方圓的賣身生涯,帶著自殺性地走向了死亡。方圓也捨棄了給她命運帶來災難的髮廊。小說到這裡結束,可能會帶有道德譴責和道德勸諭的意味,髮廊改變了人的命運,毀滅了美好的家庭。可是作者奇峰崛起,讓方圓重新回到廣州去開發廊,至於原因,吳玄寫道:
……
圖書目錄
序:面對靈魂,我們黯然神傷(王乾)
玄白
西地
髮廊
門外少年
虛構的時代
誰的身體
後記:貓的遊戲精神
文摘
書摘
劉白夫人雁南正在屋裡坐月子。坐月子的任務就是吃喝拉睡,不準看書不準看電視不準打毛線。雁南閒得發慌,見劉白樂呵呵端了兩盒圍棋回來,就說我們來一盤。
劉白說,不會。
真掃興,忘了你不會,雁南揉揉棋子,又說,是雲子,手感很好,送我的吧?
不,人家送我的。
那就是送我,反正你不會。
可人家說我是棋王呢。
雁南大笑說,有意思,誰說你是棋王?
就是廣場上天天擺石子玩兒的那個棋癲子。
是他?雁南吃了一驚,問,他怎么送棋給你?
他說我是棋王,就送我了。
你棋王個屁。
怎么是屁,你先成為棋後,我不就是棋王了?
雁南興致大增說這還差不多,隨即動員劉白也學圍棋,說畢竟棋癲子有眼光,你確實是塊下棋料子,我怎么不早發現,免得老找不到對手。
劉白懶懶地說,教吧。雁南受寵若驚便有板有眼地教,先講序言,說圍棋是國技,很高雅很中國特色的一種文化,相傳是堯所創。弈者,易也。黑白象徵陰陽,可能與《易經》同出一源,或者就是《易經》的演示,是一門玄之又玄無法窮究的藝術。那時文化界正流行《易經》熱,劉白像大多數文化人,雖然並不了解《易經》,卻很推崇,聽說圍棋與《易經》有關聯,頓時臉上莊嚴肅穆十分,呆子似的坐著。雁南攤開棋盤,比比畫畫,不一會兒,劉白覺著懂了,說原來這么簡單。雁南說大繁若簡,妙就妙在規則簡單。劉白說對。忘了雁南坐月子不能用腦,急著想試一盤,高手般拿雙指夾起一粒黑子“啪”地一著打到星位上說,來!嬰兒即被驚醒,呀呀亂哭,嚇得雁南直伸舌頭,忙著去哄,一邊噓噓噓地把尿,嬰兒很快便又睡了,雁南說,你把星位都擺上黑子。
劉白說,我不要讓。
那怎么下?
就這樣你一顆我一顆下。
就讓你試試吧。雁南隨手拿子就碰,幾招下來黑子被吃得一粒不剩,劉白扔了棋子,非常沮喪。
氣什麼?你已經學會就不錯了,我的棋是家傳的,幾代人心血呢。你不是不知道,不讓怎么行?
氣倒不氣。我懊喪的是怎么不早學圍棋,這棋真不是雕蟲小技,什麼氣、勢、劫,還挺哲學的。
當然。
一會兒劉白說,怪。
怪什麼?
說圍棋是國技?
路人發覺老柳樹下又多了一個人,重新勾起了興斂,都駐足探問劉白並不作答,任他們發著各式各樣的議恍】卓櫻缶<勁兒追著問,劉白,你乾什麼?
劉白移過身子說,還能幹什麼?
跟他下棋?
看看。
有什麼好看?
妙極了,你也看看。
熟人看看又看看,說看不懂,實在沒什麼可看,劉白看他們掃興,也就不再勉強。
中午雁南見劉白沒有回來,吃了飯,也來廣場看個究竟。這是夏天,廣場一片白光,老柳樹被曬得蔫枯,行人都躲陽傘下或草帽下急走。劉白依然蹲那裡樣子像——只燙熟的蝦,臉上滾著熱汗。雁南說,看出名堂沒有?
劉白很激動地點頭。
還是回去吧,看你熱的。
還行。你看他,一點汗沒有,心靜體自涼。
雁南細看棋癲子,果然無汗,覺得不可思議,說真玄。
是玄,他的棋更玄,回去我把譜記下來慢慢研究,這是圍棋史上的奇蹟。
我們這樣說話,會不會影響他的思路?
不會吧。早上不斷有人打攪,我說了不少話,不見他有反應。
太熱了,太陽真辣,我都站不住了,我看你還是等秋天再看吧,這樣暴曬要中暑的。
不行,曬死了也要看,其實也不熱,就是汗多點。
路上我聽見有人議論紛紛,說老柳樹風水好,又多了一個瘋子。
我也聽見了。
我去給你弄點吃的,給他也帶一點兒吧。
不要,不能破壞他的習慣,以免發生意外。
傘給你。
不要,我也鍛鍊鍛鍊。
這年夏天,劉白在廣場上度過。因為地面太燙,他一直蹲著觀棋,沒有練就像棋癲子那樣席地而坐的功夫,臉曬得黑紅,肉瘦了一圈,但是沒有中暑。太陽能使草木枯蔫,大地乾裂,卻曬不倒一個劉白,這也是令人費解的。大概腦子清靜,也就水火不入。瘋子都生活在季節之
外,夏穿棉襖,冬穿單衣,時常可以見到。這其間發生了一件趣事,劉白的母親從鄉下趕到廣場,見兒子果然暴曬著看人玩石子,頓時號啕大哭。劉白說,媽,你怎么啦?劉母說,白兒,你這是怎么啦?三伏天在這裡曬著?我聽大家說你瘋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就瘋了,我就你一個兒子啊。劉白說,我幹事情,我哪裡瘋了。劉母說,你真的沒瘋嗎,讓媽考考你,你還記不記得你3歲時在地上抓雞屎吃……這則笑話,後來隨《滄桑譜》在棋界廣為流傳。
太陽轟轟烈烈烤了劉白3個月,沒烤倒劉白,只好收起了炎威。秋風起了,然而意外也發生了,棋癲子不見了。這是9月8日,令棋界傷感的一個日子,《滄桑譜》因此不得不畫上句號。
事先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棋癲子要在這天消失。那日清晨,劉白一如既往走到廣場,見樹下空空蕩蕩,說奇怪,他今天怎么遲了?也不著急,蹲到老位置上靜候,他已習慣於蹲著。這是個好日子,風涼而不寒,天空高遠得令人神往,劉白默默地讚美著天氣。廣場上漸有人活動,一些老人疏朗地排列各處練太極拳,輕柔曼舞,飄然欲仙。太陽升到廣場上空,四圍熙熙攘攘,人聲嘈雜。棋癲子還是沒有來。劉白這才意識到他今天不會來了,他突然覺得煩躁,心中有種不祥的預兆,要去找他,又發覺自己並不知道他的住處,甚至不知道他來去的方向。那就只好漫無目標滿城去找。劉白逢人就問看見棋癲子沒有?不是坐老柳樹下?不見了。那就不見了。再問他住處。誰也不曾注意他的住處,好像他根本不需要有個住處。劉白找到天黑,只覺著渺茫,心裡陡然產生虛幻感,覺得棋癲子並不曾真實地存在過,自己整整一個夏季蹲樹下觀棋只是一場夢。
劉白疲乏地回家,傷心道,棋癲子不見了。
怎么不見了?
就這樣不見了。我找他一天,哪裡都跑遍一點蹤影也沒有。
雁南凝思一會兒說,這之前有沒有反常現象?
沒有。
你有沒有打攪他。
沒有。我沒有打攪他,從來沒有跟他說過話,也不敢。誰也沒有打攪過他。
他是不是討厭你觀棋,躲起來了?
不對呀,要是這樣,我觀棋的第二天就該躲了,幹嗎過了那么久才躲?我有種不祥的預兆,怕他是死了。
我也這樣想。
不管怎樣,我們都得找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