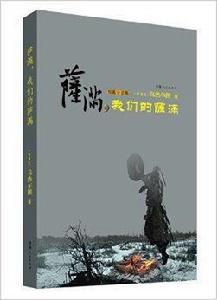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薩滿,我們的薩滿(短篇小說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鄂溫克族)烏熱爾圖
烏熱爾圖,鄂溫克族作家,出生於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浩特。處女作是《大嶺小衛士》。創作主要為短篇小說,出版有《烏熱爾圖短篇小說選》。代表作有《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曾連續三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烏熱爾圖的作品多以古老神秘的森林為背景,著力表現鄂溫克族人民的生存方式。他善於選取典型環境和情節,抓住矛盾衝突,刻畫人物的心理和靈魂,具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和藝術感染力。
圖書目錄
序言
獵犬
馬的故事
老人和鹿
棕色的熊
越過克波河
七又犄角的公鹿
琥珀色的篝火
最後一次出獵
雪
瑪魯呀,瑪魯
清晨點起一堆火
沃克和泌利格
在哪兒簽上我的名兒
夢,還有獵營地捅刀子的事
灰色馴鹿皮的夜晚
薩滿,我們的薩滿
你讓我順水漂流
叢林幽幽
林中獵手的剪影
我在林中狩獵的日子
序言
烏熱爾圖的小說多寫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前幾年,據今遠的有三十年,近的也有二十多年了。他是重要的中國當代作家,也是第一位鄂溫克族作家,但似乎並沒有產生過轟動性的影響。他的寫作與時代的文學主流總是若即若離,比如說80年代走馬燈式的各種風潮,根子裡往往都有著個人主義的理念,但烏熱爾圖從來沒有強調過個人,而是更多地強調集體性質的部族;90年代,前衛的作家們的“新歷史主義’’和“日常生活美學”,消解了之前現實主義式的寫作手法,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主體性進入黃昏了,但烏熱爾圖反倒重新開始歷史的“準學術’’寫作和少數民族主體性的構建……如果不是僅僅把它們當作文學史材料,或者休閒消遣的產品(當然,它們因為題材的特異,完全可以滿足追求“異族風情’’的功能),烏熱爾圖的這些作品在當下還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再讀他的作品?他如果沒有過時,原因何在?
烏熱爾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文學史地位,儘管有關他的經典化過程還在進行中,但任何一個致力於中國當代文學史或者批評的人,都無法忽略他的有關鄂溫克人森林狩獵題材的作品:他為中國當代小說譜系輸入了一個全新的意象一“獵人”和一個獨特的現場——“森林”,其中滲透的帶有“野陛的思維”色彩的生態與文化觀念,無疑已經成為兒童文學、動物小說、尋根文學、生態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等各種界定中可以不斷生髮滋長的精神資源,僅此兩點就足以讓人記住,更何況他在1990年代之後轉型為非虛構寫作所表達出來的自覺的族群聲音、文化記憶和少數者話語。所有這些話題,每一個都足以形成獨立的論述空間。不過我認為,重新閱讀烏熱爾圖的小說最核心的意義在於,可以使我們發現一種對集體性的再尋求,這種集體性以族群共同體文化的面目出現,從中可以發現新中國以來關於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起承轉合的思想演變的痕跡。這種對於集體陛的重新張揚,有別於新中國初期那種社會主義人民的集體性主體,而是在後者解體之後尋找到族群文化的歸宿,從而提供了一個精神的棲息之地。
時間給予了這些作品雙重維度,即當初寫作、發表它們時的歷史語境,以及當下的社會生活現實語境。帶著雙重視角的自覺,觀察烏熱爾圖步入文壇三十餘年的寫作,其主題和形式的變化有跡可循:最初以動物和獵人題材見長,作品的情節、結構都比較簡單,疏於描寫,長於氛圍與心理的勾勒,更多的是以對話形式突出某些抽象的理念。這些小說多次獲獎,為他贏得了聲譽。198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轉入以寫意筆觸、象徵手法書寫鄂溫克部族在遭逢現代性衝擊時的生產、生活與精神的變化,因為“地方性知識”的熟稔和鮮明的情感態度,加之藝術技巧的嫻熟,這些小說使他獲得了更多批評者的解讀和闡釋;1993年以後,他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後開始轉入非虛構的散文體寫作之中,尤其是近年來,更著力於對鄂溫克歷史的整理與重述。從這個發展軌跡可以看出一個少數民族出身的作家,在順應外界環境和自身精神成長中如何塑造自我、尋求認同並最終獲得了特定的形象。《薩滿,我們的薩滿》這部小說集基本囊括了他在各個階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這當然是最簡略的概括,烏熱爾圖還有一些自己認為不重要或者不符合他後來的文學理念的作品,在再版的小說集中已經去除了。對他進行全面評價並不是本文的目的,並且已經有很多人在進行研究了。在這裡,我只就他最重要的小說討論一個少數民族作家通過他的寫作能夠給我們的當代文學提供什麼樣的經驗與啟示。這些經驗與啟示可能帶有邊緣文化的特質,但卻又具有普遍性意義,它們顯示了一個作家如何敏感地意識到某種社會變革會引發的後果,同時又以堅定的情感態度站穩立場,樹立了別具一格的價值取向,並且儘自己的能力尋求某種救贖之道。在烏熱爾圖這裡,就表現為他對鄂溫克文化的認同和建立鄂溫克文化主體的努力。他的作品無意充當社會與時代的鏡子,卻具有像薩滿那樣的預言神通;他的藝術手法與魔幻現實主義頗有相通之處,卻可能是最本土的日常美學表現;他的倫理與道德皈依看似一意孤行,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化不可或缺的動力之一。如果要給重讀烏熱爾圖的小說一個理由,我想,就是他在以全球化為代表的啟蒙現代性語境中,執拗地背轉身去,著力弘揚一種奄奄一息的傳統,並且力圖在弱勢中重建另一種集體性,復活那些不同於主流的認識世界的方式。
代言與集體性的尋找
如果採用以賽亞·柏林的說法,烏熱爾圖無疑屬於那種刺蝟型的作者——一直以來,儘管題材、體裁略有變化,但都是在書寫自己的原鄉族群經驗,一以貫之的小說主題是“變遷及傷痛”。他的作品帶有濃厚的自傳式的色彩,但是與純粹的經歷寫作不同,他將他在大興安嶺叢林中的鄂溫克部族那裡獲得的經歷提煉為經驗,並且上升為一種方法。
鄂溫克族於1957年在新中國民族識別中獲得命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定的民族。有關它的族源的源流考證,說法不一,烏熱爾圖本人也有自己的一些見解。這些說法暫時擱置一邊,我想說的是,當鄂溫克人從“索倫”“通古斯”“雅庫特”“霍恩克爾”“喀木尼堪”“特格”等種種稱謂中脫離出來,獲得當代集體性命名後,這種身份就具有了能動性,成為凝聚族眾的一種感召符號。烏熱爾圖在自傳式的回憶《我在林中狩獵的日T-))(2011年)中,以後見的回溯勾勒了對於自己族群的認同,他寫到十七歲時下鄉插隊,“鄂溫克獵民定居點生活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說真的,那時我對自己的民族身份還很含糊”,但是後來在火車上巧遇父親,聽到父親和一位鄂溫克獵民用母語攀談,“我覺得周圍的聲響消失了,只有那鄂溫克母語平緩的音調帶著一股甜味,在我耳邊飄蕩;父親和我,也包括小八月,都罩在這聲音編織的光環中,不再懼怕任何威嚇與欺侮了。那一刻,有股暖流朝我湧來”。回歸到語言編織的族群共同體中,母語及其所代表的傳統給予了時代狂風中動盪的個體以子宮般的溫暖和寧靜。時隔多年之後的這個細節,在書寫中帶上了濃郁的主觀化色彩,如果不追究細節本身的真實性,這種心理上的傾向無疑體現了作者本人的現時態度。而這段時間並不太長的狩獵生活,成了他此後有關叢林小說的基本素材。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的插隊經歷是一個真正的“再教育”的過程,它所積蓄的能量直到數年後才逐漸揮發出來。……樹,生一堆火,傻瓜說。你要用我,先找一塊磨石來磨快我,斧頭說。他來到磨石跟前,磨石對他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磨石問他。我要去找一塊磨石,用它磨快一把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磨石說,你要用我,先找水來沾濕我。他來到小河跟前,小河對他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小河問他。傻瓜說,我要找點水,用水沾濕磨石,在磨石上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你要用我,先找頭鹿從我身上游過,小河說。他來到鹿的跟前,鹿對他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鹿問他。我要去找鹿,讓鹿游過河,用水沾濕磨石,用磨石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傻瓜說。你要用我先讓我吃上綠草,鹿說。他走到綠草跟前,綠草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綠草問他。我來找綠草,讓鹿來吃,鹿好游過河,用水沾濕磨石,用磨石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傻瓜說。你要用我先找雨婆,下一場大雨,綠草說。他來到雨婆跟前,雨婆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雨婆問他。我來找你,請你下場大雨,讓青草綠了,鹿來吃綠草,去游過小河,用水沾濕磨石,用磨石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傻瓜說。你要用我,先去找風婆,刮來一陣大風,雨婆說。他來到風婆跟前,風婆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風婆問。我來找你,請你刮一場大風,讓雨婆下一場大雨,讓青草綠了,鹿去吃綠草,好游過小河,用水沾濕磨石,用磨石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傻瓜說。你要用我,先讓太陽曬乾我的頭髮,風婆說。他來到太陽跟前,太陽說,你好哇。傻瓜說,你好。你這是去乾什麼?太陽問。我來找你,請你曬乾風婆的頭髮,風婆颳起大風,雨婆送來雨,讓青草綠了,鹿吃綠草,好游過小河,用水沾濕磨石,磨快斧頭,用斧頭砍倒松樹,用松樹生起火,傻瓜說。好吧,太陽說。太陽升起山頂,曬乾了風婆的頭髮,風婆甩甩頭髮,颳起大風,雨婆乘風下起雨,青草綠了,鹿吃了綠草,游過小河,沾濕了磨石,磨石磨快了斧頭,斧頭砍倒了松樹,松樹架成一堆,傻瓜總算生起一堆火。
這個故事既是小說中對於年輕人要敬畏萬物的教誨,同時也是講述者本人在重溫中對於傳統的不斷淬鍊。最關鍵的是,它所表現出來的關係性的意識。民族與民間智慧的復活,使得烏熱爾圖的小說具有了一種從少數者的角度來看更加普遍的意義。從形態和觀念來說,他的作品屬於費孝通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理念階段,即少數者群體張揚自己的文化,同時將自身的文化理念置諸於廣闊的社會關係之中,“和而不同”只有先有著如此多樣性的“不同”,才能最終達到“天下大同”的“和”。
如同查爾斯·泰勒(ChadesTaylor)所說,在現代性的語境中,那種固有的宇宙秩序、“偉大的存在鏈條”發生了斷裂,給定的秩序受到懷疑,這就是所謂的祛魅過程,現代自由因此而產生。但是自由也要付出代價,這是一種破碎的世界觀,人的異化由此產生,因為在馬克斯·韋伯式的“一個無神的沒有預言者的時代”中,世界的神秘性蕩然無存,就產生了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與“大地”之間的鬥爭。祛魅導致了自然神性的解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衝擊重組了原有秩序,自然和人之間也被重置為對象化和客體化的關係,親密感喪失了,心靈也失去了依託。
烏熱爾圖意在通過對鄂溫克族群與生活空間的恢復,重新連線起斷裂的存在之鏈,修復支離破碎的親密感,呈現出一個“不同”的文學世界,正是有著這樣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存在,才保持了文學生態的平衡與活力,沒有窒息於強勢話語,比如政治和商業的意識形態的專斷。
重新解讀烏熱爾圖,以及與他類似的諸多少數民族作家,也許能夠在文學“共和”的意義上有更多的發現。是為序。
2n1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