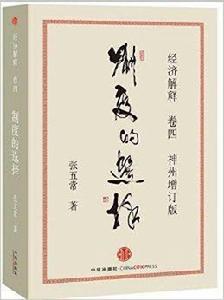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張五常自稱經濟解釋系列是“認真寫成的最後一套經濟學著作”。被世人公認為是集張五常平生學術功力之大成,也是具有深遠影響的經濟學經典著作。經濟解釋系列基本囊括了張五常教授畢生的學術思想精髓。
作者簡介
張五常,香港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他於1967年獲博士學位後,先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他進一步發展產權理論及交易費用概念,主張只要產權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資源最有效運用。他以《佃農理論》和《蜜蜂的神話》兩篇文章享譽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學經濟系任教,開始在香港報界以產權理論分析時局,在內地和香港兩地引發強烈的學術反響。曾出版作品:《佃農理論》、《五常學經濟》、《經濟解釋》、《中國的前景》、《中國的經濟制度》、《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等。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經濟學的缺環
第一節:缺環的闡釋
第二節:自然淘汰的思維
第三節: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第四節:無從觀察的不幸發展
第五節:契約理論的基礎
第二章:科斯定律與租值消散
第一節:科斯的故事
第二節:科斯定律的闡釋
第三節:交易費用可從租值消散看
第四節:外部性理論的胡鬧與世界的現實
第五節:蜜蜂的神話與利他的行為
第六節:租值消散理論的起源與失誤
第七節:公海漁業、私產替代、利益團體
第八節:收入權利的界定與效率稅制
第九節:價格管制理論
第十節:科斯與我的和而不同之處
附錄:國慶大堵車的經濟觀
第三章:契約的一般理論
第一節:複雜理論與複雜變化是兩回事
第二節:約束競爭是契約的一般用途
第三節:資產四權
第四節:從契約結構看外部性理論的無知
第五節:履行定律與選量作價
第六節:按件數算工資與收入分配
第七節:小賬的變化
第八節:交易費用與市場分離
第九節:公司性質的思想發展
第十節:從契約角度看公司與市場
第十一節:公司無界、選擇作價與適度均衡
第十二節:失業的解釋
第四章:從佃農分成到中國制度
第一節:知識累積、土地價值與社會詛咒
第二節:從斯密的佃農分析說起
第三節:馬歇爾的幾何失誤
第四節:換軸看分成切地清晰
第五節:訊息費用解釋分成
第六節:推斷中國改制的理論結構
第七節:層層分成與縣際競爭
附錄:從黃奇帆的發展思維說中國的財富累積
第五章:收入分配與國家理論
第一節:分配理論與貧富分化
第二節:市場與非市場的等級排列
第三節:中國舊家庭的禮教與國家的盛衰
第四節:國家理論:什麼是國家?
附錄一:國民教育與藝術文化
附錄二:從文化教育的收入回報說倉庫選擇
附錄三:樓價與扶貧:我在北京究竟說了些什麼?
第六章:經濟調控與貨幣制度
第一節:商業周期與貨幣調控
第二節:政府主導投資與獎罰不對稱的困擾
第三節:供給學派的闡釋
第四節:貨幣用途與欺騙行為
第五節:以物品成交價作指數為錨的理想貨幣制
附錄一:中國騙術考——與羅姆尼商榷
附錄二:從權利角度看國際收支平衡表
附錄三:管制資本項目之謎
第七章:一蓑煙雨任平生
第一節:經濟解釋的範疇
第二節:創作玩意與思想傳世
兩個附錄的引言
附錄一:悼老師阿爾欽
附錄二:羅納德·哈里·科斯
文摘
第一章﹕經濟學的缺環
二○○七年五月至八月間﹐我以《經濟學的缺環》為題發表了一系列十一期文章﹐目的是做一些“熱身”運動﹐讓自己的腦子進入狀態﹐因為答應了科斯寫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自二○○二年舊版《經濟解釋》卷三《制度的選擇》結筆後,嚴謹的學術論著我沒有繼續﹐恐怕腦子不中用了﹐所以先寫那十一期操練一下。當時覺得還可以。然而,二○○八年的春天《中國的經濟制度》完稿後﹐反覆重讀﹐察覺到在契約的思維上自己進入了一個此前沒有到過的層面。尤其是《中國》的第三節——《契約的一般概念》——科斯讀後認為重要。這新層面的出現使我今天意識到《制度的選擇》不應該修改﹐而是要從頭再寫。事實上﹐這重寫在卷二《收入與成本》修改了一小部分後就開始了。
第一節﹕缺環的闡釋
傳統的經濟學分析﹐關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稱“微觀”﹔失業﹑貨幣﹑通脹等話題稱“巨觀”。契約的安排這組現象被漠視了﹐成為一個重要的缺環。不引進契約分析﹐交易費用這項局限被處理得拖泥帶水﹐我們無從深入地分析資源使用﹑收入分配﹐以及失業﹑通脹等現象。例如卷二《收入與成本》的第三章我從公司契約的角度分析失業﹐卷三《受價與覓價》的第六章我提出契約結構的變化主宰著上頭成本與直接成本之間的灰色地帶——所到之處前無古人,傳統經濟學是無從處理的。嚴格來說﹐漠視契約這個重要環節﹐我們不容易從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理論基礎解釋些什麼。
我們可以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成功地解釋魯賓遜在他的一人世界的行為﹐因為他的世界交易費用的確是零。但轉到我們大家活著的社會﹐我們要怎樣假設交易費用才對呢﹖我說過﹐在實驗室做實驗﹐指明要用清潔的試管﹐我們不可以用髒試管而假設是清潔的。試管是潔還是髒是一個需要指定的條件﹐自然科學稱驗證條件﹐經濟學稱局限條件。交易或社會費用是局限條件的一種﹐要解釋行為這條件的假設不容許與事實不符。不幸的是﹐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我們不能像在人造的實驗室那樣﹐把髒試管清洗一番。我們要在實地考查那些有關的驗證條件究竟是怎么樣的。
這種考查永遠不易﹐而牽涉到交易或制度費用一般困難。說這是因為交易費用那是因為交易費用不一定錯﹐但如此這般地假設真實世界的局限是近於無聊的玩意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是先以交易費用解釋契約的選擇﹐然後從契約的局限約束再解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現象或行為。不是那么容易﹐但可以做到﹐而這樣一來﹐因為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缺環﹐我們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就有了一條可走的通道。
選擇問局限﹐不問好不好
契約與制度是同一回事﹐只是後者通常牽涉到較為廣闊的範圍。同學們要注意﹐我說的制度選擇不是問什麼制度好什麼制度不好﹐而是問為什麼會有這種或那種制度﹐即是問為什麼會有這種或那種契約了。問為什麼工業會有件工契約跟問昔日的中國為什麼會有人民公社﹐二者的性質相同﹐雖然後者我沒有深入研究過﹐想來遠為難於處理。至於人民公社帶來饑荒則遠為容易解釋﹐是公社契約帶來的效果。解釋公社契約是制度選擇的分析﹐不容易﹐但經濟學不問﹕饑荒是好還是不好﹖
饑荒往往是契約或制度的後果。當然沒有誰會選擇自取滅亡﹐但我選走的經濟學範疇﹐解釋或推斷行為只能從選擇這個基礎假設入手﹐局限有變其選擇會跟著變。當然還有其他解釋人類不幸的理論﹐而以經濟理論混合著博弈理論來解釋自取滅亡的分析﹐三十年來頗時尚。我不認為博弈理論可以驗證﹐從個人信奉的科學方法看這些理論不是有解釋力的學問。說過了﹐我選走的路是以考查可以觀察到的局限轉變來推斷行為的轉變。自己肯定走得對﹐但不是唯一可以解釋人類行為或經濟現象的方法。
制度是契約的安排。我的處理是﹕這安排是選擇的結果﹐是好是壞是倫理道德的話題﹐不是科學可以協助找到答案﹐我管不著。令人遺憾的是﹕絕少經濟學者從契約安排的角度看制度。說漠視契約分析是經濟學的嚴重缺環也是說對制度的理解也是一個缺環了。不能說這缺環今天還存在﹕事實上“契約”一詞在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下變得朗朗上口。然而我不認為這新發展的路向走得對﹐是後話。
第二節﹕自然淘汰的思維
一些行內朋友說關於契約的經濟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年發表的一篇關於契約選擇的文章﹐應該不對。瑞典的沃因(Lars Werin)說契約牽涉到一個結構起自我的《佃農理論》﹐可能對。契約(contract)一詞﹐在我之前經濟學一般只用於描述帕累托至善點的契約曲線(contract curve)。回顧經濟思想的歷史,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就用了一整章分析農地使用的制度安排的演進﹐也即是農業契約安排的演進了。
斯前輩之見﹐是原始的奴隸制度是最沒有經濟效率的制度﹐因為奴隸只管吃﹐不管做。他因而推論,佃農分成逐步替代了奴隸﹔然而﹐因為分成要分一部分產出給地主﹐有政府抽稅的效果﹐經濟效率也不善。他於是認為一個固定租金的制度比佃農分成優勝。再推下去﹐斯密認為固定租金的安排往往為期短暫﹐耕耘的農民沒有安全感﹐在生產效率上還有問題。他於是認為﹐最有效率的農地使用制度是一個有長久年期的固定租金制度﹐但這後者制度是英國的農業獨有。這個英國農地制度優勝的看法在經濟學傳統持續了很多年﹐直至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卜凱教授調查研究中國的農業才提出有別之見﹐而邏輯上證明斯密錯可見於一九六七年我寫好的《佃農理論》。
斷章取義誤解前輩
這裡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話題。斯密分析農地使用演變的主旨﹐可不是有沒有經濟效率那么簡單。他以一整章示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個重要思維。斯密被引用無數次的名言——“我們的晚餐可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商人﹐或麵包師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利益的特別關注﹔我們認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並非行善﹐而是為了他們的自利”——其實是斷章取義地理解錯了他。如果細讀這些話之前的文理﹐我們會察覺到斯密說的是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人類自私是因為不能不自私!這樣看﹐跟他早一本小書《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的論點加起來就變得沒有矛盾﹕早一本說人類天生有同情心﹐後一本說可惜不自私不能生存。
真巧﹐動筆寫這章時我讀到林行止的《信報》專欄﹐題為《現代經濟學奠基者——達爾文取代斯密》﹐內容提到美國一位經濟學教授說﹕“一百年後﹐經濟學家可能認為經濟學的智性奠基者﹐是達爾文而不是斯密﹗”有點奇怪。五十年前我讀斯密與達爾文﹐認為後者的“適者生存”意識源自前者。當時科斯﹑施蒂格勒等前輩皆這樣看﹐怎么今天徒弟變作師傅了﹖
達爾文是數世紀一見的科學天才﹐精彩的論著無數﹐其中屢次提及生命的經濟原則(the economy of life)。他是富家子弟﹐用不著打工為生計﹐正規的生物學訓練不是那么好。天才絕頂無疑問﹐受到斯密《國富論》的影響也無疑問。今天﹐衡量人類科學思想發展的專家們﹐不少認為達爾文的“自然淘汰”是古往今來最重要的思維。這思維源自斯密﹕整本《國富論》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
適者生存要從局限轉變看
這就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斯密分析農地使用制度演變那一章﹐以事實衡量﹐近於全盤錯了﹗奴隸制度不是那么無效率﹐佃農分成沒有遭淘汰﹐而斯氏高舉的英國獨有的長期固定租約制度﹐在中國宋代起有記載﹐稱永佃制﹐生產效率不是那么高﹐明清之後漸被遺棄。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調查了中國八個省份﹐得到的結果是一九三四年永佃制占所有農地使用租約百分之十一。相比起來﹐百分之二十九的租約無期限——每季收成後可以終止﹔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同樣地區與地質﹐每畝的產量大致相同。這些數字因而不支持斯密之見。
原則上﹐適者生存這個論點不可能錯﹐因為可以闡釋為套套邏輯(tautology)。我們要怎樣看才對呢﹖我個人的看法﹐是契約或制度的轉變源於局限條件的轉變﹐尤其是交易或制度費用這種局限。這樣,適者生存要從某些局限的存在或不存在看。源於局限轉變而變的契約或制度安排可以很微小﹐不容易察覺﹐有時近於式微又再盛行﹐正如有些生物種類近於滅絕又再興盛。這後者現象達爾文當年可能不知道。像人民公社那個層面的大轉變﹐牽涉到的局限轉變當然是驚世駭俗的了。
我跟蹤過中國的人民公社從大鍋飯制轉用工分制﹐繼而從生產大隊到生產小隊﹐再繼而到包產到組﹑到戶﹐承包契約﹐層層承包﹐從而發展到今天的縣際競爭制度﹐等等﹐皆可以看為契約或制度安排的轉變﹐過程中的局限轉變是明確的。恨不得自己還年輕﹐可以從頭詳盡地考查與分析中國六十多年的局限轉變帶來的制度演變的過程。應該是相當清晰的。人類歷史很少見到這么精彩而又有明確連貫性的經驗。
回頭說達爾文的自然淘汰或適者生存觀﹐去年(二〇一一)我給沃因的信說﹐我搞不清楚是理論還是套套邏輯。他回信說歐洲有不少學者也這樣問﹐但得不到肯定的答案。問題其實不重要﹐因為套套邏輯可以是非常重要的思維﹐提供著一個範疇約束及引領著我們怎樣想。我認為在西方經濟學二百多年的發展中﹐引用達爾文的思維而得到石破天驚的貢獻的﹐是老師阿爾欽一九五○年發表的《不確定﹑進化﹐與經濟理論》。該文回應當時行內的一個大爭議﹕前景無從確定﹐我們怎可以用爭取財富或收入極大化這個假設來解釋行為呢﹖阿師答得簡單精彩﹕在資源缺乏的競爭下﹐適者生存是收入極大化的證據﹗人的意圖為何大可不論﹐結果是支持著個人爭取收入極大化這個假設。如此類推﹐契約或制度的選擇也是局限轉變約束著的適者生存了。
馬歇爾與詹森皆中計
斯密之後﹐分析農地使用制度的西方學者不少(見拙作《佃農理論》第三章)﹐可惜他們的分析沒有從契約結構的角度入手﹐這裡說的經濟學缺環因而沒有被填補了。最令我惋惜的是馬歇爾。此君知道佃農分成是一種契約﹐認為變化多﹐知道深入研究重要。一八九四年﹐馬氏做英國《經濟學報》的主編時﹐把一位名為Henry Higgs寫的《法國西部的佃農分成》放在首位﹐高舉這篇文章。可惜該文作者只調查了一個農戶﹐而此戶的佃農分成率剛好是五十﹑五十。馬歇爾聽到這分成率可以變﹐但Higgs誤導了他﹐使他同意密爾提出的佃農分成比率是由風俗決定的說法。如果馬氏知道佃農分成的比率有大變化是實情﹐以他的天賦﹐找到多年後我分析的答案用不著三十分鐘吧﹗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的詹森(D. Gale Johnson)告訴我﹐這個佃農分成五十﹑五十的“風俗”傳言真的害死人﹗他那一九五○年發表的關於佃農的文章也被這風俗之見約束著﹐跟阿羅一起以方程式證來證去也得到無效率的結果。
缺環依舊﹐主要是因為經濟學者沒有深入地考查契約結構。詹森當年知道我是在填補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缺環﹐不斷地鼓勵﹐我終生感激。
第三節﹕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詞是威廉姆森(O. Williamson)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今天﹐中國的朋友喜歡稱我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不一定錯。一九九五年巴澤爾在他的論文結集的序言中寫道﹕“我今天認為﹐一九六九年史提芬來到西雅圖時﹐他已經是經濟學行內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第一把手了。”是一夫之見。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就是產權及交易費用的學問﹐而巴兄後來也是這範疇的一個重要人物。
今天回顧﹐六十年代時﹐從事產權及交易費用研究的主要是四個人﹕阿爾欽﹑科斯﹑德姆塞茨和我。在此之前﹐在類同範疇作出重要貢獻的有奈特(一九二四)﹑科斯(一九三七)﹑哈耶克(一九四五)﹑戴維德(五十年代口述)﹑H. S. Gordon(戈登﹐一九五四)等人。他們的作品雖然重要﹐但過於零散﹐沒有凝聚力﹐帶不起一個思想範疇(paradigm)的發展。六十年代初期﹐有關交易費用的三篇文章差不多同時出現﹕科斯寫社會成本問題(一九六○﹐其實面世是一九六一)﹔施蒂格勒寫訊息費用(一九六一);阿羅寫發明的收錢困難(一九六二)。這三位皆大師人物﹐但我不能把後二者算進去﹐因為他們沒有分析產權﹐沒有進入制度的範疇內。
“舊”與“新”的分別
有“新”不可以沒有“舊”。舊制度經濟學是關於什麼呢﹖有兩部分。其一是“制度比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主要是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什麼好什麼不好﹐概念模糊﹐內容空洞。那些是“二戰”後的“冷戰”學問﹐是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之爭。與此同時﹐經濟發展學的胡說八道盛極一時。弗里德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消費函式理論》是一顆亮星掠空而過﹐讓大家看清楚一個好去處﹕經濟學可以解釋現象。科學方法的大辯論在經濟學從那時開始﹐持續了約二十年。
舊制度經濟學的第二部分﹐是經濟歷史。我很喜愛這部分﹐因為其中的表表者考查史實嚴謹詳盡﹐而歷史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一般是有趣的話題。經濟歷史搞得深入的都是有學問的人﹐吸引著我。很不幸,當時的經濟歷史專家一般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欠缺充分的掌握﹐對假說驗證的法門趕不上潮流﹐因而被操作方程式的小看了。
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新制度經濟學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起﹐其出現是為了解釋現象﹐是為了驗證假說﹐歷史與事實的考查受到重視﹐從事者對邊際分析有充分的掌握。要點是引進產權及交易費用這兩項不容易處理的局限。這是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初期的發展﹐跟著的我失望。
契約結構的思維源自捆綁銷售
我是一九六一年進入洛杉磯加大研究院的。六二年開始細讀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讀了三年。六七年的秋天我才有機會認識科斯﹐那是我寫好《佃農理論》之後了。起碼有三本書介紹科斯定律之後以我的佃農理論作為套用該定律的示範﹐可見科斯對我的影響隱瞞不了。科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下章才說。其實戴維德的捆綁銷售口述傳統對我的佃農理論的影響可能更大。這是因為捆綁銷售顯然是一種有結構性的契約——只有一個價而沒有其他條款的交易契約沒有結構。佃農分成的契約沒有一個明顯的價﹐所以我逼著要從有結構性的契約那方面想。佃農理論動筆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赫舒拉發與阿爾欽。我重複地聽他們的課聽了三年﹐而佃農理論是在他倆指導下寫成的。
德姆塞茨的貢獻
六十年代初期德姆塞茨也在洛杉磯加大。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員。此君善忘﹐後來竟然完全記不起我替他改過卷﹗在加大時他的著作不怎么樣﹐但六三年轉到芝大﹐受到施蒂格勒與科斯的影響﹐一下子變作天才。六四年初阿爾欽偷偷地給我一份說明不可示人的厚文稿﹐德姆塞茨寫的(後來分為兩篇文章發表)﹐對我影響很大。德兄是難得一見的文筆表達得清晰絕倫的人。受到科斯的影響﹐他把交易費用的考慮帶到闡釋帕累托至善點那邊去。得到啟發﹐我後來把問題推到盡﹐得到的結論是如果所有局限條件都放進分析﹐帕累托條件或至善點一定得到滿足﹐無效率或浪費的出現﹐是因為某些局限沒有放進分析﹐而解釋行為所需要指定的局限不一定滿足帕累托。換言之﹐可以驗證的假說需要引進的局限﹐不需要滿足帕累托﹐而無效率的出現永遠是源於有不需要指定的局限被漠視了。這教我後來分析問題時必用如下法門:凡是足以解釋行為但沒有滿足帕累托的假說﹐我必定停下來考慮是哪些局限條件我沒有放進去﹐衡量這些被排除的局限與要解釋的現象是否沒有關係的。 阿爾欽的口述傳統
轉談阿爾欽的貢獻吧。兩年前某媒體問誰對我的影響最大﹐是弗里德曼還是科斯﹖我回答說都不是,是阿爾欽。我歷來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阿爾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經濟學者。不止我一個人這樣看﹐但我有我的理由。
阿爾欽當年算不上是名滿天下(今天是)﹐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但過於分散,沒有主題。其二是他的偉大思想主要是授課時的自言自語﹐以及跟他研討時聽者得到的啟發。為什麼會是這樣我不懂。他有些了不起的思想寫進大學一年級的課本去﹐沒有像在正規的學報發表那樣有系統地發揮。例如今天在中國好些同學欣賞的一句話——價格決定什麼遠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重要——我只是從阿師的口述聽到﹐發展開來是非常重要的思想。主要是由我發展的﹕我推到租值消散及減少租值消散那邊去。阿爾欽歷來高興我拿著他的口述用文字發揮——我當然不會忘記說來源是他的。
一個例子可讓同學們知道阿爾欽思想的驚人深度。在課堂上教需求定律﹐他不畫曲線﹐不用方程式﹐不教彈性係數﹐不教消費者盈餘﹐不談等優曲線﹐不管收入效應或替代效應。只談一條向右下傾斜的曲線的含意﹐他可以自言自語地講五個星期﹗天下沒有誰可以做到。我重複地聽了他的課﹐次次不同,加上憑自己的一小點本領﹐作修改﹐加補充﹐推出無限變化﹐就成為我今天教同學的洋洋大觀的需求定律了。
我認為阿師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可不是他七十年代跟他人合著的兩篇大名文章﹐而是他口述的關於產權與競爭的傳統。這傳統在《科學說需求》第三章我寫過﹐本章第五節會再深入地發揮。今天阿爾欽被稱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主要是他的學生傳開來的。
第四節﹕無從觀察的不幸發展
我今天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不幸發展﹐源於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推敲契約的選擇時﹐舉棋不定﹐引進了“卸責”(或偷懶)這個無從觀察的變數。後來一九六九年發表的關於契約選擇的文章﹐其中有兩段話寫來大費思量﹕
任何契約組合著不同物主﹐牽涉到洽商費用之外﹐還有監管投入與分配收入的費用。這些費用加起來是交易費用﹐分成契約的交易費用看來要比固定租金契約或工資契約的為高。佃農分成﹐除了分成率的議定及履行的監管﹐還有土地與非土地的投入比率需要決定﹐種植的選擇需要洽商。⋯⋯固定租金或工資契約呢﹖租金或工資決定了﹐只需契約的其中一方就可以決定土地或非土地的投入與種植的選擇。還有,佃農分成是基於產出的真實的量﹐地主必須監察實際的產量為何。這樣﹐議訂契約條款與監管行為﹐分成契約的交易費用會比固定租金或工資契約的為高。
固定租金與工資契約的交易費用排列則顯得不明確。土地或大或小的監管費用應該比勞動力的監管費用為低。這是說﹐卸責(shirking)或偷懶的行為﹐在工資契約及分成契約均存在﹐監管費用不菲。另一方面﹐雖然卸責的行為在固定租金契約下不嚴重﹐土地與其他土地附帶著的資產的維護﹐地主的監察費用會比分成或工資契約為高。這樣衡量﹐為了節省交易費用﹐分成契約永遠不會被採用。為什麼會有分成契約呢﹖
據我所知﹐卸責或偷懶等話題﹐這是第一次在經濟文章中出現﹐而我在該文補加了一個長註腳﹐把shirking帶到件工契約﹑餐館付小費等契約去。後來這篇文章被認為是觸發了代辦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的發展。
一九六八年阿爾欽造訪芝大﹐師徒驀地相逢﹐傾談的時間當然多了。午餐時我跟阿師研討卸責這個問題﹐舉出當時困擾著我的抬石下山的例子﹕兩個人抬石下山﹐合作一起抬每次的量大於兩個人分開抬加起來的量。但合作抬石﹐甲會把重量推到乙那邊去﹐乙亦會把重量推到甲那邊﹐結果是每次二人合作抬得的總量會高於二人分開抬的總量(因為不這樣他們不會合作)﹐但會低於二人合作不卸責的總量。有卸責行為﹐二人合作的總量從何而定呢﹖ 廣西縴夫惹來麻煩
一九七○年﹐多倫多大學的John McManus到我西雅圖的家小住。他正在用我的卸責思維寫公司理論﹐我向他舉出“二戰”逃難時在廣西見到的縴夫在岸上拉船﹐有人持著鞭子監管縴夫的例子。當時母親對我說﹐持著鞭子的人是縴夫們雇用的。一九七一年﹐我的想法改變了﹐認為卸責無從觀察﹐以之推出的假說無從驗證。跟著科斯問我對卸責怎樣看。我說想法改變了﹐認為這概念不管用。我可不知道,McManus的公司文章寄到科斯主編的學報。後來該文延遲到一九七五年才在《加拿大經濟學報》發表。其實不管作者是誰﹐我不會反對發表該文。
廣西縴夫的例子後來在新制度經濟學大行其道。McManus說是我的﹐M. Jensen與W. Meckling一九七六年發表的公司理論說是McManus的﹐再後來一位澳洲教授竟然用我的名字為題﹐批評縴夫雇用持鞭者之說不對。其實麻煩的地方不是錯﹐而是不可能錯﹐於是無從驗證﹐沒有解釋用場﹕卸責或偷懶無從觀察﹐而法律的定義不論﹐究竟是誰雇用誰只有天曉得。當年香港大學要聘請新校長﹐同事問我意見﹐我說希望新來的知道是我們雇用他﹐不是他雇用我們。是說笑﹐但有誰可以證實我說的不對呢﹖
卸責﹑敲詐﹑機會主義
一九七二年﹐阿爾欽與德姆塞茨合作﹐以卸責為主題發表的一篇關於經濟組織或公司為何出現的文章﹐說合作大家有利﹐但卸責的行為需要監管﹐有監管功能的公司組織於是出現。該文是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發表過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我不同意他們的分析﹐認為卸責無從觀察﹐以之作為基礎的假說因而無從驗證。一九七八年﹐B. Klein﹑R. G. Crawford和阿爾欽三位合作發表了一篇也是大紅大紫的關於公司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中譯縱向一體化)的文章﹐卸責之外加進了勒索﹑敲詐等理念,我認為也是無從觀察﹐於是無從驗證。
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市場與等級》也紅極一時﹐在卸責等行為上提出了機會主義
(opportunism)等多項術語。以“機會主義”為首的術語其實是說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但他把大家知道的基礎假設分類組合﹐可惜無從觀察﹐推不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是說威廉姆森的分析沒有道理﹐而是我想不出怎樣驗證﹐也沒有見過有說服力的實證研究。同樣﹐我不否認人會卸責﹑勒索﹑恐嚇或敲詐﹐但我們可以怎樣在觀察上鑑定呢﹖這些理念促使六十年代變得式微的博弈理論八十年代初期捲土重來﹐其普及興趣遠超早一浪的五十年代。也同樣﹐我們不能否認人會博弈——我不否認自己也博弈——但怎樣用觀察到的行為或現象來驗證博弈假說是一個我解不開的難題。我們讀到的無數博弈例子只是說故事﹐不是有機會被事實推翻的假說。
石油運輸推理與事實不符
讓我回頭說上文提到的Klein-Crawford-Alchian合著的關於縱向一體化的文章。該文的主旨是在一家機構之內﹐如果用於產出的資產對該機構有特殊的﹑不可分割的用途﹐不把這種資產合併使該機構一體化會遇到卸責﹑勒索﹑敲詐等干擾﹐使機構擁有的投資租值(即我說的上頭成本)被榨取了。在初稿中他們舉出兩個有說服力的例子﹕石油企業傾向於建造自己的輸油管﹐但租用運載石油的船。理由是運油船不同的企業皆可以用﹐租用因而普及﹐但輸油管是專為石油出處與煉油廠之間的運輸而設﹐企業不自己建造﹐靠租用輸油管﹐豈不會容易地被油管的擁有者勒索或敲詐了﹖是可信的故事﹐也是以物為本的推理,比威廉姆森及博弈理論等以人為本的推理高明多了。
我當時做加州標準石油的顧問﹐對石油運輸的實情是專家﹐知道事實不對﹐於是去信阿爾欽﹐說﹕所有有規模的石油企業都各自擁有他們的運油船隊。三位作者因而把運油船傾向於租用的例子刪除。當時我被雇用為換油契約的反托拉斯顧問(見《受價與覓價》第五章第三節)﹐知道一家石油機構可以容易地通過石油交換契約而用另一家的輸油管﹐可以容易地租用油管﹐也有不採油不煉油﹑只建造輸油管租給石油企業的機構。可惜當時作為反托拉斯顧問﹐契約指明我不能跟外人談換油這個話題。推理邏輯對﹐但事實錯得一團糟﹐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兩方面的困難
我認為困難起於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卸責或勒索等行為雖然不能說沒有﹐但在觀察上我們無從肯定是些什麼。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觀察上排列某些費用的增加或減少﹐例如我們可以從排隊輪購的人數增加而說購買的時間費用會增加﹐從而以這樣的局限轉變解釋行為。但勒索無從觀察﹕某甲對我笑得有點怪﹐甚或直說要勒索我﹐我怎可以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呢﹖我們要從可以觀察到的局限轉變來解釋契約安排的轉變﹐然後再以之解釋行為。
第二方面﹐不管是卸責還是敲詐﹑勒索﹐交易費用的局限千變萬化﹐我們不容易猜測這些局限轉變帶來的契約安排會是怎么樣的。一個上佳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石油交換契約。一九七六年加州標準石油聘請我做顧問﹐因為石油交換惹來反托拉斯官司﹐要求我解釋是發生著些什麼事。我很快就意識到﹐石油工業的專家們根本不知細節﹐不清楚石油交換是怎么一回事。甲公司問乙公司﹕我有油﹐可以在某地交給你,你可否從某地還給我呢﹖大家同意﹐換油契約就簽訂了。因為換油往往要換幾次才得到自己需要的﹐我要花兩年時間才能清楚地以理論及事實證明石油交換是為了節省運輸費用。簡單嗎﹖有關的反托拉斯官司打了不止二十年﹗
這裡的問題是上文提到的寫縱向一體化的三君子﹐說輸油管不租用﹐要自己建造﹐因為有勒索﹑敲詐等行為﹐但事實是當時石油公司之間以換油契約處理了不止半個世紀﹐而這些交換是輸油管租用的替代﹐也可以看為是一種富於想像力的輸油管租用安排。不作實地考查打死你也想不到﹗經濟學者不應該坐在辦公室猜測外面的世界。他們要從考查真實世界出發﹐然後從觀察到的局限轉變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作解釋。
布魯納的影響
今天回顧﹐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非常強勁。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被認為經濟學少林寺的﹐我的感受是跟洛杉磯加大互有長短﹐差不多。六十年代初期加大有一個布魯納(Karl Brunner)。我可以容易地推出加大的阿爾欽與芝大的弗里德曼抗衡﹐但芝大可沒有一個布魯納。
布老師跟我合不來。我喜歡先以預感魂游四方的思考方法﹐他不接受﹐而我憑想像語驚四座的行為,在布老師的課上我不敢開口。布魯納是我知道的最重視邏輯規格的經濟學者﹐每一個關係他要拆到盡來看﹐每一個字的意思他不放過。初時我覺得他有點小題大做﹐但過了不久我意識到﹐任何問題推理推到盡頭﹐答案一定要通得過布魯納劃定下來的邏輯規格那一關。
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我開始上布魯納的課﹐學巨觀。來得震撼是他指出凱恩斯提出的投資等於儲蓄的均衡點﹐可不是傳統說的意圖不意圖﹐也不是事前或事後等胡說八道﹐而是有可以觀察及無從觀察的分別。可以觀察到的投資與儲蓄永遠一樣﹐但意圖的投資與意圖的儲蓄則無從觀察﹐不是真有其物。這就帶到凱恩斯說的投資等於儲蓄的均衡﹐只可能是思想上的推論﹐不是真有其事﹐跟物理學說的真有其事的均衡是兩回事。若干年後﹐我認為凱恩斯學派的均衡分析全盤錯了﹕投資與儲蓄永遠相等﹐只是在好些情況下市民偏向投資於不事產出的項目﹐導致經濟不景﹐不是因為市民增加了儲蓄的意圖(見《收入與成本》第三章第一節)。
無從觀察可免則免
跟物理學不同﹐經濟學的均衡是一個概念﹐不是事實。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駕車和科斯從溫哥華到西雅圖﹐途中他說“均衡”沒有用處﹐應該取締。我回應說經濟學的均衡跟物理學不同﹐前者不是事實,但應該保留﹐因為經濟學的均衡是指有足夠局限條件的指定﹐邏輯上可以推出有機會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假說﹐而不均衡是指局限指定不足﹐於是無從驗證。科斯的回應﹐是我可能成為另一個馬歇爾。他可不知道﹐我對經濟學的均衡闡釋源自布魯納﹐也跟阿爾欽研討過。從來不否認我的思想全部是偷來的——我的本領只不過是搞出變化。
這就帶到一個遠為嚴重的問題。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交叉那個均衡點也是空中樓閣﹐在真實世界不存在。需求量與供應量其實是同類的量﹐因為供應是為了需求(見《受價與覓價》第二章第四節)。這裡的麻煩﹐是經濟學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說價格下降需求量上升﹐但需求量是指意圖之量﹐不是真有其物,需求定律的本身於是無從驗證。
一個可以驗證的假說﹐說如果甲的出現會導致乙的出現﹐甲與乙必須可以在真實世界觀察到才可以驗證。現在需求定律中的需求量不是真有其物﹐而這定律不可或缺﹐我們要怎樣憑這定律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是大費思量的難題。單是處理一個無從觀察的“需求量”變數﹐我們要把這個意圖變數轉到一個事實變數那邊去﹐為此我想了很長時日(見《科學說需求》第六章)﹐而今天新制度經濟學及博弈理論的發展﹐惹來無數無從觀察的術語或變數﹐不可能不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
在《科學說需求》第四章寫《功用的理念》時,我說“功用”是邊沁想出來的﹐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為恐搞出套套邏輯﹐我不用。貝克爾及不少大師喜歡用﹐是他們的取向。但他們應該知道﹐要以功用理論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一定要推出有兩個或以上的可以觀察到的變數的聯繫才可以驗證。他們怎樣處理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可以完全不用“功用”這個理念而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老實說﹐簡單得多﹐強力得多﹐準確得多。
我不懷疑自己的經濟解釋可以來去縱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每一步我避開了無從觀察的變數。在經濟學上﹐我不能不接受因而要悉心處理的無從觀察的變數只是需求量﹐其他無從觀察的變數我避如蛇蠍也。
第五節﹕契約理論的基礎
我在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交易費用與契約理論,算不算是新制度經濟學是無關宏旨的。從一九六八年發表的《私產與佃農》到二○○八年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自己比較稱意的作品全部是以交易費用與契約為主題。沒有刻意這樣做﹐只是走上了一條通道就繼續走下去。可幸變化多﹐自己認為有趣﹐有滿足感。走這條路的行家奇怪地少﹐只我一士諤諤﹐新鮮的題材俯拾即是。要說的是﹐《經濟解釋》的前三卷牽涉到的主要是傳統的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我把這些傳統之見修改了不少﹐沒有解釋力的或可以被較簡單理論替代的給我淘汰了。我喜歡簡單的理論﹐但要搞出變化。在寫前三卷的過程中我免不了在這裡那裡加進契約與交易費用的思維﹐跟傳統範疇的分離因而再增加了。
需要補加一個理論架構
我認為在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馬歇爾傳統提供的架構相當完整﹐只是在收入分配這方面費雪的利息理論不能不加進去。馬氏傳統對成本與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漠視了交易費用﹐對假說驗證興趣不足——這些缺失大致上我作了修改與補充。還有的是﹐馬氏的傳統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我認為不對﹐簡略地說過﹐本卷分析公司的契約性質時會再澄清。
本章寫經濟學的缺環﹐說傳統漠視了契約安排這組重要現象﹐其實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契約的一般理論﹐即是說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之外我們還需要有一個關於契約安排的理論架構。可惜為了一個頭痛問題我遲遲不敢動筆。真的很難。每個人在局限約束下爭取利益極大化是我接受的假設﹐沒有意圖偏離或發明新的。然而﹐單是二十世紀的史實﹐有好幾次人類差不多毀滅自己。我不懷疑人類自我毀滅是可能發生的事﹐但每個人爭取自己的利益極大化怎可以導致這樣的悲劇呢﹖老師赫舒拉發曾經出版過一本書﹐以星球大戰的一個續集之名為題﹐稱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力量的暗面》)﹐我對他說這名目起得好!這是以博弈理論處理人類的自我毀滅。師徒皆認為大悲劇可能出現﹐但徒弟認為博弈理論無從驗證﹐因而不是好去處。
人類自我毀滅的契約安排
這就是問題。斯密的古典傳統看不到悲劇﹔馬歇爾的新古典傳統也看不到悲劇。薩繆爾森說得好:“上帝鑄造了什麼﹖帕累托至善點﹗”原則上﹐一般而言﹐在局限下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只會改善社會﹐何來人類滅絕了﹖在馬歇爾傳統的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個理論架構下﹐無論局限怎樣轉變﹐除非遇上考古家說的滅絕恐龍的天災﹐大悲劇不會發生。換言之﹐邏輯上﹐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不容許大悲劇出現。然而﹐二十世紀的經驗說人類自我毀滅是可以出現的。
我終於想到的答案﹐是大悲劇只能源於制度出現了問題﹐也即是契約的安排出現了問題。這裡的關鍵﹐是契約或制度可能帶來大悲劇主要源於某些安排是眾多的人不能不一起參與的﹐而參與後不能退出。你跟另一個人合夥做生意﹐破產收場﹐對社會不利,但為禍不大。數萬人購買一間公司的股票﹐破產對社會更不利﹐但每個股民隨時可把股票出售﹐退出﹐對社會整體的不利影響有明確的限度。然而﹐如果一個社會的每個人都要參與一個組織的契約安排﹐不能選擇不參與﹐也不能在中途退出——好比昔日中國的人民公社——大災難可能出現。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契約安排﹐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契約﹐國民要一起參與﹐退出走投無路﹐大家因而被捆綁在一起﹐是大災難出現的一個必需條件。不是大災難的足夠條件﹐而是必需的。
我不要在這裡分析那些不罕有的走投無路而又不能退出的契約或制度安排﹐因為這類安排必然牽涉到政治﹐我不懂。然而﹐要推出一個有一般性的契約理論架構﹐漠視不能不參與也不能退出那部分是美中不足。本卷寫到第五章我會從三方面猛攻一下行內朋友期待我寫已久的國家理論(theory of the state),“走投無路”會是其中的一個含意。
阿師之見提供架構基礎
我要從阿爾欽的思維說起。阿師之見﹐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社會必有競爭﹐而界定競爭勝負的遊戲規則是產權制度。阿師也認為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決定誰勝誰負的準則是市價。價格決定什麼因而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重要﹕通過競爭的勝負選擇﹐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就被市場決定了。
從這個簡單而又清晰的角度看產權沒有科斯定律那樣看產權來得那么震撼﹐但阿爾欽的看法提供了一個分析架構的基礎﹐比科斯的遠為容易發揮。作為後學我二者皆用。這裡先從阿師教的發揮﹐從科斯定律發揮的是第二章的話題。我是唯一得到阿爾欽及科斯親自傳授的後學——他們的主要學問大致上我都吸收了。是運情﹐天下只我一個。阿爾欽比我年長二十二歲﹔科斯比我年長二十五歲——前者教了我四年﹐後者是我的深交。沒有一個同學或行內朋友有我的際遇。
只一種準則沒有租值消散 發揮阿師的思想﹐我的延伸主要是三點。第一點﹐當年我首先想到的﹐是作為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市價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這是因為在市場交易﹐要獲取他人的物品你必須自己先有產出﹐對社會有所貢獻﹐才可以在市場通過市價交換。當時在西雅圖華大我跟巴澤爾研討了多次﹐想不出不會在某程度上導致租值消散的任何其他準則——從排隊輪購到論資排輩到人際關係等等的可以決定勝負的準則,某程度必有租值消散出現。你建議市價之外的任何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我可以告訴你租值消散會在哪裡出現——這是當年巴兄和我的共識——只有市場的交換價格推不出租值消散。
這就帶到後來我寫公司性質時的一個意識﹕市價的採用是一項相當奢侈的玩意﹐因為產權的界定﹑契約的履行等的社會或交易費用不菲。在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中﹐能通過市價決定勝負的只是一小部分。這也使我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會走的路時﹐採用的簡單要點﹐是只要社會或交易費用略為減少﹐增加了一點以市價為競爭準則的經濟活動﹐在國民收入的比例上租值消散會大幅下降﹐經濟成長可以一日千里。當時舒爾茨﹑貝克爾﹑弗里德曼等大師不同意我對中國的推斷﹐我無從向他們解釋我用的是他們不熟識的思想範疇。是的﹐一九八一年我清楚地看到減低租值消散或減低社會費用的局限轉變在中國開始出現﹐而又認為這轉變將會持續。
競爭不可以沒有約束
第二點﹐源於阿爾欽及奈特的思維﹐是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我跟著想到毫無約束的競爭必會導致龐大的租值消散﹐足以導致人類滅亡﹐因而想到減少租值消散是社會的一般取向。
競爭一定要有約束這個觀點﹐中國的經驗給我很大的啟發。一九七九年到廣州一行﹐見到當時盛行的走後門與幹部的等級排列﹐示範著差距很大的收入享受﹐讓我耳目一新。我當時的意識﹐是生下來人的天賦就不平等﹐在一個廢除私有產權的制度下﹐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可能達到社會的均衡。幾年之後﹐這觀點得到明顯的改進﹕以人的等級排列權利﹐是在沒有產權約束競爭的情況下的一個需要的安排﹐因為可以協助減低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帶來的租值消散。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從以等級排列權利轉到以資產排列權利那邊去﹐租值消散因而下降了。為何會成功地轉換了競爭準則﹐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有詳盡的解釋。
所有競爭約束可從契約看
最後一點﹐算全部是我自己的吧(一笑)。這點是﹕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而這些約束可以看為契約的安排。私有產權﹑論資排輩﹑管制規例﹑風俗宗教等﹐皆可以看為廣義的契約安排﹐因為這些約束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需要互相遵守的規則﹐無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接受的。契約的存在不一定要有市場成交。從契約的角度看約束競爭重要﹐因為產權的理念往往來得抽象﹐相比起來﹐契約的角度是比較直接地帶到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那些方面去。不是說所有競爭的約束都要從契約的角度看﹐而是說可以這樣看,好些時這角度看得比較快﹐也比較清晰。
這裡同學們要小心了。產權與交易費用是約束人類行為的局限﹔契約安排的約束也是局限。後者的變化源於前者的變化。有時我喜歡用前者﹐有時喜歡用後者﹐但不能二者一起用﹐因為是重複了。
一人世界沒有社會。沒有社會不會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產權的問題因而談不上。沒有社會不會有交易費用﹐也沒有租值消散。在好些情況下﹐把社會或交易費用作為租值消散看可以把問題看得清楚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把約束競爭的費用看作制度或交易費用﹐也即是可以看作是契約安排與監管的費用了。上文說過﹐契約是為約束競爭而出現的。
本章以《經濟學的缺環》為題﹐其主旨是說傳統經濟學對契約的漠視﹐帶來的不幸效果是人類因為競爭而出現的多種行為我們解釋不了。這是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前的困境。今天我們有了長進﹐雖然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很失望。如果同學們能用心細讀《經濟解釋》的前三卷﹐會察覺到我對市場與生產行為的解釋跟傳統的解釋有很多地方不同。這是因為在寫前三卷的過程中﹐我不斷地以契約及交易費用的思維來填補傳統的互相矛盾或一片空白的地方。
同學們也會察覺﹐本卷讀下去有好些題材我是重複再說的。這是同學們的要求。雖然我已經盡己所能寫得淺白﹐但題材著實不易﹐按節發表時不少同學認為我用不同的文字再說有助於他們能明白多一點。
序言
從新古典發展起來的經濟理論又稱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即是人的行為或行為促成的現象一律是人類自己選擇的結果﹐包括自取滅亡的行為,而這選擇是受到局限條件的約束。局限的轉變可以翻為成本或代價的轉變。代價也是價﹐所以不管有沒有市場﹐需求定律同樣用得著。
複雜無數倍的分析是我們的社會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老師阿爾欽說因為競爭出現了產權﹔我改了一下﹐說約束競爭出現了契約﹐進一步稱約束競爭的契約費用為交易或制度費用。這些費用是成本﹐或是代價﹐也即是價﹐其變動引起的行為又再要受到需求定律的約束了。
契約是制度﹐契約的選擇就是制度的選擇。經濟科學不問觀察到的契約或制度是好還是不好。實際的看法是﹕契約或制度是人類選擇的結果。我們因而問為什麼會有這種那種不同契約或不同制度的安排。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思考《佃農理論》時﹐我把佃農作為契約看﹐問﹕為什麼會有佃農分成這種契約呢﹖一九六七年初我以一整章處理契約的選擇﹐一九六八在芝加哥大學找到新資料﹐作了補充﹐《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契約安排的選擇》一九六九年四月發表。那是我知道的第一篇開門見山地處理契約的經濟學文章。
然而﹐雖然契約也是制度﹐但比起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市場的契約選擇屬小兒科。我要到十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才開始苦思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結果是一九八一年寫好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篇長文。因為行內朋友反對的無數﹐該文要到一九八二年才發表。推斷肯定﹐理論清晰﹐而跟著中國的發展仿佛是拿著該文對著鏡子看。這個毫無碰巧成分的準確推斷使我對自己關於制度選擇的分析充滿信心﹐今天回顧這信心來得不易﹐因為曾經有四位獲諾獎的經濟學朋友當年反對該文的推斷。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從那時到今天我在契約與制度的思考上沒有中斷過。這次從頭再寫二○○二年出版的《制度的選擇》﹐在沒有其他重要工作的干擾下用了十八個月。思想集中﹐應該有很大的改進。
張五常
二○一三年聖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