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格蘭
科格蘭(1841—1909),法國著名演員,由於他的弟弟也是一位名演員,因而一般稱他為老科格蘭。他出身於一個麵包師的家庭,在巴黎音樂院戲劇班受過正規演劇教育,一八六一年第一次登台,不久即孚聲譽。科格蘭一生以演喜劇為主,長期在法蘭西劇院演出,—八八六年後曾到歐美各地作旅行演出,均獲成功。後來他曾帶過自己的劇團,也主持過一個劇場,主要從事導演工作。科格蘭的天賦外形和演技都很好,善於出色地解釋和設計角色,演出風格節制有度,被認為是法國表現派表演流派的代表。他還作過一些藝術演講,寫過一些表演論文,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小冊子《演員的藝術》。
其作品《演員的藝術》
《演員的藝術》凡十四節,論及表演的各個方面,概而不枯,實而不煩,是一篇很好的戲劇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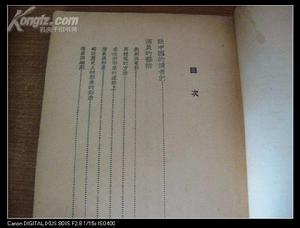 中央電影局52年初版《演員的藝術》
中央電影局52年初版《演員的藝術》科格蘭是狄德羅表演理論的基本精神的繼承者。狄德羅寫那篇著名的《關於演員的是非談》是在一七七三年,但發表卻晚至一八三〇年,狄德羅已去世快半個世紀了。科格蘭寫《演員的藝術》是又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事。狄德羅既非演員,又非導演,他是從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的高度,憑藉著深厚的審美素養來觀察表演藝術的,因而也難免夾帶一些在科格蘭這樣的戲劇實踐家看來有點隔靴搔癢的外行話。但是,他關於演員要感動別人自己未必要感動、重要的是嚴格控制自己等等的基本論斷,科格蘭認為是正確而可貴的,因而把它作為建立自己的表演理論的一個重要傳統依據。任何一門學科的理論,不是單憑—個學者的思辯能力就能完整建立起來的。狄德羅對表演藝術的可貴觀點由於缺少理論家本人的實踐滋養,未能蔚成規模;而在理論水平上顯然要低得多的科格蘭,卻把狄德羅的觀點伸發、補充、調理成了很象樣子的表現派表演理論形態。《演員的藝術》第十節在談到演員表演不能全然丟開自己時說:
我重複一遍:藝術不是“合一”,而是“表現”!
人們總是把這句話作為概括“表現派”的基本特徵的警句,並認為這就是“表現派”名稱的淵源。
科格蘭表演理論的基石是所謂兩個“自我”。這也是他對戲劇理論的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貢獻。科格蘭認為,表演藝術與其他各種藝術相比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創造者和創造工具的統一,演員既是藝術創造的操縱者,又是藝術創造的工具;但即使統一於一身,這種兩重性並沒有消泯,相反,正是從這兩重性的互動關係中,可以找到表演藝術的奧妙所在。所謂兩個“自我”,就是兩重性的形象化說法。科格蘭的這一段話是現代各國演劇界所熟知的:
在創作藝術作品時,畫家使用畫布和畫筆;雕刻家使用粘土和雕刀;詩人使用文字和詩才,即韻律、音步和韻腳。藝術因工具而異。演員的工具就是他自己。
兩個自我
他的藝術材料,也就是他為了創造一件作品而對之進行加工和塑造的東西,是他自己的臉、他自己的身體和他自己的生活。因此,演員應當具有雙重性:他的一部分自我是表演者,即操縱者,另一部分自我是他所操縱的工具。第一自我構思,或者不如說,按照作者的構思想像出所要扮演的人物(因為構思是作者的事),不管是達爾杜弗、哈姆雷特、阿諾爾弗或羅密歐;然後由第二自我把構思實現出來。演員創造人物的天才,就在這種雙重性之中。
這個理論創見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一語道破了表演藝術的特質,而且由於這種特質是建築在一對既統一又對立的矛盾之上的,具有很大的伸發和迴旋的餘地。即便是與科格蘭對立的表演藝術學派,也可以運用兩個“自我”的學說來闡釋自己的主張,只不過在這兩者的關係上有不同的理解和處置方式罷了。在科格蘭之前曾有不少人論述過演員與角色的矛盾,科格蘭的貢獻是把這對矛盾引入實際表演過程,引入演員自身,從而成了一對內在矛盾,比一般地討論演員與角色的關係更深入、更緊切了。
科格蘭首先借用這對矛盾,說明演員作為工具的一面,即第二自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第一自我當然是一切藝術家都具備的,但第二自我卻不是這樣了,有的不具備,有的不顯然,而且都不會把有血有肉的第二自我作為藝術創造的全部成果。科格蘭說,在構思要創造的人物形象的時候,主要是第一自我在活動,這種活動方式與畫家構思形象有相似之處,但是,畫家是把構思的成果體現在畫布上,而演員則把構思的成果體現在第二自我上,即體現在自己身上——與構思者的“自我”共處一體但又擔負著不同使命的另一半“自我”之上。在排演過程中,原先進行著構思的第一自我是不是已經完成任務而消遁死滅了呢?沒有,它在這個時候充當著批評者和監督者,以使構思在第二自我中體現得忠實、準確、生動。這是一個頗為艱苦的過程:第一步,監督第二自我把角色的服裝穿上,把該有的步態、神情摹仿過去,主要是外形上的縫剪裁貼,力求逼真;第二步,還要讓第二自我象角色一樣言談舉止,把角色的整個靈魂都捧攝出來,灌注於自身。這每一步,都要讓原先擔負構思任務、現在擔負批評和監督任務的第一自我滿意。只有在這時,演員才可以一個角色的身份登台,他已完成了轉化。觀眾見到他,不應該叫演員的名字而應該叫角色的名字了。科格蘭在這裡生動地述說了演出的準備過程,實際上也把表演藝術的創作特性揭示了出來。把自己構思的形象(根據劇本),全面地轉移到自己身上,這就是演員的藝術。在論述這一過程時,科格蘭把第一自我的主要功能規定為保證第二自我對角色的忠實,因此與“體驗派”表演學派還沒有發生矛盾。體驗派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員的自我修養》一書中曾引述科格蘭對這一準備過程(即正式上演前的排演過程)的描繪,並認為至此科格蘭與體驗派還是一致的。
分歧主要發生在表演過程中。科格蘭表演理論的重心也體現在這裡。簡言之,當演員化為角色在舞台上活動的時候,千萬不能失去自己,千萬不能失去冷靜的控制。這就使兩個自我的矛盾關係又翻出了一個層次:即使在正式表演時,第一自我仍然是個未離職守的監督者。
科格蘭所謂第一自我對第二自我的監督,實際上就是在表演時理智對於肉體的監督。這中間沒有感情的地位。作為第二自我的肉體,當它逼肖角色地行動的時候,當然也要表現出種種感情,但這僅止於“表現”而已,是第一自我的理智作用的產物。因此,這不是由感情到感情的過程,而是由理智到肉體的過程。科格蘭關於這一方面的見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段著名論述中:
第一自我的支配力越強,藝術家就越偉大。理想的境界是:第二自我,我們卑賤的肉體,就象一塊柔軟的粘土,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不同的角色捏出不同的形狀來。
演員必須控制自己,即使當深受他的表演感動的觀眾以為他已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的時候,他仍然應當看清自己正在做什麼,判斷自己的表演並且控制住自己——一句話,在他竭盡全力,異常逼真地表現某種情感的同時,他應當絲毫不感受這些情感。
要研究你的角色,化入你的角色之中,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不要失去你自己,要把韁繩握在自己手中。無論你興奮若狂或是痛不欲生,你的第二自我必須始終處於你的永遠無動於衷的第一自我監督之下,保持在你事先考慮好並事先設定的軌道之中。
這是表現派表演學派的重要經典。一句話:演員要清醒、自如地掌握著全部表演。
但是,科格蘭又一再申述,這種自我掌握和自我控制絕不顯露在外。顯露出來的是角色,而且是一個純粹的角色,不留演員自身的殘痕。演員的掌握和控制,演員的冷靜和理智,只是悄悄地、暗暗地在起作用。為了說明這中間的微妙關係,科格蘭舉了莎士比亞和莫里哀劇作的例子。莎士比亞和莫里哀筆下的那些人物,幾乎沒有一個可以找出這兩位作者自己的面影來,每個角色都是活生生的典型;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兩位作者的人物作一個總體考察,那就會發現其中一條鴻溝:即使寫同一身份的角色,莎士比亞和莫里哀也會顯出明顯的區別,更何況他們對人物又有不同的選擇。這樣,就單個角色來說似乎都不見作者的烙印,但他們又都歸屬於兩個世界:莎士比亞的角色世界和莫里哀的角色世界,各不相淆。作者的烙印終於看出來了,而且是那樣的明確。科格蘭認為演員也是如此,初看演出的時候觀眾見到的是角色而不是演員,但如果觀眾在以後看到別的演員演同—個角色,就會猛然看到區別,領悟到第一個演員加給角色的烙印。把某一位演員創造過的角色加以全面考察,演員的自身特點就更顯然了。用科格蘭的話來說便是:“他可以在他的角色身上蓋上自己的烙印,但這個烙印必須同具體人物化為一體,使觀眾只有在深思和對照之後才能感覺到它的存在。”科格蘭很好地說明了演出風格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的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自我對於第二自我的監督,儘管自始至終未曾放鬆,但卻一直隱匿得很好,勾魂攝魄於無影無蹤之間。
為什麼演員必須清醒地控制住表演呢?為什麼第一自我的監督作用永遠不能喪失呢?科格蘭的理由主要有兩條:一是為了美,二是為了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