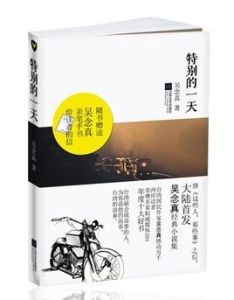內容簡介
《
書中包含吳念真早期創作的七部短篇小說。其中《白雞記》《是的,阿姆雷特先生!》連續入選台灣聯合報第三屆和第四屆小說獎佳作獎;《白鶴展翅》獲台灣吳濁流文學獎小說創作正獎。大部分以描寫台灣北部礦區的鄉間生活為主,故事裡飽含對村莊的濃濃鄉愁和人情味道。故事中對溪尾、瑞芳等台灣地方的描摹寫出了一個個大陸讀者所陌生的台灣面孔,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在鄉村勞作的底層人們,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外部世界飛速發展及城市化對礦區和農人們原本生活的衝擊在這些小故事中也都有反映,既有溫情,卻也悲涼。
吳念真的小說作品充滿悲憫的情懷,故事真實的呈現底層人們生活的艱辛和個體在社會生活的洪流中的無助與茫然。文字樸實內斂,講述充滿耐心和同情心,但情感上又是不失理智和節制的,展示命運的殘酷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讀者可從書中了解到台灣北部九份、溪尾、瑞芳等地的地方風貌人情,作品涉及鄉間生活層面較多。
作者簡介
吳念真,原名吳文欽。1952年出生於台北縣。1973年開始從事小說創作,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小說獎。1981年起,陸續寫了《戀戀風塵》《老莫的第二個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電影劇本,曾獲五次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兩次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
編輯推薦
《特別的一天》里的故事真實的呈現底層人們生活的艱辛和個體在社會生活的洪流中的無助與茫然。文字樸實內斂,講述充滿耐心和同情心,但情感上又是不失理智和節制的,展示命運的殘酷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適合小說愛好者閱讀。
後記
這是年少時候所寫的一些文字。
時間大約是1980年代初期,我二十幾到三十歲之間。
如果用此刻已然蒼老的心境回頭去看,還真不得不承認那是一段充滿力氣和希望的日子。
當時的台灣似乎正內醞著一股強大的能量,隨時準備迸發,一如當年一個朋友曾經寫過的一幅字:
不耐長年兮焦望,劍鞘嘎嘎兮清響,勇士拔刀兮昂首,腳踏寒霜。
無論在政治、文學、舞蹈、戲劇和音樂、電影上頭都有一群年輕人在衝撞限制,尋求改變,並且那么單純地相信著:總有一天we shall overcome!
那時候我白天打工謀生,晚上在大學夜間部會計繫上課,假日則騎著一部破機車到處闖蕩或找人攪和,看到什麼,想到什麼就急著透過文字和別人分享或訴說,因為自己同樣那么單純且稚嫩地相信:社會底層的壓抑、苦難和憂傷都可以透過許多人的文字揭露而得到撫慰或解放。
當然後來也許發現文字“功能”的局限,因而舍文字而就影像,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電影劇本上面,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當時的稚嫩、短淺也就留在當時的文字上,成了無法掩飾的證據。
這是我在進入電影行業之前的最後一本小說集,之後卻也就不曾再以小說的形式寫過任何東西。當時從不知道“時間”其實才是最後的勝利者。他一邊無情地催人老去,一邊卻又以無比強大的力量改變了所有限制和“不可能”。
當在寫這些小說的時候,我無法想像台灣之後的改變,更無法想像有一天兩岸竟然可以如此緊密地聯繫,可以透過各種媒介甚至近距離的生活觀察和體驗去了解彼此,了解彼此的現在甚至早已被歲月吞噬的過去。
因此,如果透過這些文字你能看到的是一個在台灣活過一甲子的人,他曾經經過的青春以及當時這個島嶼上的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我就已心滿意足。
而這一切的緣份都要感謝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美意和……勇氣。
吳念真
2012.春天
目錄
自序/吳念真
也是廣告也是序——一個不要當傑出青年的人/小野
壹 白雞記
貳 巡夜
叄 是的,哈姆雷特先生
肆 病房
伍 白鶴展翅
陸 特別的一天
柒 悲劇腳本
跋/吳念真
序言
吳念真
重寫一篇序,卻有寫墓志銘的感覺。埋葬的是自己的小說,或者,寫小說的自己。
最後一篇小說,就是收在這個集子裡的《悲劇腳本》,是十六年前寫的。記得那年瑞芳楓仔瀨的礦場發生災變,聯副的瘂弦先生要我寫一篇“小說”。
楓仔瀨災變現場的記憶猶新:搶救人員忙著接電加裝抽水馬達,現場燈火通明,老爸也跟去那兒幫忙,很沒有效率,可能也沒人理會地大呼小叫。礦務局一個官員跟記者說可能沒有什麼生還的人了,“因為……”他說,“他們名字的筆畫都不太好。”
而就在大約五十尺外,阻絕“閒雜人等”的紅色塑膠繩旁,一個歐巴桑卻絕望而認命地在為礦坑裡的兒子燒腳尾錢。兒子的兒子跪在一邊,從制服的學號看得出是四年級,十歲吧,表情是一臉疑惑、好奇以及因為圍觀的人多而不得不撐出來的嚴肅、正經;當時正是薄暮,微雨,燃燒的冥紙隨風翻飛,火光時明時暗,是一個悲劇場面的絕佳氛圍。我本能地從包包里抓出相機,焦點放在歐巴桑的眼睛和下巴之間,等待她把冥紙放入火中,不得不移近身子時,臉部下沿便有足夠的光讓我按下快門。
等待中,歐巴桑不經意地看了我一眼。
只是不經意的一瞥吧,對我來說,卻成了永恆的逼視。
那眼神極其複雜,像是禮貌的致意,像詢問、質疑,像埋怨,像咒罵、輕視、敵意……甚至哀求,或者,同情——同情這個正以“興奮”的心情企圖抓住自認為傑出的一剎那的無知的旁觀者。而,這個旁觀者卻正是出身自這個悲劇場景的自家子弟。
後來,我把相機收了起來,此後,直到現在,除了孩子,除了家庭生活之外,我不曾把鏡頭瞄向其他人。
幾天后,我寫了《悲劇腳本》這篇小說,因為解除了“虛構”之外,我根本無法掌握真正的情緒和文字進入真實的人間。
小說登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在中影上班了,從此與影像為伍,從此任何文字的終極目標都是為影像服務。
十六年後的現在,父親過世了,楓仔瀨的礦場早就不見了,相機的長短鏡頭都早巳發霉了,機身雖然完整,但連卷片器都生鏽失靈了……
而那個歐巴桑還在嗎?我常想起她的眼神。她大概永遠都不會知道,當年那么不經意的一瞥,卻讓一個人從此和他人生的一個階段永遠地告別。
《特別的一天》當初遠流要出版時拖延了許久,拖延的是我自己,理由正是那種已然決定告別,何必留下痕跡的心情。後來,是當時小說館的主編陳雨航把所有稿子收齊、打字、校對、編輯完畢拿到我家,我唯一要做的是寫一篇序,沒想到,我還是照延不誤,結果,是好友小野為我寫的。許多人都說他的序比我的小說好玩,我當然也這么覺得。
這回,遠流再度重出《特別的一天》,理由是什麼我不知道,不過,我猜,大概是他們知道這個人要再寫小說已經很難了吧?乾脆就用這本書做這個作者的告別紀念。如果是,我這個序就真的是墓志銘了——是留給自己的小說和曾經寫小說的自己。
銘曰:躺在這本書里的文字和作者一樣,面對可能的禮貌的致意,或詢問,或質疑,或埋怨、咒罵、輕視、敵意……或者同情,都只能無言以對——因為兩者都已經死了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