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城假日》又名《首爾的假日》(Holiday in Se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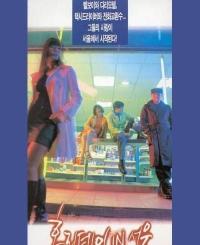
主演:張東健、金民鍾、 陳熙京、崔真實,
類型:劇情,韓國上映日期:
1997年3月22日。劇情簡介
本片由兩個聯繫並不是太緊密的故事組成。第一個故事裡面男侍者愛上了女房客,她是一位和男友來酒店度假的長腿模特,可是不想男友卻在一場交通意外中突然死去。第二個故事時關於一個愛上了接線員的計程車司機的故事,那位接線員則愛著一位一位男人。主人公們既是在有人陪伴的時候也不能抑制內心的空虛和孤獨,他們奮力抓住沒一絲的情愛來溫暖自己,因為知道愛情這東西絕對不會長久。
第一個故事:一個被女友拋棄的酒店服務生A,特別痴迷有一雙美腿的女人。一天,在酒店裡看到了能讓他心儀的女人--一個做腿部模特的女人,可是,女人每次來酒店都是與男友一起,這讓服務生很尷尬。A在女人每次來酒店時,都會以服務的名義找機會接觸女人。後來在報上得知,女人的男友被車撞死,很想找機會去安慰女人,可是女人卻有很長時間沒有出現。終於有一天,A又看到了來酒店的女人,於是,在女人走出酒店時跟了上去,在咖啡館裡,女人向A訴說了自己男友的故事,告訴A男友是一個匪徒,並說“我不在乎他的過去,可他為什麼要隱瞞我呢?”。A說,在報上得知這一訊息後,很象安慰她。於是,女人請A幫忙,將男友的骨灰撒掉。兩人來到酒吧,A很想為女人作些“送花”以外的事情,卻不知所措,只好將一瓶瓶的酒灌進自己不勝酒力的身體。夜晚,當A擁抱女人溫暖的身體時才醒悟,本想去撫慰女人的寂寞與痛苦,其實得到愛撫與慰藉的卻是自己。當A發現,女人又一次住進酒店時,決定為女人準備豐富的早餐送去,可是,當他在不得敲門而入後,明白事情不妙,於是用酒店的鑰匙破門而入,發現,女人已經割脈倒在血泊中,慶幸的是,女人沒有死去,但是,A沒有再見到女人。過了許久,A收到女人從一個島嶼上寄來的信與照片,女人告訴A,自己想忘卻這裡的冷漠與淒涼,唯一不想忘卻的是A的撫慰與照片。
第二個故事:同在這一酒店裡的女接線員金小姐,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壞女孩。父親於金還沒有出生前在越南戰場上喪命,母親因為“自身也有很多問題”無暇顧忌金,於是,金從小就在電話里與父親通話,覺得另一個世界的父親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與自己交流的人,這種遊戲一直持續著,成了金唯一可以傾訴的方式。金在下夜班乘計程車時,遇到了出租司機B(東健飾演),因為無錢付車費,在金的家裡以出賣身體做了補償。第二天清晨,金扔下還在熟睡的B走出家門。此時的金正在與一個已婚的電話商人交往著,是金亂打電話認識的,因為覺得商人的聲音象想像中的父親,所以與之見面,交往,上床。金在一個書店裡打電話給商人,希望與之見面,可商人找藉口掛斷了電話。金不甘,夜裡等在商人的店外,但是,商人告訴金,金破壞了遊戲規則,自己不能與她在一起,將金推下車後駛去。金跑到商人住處,打電話給商人,並砸了商人的車後逃掉。百無聊賴的金在回家的途中又將一男子帶回家中,可沒想到的是,出租司機B仍睡在金的床上,嚇的男子奪路而逃。金見狀放聲大笑,繼而,轉為無奈淒涼的哭泣。床上的B仍酣然沉睡,毫無覺察。清晨,已經連續睡了57個小時的B終於醒來,環顧著金的破敗小屋,發現有不少的書籍,桌上擺放著身著戎裝的金的父親的很多照片,B將被子蓋在睡在地上的金身上,離去。
又一夜,金再一次做上了B的計程車,金將B帶到一個橋上,金問B為何如此長的時間嗜睡不醒,B告訴金,自己有嚴重的失眠症。金將一個軍人的肩牌送給了B,B問金為何來這裡,金說自殺,B淺笑,問為何,金說太悶,B收起笑容,微微點頭,拿出煙用身體遮住風點燃,此時橋下已經傳來了金落水的聲音,B感嘆一聲“為何是我”,隨後跳入水中。B將救起的金送回家,分別時,金問B為何救自己,B說,可以掙到車費,金下車,將車費遞給B,告訴B,以後不要多管閒事。假日裡,B騎腳踏車載金兜風,金要B與自己一起來到商人的店裡,當著商人的面,故意與B親熱,想刺激和激怒商人。後B載著金賓士在公路與曠野上,最後來到海邊,B又沉睡過去,而且覺得這是自己睡得最香甜的一覺。商人與金聯繫,說可以與金見面,但是,金不可以破壞自己的家庭,並約好第二天在金家附近的小店裡見面。B等在小店得外面,透過玻璃窗看著店內的兩人交談,兩人交談不歡,商人走出小店,金跟在後面,直到商人的車前,金在阻止商人離去,商人對金動粗,將其打倒在地後,開車離去。B在車中目睹一切,看到金自己站起走回家去後,開車追上商人。。。。B來到金的家中,對金說,自己明白金的感受,因為上次金對自己說過不要多管閒事,所以自己只能袖手旁觀。金破涕為笑,B約金出去小吃,兩人在一小店裡喝酒,此時,被痛打過的商人走進來,跪在金的面前,對金說抱歉,自己是因為喜歡電話里金的聲音才與她交往的,並請求金的原諒,希望金不要破壞自己的家庭。金看著眼前的商人,明白了一切,她趕走了商人,呆站在那裡。一旁的B走過來,用手輕拍金的肩膀,想安慰金,不料,金一個耳光打過去,歇斯底里的對B哭喊道:笨蛋!要你多管閒事!白痴!快回家睡覺!你如何讓我落得這副可憐相。你也許以為自己是個英雄,才不是,跟他相比,你一無是處,你根本不知何為寂寞,你只懂得開機車,以為那很有型,你視寂寞為遊戲,我視寂寞為煉獄,你知道嗎?就算在孤兒院你也不會哭,但我會哭,會打架,會講粗口,會求存。。。。B愕然。是呀,B覺得她說的對:自己也許不知道何謂寂寞,有時候自己也渴望能哭、做要求和罵人,回想起來,自己愛生命中的每一個女人,但沒人能明白自己,包括自己在內。B在想,現在有別人對她們說“我愛你”嗎?並決定放棄這樣愛一個人!此後,B再沒見到金。
一年後,B在行車時, 看到了身穿制服的金,隨後追到捷運里,無果。在看著列車駛出站台的茫然中,忽然發現了對面剛剛放下電話的金,倆人隔著站台的距離遙望,相視而笑。。。
酒店裡,模特女人來到前台,看到已經升職的A。對正在望著自己照片的A說,你升職了,A點頭,將登記表遞給女人,說:909房,你一個人嗎?女人接過鑰匙一邊走一邊回答,當然。
這個故事是這樣串聯起來的:A與B,在某一個公共電話亭偶遇過,B還用車載過A,兩人都覺彼此見過面,但又都遺忘在忙碌喧囂的城市節奏里,沒有更深的印象。由A引出金,因為同在一家酒店,因金在酒店裡的緋聞故事,使A注意到金,而A也有自己的故事發生(如上)。由金引出B,因為要乘計程車,有聯繫很自然,所以就有了B與金的故事,而金同時也有自己的生活內容(與商人),由此將B引如其中,彼此糾纏交相發展。
這種拼盤式的結構看似混亂,其實,脈絡清晰,只是,它以跳躍式的思維展現著現代都市裡的人際關係,不確定,惶恐,迷惘,短促,冷漠,孤獨。與現代都市的生活節奏很相符。
劇中的幾個人,都在努力的尋求著寂寞中的溫暖,試圖在冷漠的城市牆體下,能夠觸摸到心靈的相互慰藉,她們各有處境,不相同也不相連,各有各的表現形式,可身體的寂寞與心靈的寂寞是相似的。
A在失去女友後,每一個星期五都變成了黑色,一個人獨吞快餐面,與魚缸里的魚說話就成了家中的全部日子。在他遇到心儀的女人後,生活有了目的,期盼與希望是生存下去的血液,這讓日子有了顏色。儘管那女人是別人的女友,那又何妨,有遺憾的希望總比圓滿的絕望令人鮮活。但是,當A真正可以面對自己的喜愛時,自己的表現確實那樣的侷促與無措,一心想給予別人愛撫的A,當愛真的來臨,卻發現自己的能力如此的軟弱,而相給予的對方卻給了自己無限的安慰。人總是在深愛的對象身上找到自己。
女模特說母親懷著自己時做過一個夢,夢見曠野里有一枝盛開的向日葵。女人覺得那枝向日葵太孤單太寂寥了,就象生活在城市裡的自己,雖然有著一份很不錯的職業,可以買名牌的衣服給自己,可以買古龍香水給男友,可是內心孤獨與寂寞是不能用這些來填補的。於是,與並不十分了解的男友交歡就是她唯一滿足自己的方式。當男友死去後,她知道了男友對自己的隱瞞,在內心裡,支撐著自己阻擋寂寞的那扇牆就開始了坍塌。當身體與心靈都承受不住這寂寞的凜冽之侵後,只有以死亡的永恆來阻止心底希望的斷裂。但是,她沒有成功,那么,毀滅之後的重生,是不是象她所描述的那樣“這裡的向日葵是那樣的嬌艷美麗”?!
金是一個陷入寂寞沼蟄之地的獵豹,她不甘心被寂寞毀滅,所以以她的方式抗爭和掙扎。她可以粗口,撒野,謾罵,可以順手偷同事的錢,她不在乎與男人上床,因為這一切只不過是她排解寂寞的一種方式。她更不在乎被人如何評價,只要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哪怕是吵架,是動粗,是挨打,是自殺,她都可以去做。就是不願讓生活死一般的沉寂,被人遺忘的一個人在孤獨寂寞的中獨行對金來說比死亡更可怕。所以,她採取一切手段去刺激商人對自己的在意,並承受商人對自己的任何無禮。商人對金來說也不是愛,而是能夠排解寂寞的稻草,那是讓自己的痛流淌的一個缺口。當B不知情的將金與商人之間的關係做一個了結後,金覺得,B是將自己又推進了寂寞的洪濤,B無意中給她築起了派遣寂寞的堤壩,將自己困在其中,所以她狂暴,她歇斯底里。對於金的轉變,我存有一絲疑慮,當她一年後身著制服出現時(我不知道是什麼職務),我在想能讓她轉變的動因,如果是B的善意舉措促動了她,那么就是她在將自己徹底掏空後採取了另一種生活填沖方式,這種端倪是不是在影片幾次交代的金“讀書”的畫面里潛伏呢,我看不懂那些書,不知是什麼內容,大概這些鏡頭為金最後的轉身已經種下了種子吧。
B是個出租司機,善良而有些愚鈍,一直的理想就是出遊四方,一直困擾的事情就是接下來去哪裡,出行給他的精神和身體都帶來充實,遊走一天的他會倒下就睡,不會被失眠困擾。可當上出租司機後,接下來去哪裡的問題解決了,失眠卻無法迴避。他簡單的生活著,愛著生命里的每一個女人,可女人並不明白他,他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他不抱怨不泄憤,只是承受著生活種賦予自己的東西,善意的對待身邊的人和事。當他以自已的理解去解救受苦的金時,金的一番痛訴讓他明白每個人對世界與生活的理解與要求是如此的差異,沒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另一個人,在一個人眼裡的善事在另一個人看來卻是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