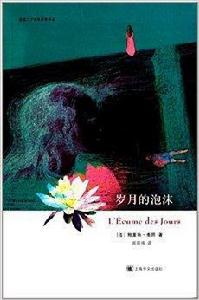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歲月的泡沫》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鮑里斯·維昂(Boris Vian) 譯者:周國強
鮑里斯·維昂(1920—1959)是二十世紀法國文壇的奇才,他不僅身兼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翻譯家、記者、歌詞作者、爵士樂小號手、電影編劇、演員、工程師等等,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兼蓄當代各流派的特色,匯大成於一身。
圖書目錄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輪廓(總序)
現實與超現實之間(譯本序)
歲月的泡沫
螞蟻
作者簡介
後記
《螞蟻》是一篇獨特的小說,1946年在薩特主編的《現代》雜誌發表,1949年收入同名短篇小說集在法國出版。
小說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諾曼第登入時的激戰片段和登入後的生活片段。諾曼第登入是盟軍反擊法西斯德國的一次關鍵性戰役,維昂當年積極支持那場正義的自衛戰爭。但勝利之後,痛定思痛,像絕大多數飽受兩次大戰浩劫的愛國人士,他也參與為保衛世界和平的反戰運動。
作者試圖以戰役的一個片段描繪戰爭的殘酷性和荒誕性。處在槍林彈雨中的主人公身不由己,盲目地聽從指揮,機械地執行命令,無奈地任憑命運偶然性的擺布。激戰中,人作為物件,緊緊與槍炮捆綁在一起,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炮灰。主人公抱著一線求生的希望,施以小計保全性命,但在隨處都可遇到荒誕死亡的現實面前,顯得多么滑稽可笑。
作者採用了一種冷漠得沒有任何情感的敘述語言,主人公看似詼諧不經,懵懂中帶著黑色幽默,而回味時又覺黯淡悽慘和憤憤不平,描寫死亡的筆觸冷靜得近乎殘忍,但辛辣地揭示和諷刺了戰爭的荒謬本質,虛偽聲色和殘酷結局。
這篇風格怪異的超短篇小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前期,被譽為帶有薩特式存在主義思潮濃厚色彩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接近新小說派風格,其實也可視為後來在美國興起的黑色幽默文學流派的一篇原創作品。
沈志明
序言
現實與超現實之間
柳鳴九
在法國20世紀文學中,這本小說被認為是一本奇書。
奇在何處?
既然人們無不認定它是一本小說,而小說的顯著標誌,一般地說來,就是一定的故事性,那么我們不妨將與故事性有關的小說成分,分為故事框架、故事情節與故事行文這樣三個層次來加以審視。
小說的故事框架,也就是小說的主要故事內容,小說中的主要事件。這是人們一般地談論一部小說時最常涉及的範疇,這個範疇只包括時代環境總背景、事件的概略、人物的主要作為與經歷以及人物關係的格局,而不包括細節與場景。在這部小說里,故事框架就是戰後年代裡兩對青年情侶都死於貧困的悲劇,前一對情侶因女方患病而陷入窮困,後一對本來就過著清貧的生活,後又因男方盲目地購置書籍而淪於破產。在這樣一個框架中,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奇;這幾乎就是一個在社會現實中屢見不鮮的故事,甚至就是一個充滿了現實性的通俗化的故事,只不過,克洛埃的病是胸中長了一朵“睡蓮”、阿麗絲最後因情人破產而殺人放火,顯得有點不尋常,不像是現實生活中常能見到的。
小說的故事情節也就是小說中事件的主要進程、發展與變化,是組合為全景的“分鏡頭”,是構成整體的部件。在這部小說里,大部分故事情節都是符合生活常態的,甚至有些是平淡無奇的,毫無怪異,如高蘭請希克吃飯、高蘭與克洛埃戀愛、結婚與旅行、幾對青年情侶之間的交往、克洛埃的生病、高蘭的貧窮化與不得不到處謀職等章節,這些章節所展現出來的完全是現代社會的日常圖景。小說中與這些符合自然常態的情節同時並存的,也有一部分不符合生活常態的滑稽誇張情節,這類情節中,大的有:阿麗絲因為希克愛購書而破產就去殺作家、殺書商、燒書店,希克因為區區稅款就死於槍口之下,高蘭與克洛埃婚禮上不近情理的場面等等。至於小說情節中滑稽誇張的“小動作”,則更多,如高蘭吸一口氣,他的背帶就啪啦作響;他陷入戀愛後,他的頭就熱燙得像火爐;滑冰者高速滑行所產生的氣流把旁邊的人掀起好幾米高;人物的袖裡破了,就用釘子釘上;兵工廠二十九歲的職員完全像一個老頭子,等等。這些情節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因素,但明顯誇張,使小說具有一種卡通片式的滑稽不經的風格。除此以外,小說中還有一部分情節,則又超出了滑稽誇張的界線而成為明顯的荒誕,如有人把鐵絲鳥籠套在脖子上當圍巾;阿麗絲拍拍希克的背,竟發出敲銅鑼的聲音;在克洛埃的葬禮上,高蘭與耶穌雕像進行對話;大門在身後關上發出的是拍屁股與親吻的聲音;一朵花在作者描寫中是一種顏色,而到人物眼裡卻變成了另一種顏色;著名作家保特(影射薩特)做演講是坐著裝甲車來的,車上每個角都有手持斧鉞的神射手;狂想的聽眾有人乘柩車而來,有人則是坐飛機讓人空投下來的;報告會的假票竟有幾萬張之多,等等。這些情節中的矛盾與悖謬,使人很容易想起荒誕派戲劇中的場景。這樣,我們就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事件行動、故事進程這一個層面,清楚地看到了非生活常態、非日常生活真實的成分,也就感到了這部作品的奇特性。
這部小說的奇特性主要還是表現在故事行文這個層面上。何謂故事行文?我指的是服務於表現小說整個故事這一總目的的那些文字語言,它們或為描繪性的,或為敘述性的,或為對白性的。如果一部作品的組成往往是以章節為單位的話,那么故事行文的單位往往就是一兩個文句,甚至只是片言隻語,它們的內涵不足以構成一個情節,而往往只構成某個具體事物的表征,或某個具體人物的動作,或某種情景、某種境況的態勢。在這部小說里,氣象萬千的奇觀,正是出現在這一個層面上。
小說行文上引人注意的奇觀,最明顯的一部分是直接體現於文字語言上的文字遊戲、雙關語。在這裡,教堂的執事成了“執食”;薩特的《存在與虛無》(L'etre et Neant)因諧音而被影射為《字母與霓虹》(Lettre et Ndon);人物想躲到一個角落裡去,因“角落”一詞與“木瓜”一詞同音(Coin-Coing)而成為了“想躲到木瓜里去”;描寫一個人態度的穩重,因“穩重”一詞(Aplomb)來自“鉛”(Plomb)而引出了“穩重被軟化”這樣的狀語,等等。這些雙關語、文字遊戲可說是法文中的“相聲”,在作品中明顯地起了兩種作用,一是對客觀對象的幽默諷刺,如“執食”就是對教會人物飽食終日的影射,二是增添作品的風趣詼諧。這兩者都顯示了作者鮑里斯·維昂那種輕鬆頑皮的創作個性,正如繆塞的詩歌名句“鐘樓上明月正圓,就像字母i上的一點”那樣顯示出他作為“浪漫主義頑皮孩子”的特點一樣。
……
在文學史上,有的作品企圖證明文學是載道說教,有的作品企圖證明文學是再現生活,有的作品企圖證明文學是唯藝術,而鮑里斯·維昂這部小說似乎是在證明文學就是一種精神遊戲。顯然,作者並不企圖在小說里進行我們中國批評界特別重視的那種“揭露與批判”,除了高蘭的婚禮與克洛埃的葬禮以及工廠勞動的某些情景外,作品裡就幾乎別無現實諷嘲的內容了。作者在具體描述與行文中那些奇觀與妙喻,不論是四季並存的景物還是雞尾酒鋼琴,等等,都是分散的,各不相干的,作者無意將它們聯成一片構成一個完整的意象,以說明某種東西,以顯示某種寓意,作者似乎僅僅滿足於展示自己一個個連通的奇思妙想,僅僅滿足於超然地、無任何功利目的地在進行連通器的精神遊戲,不論是政治功利目的、道德宗教功利目的,或者是藝術功利目的。
超現實主義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文學思潮流派,然而,它在文學中卻沒有留下真正屬於自己的傳世傑作。人們經常為此感到惋惜。這是這個思潮流派的“悲劇”。對此悲劇的原因做出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務,在這裡,我只想指出,如果以上的解析還不是牽強附會的,那么是否可以說鮑里斯·維昂這部小說可算是超現實主義在法國20世紀文學中滋潤的一朵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