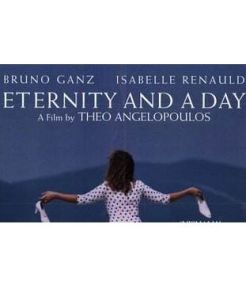影片地位
《永恆與一日》是赫赫有名的希臘導演西奧·安傑羅普洛斯執導的第11部影片,也是一部蘊含著深刻政治和文化主題的史詩般的巨片。在1998年的坎城電影節上,評審們一致認為該片是“本年度唯一一部出類拔萃的影片”,因而將大獎“金棕櫚獎”授於它。
 《永恆與一日》
《永恆與一日》內容梗概
在看了戈達爾《筋疲力盡》之後,安哲羅普洛斯決定,自己必須到法國去學電影。可是當他去了高等電影學院(IDHEC)後,卻因為自己執意要做小型電影實驗,不滿老師教授的基本知識而面臨被開除的境況,所幸法國著名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賞識他,讓他住在自己家中。有趣的是,時至今日,這幫同學中仍在堅持拍電影的只有他一人。
在安哲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反覆講述著個人如何受困於歷史的變動。政治和歷史的動亂早就伴隨著他的童年記憶,他甚至曾和母親在墳場尋找作為政治犯的父親的屍體,以及經歷他的突然回家。這些後來都進入了他的電影。在獨裁專制的世界中,他對世界未來的變化充滿希冀,然而獨裁崩潰後多方思考,卻發現,世界並沒有發生變化。這就是安哲對待世界的一種姿態,它本質上是一種憂鬱。主演《塞瑟島之旅》(與名畫《發舟西苔島》同名電影)的馬斯楚安尼說:“現在我們越過邊界了——但是要越過多少道邊界,才能回到家?”於是安哲說:“對我而言,要找到一個地方,讓我能跟自己、跟環境和諧相處,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間房屋,不是一個國度。——然而這樣的地方,並不存在。最後的答案是:當我回來,就是再度出發的時候。”
此後的安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開始關注邊界,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地理界線,還有人和人之間的隔膜,人的失去家園的漂泊感。
影評選摘
《永恆與一日》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安哲的主人公這次和他一樣是詩人,他來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續寫詩篇,告別親人,喚醒回憶,尋找語詞,為的是想要抓住有限的這一刻,去碰觸永恆,達到超脫。和阿爾巴尼亞男孩經歷偶然的、短暫的一段旅程後,雖然注定在某一刻要分離,告別。可是經過這一天的尋找,他已在精神上和曾經熱切擁抱某一天的妻子相遇,和通過有限詞語達到無限的詩人相遇。越過看似是終點的邊界之後,新的一切又在人的眼前鋪開,湧現。
看安氏的電影就像隨他進行著一場場生命之旅,風景似曾相識,卻總有新的收穫。那標誌性的環繞長鏡頭就像他所說:“長鏡頭的好處就在於你每次觀賞它,都能從裡面提煉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人們評價他對鏡頭的掌控已臻化境,凝練得讓你只能屏息凝視,絕無任何閒筆。它們似乎已經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內在節奏,緩慢的凝視飽蘸著悲天憫人的情緒。想像和現實的界限在這裡完全被打破,心靈中一切的象你在這裡都可以遇到,精神世界藉此得以外化。
最後,讓我們用《永恆與一日》上幾段經典的台詞作結:
為什麼?為何世事總是不如意?為什麼?為何我們必須腐朽,徘徊在痛苦與欲望之間?為何我一生都在漂泊?為何當我難得有機會,有幸使用我的母語時,我才有家的感覺?當我仍能從寂靜中,尋回失落或遺忘的話語,我的腳步才會再次回歸家中?為什麼?媽,為什麼……我們不懂得如何去愛?
我在海邊寫信給你,一次又一次。我寫信給你,對你說話,當……當你偶爾想起這一天,請記住,我全神凝望著它,我熱切接觸著它,給我這一天!
你活在我身邊,心卻不在,有一天你會離去,風帶走你的眼光,但是……請給我這一天,就當我倆沒有明天。給我這一天。
黎明最後一顆清亮晨星,預告驕陽的來臨,迷霧陰影皆不敢損及,那萬里無雲的蒼穹,一陣微風愉悅吹來,輕撫天空下的臉龐,仿佛向心靈深處呢喃。生命甜美……生命甜美。
明天,明天是什麼?我問過你:明天會持續多久?你說……
比永遠多一天。 (另譯:永遠,或一天)
導演背景
 永恆與一日
永恆與一日安哲羅普洛斯在這部電影中再次顯示了他的詩歌才華,如果說有人用詩的概念拍攝電影,那是安氏無疑,就像《尤利西斯之旅》是向瑪納吉斯兄弟致敬一樣,這是一部向希臘詩人索洛莫斯致敬的電影,所以在電影中使用諸多詩歌元素,不僅僅是語言方面的,而是從根本上具備了詩的特質,行雲流水的節奏,舒緩如牧歌一般,移步換景而非簡單的蒙太奇,達到了一唱三嘆的效果,推開一道門,門外是三十年前美麗的妻子,沿著一條河,岸邊站著回到希臘的索洛莫斯,只有詩人才是這樣的,跳躍到你的意外並剛好能達到的遠處,另外,電影中使用的意象也表明,巴爾幹山歌海謠已經深入安氏的骨髓,公車上的乘客,跟隨公車的消防隊員,焚燒衣服的烈焰,以及邊境上的鐵絲網,都成了信手拈來的意向,配上如泣如訴的音樂,使人身心迷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