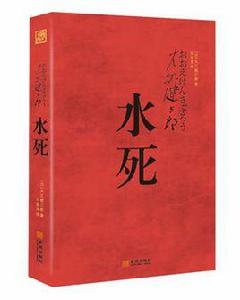內容簡介
《水死》的故事始於二戰日本即將戰敗之際。“我”是已經步入老年的作家,曾獲得國際文學大獎。當“我”還是少年時,“父親”回響青年軍官們的建議奪取神風敢死隊的飛機並掛上炸彈,飛往“帝都”東京轟炸皇宮,炸死天皇以挽回戰敗投降的悲慘結局。
《水死》的核心人物之一“我”父親——長江古義人尊稱“長江先生”,在戰爭進入最後的慘烈階段時,“長江先生”以酒肉招待手持高知縣一位先生的介紹信函來到村裡的年輕軍官,席間聽他們說起“必須改變維新以來的歷史進程”,以避開即將到來的戰敗結局。於是,“我”父親帶領家人大黃越過四國山脈拜訪高知的先生,受其教誨之後得到大部頭《金枝》全集中的三卷。尤其在第三卷“殺死神王”的相關處,將書借給“我”父親的那位先生特意在應予重點閱讀處——畫上記號,其中一頁的內容是這樣的:不管有多少關心和提防,總不能防止人神變老、衰弱並最後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預見到這個悲慘的不可避免的事,並儘可能地應付得好一些。這是非常可怕的危險,防止危險的辦法只有一個。
人神的能力一露出衰退的跡象,就必須馬上將他殺死,必須在將要來的衰退產生嚴重損害之前,把它的靈魂轉給一個精力充沛的繼承者。使人神致死,而不讓他死於老病,這樣做的優點對原始人來說是相當明顯的,而將他殺掉,他的崇拜者就能,第一,在他的靈魂逃走時肯定會抓到並將它轉給適當的繼承者;第二,在他自然精力衰減之前將他處死,他們就能保證世界不會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所以,殺掉人神並在其靈魂的壯年期將它轉交給一個精力充沛的繼承者,這樣做,每個目的都達到了,一切災難都消除了。
更直率地說,是要“將貫穿三卷本的‘殺死人神’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國家的神話構想,現實性地與這個國家的天皇制直接聯繫在一起”。於是,“在最後那次會議上大家情緒激昂,認為戰爭好像將比此前一直議論的時間更早地以失敗而告終,因而必須立即實施長江先生的一貫主張——用特攻隊的飛機轟炸帝都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這裡所說帝國之都的中心正是皇宮。不言而喻,轟炸皇宮的目的當然是殺死天皇,以此來防止國運的衰微。
當一位與會軍官提出為了藏匿秘密弄來的載有炸彈的飛機,需要在森林中因隕石撞擊而產生的開闊地修建臨時機場並炸掉那塊巨大的隕石時,“長江先生”卻激烈地大聲反對,認為外人不可以踏入森林中那塊名為“鞘”的開闊地,因為那裡“自很古的時代以來就是非常重要的場所,根本不是為修建臨時機場而大興土木的地方”,因而不容“你們這些外人的腳踏入‘鞘’”半步。
森林這個邊緣場域的神話和傳說顯然遠遠超過國家主義思想以及殺王/殺天皇的計畫對“長江先生”帶來的影響,“我”父親無法容忍因修建臨時機場而破壞那座擁有暴動歷史之記憶的森林,同樣無法容忍青年軍官們踏入森林中那片神話和傳說的空間,哪怕這樣做是為了殺死天皇這個人神“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國家”。“我”父親的下場是悲慘的,為了在保住那座森林的同時設法殺死天皇,他只能先行殉死以明志,從而激勵青年軍官們起飛特攻隊的飛機轟炸帝都中心。翌日晚間,他獨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順流而下,帶著那三卷《金枝》和永遠都不可能實現了的殺王想像,溺死在不遠處的下游。
那隻“紅色皮箱”後來被警察送了回來。多年來,“我”一直希望查閱那隻皮箱中的資料,以便將這段事實構思為“水死小說”,卻因得不到母親支持而無法查閱箱中資料,便依據想像創作了小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卻未能成功描繪事件的經緯。
作品目錄
| 《水死》 | |
| 第一部 | “水死小說” |
| 序 章 | 笑話 |
| 第一章 | “穴居人”到來 |
| 第二章 | 戲劇版《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彩排 |
| 第三章 | “紅皮箱” |
| 第四章 | 笑話被貫徹 |
| 第五章 | 大眩暈 |
| 第二部 | 女人們處於優勢 |
| 第六章 | “扔死狗”戲劇 |
| 第七章 | 餘波蕩漾 |
| 第八章 | 大黃 |
| 第九章 | “晚年的工作” |
| 第十章 | 更正記憶或夢境 |
| 第十一章 | 父親想要從《金枝》中讀出什麼? |
創作背景
大江健三郎曾因發表長篇隨筆《沖繩札記》揭露發生在沖繩的人間慘劇,而被日本右翼勢力告上法庭。做答辯的同時,大江健三郎思考,如果小說中的主人公站在被告席上會如何辯論,隨後以此為主要線索創作了《水死》長篇小說。
在沖繩縣立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的第四展廳,碑文上題有“鎮魂”二字,所有戰死的姬百合部隊成員的照片都懸掛在那裡,但沒有任何文字說明;然而在民間設立的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內,卻清晰闡明日軍在戰爭中不負責任與加害行為。圍繞戰時日軍是否對沖繩民眾有加害行為,展示或者說明嚴重對立,它延伸到學術界,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因為在其《沖繩札記》一書中揭示日軍對沖繩民眾的加害行為,被日本右翼告上法庭。法庭內外,雙方展開激烈對抗。
主要人物
“我”
“我”三十歲剛出頭,是一名小說家,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系,已經是老人了,曾獲得國際文學大獎。“我”早在學生時期就開始寫作。在主人公“我”十歲的時,他經常夢見自己在“水死小說”中的場景。當“我”二十歲時,他從某位英國詩人的詩作中認識了“水死”單詞,“小說家”——“我”雖然連短篇小說都不曾試寫,那部“水死小說”卻已在思維中形同確定。“我”的長子阿亮,患有先天頭蓋骨缺損症。
長江古義人
“我”父親——長江古義人尊稱“長江先生”。1945年的夏天,長江因洪水溺水而死亡。
長江古義人無法容忍因修建臨時機場而破壞那座擁有暴動歷史之記憶的森林,同樣無法容忍青年軍官們踏入森林中那片神話和傳說的空間,哪怕這樣做是為了殺死天皇這個人神“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國家”。“我”父親——“長江先生”的下場是悲慘的,為了在保住森林的同時設法殺死天皇,他只能先行殉死以明志,從而激勵青年軍官們起飛特攻隊的飛機轟炸“帝都中心”。他獨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順流而下,帶著那三卷《金枝》和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殺王想像,溺死在不遠處的下游。“長江先生”的這種思想和行事風格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大弟子大黃。當年,在青年軍官們的脅迫下,大黃曾目睹恩師為了自己的時代精神而殉死,其後,大黃為繼承遺志而組建國家主義團體,長年以來在當地的國家主義分子心目中擁有很大威信,且與具有國家主義思想的各色人等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水死》的主題思想即抵抗“天皇陛下萬歲”的“時代精神”
“絕對天皇制”也稱為“近代天皇制”,二戰後被“象徵天皇制”所取代。戰前和戰爭期間支撐著“絕對天皇制”的社會倫理並沒有因此而消滅,成為復活國家主義的肥沃土壤。
作者大江健三郎認為,引發日本社會種種危險徵兆的根源皆在於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呼籲人們奮起斬殺存留於諸多日本人精神底層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這個龐大無比、無處不在的“王”,迎接將給日本帶來和平的民主主義的“新王。”
《水死》反映出二戰前後不同時期潛隱在諸多日本人精神底層的負面精神遺產——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時代精神。同時,在絕望中看到希望——以“穴居人”為象徵的民主主義之時代精神。
“我”父親——長江古義人身上存在著兩種時代精神,第一種是日本以軍國主義教育為主體的“時代精神”,也就是“作為神的天皇/現人神的精神”;另一種則是日本戰後接受的民主主義教育,以新憲法為主體而構建的“和平主義精神”。
日本國家主義的幽靈仍然存在於包括古義人在內的諸多日本人的內心裡。換句話說,幾乎每個日本人內心裡都不同程度地存留著以“天皇陛下萬歲”為象徵的昭和精神,這種時代精神接連著戰爭、死亡和毀滅。
古義人對他自己來說最為重要的,便是表現具有積極價值的時代精神,即便為時代精神殉死也在所不惜。在日本民主主義教育精神的影響下,古義人到達“森林”中的故鄉,與來自城市的男女青年組成的“穴居人”劇團合作。
18年後,當髫發子為了“無論如何也必須進行抵抗,要圍繞這個國家人們的根本性的特性進行批判”而登台飾演森林裡的暴動女英雄時,她試圖將女英雄在森林裡的受難與自己在東京的受難聯繫起來,從而揭露140年以來日本的女人們一直在遭受著男人的強姦和國家的強姦這個慘痛事實。她想用140年前參加暴動的女人們吟唱的曲調,勇敢地唱出“男人強姦咱們,國家強姦咱們/咱們女人出來參加暴動呀/不要被騙呀、不要被騙呀!”
由於髫發子不願屈從於伯父的淫威去改變揭露其醜行的台詞,她再次遭徹夜強姦。髫發子的伯父,妄想摧毀她的身體和意志,以便讓她第二天登不了台。
如果說,18年前髫發子的伯父對親侄女的強姦只是出於獸慾,那么18年後的強姦就是獸慾復加政治迫害了,這一切確切無誤地印證了髫發子所要唱出的“男人強姦咱們,國家強姦咱們”的心聲。
《水死》是兩種“時代精神”較量的直接產物。面對“時代精神”——超國家主義的昭和精神和提倡和平的民主主義精神,長江古義人選擇了為後一種精神殉死。
敘事藝術
小說以作家長江古義人為敘事者“我”探明父親之死真相展開敘事。太平洋戰爭末期,古義人的父親與擔憂戰況不利於日本的青年將校們來往密切。一天晚上,“我”的父親決意採取暴力行動,獨自一人駕著小船離開村莊,結果在洪水中溺水身亡。古義人早在四十年前就曾構思將父親“水死事件”小說化,但因創作技法“不夠嫻熟”被迫擱淺。時隔近半個世紀之後,他“終於確信自己有能力復原父親之死真相”,於是以母親在“紅色皮箱”里保存的有關父親生前的資料為線索,完成了他“晚年工作”的集大成《水死》。該作品問世後,在日本文學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各大報刊和雜誌紛紛登出書評。日本著名評論家三浦雅士率先指出:《水死》是一部勢在必寫的“水死”物語。該部必寫的小說《水死》的核心部分,是已完成小說《親手拭去我眼淚的日子》。
《水死》從敘事策略上直指小說創作本身,旨在揭示日本昭和時期的“時代精神”,乃至20世紀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從詩的真實與隱喻、“戲劇化”的敘事結構和多元的敘事主體切入,透析大江文學在創作技法上的革新和主題上的突破,洞察大江文學“晚年工作”的射程。詩的真實與隱喻引用他人詩作,以隱喻的形式從詩學的高度不斷深化作品主題,真實地反映現實世界,已成為大江文學的一大特質,但在小說卷首同時引用英、日文並置的詩之樣式尚屬首次。《水死》中引用詩歌樣式與以往作品的不同之處,也是該小說敘事技法上的一大革新。
《水死》中,作者在不同情境下以英、日文的形式並置,反覆引用艾略特的詩歌《荒原》中的一節“死在水中”:“海底的潮流/悄悄低語/撿拾他的骨頭/在他飄上沉下之際/他度過了老年和青春歲月/進入了漩渦/”。
作者通過在不同情境下引用同一節詩的不同譯文,豐富了小說語言的多義性。比如,小說中引用艾略特的“死在水中”的一節詩時,對其中的一句詩同時引用了兩種譯文。深瀬基寛譯:度過了老年和青年時期的不同階段。西脇順三郎譯:年老的日子、年輕時的日子,一個接一個地浮現在他的記憶中。從譯文中可以看出,古義人在意的主要是譯為“老年”,西脇將它譯為“年老的日子”,而根據艾略特原詩的直譯則是“他度過了有生之年的各個階段”。但是,在此,大江健三郎最關心的是死在水中的人物弗萊巴斯。當年,他年輕貌美,雖說是度過了輝煌的一生,但其實僅僅是他壯懷激烈的青春和痛苦的童年時期而已。從該段對話中,讀者可領略到小說中引用他人“詩歌”的特點和魅力所在。“這一想像顯然超越了文本自身的寓意,使卷首引語與章節中的戲劇性事件構成張力,在敘事藝術上具有“對話”功能。
當年在“年輕貌美”之時死於水中的弗萊巴斯,與當時正直壯年就在洪水中溺水而死的古義人父親的情形重疊。在此,如果進一步聯想:兩位英年早逝者是如何度過“壯懷激烈的青春和痛苦的童年時期”,即可發現其中的重疊和聯想,旨在啟發讀者繼續思考:二戰的結束(也即軍國主義時代的結束)與“我”的父親之死——反抗“天皇制”下的國粹主義——密切相關,從而凸顯了作品的重要主題。
如此敘事技法之所以能取得藝術效果,關鍵在於通過詩歌“死在水中”的一系列隱喻詞語的處理,在讀者心目中喚起視覺性的圖像。小說中通過隱喻喚起圖像或視覺再現的人物形象重疊——“父親”與弗萊巴斯;“我”與“父親”——折射出了歷史層面上的、父子傳承的文化反叛。結合這一引申意義,來理解詩歌中再現的“海底的潮流”、“骨頭”和“漩渦”等意象,就會更加深化對作品的理解。
比如,特里林認為,“死在水中”講述的“水”的意象蘊含著生命的獲取,而“火”則扮演著破壞性的力量。溺死的腓尼基水手弗萊巴斯,被一首簡潔的輓歌來悼念。這就是通過引用詩歌的形式,賦予小說中“‘水’與‘火’的意象”。也即,《水死》既是一首悼念父親的輓歌,又是歌頌父親歷經人生洗禮、至今仍然“威嚴行走在波浪里”,而且這裡的“波浪”又與峽谷村莊“淼淼”的“森林”意象重疊。
結合作者創作《水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從中不難發見:作品中表現的由個人境遇的挫折生髮的死亡動機所折射出的情緒,正是作者對日本近代史和現實社會的絕望抗議和吶喊。
“戲劇化”的敘事結構即所謂小說的戲劇化,並不是將小說寫成戲劇,而是將相互對立的復調聲音導入小說,形成交響樂式的多聲部的敘事結構。
《水死》以戲劇演員穴井子和作家“我”共同探討如何將四十年前放棄的“水死小說”展開戲劇化敘事。作家古義人正在寫“水死小說”,而穴井子一邊等待著未完成的小說,一邊已經做好計畫——在尊重作家古義人過去的所有作品的基礎上,把“水死小說”作為其“晚年工作”的集大成,將古義人和故事中再現的“我”的“父親”,以戲劇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水死》就被設定為一個開放性的文本,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導入不同的乃至相互對立的復調聲音。
穴井子以朗誦劇的形式,將“我”的小說《親手拭去我的眼淚》呈現在讀者面前。戲劇舞台背景:“在一個夏天的院子裡,蔥綠的枝葉間盛開著淡紫色和深紅色的薔薇花。”穴井子朗誦:“總之,8月某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我’和一些軍人推著坐在一個木製車子上的父親,緩緩離開峽谷村莊,打算去一個地方城市發起暴動。”此時,作家“我”一邊在台下觀看演出,一邊想起“我”和母親曾因小說《親手拭去我的眼淚》鬧到“恩斷義絕”的地步。
小說主要內容:暴動發起於1945年8月16日,當時,在日本帝國的版圖內,還沒有出現因軍人對日本投降不滿而舉行槍戰暴動事件。於是,為了給叛軍籌集資金,“我”和一些軍人推著坐在木製車子上的父親去襲擊松山銀行,結果父親被亂槍射死。在此,舞台上的朗誦劇與舞台下“我”的回憶,在敘事藝術上發揮著歷史層面上的對話作用。
首先,8月16日這個特殊的記憶符號,立即喚起讀者對歷史的追憶: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宣告無條件投降。而朗誦劇中特意把8月16日改為“8月某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其中,如果說“天空一片漆黑”暗示著二戰中慘敗的、日本國民的絕望心境,那么那天“早晨”父親帶領“我”和一些軍人採取的行動,則象徵著希望。同時,這種希望又與朗誦劇背景相呼應。其次,通過戲劇化的敘事,不僅使空間變容為複數空間——既是歷史空間,又是當下空間,而且使敘事主體“我”也演變為複數的“我”——“我”既是作家,也是聽眾,與此同時朗誦者穴井子也是“我”的一部分。
因此,《水死》雖然承接過去作品中一以貫之的固有表現技法,但因敘事視角的微調,又構築了一種新的敘事樣式。如果說上述的朗誦劇僅僅是朗誦者與“我”的對話,那么,同樣以朗誦劇導入的夏目漱石的小說《心》則更是別出心裁,直接升級為朗誦者與觀眾的對話,並將日本近代史的原點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進一步深化了作品主題。
在四國森林的圓形劇場,朗誦者穴井子扮演“我”的老師,他說:“深受明治精神影響的我,如果要殉死,那也只能為明治精神殉死。”對此,舞台下的觀眾紛紛發言,給予反駁。首先是扮演“高中生”的觀眾提出異議:“老師,你背叛了朋友K,結果導致其自殺,這與明治精神有何相干?”接著是扮演“國民”的觀眾辯解道:“難道你懷疑老師為明治精神做出的尊貴選擇殉死嗎?”在此讀者不難發現:“國民”的觀點代表著迄今為止一般讀者對夏目漱石的著作《心》的主題的理解。
比如,夏目漱石研究專家三好行雄的觀點:漱石讓老師殉死於“明治精神”,統一了作品的主題。我們在直面“充滿自由、獨立和自我的現代”社會時,不僅要將其作為命運接受,同時要有忍受孤獨和寂寞的精神,即無論試圖通過肉體的侮辱獲得高貴精神的K,還是雖然懷疑K的無謀,但結果仍以自我處罰的形式進行贖罪的老師,他們都是“明治精神”的體現者。
而“高中生”提出的質問,與作者長期以來對世俗的解讀《心》之主題的不滿相通。
1945年的夏天,長江古義人冒著暴雨獨自乘上小船離家出走,結果因洪水溺水而死。“溺水”並非“父親”的真正死因。小說中讓“父親”的弟子大黃的靈魂登場,以同時代代言人的身份證明:“父親”是為反抗那個時代的“軍國主義”精神殉死。因此,《水死》是一部再現主人公長江古義人經歷的兩個相互矛盾的“時代精神”的傑作。所謂相互矛盾的“時代精神”,即戰前的軍國主義和戰後的民主主義。而且,這一對“時代精神”正是古義人“我”從父親身上繼承而來的、反抗國家權力的民眾精神。
《水死》以小說中導入戲劇的樣式展現故事。“我”經常以旁觀者的身份出現,在觀看戲劇時視覺與聽覺並用。運用復調式的對話是大江健三郎的文學作品由重視視覺轉向視覺和聽覺並用的一大變革。
作品評論
《水死》的整體故事簡單,但敘事結構非常複雜。他的寫作資源抽離了日常生活,尤其是晚年完全進入了教科書和圖書館式的寫作狀態,體現出不同領域知識的融合。再加之其對靈魂和精神世界的關注等內容,都加大了作品閱讀的難度。作者與主人公的經歷相似度很高,使作品具有很強的“私小說”色彩。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家本人,就無法有效和充分地理解其作品,因為作家深刻地參與了小說的思想和意蘊的經營,他本人的生活與作品也形成了互文乃至同構的關係,提供了一種有別於過去經典小說的更加寬闊和複雜的敘事模式。
——中國作家網
讀大江健三郎作品《水死》,想起了屈原《離騷》中的句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莫言
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出生於愛媛縣森林中一個小山村,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專修法國文學專業。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華》、《飼育》、《掐去病芽,勒死壞種》、《廣島札記》、《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