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履歷
陝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
李小洛,20世紀70年代初生於陝西安康,學醫,繪畫 。2004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 曾參加第22屆青春詩會。第六次全國青創會、就讀第7屆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獲第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第四屆華文青年詩人獎 ,郭沫若詩歌獎、柳青文學獎 、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中國當代十大傑出青年詩人 首都師範大學2006年度駐校詩人 ,“陝西省百名青年文學藝術家” 、安康市文聯副主席 ,安康市作協副主席,安康市政協委員。中國作協會員,陝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 陝西省作協理事 。著有詩集《偏愛》 ,《我的三姐妹》 等。
老詩人林莽說:“李小洛是新世紀以來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詩人,她的創作銜接傳統,摒卻矯情,緣於生活、感悟生命,在當下詩壇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評論界認為她的詩歌開取了中國女性詩歌的一個新的向度,是“從哲學的峰巒噴涌而來以陝南安康為背景的“安康性”的寫作,為當代詩歌開闢了一個新的路徑“。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文藝報》、《文學報》、《羊城晚報》、《陝西日報》、《西安晚報》、《中國婦女報》、《南方都市報》、《齊魯晚報》等數十家新聞媒體都對其詩歌創作了專題報導。短短數年時間,她成了中國女性詩歌某一側面的代名詞、詩壇上的一個瑰麗的現象,她的詩歌被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共同喜愛、關注。她成了陝南文化的一張生動、美麗而婉約的名片。
創作談
在我寫下那些詩歌的時候,我連讀者都沒去想,哪裡又會想到過“她們”這個詞,想到更多的“時代”問題。我只不過是秦嶺腳下、漢江邊上安康小城裡的一個小女子而已,我也只不過是用自己的左手捕捉了一些從腦子裡一閃而過的閃電罷了。我自由自在地穿行在這樣一個小城裡,不必跑得比閃電更快,只要提防著真正的閃電的到來就可以。不必擔憂生活在別處,只要小心翼翼地牴觸著那些舊憶的侵襲就好。
路過南環路上那些賣魚蟲的小店的時候,我會一家一家進去,在那些魚缸前停下來,看一看玻璃缸里的金魚,看著水泡上升,魚使勁地呼吸。登上城堤,我看見城南城北大片的土地,田野里忙著拔草種地的農夫,從土地的一頭走到另一頭;街道兩旁“非”字形排列的許多灰黑的瓦房,一家店鋪里那個正在忙著加工壽衣的老裁縫,也許是和我一樣,他也看見了正在天空上飛著的一隻烏鴉,扇動著疲憊的翅膀,背著一個沉重的軀體飛快地從窪地、山岡以及桑樹的枝條上掠過。
每天晚上,我睡得很遲,不去想要等待什麼。我像一顆小個子的蠶豆蜷縮在床鋪的左邊,占據黑夜的一小部分。有時候,看一本放在枕邊的文字。有時候,乾脆從被窩裡爬起來,去到一個廣場,站在夜晚的中央,站在還沒完全竣工的雕塑前,聽北風經過城市上空發出的嗚嗚哭聲。
我會給自己注射50毫克西地泮讓自己安定下來,不去想靈魂和其他。有時候,我也會懷疑自己的耳朵,懷疑耳朵里聽到的那些響聲不是我的錯覺,而是一種鬼魂的聲音。或者是詩歌。多少年了,我想也正是它們,挾裹著我不停地向前,像一條孤獨的鐵軌,去更遠的地方。
只有到了露水厚重的清晨,我才會坐在窗前寫那些分行的文字。我才會反覆地提到早晨,提到剛剛升起的太陽撥開的烏雲,提到郵電大樓里忙出忙進的郵差,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那些滿面倦容的旅客和他們鼓囊囊活下去的行李。才會想起我的商人父親。2002年,他離開了我,在早春一個寒冷的日子。越過人和鬼魂的界線,他用了不到10分鐘的時間。在護送父親遠去的山道上,我成了最後一個人。山坡上,滿天滿地狂生狂放的桐花和刺槐花穗從枝頭上垂下來,垂過低矮的荒草,落在黝黑的苔癬上,像蒼天的眼淚。我知道,我的一件行李已經丟了,永遠也找不回來了。父親為了給予我另一條通道,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通道,讓我相信父親的靈魂一定還停留在這世界的某一片天空上,或者和別的什麼人住在了一起,也讓我和父親以及更多的靈魂開始了對話,並從此得以用詩歌來表達這些對話。
在那些讓我終於可以看到的一個模糊不清的世界的濃霧中,我就是這樣,在父親以及和父親一樣的人離開的道路上,和他說話,和“烏有”們說話,並帶著一些詩歌的行李作為禮品,在我和他們和日常世界之間建立著父女、朋友一樣的“人鬼”關係,從而走向一些早已存在的詩歌。 (李小洛)
作品節選
省下我
 噙淚定格一生,一吻風一個夢
噙淚定格一生,一吻風一個夢省下我吃的蔬菜、糧食和水果
省下我用的書本、稿紙和筆墨。
省下我穿的絲綢,我用的口紅、香水
省下我撥打的電話,佩戴的首飾。
省下我住的房子,收留父親。
省下我的戀愛,節省玫瑰和戒指
省下我的淚水,去澆灌麥子和中國。
省下我對這個世界無休無止的願望和要求吧
省下我對這個世界一切的罪罰和折磨。
然後,請把我拿走。
拿走一個多餘的人,一個
這樣多餘的活著
多餘的用著姓名的人。
(刊於《花城》2004年第4期)
這個冬天不太冷
這個冬天不太冷,廣場上的雕塑還沒有竣工
我從一扇關閉已久的門裡走出來
穿過了這個熱火朝天勞動的場景
這個冬天不太冷,箱子裡的啤酒
還剩下了最後兩瓶,我靠在剛剛燃起的
爐火邊,慢慢地喝著它們
我像擔心著一場早已開始的宴席
擔心一些人會提前走掉
而不忍,把杯子裡的酒,一飲而盡
這個冬天,風經過琴鍵時
發出了嗚嗚的聲音。補丁在天空上
像一些飄浮的雲。我站在夜晚的中央
像一隻被人類領養的小蒼蠅
像孤獨的藥棉住在人民的傷口裡
每天晚上,我是那么晚的睡下
我是那么早的醒來
我是那么的思念著,一個
躲起來,讓人找不到的人
啊,那個荒涼、遙遠、面孔模糊
遲早要來敲門的人
(刊於《花城》2004年第4期)
在街上遇見一個熟人
那個人其實與這些無關
與後來的火車也無關
她只是存在於一個早晨的背景中
孤獨的走過了那個現場
甚至只像一滴雨水敲打在雨傘上
這時候,她只是一種突然的表情
讓我站在人流分至的路口
不知該快樂起來還是要更為憂傷
這時候,她只是
讓我想起來
你說過會去一個島上
那個地方沒有樓房
也沒有電話
我還想起來
距離這個日子
已經愈來愈近了
(刊於《花城》2004年第4期)
想起一個人
在這個冬天
我想起來一個人
想起曾經和一個人在一間房子住過很多年
很多年了
都想問他一句話
在他剛搬進來的時候
我還沒有想起來這句話
我穿棉布的裙子
吃嫩綠的蔬菜
魚缸里裝滿了清水和菊花
那句話是在一場搬動磚頭
砌牆的勞動里誕生的想法
當我想問問他
後來他卻搬走了
在一個下雪天
一步一步,從雪地里拔出了他來時的腳印
再後來的事情有一些改變
我再也沒有在上樓下樓時
或者變換的天氣里見過他
他去了南方
也許回了鄉下的老家
那句話,就這樣一直擱著
像擱在冰面上的一條破船
一場 春風吹來,終於吹疼了我的面頰
(刊於《花城》2004年第4期)
等一個人
等一個人,就去大街上
看看,在櫥窗的玻璃前
照一照棉布的衣裙
等一個人,就去郵電大樓
看看,我不寫信,電話里
我也說不清這個城市多變的氣溫
那些穿綠衣服的郵差們,忙出忙進
我只是一個過路的人
等一個人,就去車站的候車室
看看,看那些可以抵達的
車次,有沒有更換或者刪減
人群中或許能有幾張親切的
面孔,能有一群北回的雁陣
它們有一些溫暖的翅膀
我卻不能借來去找我愛的人
等一個人,就要懇求冬天的太陽
不要走進黃昏的叢林,就要等到屋檐下
冰凌開始融化,螞蟻們也搬進新
房子,那只在老家的春天裡銜泥的燕子
也嫁給了幸福的陌生人
(刊於《花城》2004年第4期)
乞求
我乞求你給我一個暖瓶
用來裝下我的淚水
我乞求你給我一個冰櫃
用來盛走我的骨灰。
我乞求你有一天能來到這兒
領回這一冷一熱的親姐妹
暖瓶你打開來飲水
回家的小路撒遍我的骨灰。
偏愛
我只是偏愛左邊一點
左眼看報,左手寫字
用左邊的眼球積聚光線
夜裡睡覺我也喜歡睡在床鋪的左邊
像顆小個子的蠶豆,占據黑夜最小的位置
每次走動,我總是先跨出左腿
每次停頓
我也總是傾向生活的左側
看上去,我總像流過這個世界
一條左撇子的河流
我固執地保持著這種習慣
其實和道聽途說的左傾
機會主義的路線無關
我儘量地挪出右邊的位置
右邊的房間,右邊的身體
右邊的藍天和草地
給那些另外的人
只是我已經習慣了
我已經習慣了接受來自左邊的疼痛
習慣了它們比右邊來得更為仔細一些
準確一些
放肆一些
慢慢地
溫暖一些
幸福一些
(選自詩集偏愛)
相關評論
最後的一滴眼淚,還有病房中逐漸暗去的光線,傳達著李小洛獨具的悽美,人生體驗的成熟。——謝 冕
李小洛的寫作姿態已經說明了一切,許多詩句都凝聚著她生命體驗中的隱痛。——吉狄馬加
纖細的藝術感覺,鮮明的性別立場,行雲流水般的文字,展示了一位70後女詩人的精神成長史。——吳思敬
一些作品可稱之為“出類拔萃”,不可多得。自由、奔放、逼真極致的表達,其動人處仍舊是純粹與真摯,寫得既放縱,又專注,既有超越的意味,又有世俗的痴情。——韓作榮
詩思鋒利不顯得刻意,個性化的節奏與心態彼此諧和。確係有感而發,感覺到位而能進一步延伸。敏感細緻中的剛勁兒尤為難得。——陳 超
一種詩意的、沉潛的自省與豁達,對生命本義的興趣和探尋,使她超越了性別的界限。——柯 平
李小洛是2005年有個性的新詩人。集中閱讀李小洛的詩,感受到“詩意生存”的樣本。她的詩自然、流動、感性,用當下口語傾訴著內心的獨白。節奏從容,情感真切,在一度的“性別”張揚的女詩人群中,她反而讓讀者鬆了一口氣 。放鬆一下,清涼一下,這就是李小洛“原創”的可貴。也許,批評家可以說也蘊含著另一種潛在缺點“沒進入深度的寫作”?——葉延濱
“從一些生活的場景里徐徐後退”這種意識讓李小洛看到了我們感到但沒有認真說起的那些事物。面對太多女性詩的孱弱之態,她的作品是達觀的。使用口語的方式,但進入了真摯的生命的體驗與思考之中。——林莽
詩集出版
 李小洛詩集《偏愛》
李小洛詩集《偏愛》書名:偏愛
著者:李小洛
經銷:全國新華書店
出版:南方出版社
版次:2009年9月第一版
-----------------------------------------------------------
李小洛的第一部個人詩歌專著《偏愛》日前由南方出版社出版發行。詩集收入了包括《一隻烏鴉在窗戶上敲》、《省下我》、《我只是偏愛左邊一點》、《我不在》、《我要這樣慢慢地活著》、《五十年後的旅行》、《病曆書》等在內的80餘首她的代表性詩作。作為國內70後詩群的代表性女詩人,李小洛的詩歌創作成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詩壇的一個具有象徵性和坐標性的詩歌現象,她在女性身份下以獨特的視角和姿態對“人的身份”的多重反思和追問不僅吸引了眾多讀者,而且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無論是李小洛近期的《偏愛》,還是她早期的文本無不呈現了一個詩人寫作背後強大的根性場閾,這就是她的故鄉安康。應該說每個人的詩歌和文學寫作中都會有屬於個人的“故鄉”,當然我所說的“故鄉”不是單純地理學意義上的,更大程度是精神指向甚至是包括詩歌理想在內的。
安康是李小洛詩歌寫作的母體,而這座秦嶺以南漢江邊上的小城暗含著怎樣的一個詩人、一個生存個體的成長履歷和詩歌寫作的深刻背景?在李小洛的詩歌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特殊的“她”的影像:敏感、好奇、憂鬱、執著、懷疑成了她性格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了她詩歌寫作症候的顯影液。
李小洛在安康這座小城裡無疑屬於靜靜的甚至帶有悲憫情懷的觀察者和生活場景的“多事”的測量者。她在這座小城奔走、停歇、觀察、思考。日夜流淌的漢江,高大的山脈,郊外廣闊而荒蕪的原野和白雪中飛動的烏鴉以及火葬場的巨大煙囪,南環路賣魚蟲的小店,簡陋而溫馨的小吃店和稠酒鋪,陵園路的梧桐樹和步行街上繁雜的人群,冬夜裡的乞丐和夏日夜晚風雨敲打的屋頂都成為實實在在的生存場景甚至成了富於象徵性的寫作背景。
多年以來李小洛在這座城市穿行,嘈雜的市井和獨處的沉寂正是一個曖昧時代詩人的生存寓言,而這種日常化的穿行忙碌正好與暗夜裡的沉靜形成互補的空間,這種空間所形成的對話性和張力衝突使得李小洛的詩歌很像是無窮盡的萬花筒,層次翻新,耐人尋味。而李小洛在詩歌寫作中成為了懷有偏愛的堅執者。
李小洛的詩作在質地上不事張揚但又極富象徵意味,她在季節的漫漫光陰和匆促轉變的生存場景中試圖發出屬於自己靈魂的聲音,這種低聲的傾訴和自我對話的情結時時處於後工業時代巨大的喧囂與吵鬧之中。在越來越欲望膨脹、生活空前加速度的時代,李小洛所能做的恰恰是為自己增添一個減速器,減速的結果是她在詩歌中發現和創設了一般詩人所普遍忽略的空間,在現場審視的冷峻深入和回溯性的黯然悵惘中詩人用情感、經驗和想像交織成了時代聲色和個體生命的斑駁光影。
李小洛的詩作與其他女性詩人比照起來,她的詩歌寫作更多是一種緩慢的、沉潛的、靜思的狀態,有著一種凝重的冷色調,這在女詩人中是少見的。而這種緩慢狀態的詩歌寫作比較具有代表性地顯現出詩人在日常生活和歲月流逝中的深切感懷和知性思索,而這種靜思的狀態使得李小洛的詩作更具有一種複雜性。
無論是現實的細節、往昔的記憶還是生髮的想像都在看似閒淡的抒寫中呈現了一個詩人融合了現實和想像的既簡單又無限繁複的世界。李小洛的詩作中不斷強化著時間性的場景,其敘寫也往往帶有舒緩的回溯性,這就使得現實和生存都沾染上了強大的主觀情思觀照之後的別樣的意蘊,同時有一種猶豫不決的調性,在張開與緊閉,遲疑與堅執,慣性的“右”和自我的“左”之間一直處於詰問和磋商之中。
李小洛的帶有執拗性的偏愛和堅執使得她更像一個後工業時代的高速路上的奔波者、出走者、尋求者和發問者,在工業時代的尾氣和縱橫交錯的城市中,也許只有詩人還能夠看到最後的草原和鄉村。任何詩人的寫作都不會脫離我們生存的時代場景而別做它聲,無論是高速公路還是加油站,在這些極具象徵性的時代場景中,詩人仍然在堅執中期待來日,仍然在偏愛著自己的所愛。
(作者霍俊明系詩人、詩評家、文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新詩批評與新詩史學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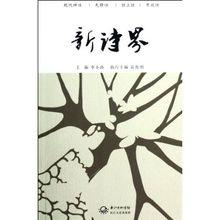 新詩界第六卷
新詩界第六卷書名:新詩界(第六卷)
作者:李小洛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7-1
《新詩界》自創刊以來推出了大量的重要的詩人、詩作和詩論。《新詩界》力圖以高瞻遠矚的精神和胸納萬壑的包客情懷涵蓋百年新詩的發展歷史和願景。以其現代禪性、開放性、包容性、獨立性、先鋒性贏得了詩歌界很大的反響。美國、荷蘭以及香港、台灣及澳門的海外詩人學者以及漢學家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
現代禪性 先鋒性 獨立性 開放性
新 詩 界 ( 第六卷 )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長江文藝出版社
顧 問
牛漢 屠岸 鄭敏 洛夫 紀弦 吉狄馬加
瘂弦 鄭玲 余光中 張默 鄭愁予 李岱松
謝冕 吳思敬 陳超 邱振中 徐敬亞 李怡
楊宗翰(台北)
編委會主任
屈善施
編委會副主任
倪嘉 胡弗
主編
李小洛
執行主編
霍俊明
編 委:屈善施 倪嘉 劉雲 胡弗 霍俊明 李小洛 李岱松
主辦單位:安康日報社 “漢江·安康”詩歌創作基地
駐校詩人情況
參加學校活動:
首都師範大學2006年度駐校詩人李小洛入校儀式及走向經典詩歌朗誦會,李小洛詩歌講座,李小洛詩歌創作研討會。
駐校期間研究生論文目錄:
在漫漫水線和淡淡光陰中培育的詩歌作物——李小洛詩歌論(霍俊明)
李小洛:在宿命的貧困中孤獨地飛翔(段從學)
獨特立場·“愛與死”·才華——漫議李小洛的詩歌創作(王士強)
耀亮生命的閃電——李小洛詩歌散論(王永)
誰在言說?——對李小洛詩歌的一種閱讀(陳亮)
整個世界住在她的詩歌里——淺析李小洛的詩歌主題特徵(羅侃平)
女性的自然——談李小洛詩歌女性生態寫作意識(林喜傑)
自戀的精神之旅(李紅雲)
“人類的光線,在暗”——李小洛詩歌的超性別寫作(盧秋紅)
以空靈的精神家園安頓沉重的肉身——李小洛醫學與文學的雙重人生(羅梅花)
別一種生存狀態——關於李小洛詩歌中“慢”的解讀(劉曉翠)
重複之魅——試析李小洛一種類型的短詩(張墨研)
孤獨者的訴說——李小洛詩歌讀後感(金慈恩)
敘事性·生命體驗·詩意生成——讀李小洛組詩《孤獨書》(龍揚志)
李小洛組詩《病曆書》的一個解釋(崔勇)
背對時代與抵達內心——李小洛詩歌《省下我》讀後(王士強)
緩緩地涉過那片詩歌水域——李小洛訪談錄(霍俊明)
面向更廣闊世界的女性寫作 ——李小洛詩歌創作研討會綜述(陳亮)
李小洛 在安康(路也)
終於等到有機會去李小洛的家鄉安康,一車人鑽過九九八十一條千米或萬米的隧道,從秦嶺那巨大的花崗岩腸胃中穿過,其間看盡漢水或其支流從山之夾縫中流淌出來的遼遠與清澈,最終當然是漸變而成的亞熱帶風光,恍然大悟李小洛原來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同時還有從前線到了敵後、從前生到了來世之感,心想,“李小洛她怎么找了這么個地方,這么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方,深深地遠遠地躲藏了起來?”於是假想,也許正是在秦嶺的巨大的庇護之下、在漢江的蜿蜒的佑助之下,這位陝南女子才得以現世安穩歲月靜好吧。
沒錯,李小洛的外貌和打扮基本上就是一副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的模樣,一看就是魚米之鄉絲綢之地生長出來的秀麗之人,天生一張標準娃娃臉,既安且康,苦難和憔悴很難在這類臉型上停留,這張臉嬌憨機靈有餘而憂憤愁苦不足,如果去唱戲,只能唱唱像紅娘那樣的小丫環,斷斷唱不了那種病歪歪地對某某書生害著相思病的苦小姐。但不知為何,就是在這樣一個人兒身上,卻又總是散發著那么一絲冷感,甚至還有點兒“酷”,我想,就姑且稱之為現代感吧。
李不洛的身份不好界定。她像小孩子耍小性子耍寶一樣變來變去,對自己的身份總是顛覆、確認、再顛覆。早年是婦產科醫生李小洛,據說是一個敢在人家肚皮上動刀見血的傢伙。後來這人忽然變成了詩人,天上掉下個李小洛,恰好掉到詩壇上來,且出手不凡,僅那首《省下我》就恨不得占領所有當代詩歌選本。在詩歌里,她找到了一種屬於她個人的語調,音質清澈乾淨,有著必要的溫厚,既不纖細,也不孱弱,調門的高低起伏不大,不媚不冷,不卑不亢,在率直里還夾雜了那么一點能讓人發出會心微笑的任性或者幽幽的嬌嗔。如果將她的一首詩掩去作者姓名,混在一群詩歌裡面,在各式各樣的眾聲匯集而成的嘈雜里,我們稍加側耳傾聽,仍然能夠僅僅通過語調的音頻線就可以把她辨認出來,“喏,她在這裡。”其詩作充滿了烏托邦式的空想和強烈的白日夢特徵,同時她那中性的語言姿態,又使得她仿佛約等於當下詩界之李宇春了——對不起,我曉得這個對應並不怎么恰當,因為這個詩人選擇的路線絕非流行,而是某種既簡單又深刻的純正。
她現在的正式工作是報紙編輯,大約編副刊,任務是在一張比較肅穆的政府報紙上找個角落植花種草。還知道她一直酷愛攝影,外出時總是隨身攜帶著她那沉重的冰涼的專業機器,時時像舉著一挺機關槍一樣瞄準這個對準那個。
她接觸網路很早,能製做出相當漂亮的網頁,不知能否勉強算作一位IT人士。當然她自小習畫 ,曾立志當畫家,對於她的畫,我當時並未太在意,見過幾幅,工筆的成份多,不時流露出稚拙的憨態。還有,她對刺繡裝飾的活計也有著濃厚興趣,幾近專業級別。總之,我最不擅長的事情,她基本上全都擅長。只是誰也無法預料這人接下來還會怎樣,她是那種——或有意或無心——不斷地往名字前面添加定語的人。
沒錯,最近一兩年來,她又嚇人一跳,似乎要將自己名字前面那個原本不太清晰的“畫家”的定語著意強調一下,要把這個定語的筆畫加黑加粗,她竟然把畫從宣紙上一直畫到了石頭上 ,還是漢江里的石頭 !她的一塊塊漢江石畫爛漫奇麗,似有楚辭之韻,陝南之地楚文化的氤氳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滲透進她的生命肌理。她對那些石頭因勢造形,借紋造意,把那些死的石頭全都畫活了,讓那些碳酸鈣獲得了生命,獲得了浪漫和自由,那些石畫裡有童心未泯的好奇與莽撞,有赤裸裸的單純和一往無前的熱烈。
希姆博爾斯卡有一首詩《和石頭交談》,寫的是凝眸於一塊石頭時,突發奇想,認為石頭應該有一個門,會答應人的請求並讓人進去參觀,而李小洛正是以循循善誘之筆撬開了那些石頭的嘴巴,讓石頭說話了!我觀其石畫,在會心微笑和驚嘆之餘,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現:她畫在石頭上的女孩、貓、民居、甚至小轎車,其容貌、其形態、其神情、其氣質,全都與李小洛本人十分相像!聽說她近來在古城西安鐘樓上辦了石畫展,成立了工作室,也許哪天我會挎一個竹籃子到她那裡去向她討要石頭,像裝雞蛋一樣把籃子裝滿了再回來,同時提醒她:請注意,不要把漢江里的石頭統統畫完!
小洛在安康,生活的既安且康,不過也並沒少為詩歌做事。2010年她所在的安康日報成立了中國詩歌研究中心、陝西省作家協會下設的漢江·安康詩歌創作基地,設立了一個面向全國80後優秀詩人頒發的安康詩歌獎,組織一系列轟轟烈烈的大型詩歌交流活動。不強調、不忽視、不誇張,不賣弄,只是呈現一副淡淡的天然模樣而已。這就是李小洛。不狂熱、不偏執、不沉湎,不粘滯,不鋒利,而這又絲毫沒有妨礙她對於生命的巨大熱情,並且對世上異於自己的生活態度也能保持相當的同情、理解和寬容。
她清清爽爽,從從容容,自信、自得、自足得令人羨慕,但還遠遠算不上爽脆斬截和野心勃勃;討厭並試圖擺脫各種束縛和秩序,看上去永遠都有離家出走的可能,卻又十分知曉這些束縛和秩序的必要性,懂得適時對它們表示出應有的尊重;她身上甚至有那么一股子懶洋洋、漫不經心、心不在蔫、模糊和不確定的勁兒。
正是這些不確定,最終匯聚而成的不是中庸,甚至也不是簡單相加得來的和諧,而是篤定清朗的悠然之態,舒展瀰漫的自然之風、舉重若輕的優雅之氣、以及我行我素的堅執的力量,這也使得李小洛成為李小洛,而區別於其他任何一個女詩人和男詩人。
( 路也,執教濟南大學文學院。著有詩集《風生來就沒有家》、《心是一架風車》等。獲過《作品》雜誌散文獎和小說獎、齊魯文學獎散文獎、泰山文藝獎詩歌獎,以及《詩刊》的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獎和新世紀十佳青年詩人獎等。首都師範大學2005年駐校詩人,美國KHN藝術中心2008年入駐詩人。)
訪談錄
緩緩地涉過那片詩歌水域
——李小洛訪談錄
李小洛:20世紀70年代出生於陝西安康,曾獲華文青年詩人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參加第22屆青春詩會,被評為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 2006年首都師範大學駐校詩人。著有詩合集《我的三姐妹》、《江非李小洛詩選》。
霍俊明:詩人,詩評家,博士,任教於北京教育學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師範學院中文系兼職教授,《新詩界》副主編,“明天·額爾古納詩歌雙年獎”評審。
霍俊明:小洛你好,你來北京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也一直在想關於怎么來做你的訪談的事情。你可能知道我有一個計畫就是要做一系列的詩人訪談,目前已經做過訪談的詩人有西川、邱華棟、路也、安琪、阿毛等。應該說,作為一個青年詩人你的“寫作年齡”是很短的,但是近兩年來你的詩歌寫作卻迅速的產生了越來越為廣泛的影響並獲得了一些在詩界看來很重要的詩歌獎項。那么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自己的詩歌受到了如此廣泛的青睞,換言之你覺得自己要在詩歌中表述什麼,或者你認為自己的詩歌有著怎樣的個性?
李小洛:是的,我是從2003年才剛剛參與到國內的詩歌現場的。這四年之中,我雖然沒有過多地去思考自己正在經歷著一個什麼樣的詩歌時期,也不大能從理論上知道自己到底在寫下一些什麼,但我已深切感受到了詩歌所帶給我的詩意和溫暖。詩意是來自母語對一顆孤獨的心靈的教化。溫暖則是來自於大家的,可以說,這四年,我真正理解了什麼是詩歌,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領會了“詩人”這個詞語。如果說到自己的詩歌,我想應該是低沉、緩慢、笨拙、自然、和真誠,是它們在完成我的敘述需要。我想也可能正是因為我在努力擯棄矯情,所以才被朋友們接受的。
霍俊明:在我的閱讀視野中很多詩人的寫作都或多或少地與地緣文化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比如路也的“郊區”特徵。我在私下裡看了你的部落格和“李小洛茶吧”,發現你的一些在我看來很重要的詩作和隨筆都與那座安康小城有關。那么,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和詩歌寫作與安康存在著怎樣的關聯?你怎樣理解“詩人的天職是還鄉?”當你來到北京之後,這個城市對你的寫作是否有著某種影響?
李小洛:應該說,密不可分。安康位於陝西南部,是秦嶺腳下,漢江邊上一座山水秀美的小城,也是“中國最吉祥的地方”。我在這裡出生,成長。這裡是我詩歌發生的現場。海德格爾曾說:“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還鄉使故土成為親近本源之處。”因為:“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惟有在故鄉才可親近本源,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如此,那些被迫捨棄與本源的接近而離開故鄉的人,總是感到那么惆悵悔恨。2006年9月,我來到了北京,一下車,看著艷陽高照,晴空萬里,道路上堵塞的車輛和人群,一時間有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這時候,正好有來自家鄉的訊息,說安康正是連綿雨季,那一刻思念一下子就將我的心緊緊揪到了一起,眼睛也在瞬間潮濕。關於故鄉的點滴訊息都讓我魂牽夢繞。所以,北京對我來說,可能只是一個驛站,我也只是一個匆匆過客,那么它也就不會構成對我的詩歌的太大改變。但在這裡,我很高興我學會了一種刻苦、努力、勤奮,以及白雲一般高遠、遼闊、純白和素淨的品質。
霍俊明:在我的閱讀感受中,近年來的女性詩歌與80年代甚或90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轉換,那么你認為目前女性詩歌是否與以前有著不同的質素和轉變?而你的詩歌寫作在我看來更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質,沒有像一些極端女性詩人那樣有著相當強烈的性別意識和話語權力的色彩。眾所周知,在百年的新詩發展進程中,女性詩人無論是從人數上還是被接受的程度上都引起了聚訟紛紜的話題,不知道你對現當代的女詩人有著怎樣的認識,你認為詩人的經驗或性別與詩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
李小洛:轉換是肯定的,而且這個轉換大家有目共睹。但轉換的表征和本質到底是什麼,我一下子又說不上來,作為個人,我也沒有仔細地去分析過自己和其他女詩人之間的差別,我只是用自己習慣的語氣和聲調去言說。詩歌是一種歷史心靈的呈現。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歷史的隱秘,我想女詩人也是一樣的,在她們的作品裡,我們應該觀察到時代所賦予我們“女人”的種種生活和心靈遭遇。當然,這是和男詩人們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之處我想還是在於男詩人們在抵抗,而女詩人們在承受,不論怎么否定,怎么去避免,這種上天所賦予的性別差異和文化馴養還是讓“我們”與“你們”的詩歌在發生著區別。從這一點上,性別經驗和性別差異還是與詩歌有著必然的關聯的,可以說,女人們寫的詩男人們寫不出來,相反亦然。
霍俊明:在你的詩歌文本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你的詩歌中存在著大量的人稱指代,尤其是“我”和“你”出現的頻率相當之高。如在《誰造的這個“我”字真好》這首詩6節31行的短詩中,“我”竟然出現了33次之多,那么你如此高強度的人稱指代暗含著你怎么的詩歌抒寫方式和經驗甚至想像的表述方式?
李小洛:是的。我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點。在我所看到的世界裡,我們生存的這個時代似乎就是一個大“我”。不僅僅是我,我們每一個生存在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里的人何嘗不是如此?可以說,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動物,不管你否認與否,終究得承認:私慾是人類的重要品性。自私導致了人的矛盾與虛偽。但我想人能把這種自私說出來會好一些,所以我就用那些“我”字認真仔細地把自己檢索了一遍,以期自己能做到這一種語境之下的自我反省。
霍俊明:你的很多詩作和隨筆都寫到了你的父親,你的父親對你的生活、性格乃至詩歌寫作存在著怎樣的影響?
李小洛:10歲以前,和父親呆在一起的時間很少,那時候,媽媽帶著我在一個鄉村國小上學,父親在外地工作,很長時間才回家一次。父親是個商人,他的青年時代曾對祖國傳統醫學發生過濃厚的興趣,也喜愛音樂,家裡有很多醫學方面的書,以及二胡,笛子,長簫,手風琴等樂器。沒事的時候我經常爬上家裡的小閣樓去翻看爸爸那些舊書,雖然裡面很多字都不認識,但那些神秘中草藥書上畫著的植物標本卻勾起我及大的興趣,它們是我練習繪畫最早臨摹的對象,父親悠揚的簫笛也給我的童年帶來了許多斑斕的夢幻。但2002年早春的一個深夜,62歲的父親突然去世,這個意外的打擊對我非常巨大,我像一個突然失去保護一下子暴露在風雨里的孤鳥,茫然無措,家的重擔,責任一下子從父親轟然倒下的肩膀上傾斜,挪移到了我的肩頭。而在這之前,我更像一個懵懂無知尚未渡過斷乳期的孩子。接下來的半年裡,我常常失眠,性格變得愈來愈孤獨、敏感。常常在夜半大汗淋漓地醒來,想想父親卻在另外一個生死相隔的世界。這種境況一直持續到第二年。對生命,對人生的重新思考,讓我慢慢走出這場巨大的傷痛和陰影,開始把精力集中到閒置多年的詩歌上來。不但如此,還因此而構成了我這一時期的詩歌品質,很多人看我的詩歌,都覺得女性的意識已經減到了最低,我想這正是和我對於父親的這種感情有關。我寫詩的時候心裡始終有一個正在說話的男人。
霍俊明:很多作家如魯迅、郭沫若、余華等都有過學醫的經歷,都知道你曾當過10年之久的婦產科醫生,儘管現在你已經不再從事這項工作,但是這種特殊的職業、身份、體驗對你的詩歌寫作有著怎樣的影響?你詩歌中的冷靜是否與此有關?
李小洛:我曾在一份簡介上寫過,在醫院十年,我看見女人怎么把女人生出來,女人怎么把男人生出來,有時候她們生著生著就撒手不管了。太多生死的無常,生命的無奈,冷漠,麻木,和麻痹的神經,在這裡都見慣不驚,習以為常。有人說,如果要把世界上的人再進行分類的話,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健康人,一類為病人。用詞語來形容兩種人的生活的話,那他們一個是白天,一個就是黑夜了。而這“白天又是不懂那黑夜的黑的”。在醫院,太陽星星月亮都失去了他們本身的光芒,疾病,疼痛,生離死別的鬧劇,每一天都在這裡無序上演,時間在這裡徹底慢下來,作為一個醫務人員,冷靜,理智,有效,快捷,及時挽救病人的生命是天職也是最基本的業務技能和素質,所以在詩歌寫作中自然會不自覺地把這些都帶進來。醫院的生活對自己還是很有很大影響的。雖然當時並不知道,但學醫,以及在醫院十年的經歷讓我對人生,對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這也是我成為一個比較清醒,理智的詩人的重要元素。
霍俊明:有時候詩歌和生存之間存在著很複雜的關係,不知道詩歌在你生活中處於什麼位置?或者說你的生活和詩歌寫作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記得你有一首詩叫《我要這樣慢慢地活著》,這是否反映了你基本的生活狀態甚至詩歌寫作與生活場景之間的關係?注意到你的一些詩歌存在著相當顯豁的時間背景,如很多詩作都寫到了秋天乃至死亡。作為一個生存個體和詩人,你感覺我們該如何領受時間的饋贈和“索取”?
李小洛:詩歌永遠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10年時間,我先在醫院,是一個婦產科醫生,後來又到報社做編輯、記者,職業在轉換,但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我對文字的眷戀和熱愛。我想以後也不會隨便改了。安康是一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小城,生活節奏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不像其他的城市那么快。每天清晨,我都在那裡的某一處房子裡慢慢醒來,慢慢地起床,疊被、刷牙、洗臉、穿鞋、出門、下樓,帶好頭盔、圍上圍巾、撥弄出埋在衣領里的頭髮、拔出鑰匙、發動機車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來的車流人流當中。可以說,在那裡,行走,或者停留,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慢、一種混沌。而我也正是在這樣的慢和混沌里才感覺到了時間的存在,感覺到時間是我的敵人,也是我的朋友,它所給我的和拿走的是一樣的,很多時候,饋贈就是索取。
霍俊明:2006年是詩歌的多事之秋。有很多媒體評出了所謂的2006年的十大詩歌事件,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這些詩歌事件乃至其背後的文化乃至社會話語權力的齟齬和衝突。在炒作、惡搞、商業的語境之下,你認為一個詩人最應該堅持的是什麼?
李小洛:網上2006年關於詩歌的一些事情我也看過了,但是沒怎么過多地去想。一個人,如果寫了詩,我想還是再更多地去寫一些詩歌為好,堅持詩人的良知,理想,立場和責任,以及詩歌內在的品質。
霍俊明:你認為現在的所謂的官方主流詩刊和民間詩刊在辦刊取向、選稿標準上是否有著差異?在近年或2006年的詩歌閱讀中,有哪些詩人給你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或者說什麼樣的詩歌在你看來是好詩,能打動你也能打動讀者?
李小洛:差異還是有,但我想應該是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民刊已經無處不在,官方刊物也在努力調整。在我看來,一首好的詩歌,首先它應該是打動,讓人產生閱讀的興趣,其次是感動,作品的內在品質、個性,包括語言魅力,能讓人產生震撼,再就是看過之後長久的回憶了。一個詩人的責任感其實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情懷。每一首詩歌都有不同的開端,不同的寫作方式,但責任都是一樣的,而情懷體現在詩歌的能動性上是最重要的。至於說到具體的詩人和作品,就太多了,要好長一串名字和目錄,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霍俊明:在你的詩歌寫作中,閱讀(甚至包括電影)對你有著怎樣的影響?或者說有哪些作家和詩人對你有著重要的影響。在讀你的一些隨筆散文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其中似乎有些三毛的影子。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的誤讀,能不能談下你對三毛的感受,因為對於70年代人而言,三毛確乎曾經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影響。
李小洛:閱讀對一個人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我是一個不合格的讀者,很少認真地去看一本書或是研究一個人,所以,現在想起一些作家和詩人的名字也只能是泛泛的,很難說自己迷戀誰、熱愛誰。三毛的作品我也看過不少,我覺得那是一個執著、灑脫、飄逸、的女人,她的文字清新、自然、細膩,不像很多女作家容易自戀,從她身上看到的是她對世界、對人類的關懷、大愛和責任,但又孩童般靈動而不乏睿智。我很喜歡她背上行囊就可以出發,然後又獨孤到死的一生。但要說到影響,我想還是不能,因為我總是覺得自己無法達到她那個活法。
霍俊明:當我們閱讀新詩史和大量的新詩研究文章時,我們會發現文壇對詩人基本上是按照“代際”來劃分的,如第三代(新生代)、第四代、中間代、70後、80後等。那么我想反思的是這些以“代際”所命名的詩歌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差異和關聯?作為一個70年代出生的詩人,你是否覺察到與前代或後代詩人之間的差異,時代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目前詩歌界有一些論爭,如有人認為90年代以來的詩歌尤其是70年代出生的詩人,他們的寫作離“現實和時代”越來越遠,你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李小洛:差異和關聯肯定在遵循著某種節奏,但是這應該期待著更為深刻的研究,或者是實踐的洗清,現在來說,很難一下子說到底,我不敢肯定什麼,也不敢否定什麼;但是對於“90年代以來的詩歌尤其是70年代出生的詩人的寫作離現實和時代越來越遠,”這樣的鬼話,我可以一下子就否定它,很顯然,這是一些沒有時間閱讀的人的囈病之語,說這樣的話的人,他起碼有5年沒讀詩歌了!是在換著方式表明自己的虛弱和無知!
霍俊明:零零落落地說了這么多,對於今後的詩歌寫作你有著怎樣的打算?
李小洛: 沒有太具體的打算。打算還在未來。 (詩歌月刊)
記者:你現在是不是靠詩歌生活的?
李小洛:肯定不是。這不是我不想靠詩歌生活,而是因為詩歌向來就不是讓人生活的,從古至今,詩歌從來都沒有淪為一種生活的工具。假如有一天有人靠詩歌生活了,我想,那時候的詩歌肯定不是現在我們所談論的詩歌了。在詩歌還是詩歌之前,我認為那些想靠詩歌生活或者是要求你靠詩歌生活的想法,必然都是非分之想。
記者:如果不寫詩,你會去乾什麼?
李小洛:這個問題如果改成“在乾什麼之餘,如果不寫詩,你會去乾什麼?”我想可能會更便於回答。詩歌應該是心靈的事,我想它和我們的職業和我們大多數的身體行動都不具有必然的關係,自然,也就不存在取捨的必然聯繫。當我寫下一首詩的時候,我往往是沒有一種“乾什麼”的感覺,而我在寫詩的時候,也很少知道那些不寫詩的人在乾什麼,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我目前還回答不了的問題。
記者:詩人和普通人有什麼區別?你和別人又有什麼區別呢?
李小洛:詩人和普通人能有什麼區別?難道詩人不是普通人?我和別人的區別,我認為應該是我是我,而別的人是別的人。
記者:你是否喜歡美容、逛街、買漂亮衣服?
李小洛:不喜歡美容,但偶爾逛街,偶爾把逛街作為一種身體的旅行,那種在人群中享受個人的孤獨的旅行。至於漂亮衣服,我總是缺乏足夠的抵抗力。有人說女人永遠都缺一件衣服,它就掛在商場的壁櫥里。我想我還喜歡收藏絲巾、披肩、圍巾什麼的,是把這些東西當成可以代替世界的美好的那一面的事物或寄託了。
記者:你理想的愛情觀和婚姻觀是什麼?是否達到這一理想?
李小洛:真正的愛情應該是距離消失之前的那一瞬,美好的婚姻應該是晚年的某些時光。既然是理想,每個人就要走在前往理想的路上。
記者:愛情和你的詩歌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對你的詩歌起到什麼作用?
李小洛:我相信這個世界上肯定有和愛情無關的詩歌,但我不相信有和愛情無關的詩人。愛情對於每一個詩人應該都是一個模糊的起步之地。(濟南都市女報)
繪畫作品
 李小洛石頭畫
李小洛石頭畫一塊石頭,方寸之間,卻被她的妙手打造得活靈活現。近日,“把安康帶回家”大型書法美術展在鐘樓博物館開幕。此次展覽展出了安康書畫家的70餘幅作品,安康青年女詩人李小洛精心創作的50餘幅漢江石畫尤其引人注目。
小小漢江石登臨鐘樓大展台,這也是漢江石畫首次亮相古城。安康是一座美麗安寧的城,滔滔漢江從這裡深情流過七百里,不僅養育了漢江沿岸的安康兒女,孕育出古樸厚重的漢水文化,更為安康留下了一筆巨大的財富――豐富多彩的漢江石。女詩人李小洛在愛石賞石的同時,更迷上了石畫。李小洛告訴記者:“我從小就喜歡石頭,又喜歡
----------------------------------------------------------------------------------------------------------------------------------
 李小洛漢江石頭畫
李小洛漢江石頭畫安康是一座美麗安寧的城,也是一座吉祥幸運的城。
滔滔漢江從這裡深情流過七百里,不僅養育了漢江沿岸如山偉岸如水旖旎的安康兒女,孕育出古樸厚重的漢水文化。潮漲潮落之間穿越滌盪靈秀的山水,也為安康留下一筆巨大的財富——豐富多彩的漢江石。
在中國,石頭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審美對象。“賞石文化”有著悠長的歷史軌跡。 石頭雖是大自然的傑作,賞石卻是人類情感、哲理、信念和價值觀的投射過程。古人賞石,“大而奇者”可迭石造園,“百仞一拳”則案頭清供,而以石為題賦詩作畫者又可謂是賞石文化的“升級版”。
安康人愛石藏石。安康籍女詩人李小洛的漢江石畫是其中重要的一員。其漢江石畫在面世之初便引起極大關注。一如當年她在中國詩壇颳起的那股颶風。一位資深書畫家、藏石家在看了她的石頭畫之後用了兩個字表達:震撼。“她的石頭畫中有一種自由,童真,笨拙共同構成的致命的大美,這非常難得。因為她讀懂了石頭,她知道石頭想說什麼……她畫野嶺梅花、畫世外三家村、畫蘆葦淡月、畫桃園幽會、畫柳堤飛鳥,畫孤舟泛浪……線條勾連,稍作點染,似不經心,卻自成奇韻;或因勢像形,借紋造意;或點線節制,質樸斂彩……她的畫有篆刻的疏密有致、有書法的疾徐流動,有郵票的方寸乾坤,有鼻煙壺畫的古典風雅。就像賈平凹從霍去病墓的石虎上看到了一種不事雕琢的自然氣韻,儉省而讓其通靈是藝術的最深秘密,想來李小洛也是深諳這個秘密的。”
有人說:李小洛的詩歌永遠值得期待,因為總是能夠帶給你意想不到的震撼和驚喜。她的繪畫也一樣值得人期待。那是一個詩人把她對故鄉天地江河之愛,對神性的仰望、以及對美的幻想和膜拜都收攝在一個個小小的充滿靈性石頭上……
水在石上走,畫在石上留。自然之美,田園詩畫,在一個女詩人這裡得到了很好的詮釋。李小洛的漢江石頭畫也或將打開一條開發陝南文化旅遊產品成功之路,目前已有多家投資商十分看好,並意欲合作開發。巧奪天工如詩如畫的漢江石也將走到更高更遠。一切都在期待中。(璽爾)
圖冊
 李小洛漢江石頭畫
李小洛漢江石頭畫 李小洛畫冊
李小洛畫冊![李小洛[陝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 李小洛[陝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img/8/ae5/nBnauM3XwIDN4YzMwATO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kzL1Y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