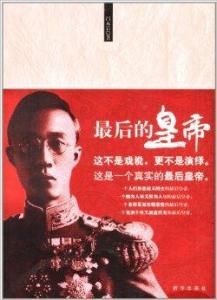內容介紹
《最後的皇帝》由呂永岩所著,是末代皇帝溥儀的傳記,《最後的皇帝》共十章:王朝落日、紫禁黃昏、津門風雨、故里雲翳、新京陰霾、華夏雷電、後宮殘照、末路霜雪、煉獄暖流、春意秋終。作者對偽滿洲國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相關歷史資料。通過對溥儀出生到落土的幾十年歷史的解讀,記述了溥儀一生中的重大轉折和曲折經歷。書中收錄300餘張歷史珍貴照片,圖文並茂的向讀者展現了一個人們熟悉而又陌生、看似荒誕實則悲愴、充滿個性又涵蓋歷史的真實的最後皇帝。以全新的視角向人們講述了溥儀到底是怎樣一個末代皇帝?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目錄
第一章王朝落日
畢竟一始一終
並不逢時的出生
肥水不流外人田
人性的弱點
仿佛一句讖語
“官可價得,政可賄成”
臭襪子政治
最具後患的國家政權關係形式
王立於沼上
對蛐蛐、蚯蚓發生了興趣
箭在弦上
一把鼻涕一把淚
生就是個庸才
致命的反覆試錯
末日王朝的一次和平演變
歷史的合力
第二章紫禁黃昏
總統與皇帝“和平共處”
最腐朽的制度
講了不少鬼故事
想當把皇帝
袁世凱的三次背叛
民國內部的國中之國
請位洋人做老師
溥儀眼裡的英雄
過早的“飽和效應”
一下子要兩個
沒能熱烈起來
孤芳自賞的婉容
逃出紫禁城計畫
出了一場大麻煩
辦法就是“忘”
太監作為“侍爺”……
更大的危險
皇后成了警衛
北京人大開了眼界
太妃們使用了眼淚
時機還不成熟
並不寧靜的夜晚
第三章津門風雨
選擇的是列強
還是很害怕
截然對立的兩派
跟隨的是日本保鏢
陶醉在鼻涕、眼淚里
死亡的槍口
國破山河在
日本手裡的一張牌
顛復活動的專家
黃鼠狼給雞拜年
心驚肉跳的事件
過於亢進的女人
徹底“了解”了一下
反對的呼聲並非沒有
只剩下一個婉容
不是豺狼的悲劇
第四章故里雲翳
入關與出關
像木偶一樣被耍了
日本眼中的肥肉
豺狗爭食一般的混亂
冬日裡的海水
隨時隨地的窩裡鬥
看到了自己的分量
一時的恐慌與強硬
表面的過場
又一次採取了妥協
板垣也在走鋼絲繩
醜陋的政治
第五章新京陰霾
覺得大有希望
“總務廳中心主義”
“研究研究”
龐大的移民方案
無條件保持一致
暗暗慶幸自己
熱臉貼霸權的冷屁股
第三次當皇帝
沒有真正去做
把他一腳踢開
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一張陰謀的網
怦然心動的美麗
一次秘密的會面
別的一種妙處
把墳墓都掘好了
冷清得出人意料
總是那么噯昧朦朧
排山倒海般的溫馨
一件事情的兩個極端
第六章華夏雷電
宣判了死刑
唯一能夠依賴的
既不同心,也不同德
瘋狂的掠奪
聽不到真訊息
一座人間地獄
皇帝的一大發明
自己的新祖宗
掛羊頭賣狗肉
引禍水澆了自己
唯欲征服支那……
東方的“馬奇諾防線”
考慮更多的是……
……
第七章後宮殘照
第八章末路霜雪
第九章煉獄暖流
第十章春意秋終
後記
參考書目
作者簡介
呂永岩,筆名為嚴文、山石。1989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歷任《戰士報》見習編輯、軍宣傳處新聞幹事、瀋陽軍區政治部前進報社編輯、瀋陽軍區創作室專業作家,專業技術四級,文職級別三級。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1的加中國作家協會。曾任瀋陽軍區《前進報》編輯、解放軍藝術學院作家班學員、陸軍某師副政委(代)。現享受正軍職工資待遇。著有中篇小說《白風峪》、《光環》、《中考大戰》,短篇小說《藍色的飛花》,評論《“空白”的魅力》,中短篇小說集《曝光的天使》、《絕對士兵》、《中國軍花在非洲》、《中國警官悲喜錄》、《最後的柔弱皇冠》、《霹靂》、《將軍志》、《雷鋒》,長篇歷史散文《獄中王朝》,中篇報告文學《驚濤托舉的永恆》等。
後記
說起來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電視台編導高國棟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已經花了上百萬元,正在拍一部關於溥儀的大型電視專題片。因為看過我此前出版的一部也是寫溥儀的長篇歷史散文《獄中王朝》,對我的敘述語言很感興趣,所以想請我擔任這部十集專題片的撰稿人。
對高國棟,我早聞其名,但未見其人。聞其名不僅是因為他創拍的電視專題片多次獲得過國際大獎,更因為我親自看過他拍攝的一些多集專題片,語言和畫面確實相當見功力,非一般人所能及,我很欽佩。沒想到高國棟這次竟然主動找上門來。我是部隊專業作家,寫作計畫經常安排得滿滿的,連寫自己更感興趣的小說的時間都沒有,但是高國棟的邀請我還是欣然接受了。後來高國棟又說,國內寫溥儀的專著他們幾乎都看遍了,從敘述語言上考慮,唯有我的比較對他們的胃口。中國有俞伯牙和鍾子期的故事。所謂知音難覓。能與高國棟合作搞一部大型電視專題片,也算一件快事。
這便是我第二次寫溥儀。
第一次寫溥儀出了一部書。第二次寫溥儀,中央電視台從2005年開始,在“探索發現”頻道和國際頻道連續播出十集。至於後來他們又先後播出過幾次,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偶爾有人會對我說,在央視上看到我撰稿的溥儀,我便知道央視又重播了。當然,專題片的容量是有限的。我真正寫溥儀的文字,要比專題片播出的多了很多。
於是便有了這部書。
溥儀的名字,對於中國人和相當一部分了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來說,似乎並不陌生。但解讀溥儀,那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一百個人會解讀出一百個溥儀。我解讀的溥儀當然與他人是有一些區別的,亦或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
溥儀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末代皇帝?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人們對他的真實或接近真實的一面到底了解有多少?
溥儀。滿姓:愛新覺羅。字:浩然。英文名:亨利。
1906年2月7日生於北府。
1908年12月2日正式繼位,年號宣統。
1911年9月10日始,受啟蒙教育。
1912年2月12日,下遜位詔。
1917年7月1日,張勛復辟,二次登極。當月13日退位。
1922年11月30日,冊封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文繡為淑妃。
1922年12月1日,舉行皇家婚禮,著立郭布羅氏榮源家的女兒婉容為皇后。
1924年11月5日,被逐出宮。
1925年2月23日,喬裝逃往天津。
1932年3月9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
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極,充當偽滿洲帝國“皇帝”。
1935年4月2日,第一次“訪日”。
1937年3月25日,冊封譚玉齡為“慶貴人”。
1940年6月22日,第二次“訪日”。
1942年8月15日,追封不明死因的譚玉齡為明賢貴妃。
1943年4月,李玉琴進宮,後被冊封為“福貴人”。
1945年8月11日,在“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監視下攜家眷“遷都”通化。
1945年8月18日,在通化大栗子溝舉行“退位”儀式。
1945年8月19日,在瀋陽機場被蘇軍俘虜,押往蘇聯。
1946年8月,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
1950年8月1日,被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9年12月4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同時獲得公民權。
1961年,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開始寫作《我的前半生》。
1962年5月1日,與李淑賢結婚。
1967年10月17日,病逝。終年61歲。
這當然不是全部的溥儀,甚至連溥儀的索引都不夠。
這裡有許多被人為地“將真事隱去”的歷史。這裡也有許多“留假語存言”的故事。這裡當然有宮闈秘聞,但這裡更多的是跌宕人生,是世態炎涼,是竹影斧聲,是啼血杜鵑。
中國人、外國人,幾乎所有對這一段歷史或者是對溥儀這個絕無僅有的末代皇帝感興趣的人,他們似乎都有一個問題一直縈繞在自己心頭。他們一直想破解這個問題,一直想解開這個謎。可是相當多的人失敗了。這失敗當然不是由於他們自身的原因,這失敗更是由於中國深層文化的原因。
中國古代曾有人對皇帝進行過分類,分類的結果他們是這樣表述的:
一等皇帝用師,
二等皇帝用士,
三等皇帝用隸。
“師”是指那些比皇帝高明的人,譬如諸葛亮。“士”是指那些與皇帝水平差不多的人,譬如商鞅。 “隸”是指那些什麼都不是,只會點頭哈腰、溜須拍馬的人。這樣的人在中國歷史上似乎多如牛毛。
古代的哲人認為,一個朝代,如果皇帝已經到了用“隸”的地步,那便是“危亡之像”了。 、
“師”、“士”、“隸”都有一個“用”字。“用”自然是皇帝用。就是說,用什麼人,這裡有學問。但怎樣去用,這裡仍然很有學問。
溥儀的一生用沒用過“師”呢?似乎用過,譬如莊士敦。溥儀用莊士敦,的確使他有了很大的進步。溥儀如果按莊士敦的主張,以一個學子的身份,出國去留學,學了本事再回國,那么,溥儀一生的歷史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種情形了。
問題在於莊士敦畢竟不是中國的諸葛亮。莊士敦考慮問題顯然有他特定的政治和民族的背景,並且還有很大的個人局限。莊士敦對中國文化有一定了解,有一定造詣,但這只能是一種皮毛。中國文化實在太博大精深了。尤其是那些滲入每個人骨髓的文化,那種依附於一種特定文化的習慣勢力,作為一個外籍人的莊士敦是很難完全領悟的。而且莊士敦還沒有認識到他所願意結交的日本人的叵測用心,而恰恰就是這一點,使溥儀一度成了一個叛國者。
鄭孝胥能算得上“士”嗎?似乎不夠。鄭孝胥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大一些的“隸”罷了。至於羅振玉,不但是“隸”,而且還是一個太多商人色彩的“隸”。
溥儀有沒有能夠用“師”或者是用“士”的機會呢?當然有。可是,當時那些能稱得上“師”或“士”的人,溥儀都沒有抓住,他們或者與溥儀天各一方,或者與溥儀擦肩而過,沒有一個能被溥儀所用。
並且就是身邊有限的那幾個並不算十分高明的人,甚至包括羅振玉這樣的“隸”,溥儀真正地用過嗎?
如果人們認真考究的話,就不難發現,與其說溥儀用了鄭孝胥或羅振玉,倒不如說是鄭孝胥、羅振玉等輩用了溥儀反而更準確。
內務府自然是用溥儀的,而且他們一直都在用溥儀。太妃們也在用溥儀,太監們也在用溥儀。還有一些政治流氓、軍閥、騙子,他們當然也不會放棄對溥儀的“用”。日本人更在用溥儀。他們用的方式可以說是絲毫不加掩飾,而且非常霸道。
於是,人們看到,溥儀無論是作為那個在登極大典上哭鬧的孩子,還是作為那個在紫禁城裡騎腳踏車,拿電話開玩笑的頑皮少年,還是作為面對火後廢墟的年輕“遜帝”,或者是在日本天皇裕仁面前手足無措的傀儡皇上,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被別人所用,而他自己從來沒有認真地用過別人,更沒有成功地用過別人。
這樣,當有人說他不過是一個歷史的註腳,或者說他是一個神奇的倖存者的時候,人們就不會感到意外了。他的確稱不上是一個皇上,他的確僅僅是一個歷史的影子,或者說是歷史的一根毫髮。據說人的毫髮包含了一個人所有的信息。那么溥儀似乎就是這樣一根包含了相當多的歷史信息的毫髮。
這個身體瘦長、眼睛近視、從小就被太監們的鬼故事嚇破了膽的令人絕望地心不在焉的溥儀,與他的那些大漠孤煙,盤馬彎弓,西北望,射天狼的粗獷的滿族祖先相比,實可謂天上人間。
據說,溥儀最崇拜的電影明星,就是無聲喜劇片中的演員兼導演哈洛德·勞埃德。這也是—個眼睛近視,並且笨拙得令人失望的傢伙。這難道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溥儀不是不想做事。當他決心整頓內務府的時候,當他義無反顧地對太監採取措施的時候,當他咬牙切齒地要對國民黨軍隊掘祖墳的行為進行報復的時候,人們似乎感覺到他要乾點什麼事兒了。他果然也在乾。可是他的乾法既不毛澤東,也不蔣介石,而且連張學良也不是。他乾來乾去,到頭來,不是把別人投入了那頗為隱蔽的陷阱,相反,當事情有了結局的時候,他才發現落入陷阱的總是他自己。
他一生經歷了許多跌宕。失去皇位,被逐,流亡,甚至成為階下囚。他似乎有許多客觀原因可以強調。可是,同是處於那個時代的人,有些人的處境似乎並不比他好,有的似乎比他還要遭很多,可是,許多人都成功了。溥儀沒有成功。等待溥儀的似乎一直都是失敗,失敗,再一次的失敗。
有人頗煞苦心地研究溥儀,研究他的前半生,又研究他的後半生。有人似乎有了驚人的發現,感到這樣一個皇上,居然實現了從帝王到公民的轉變,這可真是個奇蹟。可是,如果人們稍加留意,如果人們認真地把溥儀一生的行為進行一種剔除政治的、民族的或其他什麼的因素,而只做純粹行為的分類並分析,人們便不難發現,溥儀一生從來都沒有變。就像我們面對高天白雲下的一幢建築物,我們看到的變化是什麼呢?顯然不是那幢建築物,變動的只是高天和白雲。或陰或晴。或是薄雲,或是積雨雲。
溥儀似乎一生都沒做過自己的主人。他依賴哪個人,他就是局部的哪個人。依賴莊士敦,他就是局部的莊士敦。不是全部的莊士敦。依賴鄭孝胥,他就是局部的鄭孝胥。依賴羅振玉,他就是局部的羅振玉。依賴那個日本“御用掛”,他就是局部的“御用掛”。
對溥儀感興趣的西方學者當然注意到了溥儀的這種超強度的依賴人格。他們曾不止一次地試圖破譯這種依賴人格的深層次的起因,他們一直都想揭開這個謎。可是他們的努力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沒有人給他們提供他們想知道的那些事實。這是中國的一塊禁地,一塊令人諱莫如深的禁地。
“我在會見他的健在的朋友、親屬、以前的侍役和獄吏的過程中,吃驚地了解到很多溥儀的情況。他的某個方面總是被迴避掉:以後的中國雖然比過去寬鬆,但和西方的標準相比,中國仍然是一個驚人的清教主義國家。甚至今天,人們仍然很不願意談論自己或他人的感情生活。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跟像我這樣的陌生人談起他的性生活時,更是極為猶豫。
羞怯的程度,從溥儀時代最後倖存的太監的臉色上,得到最生動的反映。一位莽撞的法國記者大膽地問他,做一個太監是什麼滋味?“去勢”以後,他能否還能激起性慾?那位太監立即結束了會見,並表示再也不見新聞界的任何人了。
我也有類似的疑問,但從未得到過答案:在溥儀的一生中,他有過一位皇后、三位妃子和一位妻子。我在北京跟那些人談過,但我從未能弄清,溥儀跟她們的感情關係到了什麼程度。就他的第一個皇后伊莉莎白來說,他跟她的肉體接觸,似乎是一系列的“大失敗”。然而他跟第一個妃子的“友好關係”至少一開始不是那么悲慘,但她很快離他而去。他後來的妃子都是少女,在一個時期,他對年輕的小姑娘的吸引力近乎兒童的情趣。
當然,所有這些在溥儀自己和他的追隨者的日記中都有所暗示,這些都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自傳。好幾次,當我催促同溥儀一起生活過的、與他各方面合作過的、甚至多嘴的親密朋友,要他們多告訴我一點時,他們那種慎重的戒備,都令我非常惱火,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也很同情他們。有些人,在他們年輕時,也許作過溥儀臨時的、而且不太情願的同性戀夥伴。中國人的隱諱是如此之深,我知道我不能期待他們說什麼。”
這是英國作家愛德華·貝爾在他寫的《末代皇帝》中的一段話。“伊莉莎白”是皇后婉容的英文名字,同溥儀的“亨利”一樣,都是莊士敦給取的。這位一再抱怨中國人過於隱諱的英國人,很長時間是美國《新聞周刊》文化版的主筆。他當然意識到了溥儀在性方面的問題。他極力想了解這方面的問題,當然不僅僅是出於獵奇的目的。他是在為溥儀的依賴人格尋找更深層次的依據。
西方學者抱怨沒有找到的那些,現在人們似乎已經清楚了。的確,溥儀的依賴人格不僅有其環境和經歷上的原因,更有其生理上的原因。這個過早被宮女們“飽和”並且造成一定後果的人,他一生都沒能恢復那種真正陽剛意義上的攻擊性。他一直都使自己處在一種被動的、躲避的位置上。他躲避他的皇后,躲避他的妃子,更躲避那些政治上、軍事上看上去比他強大的人們。他似乎一直都沒能使自己真正地堅挺起來,無論是在生活的床上,還是在政治的龍椅上。他的一生不僅僅是作為皇帝的失敗,更是一種作為男人的失敗。或許正是由於作為男人的失敗,才導致了他作為皇帝的失敗。
於是,人們又看到了那些作為僕人身份出現的太監。人們不知道他們在對溥儀做那種手腳的時候,他們是怎么想的。人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想到了後來可能出現的那一系列後果。或許他們不會想到。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說,他們當時和過後的動機肯定都不是那么高尚的。他們似乎從來都沒有高尚過。作為一個人,他們的遭遇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作為參與政治的人,他們給一個皇上,給一個國家以至一個民族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甚至是禍害是顯而易見的。他們當然是一些“隸”。這種“隸”在中國政治史上似乎還不能說已經完全消亡了。
人們當然應該記住溥儀,歷史當然不會遺忘溥儀。溥儀當然是一部書,是一面鏡子,是一座奇異的迷宮,是一部紛紜的歷史。他似乎能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政治,關於文化,關於道德,關於人性,關於力必多……從這裡進入,人們似乎不僅僅看到了宮闈秘聞,看到了昨天。更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明天,看到了歷史、社會、人生的許多,許多……
作者
2011年10月於大夢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