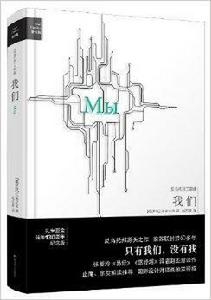作者簡介
作者:扎米亞金(1884—1937),俄羅斯白銀時代的重要作家,以風格獨具的民間口語敘述文體和幽默諷刺的筆墨馳譽文壇,被稱為“語言大師”、“新現實主義小說的一代宗師”。中學時以語文成績突出獲得獎章。1902年進入彼得堡工學院攻讀造船工程學,其間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兩次被流放。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國參與建造後來命名為“列寧號”的破冰船;十月革命後回到蘇聯,在彼得堡工學院任教,同時參與文學活動。後來因創作針砭蘇聯政府弊端的作品(主要是《我們》)而遭到封禁。1931年寫信給史達林請求出國,獲準出國。此後流亡歐洲,定居巴黎。1937年3月,因心絞痛病逝。主要作品有《外省小城》、《遙遠的地方》、《島民》、《我們》等。
譯者:趙丕慧(1964- ),輔仁大學英文碩士,現任教於台灣靜宜大學和朝陽科技大學。譯作有《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易經》《雷峰塔》《傷心咖啡館之歌》《絲之屋》《黑塔》《穿條紋衣的男孩》《不能說的名字》《珍愛人生》《我在怪怪島的日子》《哭泣的樹》《幻影書》《漂亮人生》等幾十種。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就是這種對極權主義的非理性一面——把人當作祭祀的犧牲,把殘忍作為目的本身,對一個賦有神的屬性的領袖的崇拜——的直覺掌握使得扎米亞金的書優於赫胥黎的書。
——《一九八四》作者 喬治·奧威爾
《我們》)哲學性可比柏拉圖之《理想國》,趣味性可比H.G.威爾斯之幻想作品,冷峻得像一把上膛左輪手槍,諷刺性直追《格列佛遊記》
——哈佛大學教授、社會學家 皮特里姆·索羅金
他(扎米亞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可置疑,而這地位多少是由其所發揮的特殊影響奠定的:在西方,扎米亞金啟發了一些與他同樣具有時代敏感性的作家,他們寫下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二十世紀之書”;在前蘇聯,扎米亞金與高爾基同為二十年代的文學導師,其門徒包括著名的“謝拉皮翁兄弟”作家群,就中左琴科、卡維林、費定等人的作品為我們素所熟悉。
——著名學者、書評人 止庵
我所創作過的最滑稽、最真切的一部作品。
——(俄)扎米亞金
名人推薦
他(扎米亞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可置疑,而這地位多少是由其所發揮的特殊影響奠定的:在西方,扎米亞金啟發了一些與他同樣具有時代敏感性的作家,他們寫下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二十世紀之書”:在前蘇聯,扎米亞金與高爾基同為二十年代的文學導師,其門徒包括著名的“謝拉皮翁兄弟”作家群,就中左琴科、卡維林、費定等人的作品為我們素所熟悉。
——著名學者、書評人 止庵
圖書目錄
焚書年代的文學珍品
札記一
札記二
札記三
札記四
札記五
札記六
札記七
札記八
札記九
札記十
札記十一
札記十二
札記十三
札記十四
札記十五
札記十六
札記十七
札記十八
札記十九
札記二十
札記二十一
札記二十二
札記二十三
札記二十四
札記二十五
札記二十六
札記二十七
札記二十八
札記二十九
札記三十
札記三十一
札記三十二
札記三十三
札記三十四
札記三十五
札記三十六
札記三十七
札記三十八
札記三十九
札記四十
大家讀
先知先覺的魅力
人需要高尚價值的想像
序言
焚書年代的文學珍品
——評扎米亞金的《我們》
喬治·奧威爾
在聽說了它的存在好幾年之後,我終於弄到了一本扎米亞金寫的《我們》,在這焚書的年代裡,這是文學珍品之一。我查閱了格萊勃·斯屈夫的《蘇俄文學二十五年》,找到了它的歷史如下:
一九三七年死於巴黎的扎米亞金是一位俄羅斯小說家和批評家,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後都出過幾部書。《我們》寫於一九二三年 ,雖然它寫的不是俄羅斯,而且同當代政治沒有直接關係——這是一部關於二十六世紀的幻想故事——但卻因意識形態上不宜的理由而遭拒絕出版。一份原稿被帶到了國外,該書便以英、法、捷克文譯本出版,但從來沒有用俄文出版。英譯本是在美國出版的,我一直沒有能夠買到一本。但是法文譯本是有的,我終於借到了一本。在我看來,這並不是一本第一流的書,但是它肯定是一本不同尋常的書,居然沒有一個英國出版商有足夠的魄力重新印行,真是令人奇怪。
關於此書,任何人會注意到的第一點是——我相信從來沒有人指出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有一部分一定是取材於此的。兩本書寫的都是人的純樸自然精神對一個理性化的、機械化的、無痛楚的世界的反叛,兩個故事都假定發生在六百年以後。兩本書的氣氛都相似,大致來說,描寫的社會是同一種社會,儘管赫胥黎的書所表現的政治意識少一些,而受最近生物學和心理學理論的影響多一些。
在扎米亞金筆下的二十六世紀裡,烏托邦里的居民已完全喪失了他們的個性,以致只以號碼相稱。他們生活在玻璃房子裡(這是寫在電視發明之前),使得名叫“觀護人”的政治警察可以更加容易地監視他們。他們都身穿同樣的制服,說起一個人來不說是“一個人”,而說是“號民”或者“淺藍色制服”。他們吃人造食物。他們的文體活動是跟著大喇叭播放的“一體國”國歌四人一組開步走。在規定的時間裡他們可以在玻璃住房四面拉下帷幕一小時(叫作“性交日”)。當然,沒有婚姻,儘管性生活看來並不是完全亂交的。為了做愛用,每人都發一本粉紅色的配給券。每人份內有六個“性交日”,一起度過一個小時的對象須在票根上籤字。一體國是由一個叫“造福者”的人統治的,由全體號民每年重選一次,投票總是一致通過的。國家的指導原則是幸福與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園裡,人本來是幸福的,但他愚蠢地要求自由,便被逐到荒野中去。如今一體國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復了他的幸福。
到此為止,與《美麗新世界》的相似之處是很觸目的。但是,儘管扎米亞金的書寫得並不怎么緊湊——它的鬆散和零碎的情節過於複雜,不易扼要介紹——但它的政治意義是另一部書中所沒有的。在赫胥黎的書里,“人的本性”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解決,因為它假定,用產前處理、服用藥物和催眠提示,人的機體是可以按任何要求方式予以專門改造的。可以像製造傻子一樣容易地製造出第一流的科學工作者來,不論在前者還是後者身上,原始本能的殘餘,如母性感情或者自由欲望都是很容易對付的。同時,書中沒有提出明白的理由說明為什麼要把社會做它所描寫的那樣細緻的分層。目的不是經濟剝削,但動機似乎也不是威嚇和支配的欲望。沒有權力欲,沒有虐待狂,沒有任何種類的鐵石心腸。在上層的人並沒有留在頂層的強烈動機,儘管大家都是傻乎乎的快活的,生活卻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使人很難相信這樣一種社會是能夠維持下去的。
扎米亞金的書,總的來說,同我們自己的處境更加有關。儘管有所受的教育和觀護人的警惕性,許多古代人類的本能仍舊存在。故事的敘述者D-503號雖然是個有才能的工程師,卻是個可憐的世俗人物,一種烏托邦里的倫敦城的比萊·布朗,經常因為身上的返祖衝動而感到害怕。他愛上了(當然,這是一樁罪行)某個I-330號,她是個地下抵抗運動的成員,一度成功地引導他參加了反叛。反叛爆發時,造福者的敵人們數目居然不少,這些人除了策劃推翻國家以外,在他們拉下帷幕以後甚至耽溺於吸菸喝酒這樣邪惡的事。D-503最後獲救,倖免於他自身錯誤帶來的後果。當局宣布,他們發現了最近動亂的原因:那是有些人患了一種叫作想像的疾病。製造想像的神經中心如今給找到了,這疾病可以用X光照射來治癒。D-503接受了治療,治療後他很容易做他一直知道該做的事——那就是把他的同黨出賣給警察。他面不改色,心平氣和地看著I-330關在一隻瓦斯鐘下受壓縮空氣的酷刑:
她注視著我,用力抓緊椅子扶手——一直到她的眼睛閉上為止。之後她被拖了出去,用電擊讓她恢復了意識,再一次被帶到瓦斯鐘下。前後一共重複了三次——可是她仍舊是一聲不吭。其他跟這個女人一塊被帶進來的人就比較誠實:有許多在第一次之後就招供了。明天他們全部都要登上階梯接受造福者的機器制裁。
造福者的機器就是斷頭台。在扎米亞金的烏托邦里有許多次處決。這都是公開舉行的,由造福者親自出席,並有御用詩人朗誦勝利頌詩作為配合。斷頭台當然不是那種老式的粗糙工具,而是一種大為改進的模型,名副其實地“消滅”了它的刀下鬼,在一剎那之間,把她化為一陣輕煙,一攤清水。這種處決實際上是以人為犧牲的奠祭,書中描寫的場面有意給添上了遠古世界陰慘的奴隸文明的色彩。就是這種對極權主義的非理性一面——把人當作祭祀的犧牲,把殘忍作為目的本身,對一個賦有神的屬性的領袖的崇拜——的直覺掌握使得扎米亞金的書優於赫胥黎的書。
很容易看出為什麼這本書的出版遭到拒絕。D-503和I-330之間的下述對話(我稍加刪節)足以使檢察官的藍鉛筆啟動起來:
“你難道不知道你是在計畫革命?”
“對,就是革命!這有什麼荒唐的?”
“因為根本就不可能有革命。我們的革命是最後一場革命,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革命。大家都知道……”
“親愛的——你是數學家。既然這樣,把最後的數告訴我吧!”
“你在說什麼啊?我……我不懂你的意思,什麼最後的數?”
“唉,最後的,終極的,最大的。”
“簡直是胡鬧!數是無限大的,哪裡來的什麼最後的數呢?”
“既然這樣,又哪裡來的什麼最後的革命呢?”
還有其他類似的段落。不過,很可能是,扎米亞金並不想把蘇維埃政權當作他諷刺的專門對象。在列寧死去的時候寫這本書,他不可能已經想到了史達林的獨裁,而且一九二三 年時俄國的情況還沒有到有人會因為生活太安全和太舒服而反叛的程度。扎米亞金的目標似乎不是某個具體國家,而是以工業文明作為隱含目標的。我沒有讀過他其他的書,但我從格萊勃·斯屈夫那裡了解到,他曾在英國待過幾年,曾對英國生活寫過一些辛辣的諷刺文章。從《我們》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尚古主義有一種強烈的傾向性。他在一九○六年遭到沙皇政府的監禁,一九二二年又遭布爾什維克的監禁,關在同一監獄的同一過道的牢房裡。因此他有理由不喜歡他所生活的政治體制,但是他的書並不是簡單地表達一種不滿。它實際上是對“機器”的研究,所謂“機器”就是人類隨便輕率地把它放出了瓶子又無法把它放回去的那個妖魔。英文版出來時,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書。
董樂山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