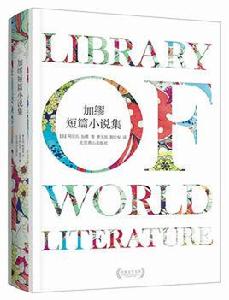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早年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後從事戲劇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法國抵抗運動。二戰後,積極投入到文學創作中。1960年,加繆自普羅旺斯去巴黎途中遭遇車禍去世,年僅47歲。
加繆是“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存在主義文學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品有《誤會》《卡利古拉》《戒嚴》《正義》《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神話》等。
內容簡介
《局外人》通過兩個部分,塑造了默爾索這個行為驚世駭俗、言談離經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小說第一部分接二連三發生的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對話、姿勢和感覺,卻變成第二部分司法機構致默爾索於死地的決定性呈堂證因。《局外人》充分揭示了這個世界的荒謬性及人與社會的對立狀況。默爾索的種種行為看似荒謬,不近人情,實則正是他用來抗擊這個荒謬世界的武器 。 《墮落》主人公克拉芒斯是一位試圖把法官和懺悔者融為一體的律師,在一家叫“墨西哥城”的酒吧間裡,他滔滔不絕地講述著自己的經歷。他的對話者很奇特。從他的口氣中,我們可以推測他在與人對話,然而,卻聽不見他的聲音,這是一位既在場又隱蔽的對話者。他自認在道德上有罪,卻依然試圖保持高高在上的審判姿態,在負罪感和驕傲造成的困境中苦苦掙扎,找不到出路。 《流放與王國》包括六個短篇:《偷情的女人》《叛逆者》《緘默的人》《來客》《約拿斯》和《生長的石頭》。主題只有一個,即流放,但作者卻運用了六種小說技巧處理了六種流放的方式。《流放與王國》並不是人們通常習見的那種匯集——若干不相連屬的作品的小說集,而是一個有聯繫、有不同側面的整體。加繆所採用的不同的小說技巧都是為這個整體服務的,並在其不同的表現形式上各有側重,有時又有交替重合。
媒體評論
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安德烈·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以外,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他死於1960年,他的死讓整個文學界感到是一種個人損失。 ——美國圖書獎獲得者 蘇珊·桑塔格
他(加繆)在本世紀(20世紀)頂住了歷史潮流,獨自繼承著源遠流長的醒世文學,他懷著頑強、嚴格、純潔、肅穆、熱情的人道主義,向當今時代的種種粗俗醜陋發起了勝負難卜的宣戰。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薩特
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
目錄
目錄
序
局外人
第一部
第二部
墮落
流放與王國
偷情的女人
叛逆者
緘默的人
來客
約拿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家
生長的石頭
前言
序
在二十世紀的著名小說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與某種“新技巧”“新手法”或“新觀念”聯繫在一起的,例如,普魯斯特與意識流、卡夫卡與荒誕、赫胥黎與對位、福克納與時空倒錯、薩洛特與潛對話、西蒙與新小說、馬爾克斯與魔幻、海勒與黑色幽默,等等。還有一些人的名字並無此類顯赫的聯繫,但是這絲毫也不曾妨礙人們將其視為傑出的小說家,例如加繆。
當然,加繆也有“荒誕”,然而創始者的光榮不屬於他;他也有“懷疑”,但其淵源更為久遠;他也曾被人歸入海明威一派,但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證明他們之間的聯繫;他也曾被人拉入新小說家一夥,但是他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榮耀。其實,他從未想過發明什麼,他也的確不曾發明什麼,他只是不趨時,不媚俗,不以艱深文淺陋。在某些批評家看來,與二十世紀所崇尚的“晦澀”“繁複”相比,“簡潔、明晰、純淨”的加繆簡直就是“沒有什麼藝術性”。
然而加繆畢竟是有藝術性的,假使所謂“藝術性”不等於雕琢、華麗、標新立異或追逐時髦之類。加繆的藝術性在於“有度”。
“風格乃是人本身”
加繆是二十世紀少有的自覺追求風格的作家。
說到風格,布封的名言盡人皆知,然其恆遭曲解卻是知者寥寥。錢鍾書先生曾指出:“吾國論者言及‘文如其人’,輒引Buffon語(Le style,c’est l’homme)為比附,亦不免耳食途說。Buffon初無是意,其Discours僅謂學問乃身外物(hors de l’homme),遣詞成章,爐錘各具,則本諸其人(\[de\]l’homme même)。‘文如其人’,乃讀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諸人’,乃作者本諸已以成文。”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考布封初衷,確謂知識、事實、發現等皆身外物,唯風格乃是人本身(Ces choses sont hors de l’hemme 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因此,風格乃是作者在其思想的表達上打上自己的印記,故“風格不會消失,不會轉移,也不會變質”。布封,《論風格》。簡言之,文以風格傳世,而風格則以人為本。
加繆所追求的風格正是布封所論述的風格,然而又不止於此,他對“文本諸人”(即“風格乃是人本身”)之“人”做了深入的探索和全新的解釋。他指出:“藝術家對取之於現實的因素重新進行分配,並且通過言語手段,做出了修正,這種修正就叫作風格,它使再創造的世界具有統一性和一定限度。”加繆,《反抗者》。所謂“修正”,就是藝術家根據人的內在的願望對現實世界的一種“糾正”,其表現之一就是藝術家所運用的小說這種文學樣式。而人的內在願望則是反抗世界的荒誕和尋求現時的幸福。因此,“這種修正是一切反抗者都具有的”。加繆,《反抗者》。這樣,加繆就把風格和反抗聯繫了起來,使之擺脫了純形式的品格,浸透了人的天然的深刻要求。布封的名言在加繆的筆下,獲得了更深厚的現實基礎,同時也獲得了更超絕的哲學層次。
加繆追求一種“高貴的風格”,一種蘊含著人的尊嚴和驕傲的風格。他指出:“最高貴的藝術風格就在於表現最大程度的反抗。”加繆,《反抗者》。這種高貴的風格並不是純粹形式的,倘若因一味講究風格而損害了真實,則高貴的風格將不復存在。同時,“高貴的風格就是不露痕跡,血肉豐滿的風格化”,加繆,《反抗者》。而風格化是既要求真實又要求適當的形式的。據此,加繆所謂“高貴的風格”可以歸結為互為依存的三種要素:一,給予最大程度的反抗以適當的形式;二,通過糾正現實而獲得真實;三,適度而含蓄的風格化。加繆不是那種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種單純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終要求內容與形式“保持經常不斷的緊密聯繫”。無論是內容溢出形式,還是形式淹沒內容,在他看來都會破壞藝術所創造的世界的統一性。而藝術,恰恰是“一種要把一切納入某種形式的難以實現的苛求”。加繆,《反抗者》。因此,加繆說:“工作和創作了二十年之後,我仍然認為我的作品尚未開始。”他一直把“真理和反映真理的藝術價值”看得高於一切。當然,加繆對於“真理”(或“真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曾經不止一次地申明,“現實主義是不可能的”。他反對資產階級現實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為前者是一種“黑暗的”文學,後者是一種“教誨的”文學,這兩種文學實際上都背離了真實。然而同時,他也不止一次地申明,“現實主義的抱負是合理的”。藝術不能“服從現實”,也不能“脫離現實”,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藝術是對世界中流逝和未完成的東西的一種反抗:它只是想要給予一種現實以另一種形式,而它又必須保持這種現實,因為這種現實是它的激動的源泉”。這種矛盾其實是一種表面的矛盾,其根源在於對現實主義這一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例如,他認為現實主義就是“準確複製現實”,就是“無止境地描寫事物”“無窮盡地列舉事物”,等等。而我們知道,現實主義完全可以有另一種定義。因此,以這種對現實主義的歧義或誤解來探討加繆對現實的態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們只須指出,加繆的小說絕不缺少現實的內容,恰恰相反,真實是他的小說的生命,只不過如他所說,他的小說同時“給現實加上某種東西,使現實稍有變化”,也就是:“小說的本質就在於永遠糾正現實世界。”無論是《局外人》對現實的承受,還是《墮落》對現實的逃避,都不曾離開人的現實,都是在人的世界中展示人對荒誕的覺醒和反抗。現實經過藝術家的“糾正”成為真實,而“糾正”就是風格化,它“包含了人的干預和藝術家在複製現實時進行糾正的意志”。加繆認為,“風格化最好是含而不露”,其本質在於“適度”。加繆的寫作藝術的根本在於“恰到好處”,甚至是寧不及而勿過。他在談及自己的寫作時,經常見諸筆端的是“限制”“堤壩”“秩序”“適度”“柵欄”等表示“不過分”的詞。例如,他說:“我知道我本性中的無政府主義,所以我需要在藝術上為自己樹起一道柵欄。”加繆答加布里埃爾·多巴萊德問。或者:“為了寫作,在表達上寧不及而勿過。總之是勿饒舌。”這種對於“度”的自覺,使加繆為文有一種挺拔瘦硬的風采。
總之,加繆是一位有風格的作家,其風格可以稱為“高貴的風格”。
《局外人》與“含混”
《局外人》一九四二年出版後,很快就得到薩特的好評。根據他的解釋,《局外人》是對“荒誕”的證明和對資產階級司法的諷刺。然而,後來的批評家紛紛越過了薩特的解釋,他們發現了《局外人》的“含混”。
現代批評家普遍認為,“含混”是文學作品的本質特徵之一。作家有意識地運用“含混”,讀者不固執地追求唯一的理解,則作品將變成一個含義深遠的多面體。加繆曾經寫道:“至少要為使沉默和創造都臻於極致而努力。”沉默不是虛無,而是富於蘊含的情狀,仿佛“此處無聲勝有聲”,創造當然也不是基於虛無的創造,而是打開沉默的硬殼。沉默與創造之間的橋樑將由“含混”來架設。《局外人》呈現出一種多層次、多側面的“含混”,其中沉默和創造都已臻於極致。
加繆自己談到《局外人》時說:“局外人描寫的是人裸露在荒誕面前。”他也曾這樣概括《局外人》:“在我們的社會裡凡在母親下葬時不哭者皆有被判處死刑之危險。”看來,薩特的評論與作家的自述相去不遠。但是,此後四十年間,局外人探索《局外人》的含義的努力一直沒有間斷。有的批評家從政治角度考察作者對阿拉伯人和法國殖民政策的態度,認為這部小說更應叫作《一個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而阿拉伯人被殺則表明法國人“對一種歷史負罪感的令人惶惑的供認”;有的批評家從精神分析的理論出發,把默爾索看作是現代的俄狄浦斯;還有的批評家把默爾索的經歷看作是一種想像的心理歷程,等等。這種主題的多義性來源於作者置於情節中的許多空白和人物行為的機械性。
人物行為的機械性很容易使淺嘗的讀者得出這樣的印象:默爾索是一個滿足於基本生理需要的人,他對外界的反應是直接的、感性的、機械的,他的推理能力低於常人,他是一個不好不壞的化外之人,是一個希望遠離社會而處於自然狀態的人。然而事情似乎不這么簡單。假使讀者仔細閱讀並且不放過作者似乎不經意的若干提示的話,他會發現默爾索並不是一個生活在世外桃源中的人。他受過高等教育,推理的能力顯然優於周圍的人,而且當他“在苦難之門上短促地叩了四下”之後,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他的寡言、他的冷漠,直到他的憤怒,原來都是他對環境的自覺的反應。他不想裝假,不想撒謊,不想言過其實,不想用社會的慣例來約束自己的言行。他是個“局外人”,然而何謂“局內”?何謂“局外”?這內與外以何為參照?批評家們曾經把他看作自然人、野蠻人、荒誕的人、精神低能的人,或者是理性的人、清醒的人、現代的人,等等。就每一種人來說,默爾索作為小說人物都是清晰的,然而就總體來說,這位小說主人公卻又是含混的。不同的批評家都有充分的證據勾畫出一個活生生的默爾索來。因此,默爾索的面目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這中間的矛盾正說明這一文學形象的豐富性。
這種蘊含豐富的矛盾不難表現在人物性格上,小說的敘述角度更使批評家感到既惶惑又興奮。他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究竟誰在說話?是默爾索還是作者?如果是默爾索,那么他在何時何地說話?如果是作者,那么他是同情還是譴責默爾索?或者,作者與默爾索合一還是與敘述者合一?這些問題使《局外人》這部小說表面上極為清晰的語言變得模糊而含混。
小說的開始是這樣一段話:“媽媽今天死了。”小說的結尾,則是默爾索在獄中等待著處決的“那一天”,也許是第二天,也許是數日以後。小說從開始到結束,粗粗算起來,至少有一年多的時間。矛盾就出現在這裡。如果確認是“今天”說的話,此後的事情皆屬想像;如果確認默爾索是在臨刑的前夜回憶往事,那就不能說“媽媽今天死了”一類的話。於是有的批評家根據小說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文體的區別,認為第一部乃是日記,第二部才是完整的邏輯的敘述。也就是說,捕前的經歷是逐日記載的,事件既無動機,彼此間也沒有聯繫,直到“我”殺了人,才突然意識到開了“苦難之門”。捕後的經歷則不同,“我”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所述之事井然有序,推理過程也十分清晰。然而,這僅僅是對小說的時序顛倒的一種解釋,批評家們還有其他多種解釋,例如有的論者以為默爾索的獨白乃是一種“偽獨白”,不可以正常的邏輯繩之;有的論者認為說話的並不是默爾索,而是某個自稱“我”的人在講述一個叫默爾索的人的故事;還有的論者認為,作者要使讀者有親睹親歷之感,於是扭曲時序而在所不惜,等等。無論如何,這種時序的扭曲使這部小說呈現出一種言簡意深的風貌,仿佛冰山,所露甚小,所藏卻極大。
《局外人》中具有象徵意義的形象也是含混的,具有兩重性,例如太陽。太陽這一形象如同大海、土地、鮮花等,在加繆的作品中象徵著生命和幸福,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財富,取之不費分文。總之,太陽是一種善的象徵。然而在《局外人》中,太陽的象徵意義卻非此一端。的確,太陽依然是美的、善的,當“滿眼無際的天空,蔚藍而金光燦爛”的時候,它可以讓人感到舒適;它也可以把女友的臉“曬成一朵花”,讓默爾索看著喜歡;它也可以適度的炎熱,讓游泳的人“只顧享受曬著陽光有多么舒服”。然而太陽有它的反面,不是陰影,而是超過了某種限度。它可以使“天空藍得晃眼”,把默爾索弄得“昏昏沉沉”;它可以是“火辣辣的”,曬得土地“直打戰”,既冷酷無情,又令人疲憊不堪;由於陽光過分地強烈,人“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渾身冒汗,進了教堂又會著涼”,真是進退兩難,沒有“出路”;它也可以像“灼熱的利劍”,讓人覺得剎那間“天穹萬物都搖晃起來”;正是在這個時候,“海洋呼出一股厚重而滾燙的氣息”,默爾索抵抗不了這氣息的力量,他失去了平衡,他也用槍聲“打破了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灘異乎尋常的寂靜”。於是,“一切都開始了”,開始的首先是“苦難”,其根源正是默爾索酷愛的太陽,那使他感到幸福的太陽。
此外,默爾索被捕前後呈現出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特點恰恰是含混和表里不一。捕前,默爾索作為一名小職員生活在流水般的日常世界,他周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各自的工作。他們的忙碌和煩惱,他們的很少變化的單調生活,他們的許多毫無意義的言談,無論如何總是構成了一個活躍的、真實的人的世界。人們有小小的痛苦,也有小小的幸福,至少有感官的愉悅。捕後,默爾索卻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那裡的人只有職務而沒有名姓,例如預審推事、檢察官、律師、記者、神甫等,這些人似乎並不是作為人而存在,他們是某種職務的代表,他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扮演某種角色。這個表面上有條理、合乎邏輯的世界實際上是虛假的、做作的,是一個非人的世界。這時的默爾索是個有邏輯的人,卻又同時是個置身局外的人。
總之,上述種種含混,即主題、人物、象徵、敘述方式和小說世界諸方面的含混,使《局外人》成為一個撲朔迷離、難以把握的整體,似乎有不可窮盡的意義,給各種歷史條件下的讀者都帶來了探索的樂趣。
《局外人》曾經被認為是清晰的、簡潔的、透明的,是現代古典主義的典範,然而它的有意的單調、枯燥和冷靜卻打破了這種直接的印象,隨著閱讀的深入而逐漸剝露出深刻而複雜的內涵,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含混作為藝術手段所具有的功能。
可以說,《局外人》的藝術集中地體現為含混。
《墮落》與象徵
加繆似乎對文類有著特殊的敏感,《局外人》被稱為“小說”,《鼠疫》不稱小說而稱“記事”,《墮落》也不稱小說,它被稱為“敘述”。法國批評家讓-約瑟·馬爾尚參照紀德的說法,對“敘述”和“小說”的區別做了如下的界定:“敘述依照陳述的規則再現事件,小說則依事件本身的順序向我們展示這些事件。我們可以藉助於這種說法大致將純小說和純敘述區分開來;小說正在發生,敘述已然發生;小說逐漸地向我們提供一種性格,敘述則解釋之;小說眼看著事件發生,敘述則使人認識之;小說是由活躍的下文組成的,敘述則由原因組成;小說展開於現時,敘述則闡明過去。這些看法的第一個後果是,如果主人公是人,敘述更注重研究一種危機(它並加以解釋),小說則沒有非此不可的主題,其主人公總是人。薩特認為紀德完全有理由指出:小說是‘一種不斷的湧現,每一章都應提出新問題,都應是出口,是方向,是激勵,是讀者的精神的一段向前延伸的堤’。”簡言之,小說偏於呈現,敘述偏於解釋。但是文學的事實證明,小說與敘述之間的區別並不是絕對的,有時甚至並不是清晰的。《墮落》名為敘述,說明加繆有解釋的意圖,他要讓讀者理解什麼事情;但是《墮落》也有不少小說的因素,如人物的心理分析、環境描寫等。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墮落》的小說因素通過象徵的運用而融進了敘述,並使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複雜的象徵。
與《局外人》和《鼠疫》相比,《墮落》呈現出一種令熟悉加繆的讀者感到驚訝的新面目:一種加繆從未有過的尖刻與痛苦交織的嘲諷的口吻,一種心靈受過創傷的、遏制不住報復心理的人的怨毒的口吻。然而,加繆對語言的苛求和對人性的挖掘卻一仍其舊,並且由於廣泛地運用象徵而在《墮落》中強化了《局外人》所具有的含混和《鼠疫》所具有的神話意識,並且因此而使《墮落》擺脫了因糾纏個人恩怨而可能產生的偏頗。象徵使《墮落》避免了狹隘性,獲得了普遍性。
地域作為象徵,在《墮落》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加繆是一位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作家,其創作基本上以北非為背景,陽光和大海是他最喜歡的地域景觀,幾乎成為他的作品主題的永久的伴隨物。但是,《墮落》的背景卻是荷蘭,這個“黃金和煙霧的夢”一樣的地方,“被霧、冰冷的土地以及像洗衣盆一樣冒著氣的大海包圍著”的國度;是瑪爾肯島,這個“了無生氣的地獄”;是阿姆斯特丹,它那“同心的運河好像地獄之圈”,而且是“最後一圈”,但丁留給叛徒的那一圈。這正是北非的明媚的陽光和清涼的大海的反面,是“否定之景”。在加繆的筆下,這種令人感到壓抑和窒息的景觀正是現代世界的象徵。與之相對,加繆沒有忘記還有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是爪哇,“遙遠的島嶼”,“在那些島嶼上,人們死的時候瘋狂而幸福”;那是希臘,“那兒的空氣是貞潔的,大海和娛樂是明朗的”;那是“太陽,海灘,信風吹拂的島嶼,回憶為之絕望的青春”。這種種美好的所在象徵著人們的追求和嚮往。兩種地域的對立為《墮落》提供了總體的框架,展示出人類的生存環境:苦難是他每日的伴侶,幸福只存在於懷念和嚮往之中。
《墮落》中的象徵又以具體的形象為載體,有時取自《聖經》或傳說,如“鴿子”之類,有時則取自與人物的命運休戚相關的日常景物,如橋、水,等等。前者意境幽邃,發人深省,後者則自然生動,並且饒有諷刺意味,例如橋。克拉芒斯第一次失去心理平衡是因為在塞納河上的藝術大橋上聽見身後升起一陣“笑聲”,後來又回憶起兩年前曾在塞納河上的王家大橋上見死不救。兩件事都發生在橋上,他因此而發誓夜裡永不過橋。橋在這裡成為某種自覺意識的觸媒劑。有趣的是,克拉芒斯逃離巴黎,選擇了阿姆斯特丹作為隱居地,然而阿姆斯特丹卻是個運河之城,擁有一千一百座大大小小的橋。一個人除非不動,動則必須過橋。克拉芒斯躲開了兩座橋,卻陷入更多的橋的包圍之中。他縱使可以永世不再過橋,卻斷然不能不談到橋、不想到橋,橋於是而成為一種頑念,時時壓迫著他、折磨著他,使他談橋色變而不能不處於永恆的自責之中。橋之為象徵,明矣。有橋則有水,神秘的笑聲與溺水的女人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克拉芒斯既已陷入橋的重重包圍之中,就必然要受到流水的無休止的追逐。果然,我們聽到了他的惴惴不安的告白:“幾年前,在我背後,在塞納河上迴響著的喊聲,被河水帶著奔向海峽,不斷地在世界上前進,越過大洋無邊的水面,正在這兒等著我,直到這一天我碰到它。我也明白了,它將繼續在所有的海上、河上等著我,總之在我苦澀的洗禮水所在的任何一處等著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負罪之人逃脫不了懲罰,而懲罰總能等到負罪之人自投羅網。水之為象徵,亦明矣。
精神的錯覺或幻覺如果成為象徵,可以具有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牌的作用,一倒俱倒,連鎖反應。例如克拉芒斯某夜在藝術大橋上聽到的那一陣“背後的笑聲”。這笑聲先是從水裡發出,繼而又在他身體的某處響起,這當然 不是某個具體的人實際存在的笑聲,只不過是克拉芒斯的雙重人格得以暴露的某種契機而已。加繆論荒誕時說:“一切偉大的行動和一切偉大的思想都有一個可笑的開端。偉大的作品常常誕生在一條街的拐角或一家飯館的小門廳里。荒誕也如此。”我們說:覺醒也如此。那種笑聲可能隨時隨地都存在,只是人們往往不注意、聽不見罷了,正如克拉芒斯所說:“這聲音沒有任何神秘之處,這是一種善意的、自然的、幾乎是友好的笑聲……”然而,正當一個人感到滿足、精神放鬆戒備的時候,這笑聲就能乘虛而入,或從外面某個地方冒出,或在自己身上某個地方響起,實際上,這是精神感到的笑聲,並不是耳朵聽到的笑聲。波德萊爾指出,“在人來說,笑是意識到他自己的優越的產物”,“是包含在象徵蘋果中的許多籽仁之一”。克拉芒斯聽見了笑聲,這意味著他已失去了優越,成為別人訕笑的對象。這笑聲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威力足以摧毀一個人的自信,或者撕去一個人的假面。
人物行為的象徵性是《墮落》的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舉凡克拉芒斯的樂善好施、攀登高峰、喜歡島嶼、試圖中止審判、當法官、懺悔者、隱匿《神秘的羔羊》,等等,都具有可以向多方面延伸的象徵意義。尤其是克拉芒斯的對話,更具獨特的風采。這是一篇對話,但對話者並無緣置喙,只剩下克拉芒斯一個人喋喋不休,然而又並非一篇獨白,克拉芒斯想盡一切手段誘使那不出聲的對話者落入圈套,讀者因此感到分明有一對話者在。主人公與一個無言的對話者對話,這種手法早已見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但加繆別出心裁,令對話者於篇末暴露身份,原來也是一位巴黎的律師,與克拉芒斯同操“這一美妙的職業”。有的論者認為,所謂對話其實並不存在,是克拉芒斯在顧影自言。準此,叫克拉芒斯的“虛假對話”立刻顯出其象徵性:克拉芒斯在努力解脫自身的夢魘,並在其失敗中顯露出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當代英雄”——的墮落。他原本希望對方是警察,或可將他逮捕乃至斬首,以便結束“在荒漠中呼喊而拒絕走出去的偽預言家的生涯”。他失敗了,他還將繼續充當那什麼也不能預言的偽預言家的角色。克拉芒斯的“虛假對話”象徵著某種結束墮落狀態的徒勞無功的努力。
《墮落》的象徵,可以被看作是當代人類世界的某種總體象徵。
《流放與王國》與技巧作為工具
加繆在為短篇小說集《流放與王國》寫的一則出版說明中指出:“這個集子包括六個短篇:《偷情的女人》《叛逆者》《緘默的人》《來客》《約拿斯》和《生長的石頭》。不過主題只有一個,即流放,然而處理的方式卻有六種,從內心獨白到現實主義的敘述。”這裡,他實際上是說,他運用了六種小說技巧處理了六種流放的方式。
“偷情的女人”雅尼娜在一次不情願的旅行中,偶然地發現遊牧民族的生活具有一種粗獷自由的美,與自己的平庸猥瑣的市民生活相比,一個是“王國”,一個是“流放”,形同霄壤。她於是有所悟,深夜中隻身遁入曠野,讓“整個天宇在她的身上展開”,與大自然達成神秘而短暫的默契。這是一種奇特的“不貞”。加繆運用了嚴格遵守時序的敘述,以眾多而真實的細節——景物以及過去極少見的有關人的形貌的描寫——為支撐,從容不迫地漸次透露出種種信息,使讀者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他又不失時機地推出富有象徵意味的形象或動作,使高潮出現之前布滿“富於包孕的時刻”,例如,“雅尼娜立時感到,一種洪亮而短促的音律,響徹整個天宇,回聲漸漸瀰漫她頭頂的空間,接著戛然而止,丟下她默然面對無邊的空曠。”我們可以想像,在這“默然”之中,雅尼娜已打定了主意。她此時已鑄成了自己的“不貞”,那星夜曠野中的一幕實際上成為弦上之箭,只是待時而發罷了。雅尼娜的故事是個極平凡的故事,加繆寫來極有感情,卻又出之以極冷靜的筆觸,反差中呈現出一種“令人不能自持”的神秘美,有寓言的風致。
《叛逆者》中,讀者所見唯有一片光怪陸離的意識的流動,通篇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的無聲的獨白,只最後一句是客觀的描述,如天外飛來,除了點明這奴隸殺了傳教士之後仍舊是個奴隸之外,又留下一個難解的疑團。這是一個改宗者的故事,他不願徘徊在善與惡之間,他懷著揚善的目的來到崇拜惡的地方。他的善不敵異邦的惡,他於是叛教而投入新主人的懷抱。然而,他又面臨著再次改宗的屈辱。他沒有被殺死,沒有成為殉教者的幸運,他始終是個奴隸,他被割去舌頭,失去了語言的能力,但他頭腦中又生出另一個“舌頭”,他還有意識能夠流動。外部的事件,內心的活動,在一系列熱得燙人的形象中交織成閃爍的一片,暴露出一個傾向於極端思想的人的可怕的精神世界。這篇小說結構嚴謹,於混亂中見出秩序,頗能表現出“一個精神錯亂的人”的情狀。其實他們精神並沒有錯亂,只是趨向極端,進入了絕境。他的無聲的獨白無異於懺悔,這懺悔因借用了大量極富象徵意味的形象而具有多向的啟發性。“叛逆者”處於流放之中,他的王國看來極為渺茫。
“緘默的人”,正是加繆最熟悉也最感親切的那些人,具體地說,那些制桶工人。他們因罷工失敗而心懷怨恨,他們在大工業的擠壓下面臨改變職業(然而他們是多么珍愛他們的手藝啊!)的威脅,他們與老闆的關係因利害的衝突而遭受扭曲,然而他們最終在老闆的女兒的病痛面前打破了沉默,這一切都被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手法準確鮮明生動地表現了出來。這篇小說寫的是復工的第一天,從伊瓦爾上班到下班,整整一天,按照時間的順序依次呈現出途中的景色、工廠里的氣氛、勞動的場面以及工人們對老闆的女兒生病這一事件所做的反應,其間很自然地插入伊瓦爾的心理活動,使經過精心選擇的大量細節具有活躍而濃郁的生活氣息,並且折射出更為廣闊的生活場景。加繆對人物著墨不多,但有名有姓的人有七八個之多,都各有性情,頗為鮮明,從主人公伊瓦爾的眼中看去,都顯得有血有肉,頗為生動。通篇小說用語樸實無華,對話直截了當,與勞動世界十分相合。小說的結尾透露出某種願望:“漂洋過海到那邊去”,似乎是對王國的朦朧的追求。《緘默的人》是一篇現實主義的小說,儘管它的作者反對現實主義。
《來客》的特點是具體、豐富、細膩的環境描寫,並在此基礎上呈現和深化主人公的孤獨感。這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國小教師達呂對於這環境始終處於不斷的選擇之中。就自然環境而言,他選擇了這片荒涼、貧瘠的高原,並且曾經“覺得自己跟土財老爺一般”,因為他“生於斯、長於斯,到了別的地方,他就有流放之感”。加繆在其他作品中從未對景物用過如此多的筆墨,荒原、石頭、雪、酷烈的太陽,眾多的形象組成這個與人極不友善的世界,從而也更襯托出主人公的選擇的嚴肅性:這裡就是他的“王國”。然而,社會環境卻使他的選擇成為一個泡影:他被迫要在把犯人交給當局和放犯人逃走之間做出選擇。他選擇了,然而他遭到誤解,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王國”:“在這片他曾無限熱愛的廣袤的土地上,他形影相弔。”社會環境描寫之細膩,在加繆來說,也不曾出現在別的作品中,例如國小教師達呂和阿拉伯犯人共居一室時的表現,被描寫得極有曲折感。環境是具體的,人物也是具體的,其心理活動也有具體的歷史背景。然而,加繆通過具有象徵性的細節和情境而淡化了政治的色彩,突出了普遍的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困難。“沙漠的門戶”“通往監獄的道路”“穿過高原的路”“曲曲彎彎的法國河流之間”,主客共居一室,犯人自投羅網,等等,都有深廣的象徵意義。《來客》這篇小說節奏雖然徐緩,內涵卻相當豐富,有一種緻密感,這使它有別於《緘默的人》那樣的現實主義小說,儘管它們細節描繪顯然是現實主義的。
初讀《約拿斯》,講的是一個“身為名累”的故事——一個畫家的藝術生命如何斷送於盛名之下。但是,作者在調侃中流露出的憤懣提醒我們:這絕不是一個輕鬆的笑話,它所寄託的思考是極為嚴肅的。“孤獨還是團結?”這個困擾著約拿斯的問題也同樣困擾著所有的人。小說的口吻是調侃的,漸漸地轉向嚴肅,仿佛一束可調的燈光,於不知不覺中突然照亮了主人公心中的疑團。讀者的疑問生於閱讀的結束,不由他不於諷刺和幽默中尋求更深刻的含義。於是,他很自然地看出:“不要再說誰是壞人,或者誰醜陋了,而應該說他故意壞,或者故意醜陋。”這樣一句隨口說出的話原來是暗指存在主義的“自由選擇”,作者的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約拿斯的結婚、找房子、電話、朋友的來訪或邀請、在各種宣言上籤名,最後被逼上自搭的閣樓,等等,這些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無一不間接或直接地與那個問題相聯繫,作者的憂慮實際上也在逐步深重。敘述口吻與所述事件之間的不協調,這是加繆從司湯達那裡學到的技巧,在這裡又一次得到充分的運用。《約拿斯》這篇小說中沒有多少細節,也沒有多少對話,一切都在大跨度的時空變化中被敘述出來,很明顯,作者在這裡更注重的是形象或事件的象徵性。這是一篇現代寓言。形象的血肉和鮮明、情節的曲折和完整、細節的豐富和真實,都不是作者所追求的,而調侃的筆調、幽默的口吻、真真假假的格言警句、虛虛實實的環境氛圍,卻明顯透出作者的苦心。
《生長的石頭》也許是集中最精彩的一篇,開頭即以有限的環境描寫,使讀者自然地站在主人公的位置上,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結尾又出人意料,頓時使主題凝聚升華,讀者甚至可以暗自驚訝:怎么不知不覺地跟著主人公走到那茅屋裡去,並且和他一樣感到“心頭充滿了紛亂的幸福之感”。作者在敘述中雖取第三人稱,但並非置身於讀者和主人公之上,而是以主人公的視角與視界為準,使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能夠儘可能地貼近主人公,並因此而儘可能地貼近作者。實際上,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主人公和讀者是漸漸地趨向融合的,他們的近乎一致的視角使小說的主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同時也使那些富有質感的形象具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和感情色彩,例如,“在幽暗而透明的水汽中,低至地平線上,幾顆星星開始點亮了”“幾隻毛羽發黃的黑禿鷲,睡在醫院對面的房頂上,熱得動彈不得”“負重的河水”,等等。這種帶有抒情性的形象描繪真實而生動地傳達出主人公內心的騷動。他似乎在躲避和追尋著什麼。在加繆的全部小說中,唯有《生長的石頭》和《偷情的女人》這兩篇對於景物給予了如此豐富而飽滿的筆墨,此種對於大自然的追求意味著對另一個世界的追求,即對“王國”的追求,因此這兩篇小說中那些經過精心選擇的形象都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然而,就主人公的態度而言,卻有主動與被動、進取與退卻的區別。在《生長的石頭》中,形象更豐富、更具體,象徵性更深遠、更複雜,因此,所呈現出的“王國”的氛圍也更濃重、更實在。《生長的石頭》更具有神話色彩。
總之,《流放與王國》並不是人們通常習見的那種匯集——若干不相連屬的作品的小說集,而是一個有聯繫、有不同側面的整體。加繆所採用的不同的小說技巧都是為這個整體服務的,並在其不同的表現形式上各有側重,有時又有交替重合。《流放與王國》因篇幅短小,不大為論者所重視,但平心而論,就藝術技巧而言,的確稱得上“純熟”。
就小說藝術,曾有人向加繆提過這樣的問題:“《墮落》與‘新小說’的探索有什麼關係?”加繆的回答可以被視為他的小說觀,也可以作為“加繆與小說藝術”這一論題的結論。他是這樣說的:“對故事的興趣與人本身共存亡,然而這並不妨礙人們總是尋求新的方式來講述,您提到的那些小說家指薩洛特、西蒙、羅伯-格利耶等所謂“新小說家”。有理由開闢新的道路。就我個人來說,所有的技巧都使我感興趣,但我感興趣的不是技巧本身。比方說,如果我想寫的作品需要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採用您所說的這種或那種技巧,或者兼而用之。現代藝術的錯誤幾乎總是使手段先於目的、形式先於內容、技巧先於主題。如果說我酷愛藝術技巧,如果說我試圖掌握所有的藝術技巧,那是因為我想自由地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工具。無論如何,我不認為《墮落》與您所說的那些探索有聯繫。事情簡單得多。我運用了一種戲劇技巧(戲劇化的獨白和潛在的對話)來描繪一個悲劇性的喜劇演員。一句話,我使形式適應主題。”
一語破的,“加繆與小說藝術”可以變成“加繆的小說藝術”了。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