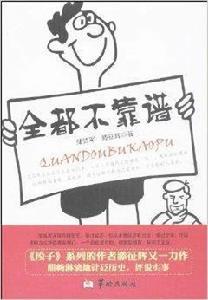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全都不靠譜》編輯推薦:一杯清茶,一杯紅酒,喧囂過後,隨手翻看《全都不靠譜》,靜靜地與自己內心對話。在這個塵埃和霧霾的世界中,還是能找到一處寧靜的角落。
作者簡介
遼寧蓋州人,總量經濟學博士,中國社科院人口學碩士。曾在國家體改所負責社會分層課題研究,後下海經商,涉及領域包括進出口、信託、傳媒、諮詢、通信、房地產等幾十種行業,擔任過國企、外企、民企任主要負責人。2000年春,於北京廣濟寺皈依佛教,後拜在香港覺真長老門下,現追隨明賢法師學習中觀。2010年末,發起成立1/13基金,旨在關注精神疾病人群。已出版了《淡定的人生處處禪》、《黃金屋:一個老總的讀書筆記》、《段子:一個老總的江湖見聞》、《段子2:老闆圈內的那些事》、《段子3:大小是個人物》、《段子4:聽滕老總講商場應酬》等暢銷書,是圈內公認的段子高手。儲賀軍,執業律師。1984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87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得法學碩士學位,199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01年在美國偉恩州立大學獲得法學碩士學位。1987年在中國法律事務中心開始從事律師工作,於1989年成為君合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1994年離開君合開始從事公司法律顧問工作,期間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作約12年。於2008年8月重返君合。著有《市場秩序論》、《與東亞談判風格》(英文:The Art of War and East Asian Negotiation Styles)(美國Willamet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校刊)(10 WMTJILDR 161)等。滕征輝
圖書目錄
一、國家那些事兒
國家那些事兒
瓜子、鑰匙和禮堂——改革那些事兒之一
莫乾山會議——改革那些事兒之二
四君子——改革那些兒事之三
人生在於拐點——淺談十大元帥
我愛毛澤東
民主的細節
三號理論
絕後
姓氏與宗族
二、往事真如煙
往事真如煙
我就是我
老滕、我與書緣
早年君合瑣記
答辯的那些往事兒
“2012”的真相
十年
硬要來的
我看未來淡如清水
段子時代
人生就像段子
我的微博人生
三、就怕商人有文化
就怕商人有文化
國慶漫言
文人三缺——讀史札記
讀書漫談
嚼完的口香糖
球迷拉登
貨幣戰爭
母親的心思
誰撿著了
北漂·北棄
拆遷如化療
反貪故事
皇帝的新衣
房地產正在救中國
四、堵車一大樂兒
堵車,權當是一大樂兒
相信——危機時刻的美利堅英雄情結
話劇——我之蜜糖
聞王歐戀四十年感懷
生活在北京的別處
搬家
小武求職記
肚量
蘭小歡
寧彎不折
扯蛋的恐龍
最深的恐懼——《2012》觀後感
扯蛋——《讓子彈飛》觀後感
五、半是海水半是陸
半是海水半是陸
一杯酒引發的血案與反思
牛逼這點事
老江湖
媽媽再也不走了
雙胞胎
我有一頭小毛驢
癌症不是病
狗日的福利
三種人
無力悲哀
贏不到的人
四大綠
非誠勿擾
後記
後記
訪談紀實
時間:2013年5月22日
地點:北京建國門北大街8號20層
人物:儲賀軍滕征輝程揚
程揚(以下簡稱“程”):怎么想起創作這一本書呢?
儲賀軍(以下簡稱“儲”)——我原來經常在《君合人文》上發表文章,發表多了,就有了把他收集整理在一起的願望,這本書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文人的“有病呻吟”。我希望把自己的生活經歷、看到想到的事情表達出來,希望得到共鳴,同時也是對自己情緒的一種宣洩。通覽我和老滕的文章,我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鳴的,都是真心的體會,心靈的感受。我們都有一種“胸懷天下”的情節,還是想評論下除了自己“一畝三分地”之外的事情。看到一些社會上的事情,有點“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一個初衷吧。
滕征輝(以下簡稱“滕”)——我寫這本書其實是個心情,一直在做經濟行業,期間經歷了很多事情,也換了很多單位,現在將近50歲了,會有很多感觸,驀然回首,想想功名利祿真的是我追求的嗎?忽然感覺這些“全都不靠譜”,唯有諸如感情、生命、親情這些才是真實的,換言之,也就是真善美才是靠譜的。所以才有了這本書的問世,裡面談了一些我對現今社會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觀點。
程:你們有共同的學校生涯。有什麼不一樣的校園經歷嗎?
儲——我是1984年入校(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當時學校校舍沒有建好,那時候學生們就都住在解放軍後勤學院,我們和老滕都喜歡看球,當然了,當時中國足球踢得還有一定的觀賞性,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混在了一起。我學的法律,他學的人口學,但後來都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從共性上講,我們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看法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但也不乏有互相批駁、爭辯之處。我覺得自己思想在同齡人中一直算是邏輯性比較強的,不知道是跟我大三以前一直都是班長有關,還是跟我學習英語、法律出身有關,我覺得英語是一種很講邏輯的語言,中國學生學習語言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學習語法,語法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事情,也可能是因此增強了我性格的嚴謹方面吧。
滕——我出生在一個小縣城,從原來不知道什麼叫大學,到後來陰錯陽差地考上了研究生,似乎都有些冥冥之中天注定的意味。記得當時在社科院時,學生分成好些派,有學習派、跳舞派、踢球派等等,我和老儲都屬於好動型的,所以就屬於踢球派。我那時候貪玩,特別喜歡踢球,也喜歡看球,那時候我們看球也分成幫派——馬拉多納派和普拉蒂尼派。在這點上我和老儲就有了分歧,我是馬拉多納派的“冬粉兒”,而他則是普拉蒂尼派的“鐵桿兒”。在這兒我特別要說一個我們共同踢球時的往事。那時候有一場球,我們84級組成的一隊,對方是83級、85級、博士生和校職工組成的一個隊,對方有一個踢球特別好的哥們兒,叫小耿,顛球可以2000個不落地兒的主兒,我和老儲都是84級的,所以老儲主動來找我制定策略。當時我們隊里有一個精力特別旺盛的小伙兒,就是那種每天不跑一萬米睡不著覺的人,我就給這哥們兒支招說,你就盯緊小耿,他走哪你盯哪。結果中場休息時候,發現這一萬米的哥們兒不見了!一會兒他回來了,答日:小耿去廁所了,我也得“盯”著啊!這哥們兒簡直敬業到了極致,都有點魔怔了!結果那場比賽我們隊大獲全勝——2:0。自此,我們84級足球隊開始變得“無敵手”起來,什麼麗都飯店隊、八九一工廠隊、財科所隊等等都被我們殺的片甲不留,酒仙橋這一帶簡直都不在話下,當時在那片兒都出盡了名。在這個過程中,我和老儲漸漸的熟識起來,老儲是足球隊的領隊兼“後勤部長”,兢兢業業,自掏腰包給我們買水買糧、商量戰術、找女生當拉拉隊,忙前忙後,任勞任怨。
程:畢業後都做了些什麼?
滕——那時候我們畢業找工作不像現在,還是很容易的,國家的人才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急需要有學歷的年輕人,於是我就去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老儲去了法務部。我從1984年畢業起,做了三四十家企業的法人代表,做過民企、國企,也做過外企。比如國康公司、華城集團、阿爾卡特等等。畢業後一個比較大的感觸就是要隨著歷史潮流走,比如90年代做證券,21世紀做上市公司和地產的話就比較容易成功,但是存在即合理,只要不違法,不要為了眼前的小利而觸碰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各行各業都是會獲得成功的。我們那時候的國企、民企、外企其實和現在的情況不大一樣。現在是國企現在越來越受重視,其實在90年代正好相反,那時候國家鼓勵大家下海、自主創業,現在是大家都想回到體制內,拿個鐵飯碗。說到外企,其實國家對外企的政策真是太優厚了,好多領域民企不能做,甚至於國企也有行業分工不能輕易地“越界”,其實我認為國家的這種人為的設定門檻短期看也許是有好處的,但長期而言我覺得未必,因為外企來國內投資是為了盈利,當他們收益到一定程度後,他們拿回國的是真金白銀,所以對我們的長遠來看這其實是一個“負數”。社科院30周年校慶時候,我出面做了一套書——《三十年三十人》,談了我們的一些往事,我們學校最早畢業的一些學生,比如黃江南、朱嘉明,還有國資委辦公廳主任張德林、君合的肖微、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等等,他們親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歷程,其中有些人還深入到決策層內部,書中談了他們如何為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出謀獻策,如何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開放對國人思想的啟迪和對社會的啟蒙等。我這三年出版了十多本書,也算是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儲——我畢業後一直做律師,先是在法務部中國法律事務中心工作,後來幾個人一起創辦了君合律師事務所,5年後,也是受外企熱的影響,想換個環境看看,於是就去了通訊公司,後來去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期間都是做法律顧問,共做了12年,在北京、底特律、瀋陽都待過,所以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各種形態我都比較了解。直到了2007年,我又回到了君合。總結這些年,我比較有感觸的有兩件事。一個就是辦君合律師事務所,正如陳毅元帥說的“創業艱難百戰多”,創業之初,真的是困難重重,所幸的是,現在君合也算是比較具有規模了,也有了自己的品牌效應。另外一個就是在通用汽車的十幾年,給我的感觸也是比較多的。我們都是中國生中國長的,但是一旦去了美國,就要適應那邊的生活和文化。一般中國人了解美國,都是通過留學、打工等等,但是真正能理解美國文化的方式,我認為是應該去那些大型的、有代表意義的企業,比如我比較熟悉的通用公司等等。1950年代初期,通用汽車總裁查理·威爾森曾自豪地宣稱,“凡是對通用有利的,都對美國有利。”由此可見通用公司在美國的象徵和代表意義。通過我在通用公司的經歷,我覺得當前我們國人對美國文化的某種崇拜是比較盲目的,這種崇拜是對美國文化的片面誤讀,其實美國文化其本身是有弱點的。我有一個願望就是等我退休後寫個話劇,名叫《辜鴻銘》。辜鴻銘是我國古代一個留學歸來而且外語很好的人,但是他回國後,就一頭扎進我國的經史子集這些傳統的文化中,因為他留學回來後,覺得中國的這些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那時候還有一個社會的主流代表——胡適之,他留學回來主張的是要全盤西化。雖然在當時辜鴻銘所代表的思想並不是社會的主流思想,但他們兩個的爭辯卻幾乎無處不在。在一定程度上,我跟辜鴻銘具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從美國回來後,我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更加濃厚的興趣,所以我如果寫話劇,一定會把這兩個人好好描述下,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程:學生生涯對於你們以後的工作生活有什麼影響?
滕——六七十年代我國的物資比較匱乏,但是我們的精神生活卻很豐富,我一直認為,我們很幸運,生活在一個精神解放、又趕上正規教育的時代,80年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時代,從國家領導人到學術圈,氛圍都是很寬鬆的一個時期,比如說在社科院讀研究生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劉國光、嚴家其老師等等都是大學問家,但是他們無一例外的都非常平易近人,跟我們聊天一點架子都沒有。我們那批人接受的都是最優秀老師的教育。因此從社科院出來後,在我們的職業生涯中,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都比較踏實,做事業的時候腦海里首先浮現的還幾乎都是“為國為民”、“為祖國奉獻青春”的想法,對個人利益的得失似乎想的並沒有那么多,更不用說想通過什麼歪門邪道去“發家致富”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現在應該有110位左右的現職的省部級幹部,差不多都是不拉幫結派的學者型領導,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那就更不勝枚舉了。在這些人的成就中我當然不算什麼,但是從我個人的生活經歷講,我投資過四家“中”字頭的媒體、也投資過中國歌曲總評榜。在個人奮鬥和追求過程中我也會心存疑問:這事對嗎?人生的追求到底應該是什麼?到底應該怎么看待現實中的人和事?我終於想得有點眉目應該是在2000年4月在廣濟寺皈依佛教後,我現在覺得人生是輪迴,人的身體、精神、情緒並不代表一切。自救救人才是我現在的生活態度,樂善好施,多為別人著想,儘量不要麻煩別人。
儲——我總共在校時間是25年,也就是花了1/4世紀的時間,讀了4個學位,當然其中有6年是在職。總體而言,我上的學校都是套用性比較強的,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和學以致用。在我上過的所有學校中,我覺得社科院對我的影響最大,一是當時正值22~25歲這個年齡段,有了一些基礎,也有了一些批判性,這時是最佳的學習年齡。其實,這也是美國法學院為什麼要求學生上完本科再上法學院的原因。二是社科院的氛圍特別好,有全國頂尖的導師,還有像老滕這樣的同學。我覺得社科院的學風是不錯的,從來注重理論修養,培養學生的能力,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裡,你可以聽到清談,但是,清談也無不與社會現象絲絲人扣。所以,我覺得在我的學生生涯打下的基礎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勤於學習,勤于思考,勇於面對社會問題。
程:有哪些人生感悟?
儲——人年輕的時候要學會把一本書越讀越薄,年紀大的時候就要學會把一本書越讀越厚。從我自身經歷而言,我現在看事情的角度和年輕時候已經有了些不同,舉幾個例子吧,比如說,哈爾濱的塔橋事件,大家普遍的輿論第一是腐敗,拿了回扣大橋修的質量不合格;第二是政府官員官官相護,硬說是橋的質量沒有問題。但是我認為,首先有沒有腐敗我不了解細節,所以姑且不做定論,但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解釋,四車同時超重,又同時在一塊橋板上把橋壓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在批評政府行為的同時,也要對超重、超載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這個問題已經成了中國交通安全最大的一個殺手,同時這種行為是在掠奪性地使用其他納稅人的資源。在美國,對於超重、超載問題的處罰是非常嚴苛的。在中國,改裝車量進行超重、超載似乎已經司空見慣了,甚至可以用“明目張胆”來形容,在有些運輸公司,他們就直接表明,運輸成本逐漸增加是現實,不超載、不超重就沒有辦法再去乾運輸了,正因為恰恰在中國沒有相關的法律對此行為進行嚴厲制裁。所以我們在關注交通腐敗問題的同時,也應該從法律的角度看待這些事情的產生和如何處理。再比如說規則制定的理念問題,如“鞭炮禁燃”、“治理酒駕”這些問題,相關規則的制定確實是收到了不錯的正面效應。但是對於“處罰闖黃燈行為”這一規則的制定,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黃燈的意義等同於紅燈,那么黃燈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在這方面,美國的做法可能會更加合理一些,美國規定黃燈的意義是“駕駛員進行判斷的時間”,這就比較人性化。當然不可否認的是近幾十年中國在交通方面的建設是令世界瞠目的,比如高速路網路用了二十年建設得很好,中國的高鐵建設也是舉世矚目,還有中國機場的建設等等。所以對於中國未來交通方面的建設,總體而言我還是很看好的。
滕——現在我們已經年過半百,回頭看看我們的經歷是一件很有意義和價值的事情。所謂“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我就談談對專業的看法。我學的是總量經濟學,專業是政府政策、公共管理的研究方向,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做服務型政府,而不能做投資型政府,其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政府的“效率”。當前應該把發展的速度降下來,把求速度變成求結構,把求數量變成求質量,在法制建設的同時,更加注重視道德的建設。
儲——確實,道德是規範人行為的根本。從道德和法律的關係來講,中國幾千年來,大多時候都是以道德為社會穩定的核心,舉個例子,就像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商標其實最早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是在古代,中國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主要是靠道德。我很崇拜亞當·斯密,因為在他的《國富論》中,能夠用極其平易的語言講明白了經濟學是什麼。但讀了他的《道德情操論》後,我認為這本書中對道德的表述不如儒學、老子、莊子談的深人、徹底。我覺得應該在道德體系建立完善的基礎上,再輔之以法律,中國社會將會度過自己的難關。
滕——我覺得道德問題,含義在中西方差不多。道德本身受兩方面約束,一個是中國固有的社會結構,即宗法社會,另一個是宗教,中國社會的回歸我認為有兩點,第一人要有所懼,第二要建立家庭的觀念,就像陳道明說的:“北京的男人都回家吃飯,社會問題都會消失。”這是一句很有寓意也很現實的玩笑話。
儲——我覺得道德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約束力,但是道德也不能太過,過了會使人迂腐,有個小故事,有個宰相,在家辦公時候用朝廷發的蠟燭,當他辦完公做自己的私事時熄滅了朝廷發的蠟燭,點燃自家的蠟燭來照亮,這就是過於用“道德”來約束自己,反而成了一種迂腐的形式主義典範。-。程:這么多不靠譜的事情。那什麼最靠譜?
儲——這么多年總結下來,我覺得世界上最靠譜的就是家庭。我現在就是下班回家當“宅男”,我現在的生活特別規律,早六點起床,六點半出門,七點開始工作,下午四點回家,晚上十一點休息,我生活這么規律,就是想多見見我的女兒們,因為我覺得和女兒在一起的時間是最幸福的時光,也是我覺得最真實最靠譜的時光,比如晚上的九點一刻的“阿軍煮奶”時光,其實就是我兩個女兒叫我幫她們煮牛奶,那一刻很普通,但是我覺得自己很幸福。不過,有時候我也會想這事兒靠譜嗎?以後過十年、二十年之後,我的兩個姑娘都長大成人了,她們有了自己的圈子和朋友了,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天天圍著父母轉了,那么我現在的這種“幸福感”就變成了不靠譜的事情了。所以現在“靠譜”與“不靠譜”我覺得沒有明顯的界限,他們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能絕對地孤立和割裂,當然我說的這些是從感覺的角度,在客觀事情上,靠譜、不靠譜還是有原則性區別的。
滕——我們現在已經年近半百,雖說算不上什麼成功,但是很知足。曾經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我們的終極理想,但是時至今日,金錢、聲望、權利真的靠譜嗎?真的是我們應該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嗎?肯定有人說“什麼啊,這些全都不靠譜!”確實,因為擁有的同時就是意味著在失去,比如當你有了金錢,那不叫擁有,那只是一個符號,當你花掉它的時候那才叫擁有,但是與此同時,你已經失去了它。聽起來也許很矛盾,但細想想事情不都是如此嗎,所以對於靠譜或者不靠譜而言,我更願意從生命的本源來看,每個人都是能成佛、都是有佛性的,我們每個人都要積攢正能量,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做對別人有幫助的事,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這才是最靠譜的人生。所以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積極地發展自己,尤其不要被眼前的一些諸如就業、生活的困難所困擾、愁雲慘澹,還是要跳出來看,生命有那么多層次,要有更高的眼界和追求,這才是最靠譜的事情。
序言
一杯清茶,一杯紅酒,喧囂過後,隨手翻看好友的《全都不靠譜》文稿,靜靜地與自己內心對話。在這個塵埃和霧霾的世界中,還是能找到二_一處寧靜的角落。
做了二十多年律師,鼓弄了五花八門的法律之術,把一些簡單的事情變得好複雜。人疲倦,心也疲倦。某一夏夜,躺在沙漠的沙丘上,仰望滿天繁星,浩渺蒼穹,猛然意識到成為宇宙中已知的唯一有生命之星球上的高級動物是多么幸運和難得。何況我們經歷了一個既有血雨腥風、噤若寒蟬,又有個性自我、意志飛揚的天翻地覆、斗轉星移的時代。人生苦短,白駒過隙,當你周圍的親朋好友陸續有人過世時更有感悟。短暫的旅程,我們該如何領略?
儲賀軍和滕征輝是我八十年代研究生的兩位同學,一位畢業後和我一樣在法律圈內自斟自酌,另一位則在金融領域饕餮大餐。令我意外並且自慚的是,這兩位同窗無論滄海桑田,無論青絲鶴髮,竟始終性情隨心、筆墨隨感。當一個人回憶過去,整理舊集時說明他已不年輕;同時,當一個人暢說心路歷程,評論人生幾何時說明他沒有虛度光陰,而是充實地咀嚼和回味了生命的五穀雜糧。
順著這筆墨,你可以回頭追尋一個生命的脈動與軌跡,不求精彩,但求鮮活。追尋者可能是親朋好友,可能是陌路閒人,也可能正是筆墨者自己。
是為序。
肖微
201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