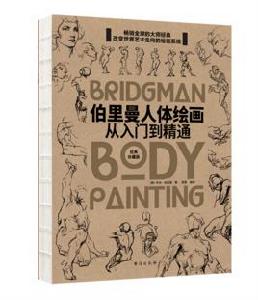基爾蘭達約、里皮、波提切利這些大師,他們可以說對手的結構了如指掌,他們每個人都畫出了屬於自己風格的手。
後來在學校里,學校都有講關於手的畫法,就比如維多利亞和荷蘭的學校,還有卓旦斯、魯本斯的學校。而凡·戴克被認為畫不出勞動者的手;米勒則畫不出紳士的手。
我們僅靠目測是不精準的,眼睛將影像傳遞到大腦,大腦處理了這些影像之後,影像才與照片不同。我們其實是在用思維去“看”,我們可以任意加強某處,任意弱化某處,我們用思維控制著眼睛,眼睛只是一個透光的通道。
米開朗琪羅、達·芬奇和拉斐爾這些大師同屬於一個時期,他們當時所能看到的模特應該是風格相近的,但他們的作品仍然風格迥異。
阿爾伯特·丟勒、小荷爾拜因、倫勃朗的作品中都有展現其各自的手,所以後來這些大師的作品被歸類為荷爾拜因畫的手、丟勒畫的手、倫勃朗畫的手。
人們已經對這些手的特點很熟悉了,這些大師的習作並沒有我們現實中看到的那么死板。在繪畫中,不只是我們直觀看到的,還摻雜了我們大腦處理過的信息,這些信息受品味和時代的影響。
所以,藝術家按照自然規律將畫手的方法規範化和統一化,以便於學習、理解。
曾經解剖學是被法律禁止的,還有宗教對解剖的憎恨。現在,人們對解剖的誤解剛剛有些好轉,人們發現了這項研究對醫學發展的深遠意義,也逐漸明白了解剖的重要性。不僅如此,解剖的研究還逐漸滲透到了其他領域。
人們耗費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研究隱藏在形體下方的機體結構。現在人們已經發現了隱藏在表面之下結構的學問,藝術界也已經吸收了這些東西,並對這種摻雜了解剖學研究的繪畫技法尋求提高。與此同時,學校里也逐漸開了這樣的課程,一些人便在學校學習這些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