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
 休謨雕像
休謨雕像大衛·休姆(David Home)(後來改名為休謨/Hume)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曆)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的一座公寓裡,父親是在寧威爾區(Ninewells)擔任律師的約瑟夫·休姆、母親是法爾科內夫人。休謨在長大後偶爾也會回到寧威爾區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將名字從休姆改為休謨,因為英國人很難以蘇格蘭的方言正確念出休姆這個名字。休謨在年僅12歲時就被家裡送到愛丁堡大學就讀(當時正常的入學年齡是14歲)。最初休謨打算從事法律職業,但不久後他發現自己有了“一種對於學習哲學和知識以外所有事物的極度厭煩感,當我的家人想像我正在閱讀屋埃特和維尼阿斯(兩位當時著名的法學家)時,我實際上卻是在閱讀西塞羅和維吉爾的著作。”休謨對於大學裡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訴一名朋友說:“你根本不能從教授身上學到任何東西,那些東西在書里都有了。”
在那個時代,一個貧窮的蘇格蘭人能選擇的生涯途徑相當少,休謨面對的是成為家庭教師或是成為商人的職員這兩個選項,他最後選擇了後者。
《人性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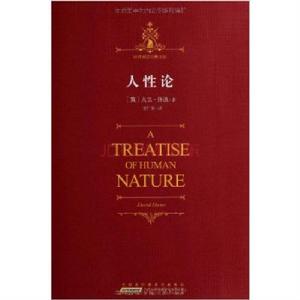 休謨 《人性論》
休謨 《人性論》1734年,在於布里斯托經商數個月之後,休謨前往了法國安茹的拉弗萊舍(La Flèche)旅遊,在那裡休謨經常與來自Prytanée軍事學校的耶穌會學生進行哲學討論,勒奈·笛卡爾也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那裡定居的四年中休謨替自己訂下了生涯計畫,決心要“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以應付我那有限的財產,以此確保我的獨立自主性,並且不用考慮任何除了增進我的文學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國定居時休謨也完成了《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當時他年僅26歲。雖然現代的學者們大多將《人性論》一書視為是休謨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學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書剛出版時並沒有獲得多少重視。休謨從英格蘭、法國及德國的學術刊物看到了書評,有些甚至很長,但是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休謨為此寫了一篇回覆:《一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之摘要;書名,人性論;該書的主要論點在此得到進一步的闡發與解釋》(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u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 Wherein The Chief Argument of that Book is farthe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1740年,這篇摘要以不具名的小冊子的形式得到出版。休謨在記載到當時自己缺乏大眾重視時這樣寫道:“媒體對這本書的反應是一片死寂,甚至連對那些狂熱的讀者群都沒有半點交代。不過我本來就養成樂觀而開朗的個性,很快就從這樣的挫折里站了起來,並繼續在鄉下努力的進行研究。”他繼續寫下了《人性論摘要》一書,但沒有寫出自己的名字,他試著縮短並精簡他之前的冗長著作以吸引更多讀者,但即使經過這樣的努力,他依然沒有成功使《人性論》一書重獲重視。撰寫《人性論》的艱辛過程使得年輕的休謨近乎精神錯亂,為了回復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謨決定暫時返回平凡生活。
《大不列顛史》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img/b/313/nBnauM3X4IDNzEjNzIjN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YzL4M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論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書後,休謨申請擔任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和精神哲學”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學拒絕。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變的時期中,休謨成為當時被官方形容為“瘋子”的安那代爾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師,這份工作只維持了一年左右便結束。不過,也是在這段時間,休謨開始撰寫他的歷史巨作《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書,這本書的寫作持續了15年,寫成時已超過了一百萬字,最後從1754至1762年間分成六冊發行。在這段期間休謨參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創辦的教規門講會(Canongate Theatre),藉此也認識了其他許多當時在愛丁堡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從1748年開始他擔任了聖克萊爾將軍的秘書長達三年,同時一邊撰寫他的《人類理解論》一書(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幾本書一樣,這本書在當時出版時也沒有獲得重視。
這時休謨遭到教會指控為異端,休謨的一名年輕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辯護,主張休謨身為無神論者是屬於教會管轄的範圍之外。儘管後來休謨被判無罪,格拉斯哥大學仍然拒絕了休謨擔任哲學教授的申請,這可能也是因為另一名正大力批評休謨形上學的哲學家Thomas Reid刻意阻撓所造成的。依據休謨的自傳,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蘇格蘭後“蘇格蘭律師公會才讓我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擔任這個職位只能獲得很少的薪水,但卻讓我有機會接觸一個這樣龐大的圖書館。”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的豐富資源使休謨得以繼續他在《大不列顛史》上的研究。
休謨最終以一個評論家和歷史學家的身份聞名,他龐大的《大不列顛史》一書敘述了從撒克遜王國到光榮革命的歷史,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在這本書里休謨將政治體制下的人民形塑為一種文化習俗的產物,這些人傳統上傾向於服從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對無法確定的情況時才會尋求改變。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宗教的差異才能使人偏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關注政治的事務。
宗教觀
休謨早期寫下的論文“論迷信與宗教”就已經立下了幾乎所有他之後有關宗教歷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謨那個年代,想批評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須抱持謹慎的態度,舉例而言僅在休謨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歲的大學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為評論基督教是“胡說八道”便被教會起訴,最後還被定罪以褻瀆罪名處以絞刑。因此休謨也是只以轉彎抹角的方式表達他的理論,大多是以虛構的角色在對話錄中呈現。休謨一直沒有承認自己是《人性論》一書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為止。他的論文《論自殺》和《論靈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書都是在他死後才出版(分別在1778和1779年出版),這些著作也都沒有註明休謨或是出版商的名字。休謨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份而做出的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學者們對於休謨究竟是自然神論者或是無神論者仍有極大的爭議。不管如何,在當時有關休謨是無神論者的傳言的確使得休謨求職時四處碰壁和受阻。
休謨曾向朋友提及一次他在偶然間被“轉化”為基督徒的過程:當他前往監督自己新居建築工地的途中跨過愛丁堡市中心一片剛乾枯的湖泊時,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於身型肥胖而爬不出來被困在了那裡。這時一些賣魚婦人剛好路過,看到了休謨的窘境,但她們很快便認出他是那位知名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救援他,直到休謨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和信經之後,這些壯碩的賣魚婦才將他拉起。休謨事後向朋友開玩笑道這些賣魚婦是“他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了”。
晚年
從1763年至1765年間休謨擔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書,在那裡他受到了伏爾泰的欽佩並且被捧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同時他也認識了讓-雅克·盧梭,兩人最初成為要好的朋友,但最後因理念不合而分散。休謨這樣描寫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時常想回歸愛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撲克牌俱樂部…以矯正並緩和這段時間以來那么多的感官刺激。”在1768年休謨回到愛丁堡定居。到了1770年左右,隨著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誇讚是休謨讓他從“教條式的噩夢”中覺醒,休謨的哲學著作開始獲得大眾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後他才獲得了他一輩子都沒有獲得的聲譽。
 休謨之墓。
休謨之墓。詹姆士·包斯威爾在休謨去世的前一周拜訪了他,休謨向包斯威爾透露他堅定的將人在死後還會有來生的理論視為“最不合理的迷信”。休謨替自己寫的墓志銘是:“生於1711,死於[……]—空白部分就讓後代子孫來填上吧。”休謨在1776年去世後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簡單的羅馬式墓地”,地點位在愛丁堡卡爾頓山丘(Calton Hill)的東側,俯瞰山坡下他位於城內的老家。
人物思想
雖然休謨屬於18世紀的哲學家,他的著作中討論到的題材大多與現代哲學界的主要爭論有密切關係,這與其他同時代的哲學家相較是相當罕見的。一些休謨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想可以歸類為以下幾點:
因果問題
休謨不贊同大多數人都相信的只要一件事物伴隨著另一件事物而來,兩件事物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關聯,使得後者伴隨前者出現(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它在那之後而來,故必然是從此而來)的思想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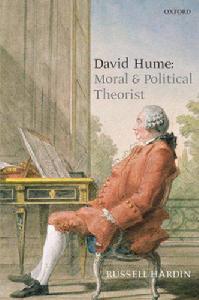 大衛·休謨
大衛·休謨休謨在《人性論》以及後來的《人類理解研究》中反駁了‘因果關係’具有真實性和必然性的理論,他指出雖然我們能觀察到一件事物隨著另一件事物而來,我們並不能觀察到任何兩件事物之間的關聯。而依據他懷疑論的知識論,我們只能夠相信那些依據我們觀察所得到的知識。休謨主張我們對於因果的概念只不過是我們期待一件事物伴隨另一件事物而來的想法罷了。“我們無從得知因果之間的關係,只能得知某些事物總是會連結在一起,而這些事物在過去的經驗里又是從不曾分開過的。我們並不能看透連結這些事物背後的理性為何,我們只能觀察到這些事物的本身,並且發現這些事物總是透過一種經常的連結而被我們在想像中歸類。”(Hume, 1740: 93)也因此我們不能說一件事物造就了另一件事物,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一件事物跟另一件事物可能有所關連。
休謨在這裡提出了“經常連結”(constant conjunction)這個詞,經常連結代表當我們看到某件事物總是“造成”另一事物時,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一件事物總是與另一件事物“經常連結”。因此,我們並沒有理由相信一件事物的確造成另一件事物,兩件事物在未來也不一定會一直“互相連結”(Popkin & Stroll, 1993: 268)。我們之所以相信因果關係並非因為因果關係是自然的本質,而是因為我們所養成的心理習慣和人性所造成的(Popkin & Stroll, 1993: 272)。
 大衛·休謨
大衛·休謨休謨提出的這個說法有力駁斥了因果關係理論,在休謨之後的一些哲學家如伯特蘭·羅素還完全拋棄了因果關係的概念,只將其視為一種迷信。但從這裡也產生了因果的問題——我們對於因果連結的認知是從何而來的?而我們又能認知到怎么樣的連結?這個問題後來引起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論辯。
休謨主張人類(以及其他動物)都有一種信賴因果關係的本能,這種本能則是來自我們神經系統中所養成的習慣,長期下來我們便無法移除這種習慣,但我們並沒有任何論點、也不能以演繹或歸納來證明這種習慣是正確的,就好像我們對於世界以外的地方一無所知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常連結”的理論一般被認為是休謨所提出的,可能有其他哲學家早在休謨之前便已提出類似的概念。
中世紀哲學家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著作中便舉出了幾名同樣不相信“因果關係”的伊斯蘭哲學家,他在《迷途指津》(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一書里這樣寫道:“簡而言之:我們不應該說‘這個’是造成‘那個’的原因。”從這些伊斯蘭哲學家的角度來看,造物主所創造出的任何東西都是獨立而不相連的,因此這些事物間並沒有一定的連結。
歸納問題
在《人類理解論》一書中,休謨主張所有人類的思考活動都可以分為兩種:追求“觀念的連結”(Relation of Ideas)與“實際的真相”(Matters of Fact)。前者牽涉到的是抽象的邏輯概念與數學,並且以直覺和邏輯演繹為主;後者則是以研究現實世界的情況為主。而為了避免被任何我們所不知道的實際真相或在我們過去經驗中不曾察覺的事實的影響,我們必須使用歸納思考。
歸納思考的原則在於假設我們過去的行動可以作為未來行動的可靠指導(這有時又被稱為自然劃一原則—uniformity of nature),舉例而言,如果依據過去的經驗太陽總是從東邊升起而從西方落下,那么歸納推理就會告訴我們太陽在未來可能還是會從東邊升起而從西方落下。但我們又要怎么解釋我們有能力做出這樣的推論呢?休謨主張我們不可能將我們的思考能力解釋為理性的產物,因為理性只有可能是從兩種方式得來,而這兩者都不可能作為我們推理思考的根基:
論證的或直覺的:這樣的思考在基本上是先驗的,我們不能以先驗的知識證明未來就會和過去一致,因為(在邏輯上)可以思考而出的明顯事實是世界早已不是一致的了。休謨在這裡並沒有清楚分出整體上的自然劃一原則與某個“特定的”劃一原則的差異。一個哲學家或許可以主張(或許就是康德那一派)在事實上我們的確很難想像世界竟不是以“某種”形式一致運作;然而休謨在這裡所提出的關鍵是,即使是自然運作中任何“特定的”劃一原則,也都有可能在未來停止運作。因此我們不能將歸納思考根基在先驗的知識基礎上。
歸納的:我們也不可能訴諸於在過去使用歸納推理的成功經驗來證明歸納推理的可靠性,因為這將會構成循環論證。
休謨接著總結道我們的思考能力並沒有一個理性的基礎,因為沒有任何形式的理性可以證實這樣的能力。在這裡要注意的是休謨並不是在主張以下幾點:他並不是主張因為歸納法不屬於演繹法,所以那並不理性(休謨並不是所謂的“演繹主義者”)。
 大衛·休謨
大衛·休謨如同休謨在一段名為“論懷疑主義與理性”的章節中所講到的,他主張的是如果理性沒有任何的依據就能夠構成我們的思想、如果思想是從頭到尾都是由理性所構成的,那么我們根本不可能會相信任何東西,包括了直覺或演繹得出的任何真相在內。
除此之外,休謨並不是主張歸納法並不可行、也並不是認為歸納法就無法達成可靠的結論,相反的,休謨主張的是這種歸納思考在事實上並不是由理性所構成的。休謨理論中的另一個重點在於:雖然休謨對於歸納法屬於理性思考的可能性抱持悲觀態度,他仍認為歸納推理帶有相當值得注意的、也是相當神奇的預見未來的能力。為了解決我們在了解歸納推理上面對的問題,休謨提出“自然”作為解決問題的答案。自然決定了要我們期待未來的事物中會有比較多與過去類似,而“這種思考方式讓我們得以透過相同的原因推斷出可能的結果,反之亦然。這種思考方式是所有人類生存於世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我們不能信賴我們的理性所做出的錯誤演繹,這種理性不但思考緩慢,而且打從我們出生下來在一生中都非常容易犯下錯誤”(《人類理解論》,5.2.22)。休謨的這個說法或許是在那個時代(前達爾文時代)對於人類歸納思考能力所做出最接近進化論的理論了,休謨在這裡也突顯了自己與所有無神論思想家的主要差異,完全呈現了他身為自然主義思想家的一面。
自我理論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img/0/8cc/nBnauM3X3ITMycDNwADN4UjM2UTM1QDN5MjM5ADMwAjMwUzLwQzL2c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
休姆[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休謨指出我們通常會假設現在的我們就和五年前的我們沒有兩樣,雖然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有了改變,呈現在五年前的我們和現在的我們都是同一個人。我們也會思考時光究竟可以在不改變一個人自身的情況下,改變一個人內在到什麼程度。不過休謨否認那神秘的自我與一個人所帶有的各式各樣人格之間是有所區分的。當我們開始自省時我們會發現:“除非依靠一種特定的感覺,我們從來不可能有任何的意識;人只不過是由許多不同的感覺累積而成的一個集合或一個包裹,這些感覺永遠處在一種快到無法想像的流動速度中互相交替汰換。”
很明顯的是在我們思考的過程中我們的各種思想永遠都在改變,我們的想像力可以輕易的從一個想法轉換到另一個類似的想法,而想法本身的特質便足以形成一個連結和聯想。同樣的,我們的感覺也必然會不斷的改變,改變了的感覺也會類似於之前的感覺。想像力必然是經過長時間的習慣所培養下來的思考方式,隨著空間和時間的改變而不斷想出更新的想法[15]。
值得注意的是,從休謨的角度來看,這些感覺並不屬於任何事物。相反的,休謨將人的靈魂比喻為一個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並非依靠著什麼恆久的核心思想,而是靠著各種不同的、不斷改變、而卻又互相連結的思想才保持了其本體。也因此個人的本體是只不過由一個人的各種個人經驗所構成的鬆散連結。
簡而言之,對休謨而言“本體”是否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各種感覺之間的因果關係、串連,以及彼此之間的類似。
實踐理性
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一些行為比其他一些行為要來的“合理”。舉例而言,吞食鋁箔片在大多數人來看是一種很奇怪的舉動。然而休謨否認那種理性在驅動或排斥特定行為上扮演了任何重要的角色,畢竟理性只是一種對於概念和經驗的計算罷了。
在休謨來看,真正重要的是在於我們如何感覺這些行為。休謨的這個理論在現代被視為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基本原則,主張一個行為的合理與否應該是取決於這個行為能否達成其預定的目標和欲望,無論這些目標欲望為何。理性只是扮演著一種媒介和工具的身份,用於告訴我們怎么樣的行為才能達成我們的目標和欲望,但理性本身永遠不能反過來指揮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目標和欲望。
也因此,如果一個人想要吞食鋁箔片,理性可以告訴那個人他應該去哪裡尋找鋁箔片,“吃鋁箔片”或是“想要吃鋁箔片”本身並沒有任何不理性的地方(當然,除非一個人有強烈的健康欲望或是感覺能力,理性才會告訴他不應該這樣做)。不過在今天,許多人認為休謨在這裡其實已經到達虛無主義的境界,並且指出了一個人其實可以故意的阻撓他自己的目標與欲望而不會違反理性原則(“我想要吃鋁箔片,讓我把我的嘴巴捆起來”)。這樣的行為必然會顯得相當不正常,但是既然理性並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也不能用以評量行為,這樣的行為也就不會違反理性了。
人物評價
艾耶爾(1936)在發表他知名的邏輯實證主義時這樣說道:“我在這篇論文裡提出的觀點是源自從貝克萊和休謨的經驗主義衍生出的邏輯結論。”
伯特蘭·羅素(1946)和Leszek Kołakowski(1968)都將休謨視為是實證主義者,認為知識只有可能是從對於事件的觀察上衍生而出—從“對感官的印象”或是“感覺的資料庫”里得出,同時其它任何不是透過觀察經驗而得的知識都是“毫無意義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915)寫到當他在構思狹義相對論時便是受到了休謨的啟發。
卡爾·波普爾(1970)指出雖然休謨思想中的理想主義在他看來是對於“常識的現實主義”(common sense realism)的有力反駁,而且他也認為常識的現實主義是個錯誤,然而他後來發現休謨在本質上其實也是一個常識的現實主義者—這個發現還讓他無法置信了好一陣子。
埃德蒙德·胡塞爾(1970)認為休謨的著作中表現出現象學的特色,因為休謨證明了一些感覺是與其他的感覺有所關聯或是互相連結而形成的,這些感覺集合起來便成為一個在心靈以外的世界。
Barry Stroud(1977)主張休謨是一名“自然主義”者,因為休謨將人類生命中的各層面都視為是與自然相連結。他將人類放在一個有智慧的自然世界中,而不只是把人視為是一種與外界不相連的思想靈魂。
Terence Penelhum(1993)則認為休謨是追隨了斯多亞學派、伊比鳩魯學派,以及懷疑主義學派傳統,因為休謨主張我們應該追隨自然以避免思想的焦慮。就如同那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一樣,休謨認為我們應該先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自然本質,而不是貿然進行任何哲學思考的冒險。
James A. Harris(2015)認為,休謨既不是名聲與金錢的追獵者,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而系統的研究計畫。休謨的一生,對文學的熱愛始終是他主要的志趣。在休謨那個時代,“文學”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涵蓋了學問的整個世界,包括歷史、神學、哲學和宗教等等。休謨一直以”學者”自居,所謂的學者就是學習的人,但是他所學的是一般性的東西,不是學術性的專業研究,也不是狹隘而好賣弄的紳士的博學。所以休謨在各個學科之間往來穿梭,自由翱翔。當他的家人以為他在讀法律教科書時,實際上,他不僅讀著西塞羅,也在讀維吉爾。他為所有一般性、原理性或根源性的問題激動著,始終地為自己的文字風格而著惱,尋找著最能夠準確表達自己又能夠被大眾所輕鬆理解的表達方式。
著作
•A Kind of History of My Life (1734)
寫給一名匿名醫師的信,請求提供能夠治癒他身上“好學的疾病”的療法。信中休謨自承在他18歲時“似乎發現了一個新的思考領域……”並且使他下定決心“拋棄其他所有快樂和事業,完全奉獻在這個領域上。”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人性論》 (1739–40)
休謨打算觀察這本書是否能獲得好評,如果是的話他會繼續寫下有關政治和回應批評的部分。然而這本書並沒有獲得任何注意(如同休謨自己所說的:“媒體對這本書的反應是一片死寂,甚至連對那些狂熱的讀者群都沒有半點交代”),也因此休謨沒有繼續進行後半段的寫作計畫。
•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tc. (1740)
原本一直被誤認為是亞當·斯密所著,直到最近才發現是休謨為了推廣他的《人性論》而寫的小冊子。
•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道德和政治論文集》 (first ed. 1741–2)
收集了休謨多年累積的一系列論文,並在休謨去世前不久被集合為一冊出版。論文顯得相當雜亂而缺乏頭緒,即使是當中討論的話題也相當模糊。這些論文討論的範圍從美學鑑賞到英國政府的本質、戀愛、婚姻和一夫多妻制都有,甚至還包含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人口統計資料。不過,有一些重要的題材和話題曾重複出現,尤其是在討論有關什麼是“高雅”的品味、風格、和道德上。休謨的論文顯然模仿了約瑟夫·艾迪生的《閒談者》雜誌的風格,休謨在年輕時相當喜歡閱讀這份雜誌。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to His Friend in Edinburgh. 愛丁堡 (1745)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人類理解研究》 (1748)
包含了針對《人性論》一書中的幾點擴充,增添了有關自由意志、神跡,以及設計論的討論。
Of Miracles—論神跡
《人類理解論》一書的第X節,通常分開出版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道德原理研究》 (1751)
另一本改寫自《人性論》以企圖獲得更多讀者青睞的書。休謨認為這是他所有哲學著作中最好的一本,無論是在哲學思想和文學風格上皆然。
•Political Discourses 愛丁堡 (1752).
包含在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1753-6)的1758-77年第二版中
•Four Dissertations 倫敦 (1757).
包含在上述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第二版中
•The History of England (原先的標題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大不列顛史》 (1754–62) 可以在自由圖書館閱讀全文
比較像是一套叢書而不只是一本書。休謨討論的歷史範圍“包含了從凱薩大帝入侵到1688年的革命”,這套書後來再版了超過100個版本。許多人將其視為是英格蘭歷史學的標準著作,直到Thomas Macaulay的History of England一書出現為止。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1757)
•My Own Life (1776)
在四月開始撰寫,不久後休謨就去世了。這本書原先打算包含在新版的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里出版。這本書後來由亞當·斯密出版,斯密稱這本書的出版使他招惹了“比我對英格蘭貿易體制的嚴苛批評還要激烈十倍的負面回應”。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自然宗教對話錄》 (1779)
死後由他的外甥出版。書中藉由三個虛構角色討論上帝是否存在,尤其是有關設計論的問題。儘管有著不少爭議,大多數學者同意書中的Philo—三個人中最抱持懷疑主義立場的人,最接近休謨本人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