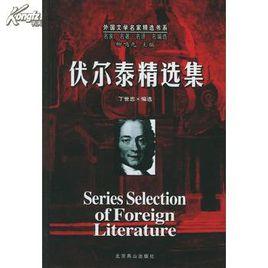內容簡介
“新文藝外國文學大師讀本”初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深受廣大讀者喜愛。適逢上海文藝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我們重新整理出版這套叢書,奉獻給新一代的讀者。
“新文藝外國文學大師讀本”所選均為世界經典作家,入選作品突出作家某一方面的藝術特色;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適當也選收一點中篇小說。
《新文藝外國文學大師讀本:伏爾泰哲理小說》是其中一冊,收錄了《查第格》、《如此世界》、《老實人》三篇文章。
目錄
選本序
查第格
如此世界
老實人
前言
法國著名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亞在他的《伏爾泰傳》中曾經這樣說過:“十七世紀是路易十四的世紀,十八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這句話代表了不少資產階級文學史家、批評家對伏爾泰的評價,它雖然不無誇張,但的確也反映了伏爾泰在當時影響之大。
伏爾泰以令人驚異的充沛精力在十八世紀的思想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動,他是哲學家、歷史學家、政論作者,他的文學創作,悲劇、喜劇、史詩、哲理詩、哲理小說都豐富多產,十八世紀末,由博馬舍編輯出版的第一個伏爾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還不包括他卷帙繁浩的全部書信;他在當時享有巨大的聲譽,被視為思想界的泰斗,整個歐洲都傾聽他的聲音。
伏爾泰本名弗朗索瓦·阿魯埃,1694年生於巴黎一個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他的青年時期正當“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的晚期,法國封建君主專制盛極而衰的時代。這個時代“金玉其表、敗絮其中”、即將全面破落的面貌和徵候,在伏爾泰著名的歷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時代》中曾有忠實的記載。路易十四逝世時,他是二十一歲,親眼看見“巴黎人在熱望自由的氣氛里舒了一口氣”,路易十四葬禮的那天,他在去聖特尼的路上,看到了沿途鄉間小酒店裡民眾歡慶痛飲的情景,不禁對此產生深長的思索。
中學畢業後,他在擔任駐外使館的秘書和法庭的書記期間,雖混跡於貴族紈禱子弟的圈子,但目無封建等級制,敢於與貴人分庭抗禮,針砭時尚,抨擊前朝政制,以鋒利的談吐和俏皮的警句聞名。由於言談中對攝政王不敬,他被逐出京城,他並未因此有所收斂,又在一首詩里諷刺了宮廷,於1717年被投進了巴士底獄,在獄中蹲了十一個月。
1726年,他來到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國,在英國居住了三年,考察了政治制度和社會習俗,研究了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和牛頓的物理學新成就,形成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主張和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他把自己的觀感和心得寫成《哲學通訊》一書,鼓吹政治改良、信仰自由和唯物主義。
l729年他回到法國,1734.年,他的《哲學通訊》出版,立即被扣上“違反宗教、妨害淳良風俗、不敬傳統學術”的罪名遭到查禁,巴黎最高法院下令逮捕伏爾泰。他逃離巴黎,在偏僻的小城西雷、他女友夏德萊夫人家裡住了十五年,在此期間,他寫作了不少史詩、悲劇、歷史著作與科學論著。
這時期,他又曾一度得到宮廷的信任,1746年被選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後又被派往德國執行外交使命,被任命為法蘭西史官,然而這一切不過是曇花一現,他又因得罪了路易十五不得不離開巴黎。
伏爾泰不斷遭受專制政體的損害,但他總是不能牢記教訓。1750年,他又懷著對開明君主的幻想,接受了普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請來到柏林。他被當做宮廷的點綴品加以利用後,又遭到了這個專制君主的侮辱。一連串的教訓終於使他總結出了這樣一條經驗:“在這個地球上,哲學家要逃避惡狗的追捕,就要有兩三個地洞。”他分別在洛桑、日內瓦以及法國瑞士邊境的菲爾奈購置住所,慶幸自己“終可倖免君主及其軍隊的搜尋”。
從此,伏爾泰進入他戰鬥的晚年,他繼續寫作了不少重要的作品,他著名的哲理小說就是產生於這個時期。特別是從1760年後,他定居在菲爾奈這塊官方難以追捕的地方,從事寫作的同時,又進行了政治社會的鬥爭。當時,整個法國和歐洲不時流傳著一些化名或匿名的文章和小冊子,猛烈地抨擊反動教會的宗教迫害、專制政體的草菅人命等黑暗現象,它們都是來自菲爾奈,出自伏爾泰的手筆。反動政府不斷焚毀這些小冊子,但它們仍不斷出現。伏爾泰這種抨擊時事、製造進步輿論的活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762年,反動教會製造了十八世紀有名的宗教迫害冤案卡拉事件,伏爾泰對這個慘無人道的案件進行了有力的控訴,為蒙冤死去的卡拉及其受迫害的全家的昭雪而鬥爭,在整個歐洲贏得了崇高的聲譽,菲爾奈成為歐洲輿論的中心,進步人士尊稱伏爾泰為“菲爾奈教長”。1778年,伏爾泰像一個“知識界的王者”凱旋式地回到巴黎,並且在他的悲劇《伊蘭納》上演的時候,受到了觀眾的歡呼和加冠,達到了光榮的頂點。不久,他於同年的五月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法國“七星叢書”所收集的伏爾泰的全部哲理小說共廿六篇。其中較早的幾篇:《如此世界》、《梅農》、《小大人》、《查第格》寫成於他去柏林之前,在蘇城曼納公爵夫人家避風的期間,其他的一些篇,包括《老實人》、《天真漢》、《耶諾與高蘭》、《白與黑》,則都是寫於他的晚年,主要是在菲爾奈的時候。我們知道,伏爾泰生前是以史詩詩人和悲劇詩人著稱的,他把史詩和悲劇的創作視為他最主要的文學工作,而把他這些中短篇的哲理小說當作他的“小玩意”、“兒戲之作”,當他在曼納公爵夫人的府上朗讀最初幾篇短小精悍、哲理洋溢、意味雋永的小說受到歡迎、被聽眾要求付印時,他曾再三拒絕,認為不值得出版。然而,從十九世紀上半葉以後,伏爾泰的悲劇和史詩早已沒有多少人去讀了,但他的哲理小說卻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特別是他的《查第格》、《老實人》、《天真漢》,已經成為十八世紀啟蒙文學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作而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的寶庫,被廣大讀者視為人類精神的傑作。
顧名思義,哲理小說的特點在於以闡明某種哲理為目的,而伏爾泰的哲理小說則是以宣傳其啟蒙思想為目的。在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中,伏爾泰並未像後來的狄德羅和盧梭那樣,為資產階級革命所必需的思想理論體系的建設作出顯著的貢獻,提出一系列正面的主張和方案,而是為廓清這一基地對封建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進行了掃蕩和破壞,他以此為己任,在自己書信的末尾幾乎都加上了縮寫的“剷除卑鄙”的口號。他的哲理小說正是他這種戰鬥精神的最好體現,特別是因為這些小說寫於他閱歷已深、學識豐富、思想成熟的老年,其闡明哲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藝術已達爐火純青的程度,這就使得它們成為了伏爾泰得心應手的戰鬥武器。
作為這樣一種思想武器,伏爾泰的哲理小說總是用來揭示十八世紀法國封建社會的不合理。他的第一個重要的短篇《如此世界》雖然寫的是一個神話故事,但卻表現了伏爾泰自己對法國社會現實的觀察和分析。小說中的柏塞波里斯城就是影射巴黎,小說所揭露出來的種種黑暗現象就是法國的現實。
同樣,中篇小說《查第格》的故事雖然偽托於古代,但也有著現實社會的影子。查第格婚後不久愛人就變心,甚至想把他的鼻子割下來給新情人治病的情節,是對法國上流社會腐敗的男女關係的諷刺;查第格幾次無辜被捕入獄、險些送命的經歷,是暗指當時司法機構的草營人命;小說中國王寵信淫邪放任的女人,把國事敗壞得一團糟,是對國王路易十五耽於聲色的影射。伏爾泰通過查第格主觀上力求“明哲保身”、但災禍總是不斷降臨頭上的經歷,企圖表現出一個政治黑暗、人情險惡、人人都不得自由、不得安寧的社會現實,小說中這一社會圖景正是伏爾泰所生活的法國君主專制社會的寫照。
《如此世界》和《查第格》中揭示現存社會不合理的主題,到了《老實人》中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深化。《老實人》是伏爾泰哲理小說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它以“一切皆善”的學說為對立面,把原來的主題提升到了新的哲理的高度。“一切皆善”的說教來源於德國十七世紀唯心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他曾提出“上帝所創造的這一個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這是一種維護現存秩序、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輿論。伏爾泰的這篇小說就是無情地嘲笑這一為神權和王權辯護的哲學。他在小說里安排了兩個主要的人物:鼓吹這種哲學的邦葛羅斯與信奉這種哲學的老實人,通過這兩個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歷,證明這個世界並不完善。面對著這樣的世界,老實人覺醒了,對那個可悲的哲學家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樂天主義了”,他最後作了這樣的總結:“地球上滿目瘡痍,到處都是災難啊”,而這,也正是伏爾泰對自己的時代社會發出的感慨!
在批判揭露的針對性方面,《天真漢》比其他的哲理小說又更為直接,它既不是通過半神話式的故事、偽托於古代的異國,也不是通過影射和旁敲側擊,而是把故事安排在十七世紀末路易十四的法國,對社會現實進行了直率的指責和批判。在這裡,作者巧妙地通過一個在加拿大未開化的部族中長大的法國血統的青年的天真性格與法國社會現實的矛盾,表現了這個高度封建文明化國度的荒誕。這個天真漢“想什麼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純樸的思想習慣,竟然為周圍的社會習俗、宗教偏見所不容,這就足以揭示這個社會的荒誕、不合理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而他按照這個社會要求、以聖經為自己行為的準則、天真地按聖經行事時,卻偏偏引起了駭世驚俗的後果,這就更有力地暴露了在封建專制社會生活中,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標準與是非標準,暴露出是非的顛倒、表里的不一、理性的淪喪以及“宗教德行”的虛妄、宗教狂熱的荒謬。
伏爾泰是一個明顯具有兩重性的作家,他既是封建專制政體的反對派,又是歐洲君主的座上客;既是貴族階級凌辱的對象,又是他們尊奉的文化知識界的頭面人物;既是一個勤奮的智力勞動者,又是一個從投機商業中牟取了巨額錢財的資產者。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的思想的複雜,在他的哲理小說里,就是強烈的反封建性往往與明顯的保守性是那么尖銳地同時並存:
如,在《如此世界》中,他雖然影射法國的現實,進行了尖銳的揭露,但與此同時又在不合理的現實中去挖掘合理的因素,一方面把用來影射巴黎的柏塞波里斯城描寫成一個墮落的、本來應該招致神怒而遭毀滅的城市,另一方面又描寫這裡有“賢明的君主”、有“連續不斷辛苦了四十年、難得有片刻安慰的大臣”。小說的最後,又由神決定“讓世界如此這般下去”。
又如,在《天真漢》中,伏爾泰世界觀中的缺陷也在主人公的身上打下了烙印,使這個人物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如對君主的看法、對宗教和教會的看法上,帶有濃厚的保守色彩,他雖然身受專制政體的迫害,他的愛人也是這個罪惡制度的犧牲品,但小說的最後,“由於特·路伏大人的提拔,天真漢成為一個優秀的軍官,得到了正人君子的讚許”,也就是說,他被統治階級籠絡過去,成為貴族上流社會的一員,而這個社會本來是與他純樸的性格完全對立的。伏爾泰最後讓貴族資產階級的“文明社會”同化了主人公的天真,天真漢和現實社會的妥協,也正反映了伏爾泰思想上的妥協。
再如,即使是在伏爾泰的理想的黃金國里,也有“賢明的國王”,看來,他把這一點看作是黃金國之所以成為幸福國度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查第格》里,為什麼主人公會有種種不幸的經歷?伏爾泰認為原因在於沒有賢明的君主,對國家的管理不當,後來查第格當上了宰相,以哲學家的方式治理國家,允許言論、信仰自由,反對教派成見和宗教狂熱,最後又當上國王,成為了一位賢君:“從此天下太平。說不盡的繁榮富庶,盛極一時。國內的政治以公平仁愛為本。百姓都感謝查第格”。伏爾泰通過這一番描寫顯然是企圖說明,改變現實的最可靠的途徑就是開明君主政治。從《查第格》到《老實人》,我們可以看到伏爾泰始終沒有擺脫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幻想,即對開明君主的嚮往,並且一再把它作為解決現實矛盾的方案。
不過,伏爾泰畢竟是一個吃了君主專制政體不少苦頭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雖然懷著開明君主的幻想,但他在現實生活中卻找不到這樣的君主,相反,他所見識過的歐洲封建國君還一一使他受過損害和屈辱,那么,如何才能消除現實生活的不合理、如何才能建立比較合理的生活呢?也許是由於以上原因,他在自己的哲理小說里,似乎並沒有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與黃金國同樣遠渺微茫不可求的開明君主的身上,而是進行了新的探索。他把自己探索的結論寫在《老實人》的結局中。最後,老實人和他的同伴經歷了現實生活的種種苦難、見識了滿目瘡痍的世界後,結成了一個小小的團體在一起生活,他們買下了一小塊土地分工負責進行耕作,他們不時也探討生活的意義,結果認為只有工作才能使人“免除三大害處:煩悶、縱慾、饑寒”,因此,得出了“種我們的園地要緊”這樣的結論,並且把它當作了他們生活的信條。這個結尾可以說是伏爾泰哲理小說中最意味深長的片段,“種我們的園地要緊”這句話也具有著某種箴言式的概括性,既是伏爾泰所提出的醫治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方案,也是他所主張的人對生活應該採取的態度。作為醫治不合理社會的方案,它顯然比對開明君主的幻想來得腳踏實地;作為對待生活應採取的態度,它在當時統治階級糜爛不堪、社會風氣腐敗惡濁的歷史條件下,也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不妨說,它正是當時整個一代資產階級進步人士、啟蒙思想家那種實幹的精神和努力工作的態度的某種富有詩意的概括。
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是藝術品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是一部作品具有持久藝術生命力的根本保證。在伏爾泰的哲理小說創作中,他沒有模仿某種過時的僵化的文學傳統,而是根據其啟蒙思想內容的需要,找到了適合的藝術形式,通過短小精悍的篇幅、靈活自如的敘述、滑稽的筆調,在半神話式的或傳奇式的故事裡注入哲理寓意,達到影射諷刺現實、宣傳啟蒙思想的目的,這就使他的哲理小說同時具有了高度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
文學創作之高低,本來就有莎士比亞化與席勒化的區別,而以闡釋哲理為目的的作品往往就更容易流於概念化和直接說教。伏爾泰的哲理小說在藝術上的可貴處首先在於避免了這種通病。他既善於通過形象來表現哲理,也善於從生活形象中發掘哲理,因此,他在小說中極少有直接的說教,總是讓形象本身向讀者啟示某種寓意,而且,還應該承認,小說中的某些哲理本來是很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形象來加以表現的,而伏爾泰在這方面也做得頗為成功。如他在《如此世界》里要說明現實社會善惡並存的複合狀況,就構思出這樣的情節:主人公用最名貴的金屬和最粗劣的泥土石子混合起來,塑造一個小小的人像,去向神靈匯報,而他表現“讓世界如此這般下去”這一妥協改良的思想,則是通過主人公向神靈的這樣一段陳詞:“你是否因為這美麗的人像不是純金打的或鑽石雕的,就把它毀滅掉。”在這一段描寫里,我們盡可以指出伏爾泰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的局限性,但不能不承認這裡有著巧妙的藝術構思。
要選擇合適的形象表現哲理,最重要的是要求形象本身具有典型性、概括性。伏爾泰在哲理小說中成功地做到了這點,他所運用的形象一般都能表現出事物的本質,他所描繪的人物都能體現十八世紀社會階級關係的真實。他寫貴族、寫教士都抓住了該類人物的本質特徵,用簡短的幾筆就突出了要害;他寫專制政治的黑暗、天主教會的反動、殘酷,都是通過典型的事例,足以給讀者造成強烈的印象;而他寫世態人情,往往選用最有代表性的細節,略加描述,即烘托出整個的風氣。因此,在他的哲理小說中,頗不乏藝術典型化的精彩片斷。
伏爾泰哲理小說中的形象描繪既具有優秀文學作品都具有的典型化的共性,也具有伏爾泰本身的特點,誇張滑稽,意味雋永。伏爾泰的描述有時近似漫畫,他對細節的真實毫不在意,總是採取誇張的手法,把他描寫的對象的某種特徵加以誇大,雖然並不構成酷似現實的圖景,但卻突出對象的本質。由於他是以不合理的現實作為描寫對象,因而他常常把那些不合理的東西誇張到了荒誕的地步,以荒誕的敘述來表現十八世紀沒落的封建專制社會的荒誕本質。這種荒誕圖景的色彩不是陰森可怕、壓抑低沉的,而是充滿著作者的嬉笑、揶揄和嘲諷,呈現出一種滑稽的基調,一種明亮的色彩。
伏爾泰的哲理小說顯然深受《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在體裁樣式、結構形式和敘事方法上,伏爾泰都從這一部東方的故事集裡得到不少借鑑,他的哲理小說敘事流暢自如,簡繁得當,傳奇色彩很濃,頗能引人入勝。他顯然還從拉伯雷那裡吸取了營養,繼承了十六世紀這位人文主義作家那種開朗樂觀的精神和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潑辣風格,只不過他不及拉伯雷那樣氣魄宏大,風格粗放,而多一層十八世紀那種精緻的文明化的色澤。至於伏爾泰的哲理小說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既然二十世紀有位優秀的法語作家曾經這樣講過,“因伏爾泰之功,法語才得以在十八世紀中風靡全歐,才成為語言的光榮”,那么,我們也就無需再作其他的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