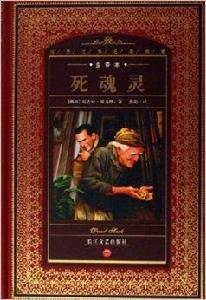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死魂靈》是“俄國文學史上無與倫比的作品”,是俄國文學走向獨創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標誌。它的問世,猶如響徹萬里長空的一聲霹靂,“震撼了整個俄羅斯”。
果戈理是19世紀俄國著名的戲劇家和小說家,他以“極度忠於生活”的現實主義精神、鮮明生動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淚的諷刺手法,成為“寫實派的開山祖師”。
《死魂靈》入選法國《讀書》雜誌推薦的“個人理想藏書”書目。
作者簡介
作者:(俄國)尼古拉·果戈理 譯者:魯迅
圖書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附錄
一 “死魂靈”第一部第二版序文
二 關於第一部的省察
三 第九章結末的改定稿
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文摘
書摘
省會NN市的一家旅館的大門口,跑進了一輛講究的,軟墊子的小小的篷車,這是獨身的人們,例如退伍陸軍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著百來個農奴的貴族之類,——一句話,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紳士這一類人所愛坐的車子。車裡面坐著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卻也不難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說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並不怎么年青了。他的到來,旅館裡並沒有什麼驚奇.也毫不惹起一點怎樣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館對面的酒店門口的兩個鄉下人,彼此講了幾句話,但也不是說坐客,倒是大抵關於馬車的。“你瞧這輪子,”這一個對那一個說。“你看怎樣,譬如到莫斯科,這還拉得到么?”——“成的,”那一個說。“到凱山④可是保不定了,我想。”一一“到凱山怕難,”那一個回答道。談話這就完結了。當馬車停在旅館前面的時候,
還遇見一個青年。他穿著又短又小的白布褲,時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產的別針連起來的,針頭上裝飾著青銅的手槍樣。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風吹去的小帽時,也向馬車看了一眼,於是走掉了。
馬車一進了中園,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國客店慣叫作夥計的,來迎接這紳士。那是一個活潑的,勤快的傢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樣一副嘴臉。他一隻手拿著抹布,跳了出來,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長的常禮服,衣領聳得高高的,幾乎埋沒了脖頸,將頭髮一搖,就帶領著這紳士,走過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樓上看上帝所賜的房子去了。
房子是極其普通的一類;因為旅館先就是極其普通的一類,像外省的市鎮上所有的旅館一樣,旅客每天付給兩盧布,就能開一間幽靜的房間:各處的角落上,都有蟑螂像梅乾似的在窺探,通到鄰室的門,是用一口衣櫥擋起來的,那邊住著鄰居,是一個靜悄悄,少說話,然而出格的愛管閒事的人.關於旅客及其個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興味。這旅館的正面的外觀,就說明著內部:那是細長的樓房,樓下並不刷白,還露著暗紅的磚頭,這原是先就不很乾淨的了,經了利害的風雨,可更加黑沉沉了。樓上也像別處一樣,刷著黃色。下面是出售馬套,繩子和環餅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確切,還不如說是窗上的店罷,是坐著一個賣斯比丁。的人,帶著一個紅銅的茶炊。,和一張臉,也紅得像他的茶炊一樣,如果他沒有一部烏黑的大鬍子,遠遠望去,是要當作視窗擺著兩個茶炊的。
這旅客還在觀察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他的行李搬進來了。首先是有些磨損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見就知道他並不是第一次走路。這箱子,是馬夫綏里方和跟丁彼得爾希加抬進來的。綏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爾希加是三十來歲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舊了的寬大的常禮服,有著正經而且容易生氣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樣的鼻子。箱子之後,搬來的是樺木塊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對靴楦和藍紙包著的烤雞子。事情一完,馬夫綏里方到馬房裡理值馬匹去了,跟丁彼得爾希加就去整頓狹小的下房,那是一個昏暗的狗窠,但他卻已經拿進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帶去了他獨有的特別的氣味。這氣味,還分給著他立刻拖了進去的袋子,那裡面是裝著侍者修飾用的一切傢伙的。他在這房子裡靠牆支起一張狹小的三條腿的床來,放上一件好像棉被的東西去,蛋餅似的薄,恐怕也蛋餅似的油;這東西,是他問旅館主人要了過來的。
用人剛剛整頓好,那主人卻跑到旅館的大廳里去了。大廳的大概情形,只要出過門的人是誰都知道的:總是油上顏色的牆壁,上面被煙燻得烏黑,下面是給旅客們的背脊磨成的傷疤,尤其是給本地的商人們,因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們總是六七個人一夥,到這裡來喝一定的幾杯茶的;照例的煙燻的天花板,照例的掛著許多玻璃珠的烏黑的燭台,侍者活潑的輪著盤子,上面像海邊的鳥兒一樣,放著許多茶杯,跑過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蠟布上的時候,它也就發跳,發響;照例是掛滿了一壁的油畫;一句話.就是無論什麼,到處都一樣,不同的至多也不過圖畫裡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讀者一定是還沒有見過的。和這相像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從什麼人,從什麼地方弄到我們俄國來的許多歷史畫上,也可以看見;其中自然也有是我們的闊人和美術愛好者聽了引導者的勸誘,從意太利買了回來的東西。這位紳士脫了帽,除下他毛絨的虹色的圍巾,這大抵是我們的太太們親手編給她丈夫,還懇切的教給他怎樣用法的;現在誰給一個鰥夫來做這事呢,我實在斷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罷了,我就從來沒有用過這樣的圍巾。總而言之,那紳士一除下他的圍巾,他就叫午膳。當搬出一切旅館的照例的食品:放著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捲兒的白菜湯,還有腦子燴豌豆,青菜香腸,烤雞子,醃王瓜,以及常備的甜的花捲兒;無論熱的或冷的,來一樣,就吃一樣的時候,他還要使侍者或是夥計來講種種的廢話:這旅館先前是誰的,現在的東家是誰了,能賺多少錢,東家可是一個大流氓之類,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阿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爺!”恰如文明了的歐洲一樣,文明的俄國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們,在旅館裡倘不和侍者說廢話,或者拿他開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