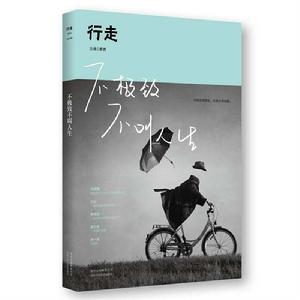內容介紹
扎西拉姆·多多:一個早晨的小小洞見,使我真正地敞開了自己,我終於願意睜開眼睛如實地去看待人生的境遇,不再神經質地小題大作,也不將其虛飾成神聖之事。
茅威濤:我只是在一點點地試探哪裡是邊界,一點點在試探看到更多的風景。每一次的跨出,哪怕是一點點,我都能感受到生命的極致。
那么你呢?是在習慣里活過安逸的一生,還是在行走里追尋極致的一生?
目錄
對話
尚雯婕×行走:瘋狂是個禮物 但不能隨意分享
足跡
紅塵:一路走到世界的巔峰
張煜:因為它就在那裡
很遠很近
金沒有:梵谷死前居住的村落
金沒有:一條深夜散步的路
攝影
邰凌軼:背影
我的極致體驗
茅威濤:一點點在試探哪裡是邊界
權振東:空中歷險記
扎西拉姆·多多:清晨八點十分
易立競:一次修行之旅
劉小七:懸崖勒馬
影像切片
泉的向日葵:殺戮中的真相
聽你怎么說
如果你進入大逃殺 你怎么界定瘋狂
你做過最瘋狂的事 你經歷過最絕望的時刻
你經歷的失控事件
視角
薏米:私奔的N種方法
小說
孫一聖:馬得木
序
費勇
《華嚴經》 雲:“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首, 為勝, 為殊勝, 為妙, 為微妙, 為上, 為無上……”意思是如果你修行佛法, 就應當做到極致。虛雲大師曾說:“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則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則不知滄海之深淺。”講的是佛法的修行、對於真理的尋求應當抱著探求究竟的態度。其實,就算你不修行佛法,做其他的事情,也應當做到極致。只有在極致處,生命才有光輝。也只有在極致處,才有可能通向最終的道路。拖泥帶水,瞻前顧後,那么,就永遠活在泥潭裡。
周夢蝶有詩:“沒有比脫軌的美麗更懾人的了。”《瘋狂原始人》里的主人公直接說,“你這樣窩在洞穴里按部就班地活著,那叫活著嗎?那叫‘沒死’”,又說,“不要躲藏,要活下去,要追隨太陽,你就能找到明天”。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洞穴里,不過這些洞穴是摩天大樓。我們的問題仍然是:因著恐懼在洞穴里安全度過一生,還是跨出洞穴隨著光明去發現未知?是在習慣里混過一生,還是在行走里活過一生?不極致的人生,是否還叫人生?
尚雯婕×行走:瘋狂是個禮物,但不能隨意分享
行:我看到人生有兩條路:一條往外走,追求物質世界的名利;一條往內,尋找自己。有些人生下來就在走一條往內的路; 有些人一心往外走,要的太多,回不來了;有些人先往外走,拿到一些他想要的東西,再往回走。
尚:我是往外走行不通,被逼回來的。我前幾年走的是所謂的大眾路線,那個時候我跟同事、合伙人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我為什麼要繼續這么走下去”。外面這條路走得也不好,裡面的也不對,我到底圖啥呢?所以我是注定走不了往外的路。
行:你要那么走,就“死”了。
尚:沒錯,我是一個從小到大,只有深刻理解我要做的事意義在哪兒,才能做成的人。大多數時候,沒有做成一件事,是因為根本不認可這個東西。像我以前唱的那首“我想我是你的女人”,還是我要求公司給我唱的,因為它是“口水歌”,可以掙錢。但我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時候就後悔了,我怎么可能是說出這句話的人呢?“我想我是你的女人”,滾蛋,誰是你女人啊!後來我就明確知道,要我去迎合別人根本就不可能,我自己都過不了自己這一關,不管掙不掙錢,我都不幹了。
行:做不喜歡的事,很會辛苦,也消耗能量;反過來是聚集能量。你等於把自己逼到一個份兒上了,得去找出路。
尚:我後來反思自己,為什麼不成功?因為沒有自己的創作,沒有自己的內容,沒有自己精神上的思考,所以我就逼著自己寫歌。那段時間我每天對自己說:“如果你不創作,你就滾出這個圈子!如果你不唱自己的歌,你就沒有資格站在那個舞台上!”內心百分之百確定必須要創作,這是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逼上梁山。
行:一個不會寫歌的人怎么創作?
尚:人把自己逼到一個份兒上了,潛力是無窮大的。我開始的時候把自己關在家裡,聽所有能刺激我的音樂,聽到整個人進入一種恍惚的狀態,就開始寫。其實我到現在都不識簡譜,一樣樂器都不會,我寫歌就哼旋律,直接錄,就用以前最古老的手機的錄音功能。
行:我聽了你最近的兩張專輯(《恩賜之地》、《最後的讚歌》),你創作的能量很驚人,並且有些東西不像是意識層面里的。
尚:很多的確不是意識層面里的,而是在潛意識裡。就像我寫歌寫了一半突然發現:“這是我寫的?好可怕。”但這是你裡面很真實的東西。這么多年來它們一直被壓著,創作是一個往內挖的過程,當你越挖越深的時候,裡面的那些慢慢出來,你發現那才是你最大的能量,才是最真實、擁有巨大力量的“本我”。
行:你說的“本我”,跟我們說的“在行走中發現自己”是一個概念。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本來的“我”,只不過慢慢走丟了,當我們跟自己相遇時,會爆發出最大的能量和力量。
尚:我在“快男”唱的那個歌《小星星》,裡面講的星星其實就是“本我”,就是在兒童時代最簡單最單純的那個“我”,那是我今後最大的一個力量來源。
行:你唱那首歌的時候,整個人在舞台上是發光的,“這條路”你找對了。
尚:如果你在一個領域的能量是零,哪怕那個領域被所有人看好,也走不動,這就是我原來在主流市場的感覺。可能我就不是“往外走”那樣的命,我必須挖掘自己、燃燒自己然後往裡面走,反而這兩年情況更好了。
行:人在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狀態是最舒服的,能量會發揮到最大,同時你也知道,什麼是你的。
尚:從我寫出自己歌曲的那一刻,腦子裡就有了一個感覺,我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從那以後,一樣東西過來,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我的,我立馬就能知道。
行:當你了解自己的時候,一切都通了,也自信了。
尚:對,以前看不清自己的時候,都是別人告訴你:“今年火這個,明年流行那個。”現在想想,多傻啊。所以當人家問我“流行是什麼”的時候,我就想告訴他,你問問自己是誰就行了。一切東西歸根到底——問你自己是誰。
行:你看,這個世界上大概有八九成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才會跟著外面的世界走。
尚:所以他們才會覺得我們很奇怪,覺得我們是瘋子。
紅塵:一路走到世界的巔峰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值得你千百次地重返,那一定是尼泊爾,喜馬拉雅。
“It's Pearl. I will be back to Pokhara!”
“我是珍珠,我將回到博卡拉!”當我在拉薩拿到簽證時,正是下午兩點陽光猛烈得把眼睛都要晃花的時候。我用手機撥了一個國際長途給博卡拉的朋友巴桑達,他的徒步公司叫安納普爾納,在喜馬拉雅山的南坡。
我的故鄉在中國的南方,那裡有一條貫穿了整個三角洲的河流叫珠江——Pearl River。
我是河流的女兒,是河流中緩慢、寂靜生長著的貝殼,貝殼裡那枚暗藏著狂野之心的小砂粒。當它抖落一身的雨水裸露在乾淨的陽光下時,它就變成了一顆閃亮的珍珠。這就是我為什麼叫Pearl——珍珠的原因,佛陀曾經把我們生長與生活的宇宙比喻成一張寬大的網、一條寬闊的河,它是由無數各式各樣的明珠組成的,每顆微小的明珠上都有無數的面相,而每顆摩尼寶珠都能反射出網上、河中的其他明珠,都蘊含著其他明珠的影像。
此時我覺得我的身體猶如一滴小水珠在溯流而上,如千百條溯流而上、回到故鄉產卵的高原冷水魚、裂腹魚。流水的盡頭是所有河流的發源地,是純淨、神聖的雪山。印度教的古詩人認為冰山雪嶺都是創造與毀滅之神濕婆的大笑累積而成的,它的笑容是晶瑩的白色,河流猶如發光的絲衣從濕婆神的頭上瀟灑流下。而當我把目光向上仰望的時候,我就看見了加德滿都,看見了博卡拉,看見了尼泊爾,看見了喜馬拉雅。
無數次地在拉薩停留,因為簽證,因為轉機。拉薩是無數旅行者的目的地,是磕等身長頭的朝聖者們的靈魂歸屬地,但它已同樣地擁擠、喧鬧、繁華。在藏語裡會很形象地稱身體為“I”,意思是“留下來的東西”,像行李一樣;在英語裡說“我”、說“自己”時,也叫“I”。當我每次在拉薩說“I”時,就好像在提醒自己,告訴自己,我只是暫時留在此地的過客或暫時住在此身的旅客,我僅僅是一個腳步的流浪者、一個編著織夢網的捕夢人、一個馭著羊皮鼓飛行的騎士,拉薩如同我靈魂的中轉站,轉世輪迴的中陰地。我身體所能安享到的短暫寧靜恰如我的前生,而我心靈的旅程卻很漫長、很遙遠,我要不停息地走過的是今生,還有來世。
從東經91°的拉薩向東經85°的加德滿都飛行的航班,會在陽光明媚的清晨10點飛越在群山起伏的喜馬拉雅上空。一字排開的10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級雪峰,那將是我此行要去尋找的精神修道之地。綿延巨大的干城章嘉峰,高出了海平面8586米,是世界的第三峰,十幾分鐘後,是世界的第四峰洛子峰、第五峰馬卡魯峰、第六峰卓奧友峰,它們如傲世的王子簇擁著昂首破入雲天的第三女神珠穆朗瑪峰。想到那些曾經攀登上珠峰的登山者們,與穿越蒼穹的空客飛機的飛行高度幾乎一樣時,不由驚嘆於人類的步履是多么的狂放恣意、異想天開。看著那一道道7000米以上的高峰築成的世界屋脊的壁壘,才知道一個一個的徒步者要從這些巨人的腳下通過而不被壓得粉身碎骨,需要何等的勇氣與胸懷。無論諾亞用歌斐木抹上松香造的方舟是停泊在《聖經》里說的土耳其的亞拉臘山,還是神秘的喜馬拉雅大神居住的雪峰,山峰都將是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一千多年前產生在喜馬拉雅山上的哲學,是把心帶回家,然後放鬆、放下。我能想像佛陀安詳而莊嚴地禪坐在雪山下的菩提樹旁,天空就在他的四周上方。而當我也像山一般地坐下來時,我的心頓時像鳥兒在天空一般升騰、飛躍、翱翔。明珠與河流、流水與山脈、天空與大地、人間與天堂,它如同我這隻飛行鳥的雙翼,賜予我的是如天空般遼闊的不死心和浩渺無限的凡塵心。
渴望從西藏荒蕪的喜馬拉雅北坡穿越樟木口岸的邊境,去到森林密布的喜馬拉雅南坡的徒步者、背包客、浪蕩子、漫遊者全都聚集在拉薩河的仙足島上,很多“藏熬”、“拉漂”混跡在這個傳說曾是仙人駐足的地方,驢友們甚至戲稱這裡是“艷遇之後的蜜月小窩”。真正的拉薩人會在河水舒緩流過的河岸邊悠閒地曬太陽、聽音樂、喝啤酒、吃燒烤。放眼望去,光影斑駁的山巒上慢悠悠移動著的羊群和牛群,像暮色降臨時來自天庭的梵音。而遠行的人則在此泊車、停留、晃蕩,再拉幫結派如同嬉皮般去到更遠的尼泊爾的“山中天堂”。
在拉姆拉錯的小酒吧里、德吉祥林的禪床上,一大群小資、憤青正圍著流浪的歌手南六在唱“我們生來就是孤獨,我們生來就是孤單”。我一直聽著南六的吉他彈唱直到暮色隱沒,直到天亮。那時薄霧黎明中的拉薩河只剩下了金色的沙礫、砂礫小坑裡的樹皮魚,還有離別時那甜蜜的憂傷。
它讓我想起西藏的大苦行僧米拉爾的一句詩:“你總是流浪,但你獲得追尋自由、幻想的心靈生活。”不管我們在水藍藍的拉薩河邊的星空和黑夜裡擁有著什麼,失去著什麼,幻想著什麼,唱吟著什麼,我心中的喜馬拉雅都不在拉薩,不在八廓街,不在布達拉宮,不在阿里。
它在路上!
野百合也有春天呀,而我最好的時光始終是在路上。
片段試讀
周夢蝶有詩:“沒有比脫軌的美麗更懾人的了。”《瘋狂原始人》里的主人公直接說,“你這樣窩在洞穴里按部就班地活著,那叫活著嗎?那叫‘沒死’”,又說,“不要躲藏,要活下去,要追隨太陽,你就能找到明天”。在21 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洞穴里,不過這些洞穴是摩天大樓。我們的問題仍然是:因著恐懼在洞穴里安全度過一生,還是跨出洞穴隨著光明去發現未知?是在習慣里混過一生,還是在行走里活過一生?不極致的人生,是否還叫人生?
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地方值得你千百次地重返,那一定是尼泊爾,喜馬拉雅。
“我是珍珠,我將回到博卡拉!”當我在拉薩拿到簽證時,正是下午兩點陽光猛烈得把眼睛都要晃花的時候。我用手機撥了一個國際長途給博卡拉的朋友巴桑達,他的徒步公司叫安納普爾納,在喜馬拉雅山的南坡。
我是河流的女兒,是河流中緩慢、寂靜生長著的貝殼,貝殼裡那枚暗藏著狂野之心的小砂粒。當它抖落一身的雨水裸露在乾淨的陽光下時,它就變成了一顆閃亮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