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吳晗
吳晗1961年春,《北京晚報》編輯部從提倡讀書,豐富知識,開拓視野,振奮精神的目的出發,請鄧拓寫一些知識性雜文。鄧拓考慮到“北京”二字和“晚報”二字的特點,就把欄目定名為《燕山夜話》。是年夏天,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也請鄧拓開闢雜文專欄。鄧拓感到力不勝任,就約吳晗、廖沫沙合作,三人各選土木,文責自負。欄目定名為《三家村札記》;署名吳南星(吳晗的吳字,鄧拓筆名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筆名繁星的星字)。《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文章的主流是積極的、健康的。它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黨的政策。其中有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有對新人新事的讚頌,有對文化藝術的鑑賞,也有少數對當時“左”傾錯誤和不良風氣的批評、諷刺,具有相當高的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寫作技巧也很好,受到讀者的歡迎。
事件開端
《三家村札記》從1961年10月開始到1964年7月結束,每人各寫20篇左右。這些文章的寫作並不是北京市委決定的,也沒有一片文章送北京市委審查過。可是,江青一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出於打倒彭真,改組北京市委的需要,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之後,進一步上掛下連,擴大到《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
事件過程
 鄧拓
鄧拓迫乾壓力,北京開始公開批判《三家村》,指資他們“利用學術文章、雜文等形式反黨反杜會主義”。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下令撤銷了《二月提綱》,《“五一六”通知》為批判“三家村”定了性。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報》開始公開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北京日報》的按語中,把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稱他們三人是“黨內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責他們“利用學術文章、雜文等形式反黨反社會主義”。同一天政治局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問題。會議最後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隨後彭真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8日,署名高炬,實則江青一手策劃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一文,在《解放軍報》發表;化名何明,實則關鋒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在《光明日報》發表。同時,上述兩報聯合刊載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材料摘編”,並加了煽動性的編者按。毛澤東明確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過,我是喜歡的。”5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文章毫無根據地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為名寫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斷章摘句,無限上綱地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叫嚷“將上有帥”,要揪出“黑後台”。在11日出刊的《紅旗》雜誌上,等在了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一時間,批判文章如潮似濤,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就此鑄成。鄧拓、吳晗、廖沫沙遭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鄧拓、吳晗含冤而死。林彪、江青一夥還在各省、市、自治區大抓“三家村”、“四家店”等,致使三家村冤案禍及全國各地的一大批作家、文人。
事件影響
在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慘遭厄運的同時,北京市及全國各地的大批幹部和民眾也受到株連,先後被打成“三家村黑幫分子”、“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夥計”等等。林彪、江青一夥以“三家村”為突破口,大搞層層揪、層層抓、追後台,上把矛頭對準
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老幹部,下把罪名強加於一般幹部、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就連給《前線》、《北京晚報》寫過稿、有過工作來往、甚至家裡有一本《前線》雜誌的,也免不了要受審查、挨批鬥。某地一位喜歡《燕山夜話》的讀者,托北京的親戚代訂了一份《北京晚報》,也被追查同“三家村”的關係。於是從山東到雲南,從廣東到黑龍江,到處揪“三家村”、“四人店”,甚至遠距北京數千里之遙的敦煌也被打成“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
民間評價
廣東詩人熊鑒為作的紀念“三家村”作的一首詩。
三家村里本無村,
留在人間卻有痕。
一自黃鐘遭毀棄,
遺音喚醒萬民魂。
粉碎“四人幫”後,廣大人民民眾尤其是學術界人士紛紛提出要為“三家村”平反。全國許多報刊先後發表文章,提出要清算“四人幫”製造的“文字獄”。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報》第三版發表了蘇雙碧寫的《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蘇雙碧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姚文的政治陰謀後說:“冤獄就是你們這些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製造的,今天我們就是要平冤獄,包括你姚文元《評新編》造成的以批《海瑞罷官》為中心的文字獄,都必須一個個地清算,一個一個地平反。冤獄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這篇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國內很多媒體都轉發了這篇文章,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播發刊登這篇文章的訊息和評論。許多讀者也紛紛寫信。一位來自雲南的老教授在信中說:“我僅僅因為認得吳晗,就被打成‘三家村’黑線,對我又批又斗又送進牛棚,差一點被折磨致死,不敢想到還有今天……真是令活著的人興奮,死去的人安慰的快事啊!”後來,新華社的一篇《一個驚心動魄的政治大陰謀—揭露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黑文出籠的經過》為“三家村”的平反起到了助推的作用。1979年2月3日,黎澎的長篇文章《一個圍殲知識分子的大陰謀—評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評》也刊出了。之後,從不同角度為吳晗及“三家村”平反的文章紛紛刊出。
冤案平反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決定。7月18日,北京市委發出檔案,宣布為“三家村”冤案平反,全文如下:
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
 吳晗和夫人袁震1939年在昆明的結婚照
吳晗和夫人袁震1939年在昆明的結婚照一、文化大革命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應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之約,撰寫《三家村札記》;鄧拓同志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以及吳晗同志寫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完全是正常的。他們的文章和著作,熱情宣傳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貫徹了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各種歪風邪氣,對廣大幹部、民眾,特別是青年進行政治教育,向讀者廣泛介紹科學文化知識,作出了貢獻。雖然他們的少數作品有缺點、錯誤,但大多數作品是好的,根本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他們之間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他們各自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
林彪、“四人幫”誣茂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同志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畫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經中央批准,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所作的錯誤結論,恢復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譽;恢復鄧拓、吳晗的黨籍,恢復廖沫沙同志的組織生活;為林彪、“四人帶”迫害致死的鄧拓、吳晗同志舉行追悼會,並發布新聞。組織專人負責清查被抄走的珍貴的書籍、文物字畫、詩稿文稿和其他財物,退還本人或家屬。
二、宣布北京市委1966年5月25日關於撤銷《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編委會和撤銷范瑾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是錯誤的。檔案予以撤銷,為上述單位和個人恢復名譽。強加於《<前線>發刊詞》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一律撤銷。
三、在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一夥的壓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編者按”的材料是不實事求是的,宣布予以撤銷。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康生一夥陰謀打倒北京市委,誣衊4月16日‘編者搖”是“假批判真包庇”.“舍車馬保將帥”等等,純屬誣陷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
四、在報刊上組織文章,批判林彪、“四人幫”一夥誣陷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罪行,肅清流毒,伸張正氣。
8月3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的訊息,摘登了北京市委的平反決定。
9月5日和14日,鄧拓及吳晗、袁震夫婦追悼會先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附:人民日報刊文
 廖沫沙與丁玲
廖沫沙與丁玲"三家村"的出現,"三家村"的長期存在,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現象。
"三家村"反黨集團,有一個妄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大陰謀。《前線》雜誌就是他們為資本主義復闢作輿論準備的一個重要工具。一九六一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四月,我曾在《前線》編輯部工作過一個時期,對於鄧拓等人的一部分活動和言論,有些了解。這裡把它揭露出來,可以幫助我們逐漸把"三家村"這個大黑幫的重重黑幕扯開。
《前線》雜誌--為資本主義復闢作輿論準備的《雜家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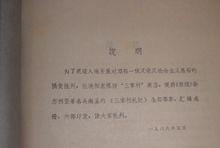 印有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文獻
印有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文獻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鄧拓在《北京晚報》上發表了《歡迎"雜家"》一文。在這篇向黨發出的挑戰書中,鄧拓代表著"三家村"反黨集團,聲嘶力竭地喊出了在他們心中憋悶了很久的聲音:"我們……應該對這樣的'雜家'表示熱烈的歡迎",應該"承認所謂'雜家'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著重點是作者加的,下同)什麼是"雜家"?所謂"雜家",就是那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分子及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資產階級"學者"之流的反動人物。這篇不超過千字的挑戰書,也就是"三家村"的"雜家"們改造《前線》雜誌的總綱領。
原來,為了給資本主義復闢作好輿論準備,鄧拓一夥還準備辦一個《雜家旬刊》,並且細緻地考慮過每個細節。也許因為這樣做起來太露骨了吧,《雜家旬刊》沒敢辦起來。可是,鄧拓把"雜家"的靈魂塞進了《前線》!請聽一聽他的自供:
"我曾經有一個興頭:辦一個雜誌,辦個《雜家旬刊》,十天出一期,八個頁面,半張報紙。每篇文章不超過千字。內容是,什麼都講,一字不空。要政治,整個的都是政治眼光貫串著,但是要生動。"這番話,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前線》編輯部紀念創刊三周年的會上講的。會後,人們還沒有走散,有人急切地向他詢問《雜家旬刊》的具體打算。鄧拓談得更露骨了:"不是為了光給人一些知識,而是廣泛談論許多方面的問題,使人從中汲取些有用的東西。搞出來的東西,要字字是炮彈。"後來,在談到如何按照這種"雜家"的靈魂"改進"《前線》雜誌的時候,鄧拓曾經進一步發揮說,在這個刊物上,要專登其它刊物所不登、所沒有的東西,要"使各方面的人都喜歡它"。
"三家村"反黨集團很懂得報刊的重要性。既要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就要網羅一批雜七雜八的人物,奪取宣傳陣地,通過報刊製造輿論,腐蝕人的靈魂,為資本主義復辟準備條件。這是他們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大陰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鄧拓心目中的《雜家旬刊》,就是"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機關報,它要搞出來的字字炮彈,都是直接射向我們黨、直接射向社會主義的。
《雜家旬刊》一時辦不起來,怎么辦?請聽鄧拓的回答:
 民眾批判鄧拓的場景
民眾批判鄧拓的場景"對於辦《雜家旬刊》,我還沒有完全死心。現在,可以從我們的刊物(即《前線》),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把'雜家'的靈魂加進去!……別的方面的東西,壓縮一下!"看吧!頑固的反革命,是要帶著花岡岩的腦袋見"上帝"的,要他們死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心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條規律。要變,就得快變。請看一九六一年《前線》第二十三期和第二十四期。"思想雜談"的頁數增多了,"背誦古文"的"琅琅書聲"被突出地報導出來了(見《燕園漫步》),吳晗的"要多讀書,用功讀書"的號召發出了,推薦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的廣告也登出來了……。僅第二十四期上,"雜七雜八"的文章就有十三頁,差不多占了整個雜誌的一半篇幅。
這樣,《前線》雜誌就在一個更大的程度上變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的宣傳工具和"機關刊物"。
由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鄧拓等人總該滿意了吧?不!他們的野心還要大,他們的要求還要多。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鄧拓在《前線》編輯部會議上又作了一次講話。他先談到當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形勢,說現在"象人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一樣,需要停一停,研究一下"。請注意"分岔路口"!在中國人民的眼裡,社會主義大道直通共產主義,哪來的什麼"分岔路口"!"三家村"反黨集團日夜夢想資本主義復辟,日夜夢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我國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鄧拓幸災樂禍,得意忘形,在這裡泄露了"天機"。鄧拓當時興高采烈,慷慨陳詞:"現在是個好宣傳的時候,不是個不好宣傳的時候,不是沒辦法的時候,應該積極樂觀。"我們知道,反動派對形勢的估計總是錯誤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如此,一九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此,"三家村"反黨集團這次仍然是如此。基於對形勢的這種"積極、樂觀"的分析,他下了動員令:"要開闢刊物自己的路子!""天下路子非常多,應該積極想辦法去宣傳,開始找的路子可能不明確,慢慢就找出來了。"
這次講話之後,《前線》更加上"綱"了,上了《歡迎"雜家"》一文中提出的總綱領。
從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開始,《前線》雜誌上陸續地增加了"知識小品"、"技藝話叢"、"求知錄"、"讀者信箱"等新的"特欄"。緊接著這次上"綱"會議,鄧拓率先示範,在十四期上拋出了他惡毒攻擊黨的大毒草《專治"健忘症"》。廖沫沙、吳晗跟踵而上,在十五期和十六期接連拋出了《志欲大而心欲小》和《再說道德》……。
從此,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發生了:有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稿件,《前線》轉給別的報刊發表了;而其它報刊所不屑用的稿子,卻可以登上《前線》。有些"銳敏"的作者,特別是屬於"雜家"一類的人物,帶著其它報刊不予發表的稿件登門拜訪鄧拓,而《前線》就很快刊用了。人好之,我棄之;人棄之,我好之。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信然!信然!
至此,"具有廣博知識的雜家"們在《前線》上更加"大放異彩"了。
至此,《前線》算是完全闖出了"自己的路子"。
"三家村"的"兄弟"是怎樣向黨發射黑槍毒箭的?
"三家村"反黨集團在進行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的顛覆活動中,有一整套狡猾毒辣的手法:"破門而出"寫"新編歷史劇",是一種;"作偽舞弊"地拋射舊貨《投槍集》,又是一種;在"三家村"黑店裡寫"札記"、講黑話,更是常用的一種。這裡,我們就來著重看看他們是怎樣運用後一種方式的。這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黨集團,他們慣用"指桑罵槐"、"旁敲側擊"的手法來鑄造毒箭。為了把進攻的矛頭"歸結及於政局",他們的文章要"發端於蒼蠅、臭蟲之微";為了達到其反黨的"政治目的"而又不露馬腳,他們的黑話要"語帶雙關"。這一點,鄧拓在《林白水之死》、《事事關心》等文中,已經透露出來。現在再看看他在內部講過的黑話。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鄧拓在對《前線》編輯部全體幹部的一次講話中,強調"要敢於發表意見"之後,很具體地講到如何利用歷史故事寫文章的問題。他說:
"現在問題很多。我們的刊物應當採取積極的精神,不管什麼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一切工作,各種問題,作為一個刊物,都要敢於發表意見。"怎么樣去發表意見呢?"不是好為人師,亂舞指揮棒,而是講一些原則問題"。關於具體的講法,他提了三點,其中特別講得詳細的一點是,"過去一些歷史上的故事,現在還可以講。可以把幾個例子,同類性質的,放在一起,進行加工,綜合在一起。使人看了是針對當前的,而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否則,現實意義不大。假如現成的故事中缺少說明問題的某一方面,要自己去找,……實在找不到,自己寫上一段話。"
這真是不打自招,真是絕妙的一段供詞!這段供詞使我們得到了一把打開"三家村"密室的鑰匙,打開"三家村"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黑話的鑰匙。為什麼以通曉歷史知識自詡的鄧拓,竟會在他的文章里任意捏造歷史事實呢?為什麼一向宣揚要尊重科學、講求真理的鄧拓,竟會在他的文章里肆意扯謊造謠呢?明白了!明白了!原來"假如現成的故事中缺少說明問題的某一方面",又找不到時,是可以"自己寫上一段話"的。不奇怪!不奇怪!因為"三家村"的主人並"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他們的黑話,寫出去讓人看,"是針對當前的",是有"現實意義"的。讀者戚益同志曾指出鄧拓的《專治"健忘症"》不是談醫道,而是談政治,《前線》編輯部按照鄧拓的授意,在給戚益同志的覆信中說,《專治"健忘症"》"是就事論事,介紹一些有關的情況和知識。"現在好了,鄧拓用自己的真話把他的假話揭穿了。這就進一步暴露了鄧拓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作賊心虛,欲蓋彌彰的醜態。
這樣做,讀者如果看不透怎么辦呢?那不是白白編造了故事嗎?不要緊,還有絕招!這就是鄧拓所一再強調的"開門見山":要開門見山地罵,開門見山地攻!要在"旁敲側擊"的題材中,提煉出一個"開門見山"的中心思想來,把它"一針見血"地刺向黨,"字字是炮彈"。請聽鄧拓的自供:
"雜談是要去找感想。……因為客觀事物中是有感想在那裡的,是有呻吟的。……關鍵是主題要好好想,其中關鍵的一句話要好好想。關鍵是要好好想想,究竟提出個什麼判斷、命題。這一句話要想透。這個想好了,必然新鮮,必然有人願意看,寫起來也一定有東西。詩、文章都是這樣,如果其中沒有箇中心、警句,那沒個寫好。要搞出一個判斷,提煉出一個中心思想來,其它的都好辦。再加上些手法,就不會失敗。包括《三家村札記》在內。"又說:"我們可以培養一些人大膽寫,寫一些一針見血的文章。……乾淨利落地一刀下去,講的很乾淨,不留痕跡。講要害,提出些有分量的結論。"這是談雜文寫法嗎?不!"刀"、"血"、"要害",一片殺氣騰騰!一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兇惡面孔!一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狠毒心腸!這是"三家村"反黨集團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術。然而,"不留痕跡"是辦不到的。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痕跡留下來了,並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鄧拓一夥是怎樣從長計議堅守陣地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鄧拓拋出了他的《三十六計》之後,收起了《燕山夜話》的招牌。難道鄧拓真的從此"洗手不乾"了嗎?沒有!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鄭板橋和"板橋體"》,就是他向党進攻的一支大毒箭。不過,從《燕山夜話》收攤以後,除了在"三家村"黑店裡繼續出售黑貨之外,鄧拓在其他報刊上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射的毒箭的確不象以前那么多了。鄧拓說他"把業餘活動的注意力轉到其它方面"去了。
轉到哪裡去了?轉入地下,從長計議,保護"三家村"老窩,堅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前線》。
鄧拓退出《燕山夜話》這塊陣地,堅守"三家村"老窩,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乘著《前線》創刊四周年的機會,鄧拓在《前線》編輯部作了一次調子低沉、語意雙關的講話。鄧拓說:
"今天是講我們本身的事。我們工作四年了,這算來是個很短的時間。但這是個很重要的開端。今後的路子還很長,誰知道還會遇到什麼問題呢?很難預料。"
這段無精打采的開場白,流露了"三家村"反黨集團的共同心情。在那時,我們國家的形勢一天天好轉了,"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處境一天天不妙了。
感慨一番之後,鄧拓對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總的精神是:要"總結經驗",保持"隊伍",堅持"陣地"。鄧拓說:"這幾年有些經驗,要好好總結。……我們有責任把辦'黨刊'的經驗好好總結起來。總結經驗,就是要把它很好地辦下去。要不要黨刊是由'黨'決定的。"
在這裡,鄧拓嘴裡的"黨",是什麼人的"黨"呢?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又要強調"總結經驗"呢?怎么不在半年前"走路到了分岔路口上""需要停一停"的時候"總結經驗"呢?因為鄧拓的反黨活動在半年前正處於狂熱的階段,而現在,則真正是到了"需要停一停"改變戰術的時候了。
鄧拓說,我們"已經有了個隊伍,雖然是個很小的隊伍,但很重要。……有了個隊伍和陣地,開了端,這是不可輕視的、重要的一點。"陣地有了,那么又該怎樣抓住這個陣地作為他們的反黨工具,怎樣使這個隊伍"忠誠"地為他們堅守陣地呢?鄧拓要求大家"要有雄心",使"靈魂有所寄託",搞一些"永久性題目","將來可以彈不虛發"。"搞好了,自然會培養出一批黨的理論戰士,將來能打仗,能獨當一面。大家都要作好準備。迎接新的任務"。看吧,鄧拓的抱負多么大!他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要做到"彈不虛發";他要培養一批"戰士",在反黨的罪惡活動中"能打仗,能獨當一面"。這樣一來,實現了資本主義復辟,他的"靈魂"就"有所寄託"了。然而他這樣的"雄心",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迎接什麼新的任務呢?鄧拓當時談到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而鄧拓自己就是個修正主義分子,共產黨的叛徒。他處處和赫魯雪夫現代修正主義集團唱一個調子,甚至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向修正主義"學習",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作政治報告的時候,曾把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者赫魯雪夫,說成是犯了錯誤可以回頭的"對革命和社會主義無限忠誠"的戰士,這樣的人,他會反對修正主義嗎?不會,絕對不會。就在這次會上,鄧拓曾以狡猾的手法向大家推薦說:"南斯拉夫的德熱拉斯,寫了一本《論新階級》,這個人還是有點東西的。要把他的書找來看看。"接著,他還宣揚說:"每個轉折時期、新舊交替的時期,修正主義就會出來。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死了,都有他最親近的人--朋友,老交情,出來修正它。按照這種說法,將來的修正主義不是會越來越多嗎?一定會越來越多!"請看,這是鼓勵大家反對修正主義嗎?鄧拓之流談反修,赫魯雪夫聽了也會暗中發笑。非常明顯,修正主義者鄧拓是在這裡表白他內心的熱烈希望,是在向他的聽眾灌輸修正主義思想,是要把他的隊伍改造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工具。
只是《前線》編輯部這個小隊伍夠用嗎?當然不夠!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鄧拓又要大家"和外邊交往要廣泛",要結交一些"基層單位的幹部","作者",以及各種雜七雜八的"朋友","要如滾雪球一樣,越交越廣,越滾越大,在各單位不斷地發現人材。……這是個大問題。"
事實上,鄧拓已經為他們的反黨集團籠絡了一些至親好友,包括某些"權威"、"大師"、"著名人士",甚至漢奸、右派,應有盡有。這些雜七雜八的人,把鄧拓當作他們的"先知"、謀士或導師。鄧拓則利用了他所竊據的領導崗位,亂舞指揮棒,拉人下水,幫他放毒。
為了把隊伍死死抓住,鄧拓還加緊"思想工作",開導大家不要怕"碰個頭破血流",要"摸真理","朝聞道,夕死可也!"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鄧拓在講話當中,曾借著找封面照片的小事發了一通感慨,說:"人狼狽一下也有好處。到處碰,碰個頭破血流,頭皮也硬了,經驗也多了,那時就好辦了。"而他著重講的問題是要"摸真理",他說,"要為了'摸真理'","真正死心塌地地鑽進去,為了真理,為了事業","現在我們就是在不斷地認識真理之中","過去的人,認為'朝聞道,夕死可也!'那么我們為何不能為追求這個'道'--真理、客觀規律而獻身努力呢!?"於是,他又提起"雄心""抱負"來,"我們要有雄心。……為什麼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會從我們熟悉的周圍的人當中產生呢?"
鄧拓在這裡講了一大堆黑話,必須給他拆穿。"摸真理"就是尋找反黨方法。"為了事業"就是為了反革命事業。"朝聞道,夕死可也"就是一旦資本主義復辟實現,雖頭破血流、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要有雄心"就是要有反黨的野心。"為什麼前途不可限量的、有成就的人,不會從我們熟悉的周圍的人當中產生呢",就是在你們所熟悉的人中,我們"三家村"的將帥有朝一日要登台篡位的,夥計們,乾吧!反革命的功勞簿上將來會給你記一大筆!
"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聯合進攻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吳晗發表了《海瑞罷官》之後,廖沫沙同吳晗之間曾在《北京晚報》上稱"兄"道"弟"地發表了一來一往的兩封公開信。不明內情的人,可能以為這"兄弟"二人見面機會不多。其實不然。這兩位兄弟以及他們的村長鄧拓,是經常"三頭對案"的。他們這樣作,是為了造成一派洶洶的氣勢,擺一副拼一拼的進攻姿態。
在"三家村"黑幫向黨發動猖狂進攻的幾年內,除了在《前線》雜誌上每期都登載《三家村札記》外,鄧拓經常放毒草的地方是《北京晚報》;吳晗則著力於在《北京日報》和《北京文藝》上寫文章、登劇本,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併到處遊說講演;廖沫沙緊緊抓住《前線》不放,在上面大放毒草。這種各有分工的作法,是互不聯繫地單幹嗎?不!他們是密切配合的聯合進攻。
"三家村"反黨集團,把持著反黨陣地的《前線》,同時使用《北京日報》,使用《北京晚報》,瘋狂地幹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三位老闆,情投意合,得心應手,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吹捧。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前線》創刊三周年的時候,廖沫沙在第二十二期《前線》上借《"孔之卓"在哪裡?》的雜文,給鄧拓的《燕山夜話》大出廣告;鄧拓則授意他所主編的《前線》雜誌,吹捧吳晗主編的塞滿毒草浸透毒素的《中國歷史小叢書》,說"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是"普及歷史知識的良好途徑",說它"注意到了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在今天社會條件下對人民的意義和作用,使讀者從歷史實際的學習中,取得有益的營養,懲前毖後,溫故知新,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在對廣大工農兵民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槍斃"革命民眾的意見方面,"三家村"反黨集團表現得極為兇狠。
一九六二年五月,吳晗寫的《說道德》在《前線》上發表後,編輯部收到了許多批判這株毒草的來信來稿。鄧拓看過這一大疊民眾來信來稿之後,大筆一揮,指令編輯部把它全部轉給吳晗去"處理"。吳晗的處理辦法,是來了一個《再說道德》,繼續放毒!
為了讓編輯部的工作人員馴服地承認這種"處理"方法的高明,鄧拓在六月二十六日對編輯部全體成員的講話中明確地指示說:"路子窄,那是人走出來的;本來它是寬的。爭論性的文章可以登",但是"不一定文章和反駁的意見都登,可以只登一面。"按照這種"可以"的作法來看,只許吳晗一而再地放毒箭,而不許別人吭一聲;只許鄧拓用"狗血"淋我們的"頭",用西洋棍棒把我們打"休克",而不允許別人說一個"不"字。
一九六二年初,廖沫沙對當前報刊工作的"意見",在《新聞業務》上登出來了;一九六三年初,吳晗的《學習集》編印出版了。從鄧拓事後談話中片言隻語地說起這兩件事的口氣看,廖、吳在事前都是曾向鄧拓請示過的。鄧拓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對《前線》編輯部幹部講話的一開頭,就提到:"《新聞業務》上登了沫沙對報紙工作的意見,我早就告訴過沫沙,有些意見只可以內部談談,何必把它寫出去!"在吳晗的《學習集》出版後,鄧拓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曾經勸告過吳晗,叫他不要把《說道德》的文章收進集子裡去。可是他不聽!這事還得惹麻煩!"畢竟是長期辦報刊的老手鄧拓詭計多端,油滑老練,比他的"兄弟"們警惕性高!可是,你們既然幹了那么多壞事,豈能逃脫了"麻煩"!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吳晗的兩次《說道德》和《海瑞罷官》已經臭名昭著,形勢顯得很緊迫。要保護住"三家村"反黨集團的全部車馬將帥已經不成,這時,在導演者的直接指使之下,鄧拓先以"金世偉"的化名寫了批判吳晗道德繼承論的文章,後來又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改頭換面,以"向陽生"的化名發表了那篇臭名遠揚的假批判文章,演出了"周瑜打黃蓋"的醜戲。"三家村"反黨集團有領導、有計畫、有組織地且戰且退了。
是誰給"三家村"黑店發了營業執照?
鄧拓一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並不是偷偷摸摸地乾的,他們並不是開地下工廠。很明顯,他們的活動,肯定是有人指使,有人支持,有人庇護的。《前線》雜誌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辦的理論刊物。令人不解的是,在國內外階級敵人大刮黑風的時候,鄧拓、廖沫沙和吳晗為什麼能夠在《前線》上連篇累牘、一期不漏地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如果不是有誰在積極支持他們,他們能夠這樣做嗎?
我們要問:是什麼人,為著什麼目的,存著什麼野心,給"三家村"黑店發了營業執照?
對這些嚴肅的問題,必須做出回答!
我是一個曾經在《前線》編輯部工作過的人員,我感到有責任把我知道的"三家村"的一些內幕揭發出來,我也希望《前線》編輯部的其他工作人員中一切願意革命的同志,都堅決地站出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同"三家村"的前台、後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徹底決裂,大膽揭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和陰謀活動。
我們一定要打垮"三家村"反黨集團,一定要剷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一定要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