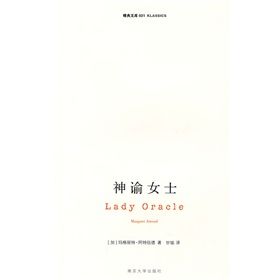編輯推薦
從胖女孩到瘦女孩,從紅頭髮到泥漿色的棕發,從倫敦到多倫多,從波蘭伯爵到激進的丈夫——瓊·福斯特完全被自己在生活中的多重身份搞得混亂了。她決定逃離一切,去往義大利的一個山城,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然而,首先她必須籌劃自己的死亡……內容簡介
一個女孩從小到大不斷試圖掙脫束縛,逃離現有的生活,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樣子過自己的人生。然而當她從肥胖到纖瘦;從紅頭髮到棕色頭髮;從多倫多到倫敦再到多倫多;從與情人同居到與丈夫結婚,又到婚外戀;從默默無聞到一夜之間成為知名女作家,她發現自己始終過著多重生活,從未擺脫過往,直到被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塗,疲憊不堪。她決定逃到義大利去過安穩的生活,並為此精心設計了自己的死亡……然而她驚訝地發現,自己依然無法擺脫過去……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於加拿大渥太華,早年在安大略北部和魁北克度過,1962年獲哈佛大學文科碩士學位,曾任加拿大作家協會主席。她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其作品迄今已在全球35個國家出版。她曾推出3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說、詩歌與批評散文。她的小說《女僕的故事》、《貓眼》與《別名格雷斯》曾獲得加拿大的吉勒爾獎與義大利的普雷米歐·蒙德羅獎,《瞎眼刺客》曾獲2000年英國布克小說獎。媒體評論
如果你覺得只有朝九晚五的現實生活最安全,你也許並不欣賞她的書。然而,如果你希望超脫這些現實,試試讀她的作品。——COSMOPOLITAN
當代英語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GermaineGREER
敏銳,有趣,聰明,坦誠,反諷。
——SCOTLANDONSUNDAY
精彩書摘
第一部第一章
我精心策劃了自己的死亡。這與我的人生不同——我的一生被各種事情纏繞,迂迴曲折,我曾經乞望掌握它,卻無濟於事。我的一生,就像巴洛克式鏡子鏡框上的漩渦和彩飾,遵循著最簡單的路線,不斷蔓延,鬆弛而且軟弱。恰恰相反,我希望我的死亡是優雅、簡單、樸素的,甚至可以有點兒莊重,像貴格會教會或我十五歲那年讀到的時裝雜誌大肆渲染的樸素黑裙子(上面只有一串珍珠)。這一次,沒有人吹喇叭,沒有擴音器,沒有閃閃的衣飾,不會懸而未決。我要不留痕跡地消失,留下一副軀體的幻影,人人都會誤以為這個影子就是赤裸裸的現實。起初,我以為自己已經做到了。
抵達特里莫多的第二天,我坐在室外的陽台上。我本來想來個日光浴,甚至幻想自己成為地中海的一道亮景——披著一頭金棕色頭髮,嬉笑著昂首闊步投向那淺綠色的海洋,將我的過去拋下,最終無所牽掛。但我突然想起自己沒有防曬霜(最高防護級別那種:沒有它我會曬焦或起雀斑),於是只能用吝嗇的房東提供的那幾條浴巾蓋住肩膀和大腿。我沒帶游泳衣,但穿著文胸和內褲也行,我想,反正路人也看不見這個陽台。
我對陽台情有獨鍾。我覺得,如果能夠久久地站在屬於我的陽台上該多好,身穿白色的拖尾長服,最好天上掛著一輪上弦月,那么一定會有事情發生:音樂響起,一個影子會出現在陽台下,一團柔軟而昏暗的影子,它向我爬來。而我就倚著陽台那鍛鐵圍欄邊顫抖,充滿恐懼、希望,不忘優雅。但這個陽台卻浪漫不足,它那幾何形的圍欄,就像50年代中等收入人士的公寓樓上的圍欄,鋪著水泥的地板已經開始腐蝕。小伙子可不會站在這種陽台下面,彈起琵琶渴望得到愛情,或叼著一朵玫瑰、袖子裡藏著短劍爬上來。而且,陽台距離地面才五尺高。可能來拜訪我的任何神秘人,更有可能沿著從高處的大街一直延伸到我的房子的一條崎嶇小徑走來,踏了一腳的煤渣。玫瑰或小刀,只存在他的想像中。
我覺得那至少是阿瑟的風格,他只會嘎吱嘎吱地走來,而不會爬上來。如果我們能重回到以前的樣子,回到他沒有變之前,那該多好……我幻想著他來找我,開著一輛租來的菲亞特汽車繞著山路而上行,那輛車肯定有些毛病。他會遲些才告訴我這輛車有哪些毛病,在這之前我們會埋入彼此的懷抱中。他會把車停放在距離牆儘量近的地方。下車前,他會從倒後鏡中看看自己的臉,調整一下自己的神情:他從來不願意出洋相,而且他總是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出洋相。然後他會從車裡鑽出來,鎖好門,防止他那並沒有裝多少錢的皮箱被盜,將鑰匙放進內衣夾克口袋裡,環顧左右。然後,他會古怪地低著頭急行,好像要躲避別人扔來的石頭或一扇低矮的門,鬼鬼祟祟地經過那道生鏽的門,小心翼翼地沿著小路走來。他經常會在國際口岸被人截住,就是因為他看起來偷偷摸摸,沒錯,十足一個間諜。
我眼前浮現出這樣的情景:消瘦的阿瑟下坡朝我走來,穿著他那蹩腳的鞋子和破舊的棉內衣,一臉木訥、不確定,權當自己是救世主,而且還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這裡。我哭了。我閉上雙眼:就在我的前方,在一片廣袤無垠的湛藍(我發現這是大西洋)的對岸,正是我拋棄在人世的每一個人。當然他們都站在沙灘上,我看過不少費里尼的電影。海風吹拂著他們的頭髮,他們微笑著朝我揮手叫喊,我自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阿瑟離我最近,他身後是身披長斗篷、不可一世的皇家豪豬(他還有另一個名字查克?布魯爾);還有山姆、馬琳和其他人。勒達?斯普羅特焦躁不安,我還可以看見費雷澤·布坎南的胳膊肘(上面打著皮革補丁),從他藏身的一片海邊灌木叢里露了出來。更遠的地方是我的母親,穿著深藍色衣服,戴著一頂白帽子,她身旁是父親模糊的身影,和我的盧姑媽。他們當中只有盧姑媽沒有看著我,她正沿著沙灘走著,做著深呼吸,欣賞海浪,偶爾停下來倒掉鞋裡的沙子。最後,她把鞋子脫了,穿著那身狐皮衣,戴著羽毛帽,腳上只穿著長襪,繼續走向遠處一個賣熱狗和橘子水的貨攤——那貨攤仿佛地平線上的海市蜃樓在召喚著她。
但除了盧姑媽以外的其他人,我都弄錯了。他們是微笑著互相揮手,而不是向我揮手。難道唯心論者並不可信,逝者對活著的人一點兒也不感興趣?雖然他們其中一些人還活著,而我才是被大家認為死了的人。他們本應該在哀悼我,但看起來卻如此興高采烈,這不公平。我試圖弄一些不祥的東西到沙灘上——一塊龐大的石頭像,一匹失足的馬——但毫無用處。事實上,這並不太像費里尼電影,反而更像我八歲時看的迪斯尼影片,講的是一頭鯨希望在大都會歌劇院獻唱的故事。他游向一條船,唱起獨唱曲,但水手們用魚叉戳了他。他每發出一個聲音,身體就化成不同顏色的靈魂,朝著太陽漂浮而去,他仍在歌唱。我猜這部電影叫《想在大都會歌劇院唱歌的鯨》。當時我哭得聲嘶力竭。
這樣的回憶的確讓我一發不可收拾,我從來學不會優雅地、安靜地哭,讓珍珠似的淚水從明眸中沿著臉頰滾下,就像《真愛》漫畫書封面畫的一樣,臉上不留污點與淚痕。我希望自己能這樣,那我就可以在人前哭泣了,而不用躲到浴室、黑暗的電影院、灌木林中或空臥室里,埋在床上的宴會服里哭。只有靜靜地哭泣,人們才會憐憫你。可我呼哧呼哧地哭著,雙眼變成熟西紅柿的顏色和形狀,抽著鼻子,握緊拳頭,呻吟著,讓人難為情。最後我成了一個小丑。悲痛總是真實的,但它卻表現成一場滑稽表演,就像白玫瑰加油站已經開敗的彩虹玫瑰,一去不返……高雅的哭泣和戴假睫毛一樣,是我永遠學不會的一門藝術。早知如此我應該請一位家庭女教師,應該念完書,應該在背上綁上一塊木板,學會水彩畫和自我控制。
人無法改變過去,盧姑媽曾經這么說。啊,但我多想改變過去,這是我真正希望做的一件事。緬懷過去讓我震顫:天那么藍,陽光照耀,左面一窪玻璃碎片閃著波光;一隻長著閃爍藍眼睛的綠色小蜥蜴趴在欄桿上,溫暖著它那冰冷的血液;山谷里傳來一聲叮噹脆響,一聲撫慰的牛哞,異鄉人平靜的聲音。我安全了,我可以重新開始。但我卻坐在陽台里,坐在一扇我出生之前就已經破碎掉的廚房窗邊,坐在一把鋁管和黃色塑膠帶做成的椅子裡,哽咽著。
這把椅子是房東維多尼先生的,他對不同顏色墨水的氈頭墨水筆——紅色、粉色、紫色、橙色——情有獨鍾,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共鳴。他總是用自己的筆向鎮上其他人炫耀自己有文化,我則用它來寫清單和情書,有時兩者兼顧,“我去買些咖啡了,×××”。想起這樣的購物經歷已不再復返,我更加悲傷……柚子切開兩半兩人分享,加上一顆如肚臍眼一般的紅黑色櫻桃,阿瑟總習慣讓它滾到盤子邊上。統統已成往事。我討厭吃的麥片粥阿瑟卻讚不絕口,粥煮糊了,結成一塊塊,因為我沒有聽他的建議,用了雙層蒸鍋來煮,這也成往事。多年來我笨手笨腳做的早飯,逝如雲煙,永不復返。這么多年來被我糟蹋的早餐啊,我為什麼這么笨呢?
我意識到自己來了全世界最不該來的地方。我本來應該到一個新鮮、純淨的地方去,一個我從未到過的地方。但我卻回到同一座小鎮,甚至同一間屋子,這間我們去年一起度過夏天的房子裡。一切都沒變:我不得不在同一個雙爐曰的爐子上做飯,用同一個煤氣罐,它總是在飯煮了一半的時候熄滅;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它的光漆面上還留著我以前粗心放上熱茶杯而燙下的白色圓環;在同一張床上入睡,床墊因年月久遠和許多租客的苦悶而起了皺褶。阿瑟的幻影纏繞著我,我已經聽見從浴室傳來微弱的漱口聲,聽到他在陽台上拉椅子發出的玻璃嘎吱的聲響,他正等著我從廚房視窗遞給他一杯咖啡。只要我睜開眼,轉過頭,他一定會在那兒,拿著報紙,距離自己的臉六英寸,膝蓋上放著袖珍字典,左手食指伸進(也許吧)耳朵里,他總是否認自己這個下意識的動作。
都是我的愚蠢,我的錯。我本該乘上灰狗大巴,到突尼西亞或加納利群島,甚至邁阿密海灘去的,再入住酒店。但我卻沒有這般毅力。到一個沒有線索、沒有標誌地、完全沒有過往的地方,那簡直與死亡無異。
這時,我正把臉埋進房東的一條浴巾里,抽搐著流淚,還用另一條浴巾蓋住自己的腦袋。這是老習慣了,我以前總是在枕頭下哭泣,不讓別人發現。但透過浴巾我聽到一陣奇怪的嘀嗒響,可能已經響了好一會。我聽著,聲響停了,我拿起了浴巾。在我的腳踝一般高、距離只有三英尺的地方,升起一個老人的腦袋,他頭戴一頂複雜的草帽。他那略顯蒼白的雙眼盯著我,露出的神色或是驚慌,或是不以為然。他的嘴半張著,牙齦的地方成了凹陷。他一定聽見我哭了。也許他以為,坐在陽台上身穿內衣褲、用毛巾遮著身體的這個女子受到了襲擊。他或許以為我喝醉了。
我沮喪地笑了笑,讓他放心,然後抓起周圍的浴巾,試著從鋁椅子裡站起身,這才記起如果一掙扎,這椅子就會摺疊起來,太晚了。我丟掉了幾條浴巾,最後才成功地退回到門裡去。
我認出了那個老人,就是每星期有一兩天下午來照料房子下面那片乾枯草坪上的朝鮮薊的老人。他會用一把生鏽的剪子除掉長高的雜草,剪掉朝鮮薊長成的堅韌的穗。和鎮上其他人不同,他從來不和我講話,也不會問候一句,他讓我毛骨悚然。我在門後從落地窗外看不見的地方穿上衣服,走進浴室用一條潮濕的毛巾擦了臉,用房東先生的衛生紙擤擤鼻涕,然後到廚房裡沏茶。
到這兒以後,我頭一次感到恐懼,這遠不止是重返故地的壓抑感,而是危險。我明明沒有消失,卻自以為如此,這並不是件好事,而且問題在於:如果我認出了那位老人,可能他也認出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