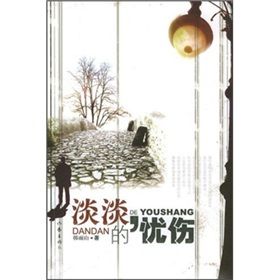內容簡介
說他沒文化,他辦事賊講究;說他人講究;他指定靠不住 比較四方人物性格,東北人確是敢於表現勇於尷尬的楷模。東北沒有少年。東北人一出生就老了,你不老也得裝老,只有裝得老才能過一生。你看看作品中的韓雨山,一夜之間揮霍了多少兒女情長,你再看看作品外的韓雨山,一個二十幾歲的東北少年,人已經是一座火山噴過,正初歇在天邊,若隱若現,走近他容易,真要靠近他卻已經很難很難。還是常言說得好,惟有憂傷,或許淡淡。媒體評論
韓雨山的這部小說讓我看了,無論是喧囂騷動也好,世事如煙也好,作家絕不會在社會記錄的層面上止步不前,他總是穿過重重屏障,找到那些內心的震撼和彷徨。——宗仁發韓雨山的小說很獨到,其實文學本身就不應該完全描寫生存狀態的美觀,但是背後的表達延伸之後應該隱含一些這樣的領悟。這篇小說是一種任性化的寫作,放任自由,肆無忌憚。但文字的本身被誇張了,使文字顯得更加真實和豐富。在文字浮華的背後,給人的衝擊和觸動一定是非比尋常。
——朱大河小說到了韓雨兇手上,已經變成了生活和身體的意識流,自由得沒有了堤壩。這樣的文本對我所追求的小說技能形成了巨大的這裡,小說已經沒有了緊,而是一味地松,松到可以看見寫作是一種享受,他迫使我追問:什麼才是生活的真實?
——東西這是中國版的《在路上》和《麥田守望者》,於虛無中看到希望,於破滅中體會價值。
——徐坤
精彩書摘
“知道是為什麼抓你回來嗎?”“知道。”“那你就趕緊的,坦白從寬吧!"”“是不是我上回宰那幾個人的事兒讓你們查出來了?"”“你別跟我得瑟!在這裡還敢窮裝,慣得你皮子緊了是不?”一個滿臉橫肉自稱是便衣的傢伙,齜牙咧嘴地對著我,聽見我一說話他就想衝過來,我還真不明白他到底想乾什麼,更不信他敢打我,嚇唬誰哪?!我也沒犯什麼事兒,再說我就是犯什麼事兒了,這年代也不流行嚴刑逼供了。眼面前兒他要真動我一下,我非裝一把混蛋無賴,求我祖宗也不給面子,就把這兒當家,但事實上我雖然不是什麼正經貨色,還真不是無賴。旁邊一個白淨的小警察過來把他拉了回去,他坐到後面的沙發上眼睛瞪得跟一塊錢硬幣鋼一樣滴溜圓,臉上的肉都在顫抖。白淨的小警察坐到了我的對面,這小孩兒長得乾乾淨淨文質彬彬的,讓我看著還賊喜歡和順眼。他一隻手上捏著一個藍色的本夾子和一支筆,坐下後先把本夾子打開了,然後拿著筆好像想在上面寫點兒什麼,但想了一會兒抬頭看了看我,又把本夾子和筆都扔到旁邊兒的桌子上了,之後向前挪了挪椅子和藹地對我說:“跟你直說了吧!其實你也沒什麼事兒,實在沒辦法我們才把你帶回來,這幾天我們這裡的電話都快爆了,都是告你那破公司的,你們招留學生根本也沒有批文,這是犯法的你知道嗎?”“能罰多少?”“這個我不大清楚,得上頭做決定,但是我估計最少也得幾十萬。”“你們搶銀行不犯法是不是?”那個剛剛跟我一陣叫喚的便衣“噌”地一下又站了起來,他滿臉漲紅,對著我又是一頓臭喊:“你個小犢子!我不削你真不行了!把你慣出脾氣來了!”我坐在那兒邊笑邊看著這個沒智商的蠢貨,他也就是沒事兒瞎詐唬,一個勁兒地傻吹,沒人拉著他也未必敢打我。那個白淨的警察又起來了,像拖死豬一樣拽著他。我開始不喜歡這個白淨的小子了,賊礙事。讓他打我,他還以為是那萬惡的舊社會哪!要論法律我未必比他懂得少,只不過他用來鞭打別人,而我用來防守自己,說白了就是目的性和實用方式不同罷了。還有我也就是有時候愛頭腦一熱什麼亂七八糟的都忘了,但至少我現在是出奇的清醒和理智的,可能是在這個特定的場合內的原因。當然這時我還是渴求著這個傻老爺們兒打我,他要真打我了,那點兒罰款我就名正言順地有著落了。可他還是坐回了那個破椅子上,真是個孬種,氣死我了。說實話我真就沒把辦這個當成一回事兒,即使是交罰款也根本沒有這么誇張,根本不可能像那小孩兒說要幾十萬就幾十萬。他們慣用的手法是比比畫畫嚇唬蒙你,一直到你開始胡言亂語為止。其實對我他們根本就不用嚇唬,就現在這點事兒有啥我肯定就說啥,沒必要閒扯些用不著的,剛剛我就是想逗逗那個跟我張牙舞爪的傢伙。白淨的警察等氣氛平息了一會兒接著說:“認交罰款嗎?要是認的話,我去跟我們領導說一聲爭取少罰點兒。”“謝了,沒有,等我掙夠了再給你們行吧?我能抽根兒煙嗎?”白淨的小警察也氣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後想了想還是從抽屜里拿出一包黃山,很不情願地扔到桌子上。看著他那極度委屈的表情,我沒搭理他也沒動他扔在桌上的煙,而是拿起桌上的電話打給我秘書張娜。這個傻丫頭剛剛嚇傻了,現在肯定還在我車上等著我。她接起電話的時候我聽她的聲音都還保持著顫抖的狀態,我安撫了她幾句,然後告訴她把我車後備箱裡的煙都給我送過來,就馬上放下電話了。剛剛我打電話時那個便衣的表情賊可愛,像餓瘋了的野狗,兩眼冒著烈火向我噴來,可中間這個小警察的鐵欄太牢固,他就是吃不著我這塊肥肉。呵呵!我沖他笑了笑,估計他馬上就要瘋了。我坐在那裡老實地想了一會兒,突然想起了點兒什麼,然後抬起頭,看著坐在我面前的這個現在也不是正氣兒了的小警察,我笑著語氣平和地問他:"你們還抓誰了?“你的那個副總,在隔壁哪!他說這事兒跟他沒關係,可是營業執照是你們倆的名,所以他怎么說都沒用。”“真跟他沒關係,他懂個六啊!你們把他放了吧!我在這兒認拘留,最多也不過幾個月的事兒。”“這事兒還輪不到你說了算。”小警察聽我這么一說也給我撂了個黑臉,同時眼睛也白了我一下。這時張娜懷抱著十多條中華煙風風火火地跑了進來,這個傻丫頭可能是嚇壞了,連個袋子都沒拿,這裡的人肯定得以為她來公開犯錯誤。她把懷裡的煙稀里嘩啦地放到桌子上了,然後一聲不吱地站在一邊,低著頭賊眉鼠眼地看看我又看看那兩個警察。我把她套在手指頭上的我的車鑰匙拿了下來,之後告訴她回家等我電話。她又站在那裡可憐巴巴地看了我一會兒,然後不敢抬頭像是犯了什麼錯誤一樣邁著小快步走了,其實我心裡清楚她還是挺珍惜這份工作的,生怕我真犯了什麼事兒使她無處容身。她走後我拿起桌上的一條煙拆開,掏出了一包抽出一根,點上了,然後自言自語地說:“我一包夠了,剩下的放在這吧!等什麼時候有時間我再到這兒來抽。”聽我說完兩個人都不說話,互相看了看,可能也沒收慣什麼禮,再一個,在這裡邊兒我這樣做,他們肯定也有點兒膽怵的,所以兩個人都滿臉尷尬地沒動。安靜了一會兒之後,白淨的小警察恢復了他和藹的語氣接著說:“其實你這事兒不大,充其量也就是個非法經營,還沒構成詐欺。但你要是硬挺著不交錢也肯定不能放你,你要是認識上邊的人跟他們溝通一下,少罰點兒也就沒事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