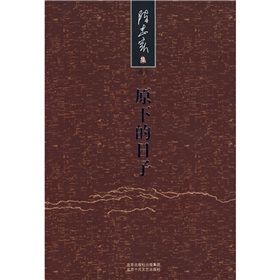內容簡介
背著一周的粗糧饃饃,我從鄉下跑到幾十里遠的城裡去念書,一日三餐,都是開水泡饃,不見油星兒,頂奢侈的時候是買一點雜拌鹹菜;穿衣自然更無從講究了,從夏到冬,單棉衣褲以及鞋襪,全部出自母親的雙手,唯有冬來防寒的一頂單帽,是出自現代化紡織機械的棉布製品。在鄉村讀國小的時候,似乎於此並沒有什麼不大良好的感覺;現在面對穿著艷麗、別致的城市學生,我無法不“顧影自卑”。說實話,由此引起的心理壓抑,甚至比難以下咽的粗糧以及單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難以忍受。作者簡介
陳忠實,1942年生於西安市灞橋區,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已出版《陳忠實小說自選集》三卷、《陳忠實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別白鴿》等40餘種作品。《信任》獲1979年全國短篇小說獎,《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1990-1991全國報告文學獎,長篇小說《白鹿原》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在日本、韓國、越南翻譯出版。曾十餘次獲得《當代》、《人民文學》、《長城》、《求是》、《長江文藝》等各大刊物獎。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目錄
師表·友情·親情第一次投稿
晶瑩的淚珠
何謂良師——我的責任編輯呂震岳
釋疑者
別路遙
雖九死其猶未悔
何謂益友——我的責任編輯何啟治
旦旦記趣
家之脈
三九的雨
山·水·樹·鳥
又見鷺鷥
擁有一方綠蔭——《我的樹》之一
綠蜘蛛,褐蜘蛛——《我的樹》之二
綠風——《我的樹》之三
火晶柿子——《我的樹》之四
一株柳
種菊小記
告別白鴿
拜見朱䴉
家有斑鳩
遇合燕子,還有麻雀
在河之洲
關於一條河的記憶和想像
體驗·言說
汽笛·布鞋·紅腰帶
最初的晚餐——《生命歷程中的第一次》之一
尷尬——《生命歷程中的第一次》之二
沉重之塵——《生命歷程中的第一次》之三
與軍徽擦肩而過
六十歲說
原下的日子
為城牆洗唾——關中辯證之一
粘面的滑稽——關中辯證之二
遙遠的猜想——關中辯證之三
孔雀該飛何處——關中辯證之四
鄉諺一例——關中辯證之五
也說鄉土情結——關中辯證之六
兩個蒲城人——關中辯證之七
藉助巨人的肩膀——翻譯小說閱讀記憶
也說中國人的情感
別人的風景
中國餐與地攤族——義大利散記之一
貞節帶與鬥獸場——義大利散記之二
那邊的世界靜悄悄——美、加散記之一
北橋,北橋——美、加散記之二
感受文盲——美、加散記之三
口紅與坦克——美、加散記之四
捷運口腳步爆響的聲浪——俄羅斯散記之一
林中那塊陽光明媚的草地——俄羅斯散記之二
自家的山水
魯鎮紀行
追尋貂蟬
伊犁有條渠
燦爛一瞬——涼山筆記之一
神秘一幕——涼山筆記之二
駱駝刺——車過柴達木之一
鹽的湖——車過柴達木之二
天之池
威海三章
漕渠三月三
在烏鎮
黃帝陵,不可言說
柴達木掠影
完成一次心靈洗禮——感動長征之一
黃洋界一炮——感動長征之二
再到鳳凰山
媧氏莊杏黃
一九八0年夏天的一頓午餐
精彩書摘
師表·友情·親情第一次投稿
背著一周的粗糧饃饃,我從鄉下跑到幾十里遠的城裡去念書,一日三餐,都是開水泡饃,不見油星兒,頂奢侈的時候是買一點雜拌鹹菜;穿衣自然更無從講究了,從夏到冬,單棉衣褲以及鞋襪,全部出自母親的雙手,唯有冬來防寒的一頂單帽,是出自現代化紡織機械的棉布製品。在鄉村讀國小的時候,似乎於此並沒有什麼不大良好的感覺;現在面對穿著艷麗、別致的城市學生,我無法不“顧影自卑”。說實話,由此引起的心理壓抑,甚至比難以下咽的粗糧以及單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難以忍受。
在這種處處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卻喜歡文學了;而喜歡文學,在一般同學的眼裡,往往是被看做極浪漫的人的極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來了一位語文老師,姓車,剛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第一次作文課,他讓學生們自擬題目,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是我以前所未遇過的新鮮事。我喜歡文學,卻討厭作文。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義的一件事》這些題目,從國小作到中學,我是越作越煩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義的一天”了。新來的車老師讓我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我有興趣了,來勁了,就把過去寫在小本上的兩首詩翻出來,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作文的興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儘快發回作文本來,我自以為那兩首詩是傑出的,會震一下的。我的作文從來沒有受過老師的表彰,更沒有被當做範文在全班宣讀的機會。我企盼有這樣的一次機會,而且正朝我走來了。
車老師抱著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講台,我的心無端地慌跳起來。然而四十五分鐘過去,要宣讀的範文宣讀了,甚至連某個同學作文里一兩句生動的句子也被摘引出來表揚了,那些令人發笑的錯句病句以及因為一個錯別字而致使語句含義全變的笑料也被點出來,終究沒有提及我的那兩首詩,我的心裡寂寒起來。離下課只剩下幾分鐘時,作文本發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車老師用紅墨水寫下的評語,倒有不少好話,而末尾卻懸下一句:“以後要自己獨立寫作。”
我愈想愈覺得不是味兒,愈覺不是味兒愈不能忍受。況且,車老師給我的作文沒有打分!我覺得受了屈辱。我拒絕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學伸手要交換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課,我拿著作文本趕到車老師的房門口,喊了一聲:“報告——”
獲準進屋後,我看見車老師正在木架上的臉盆里洗手。他偏過頭問:“什麼事?”
我揚起作文本:“我想問問,你給我的評語是什麼意思?”
車老師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點燃一支煙,說:“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攤開在桌子上,指著評語末尾的那句話:“這‘要自己獨立寫作’我不明白,請你解釋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獨立寫作。”
“那……這詩不是我寫的?是抄別人的?”
“我沒有這樣說。”
“可你的評語這樣子寫了!”
他冷峻地瞅著我。冷峻的眼裡有自以為是的得意,也有對我的輕蔑的嘲弄,更混含著被冒犯了的慍怒。他噴出一口煙,終於下定決心說:“也可以這么看。”
我急了:“憑什麼說我抄別人的?”
他冷靜地說:“不需要憑證。”
我氣得說不出話……
他悠悠抽菸:“我不要憑證就可以這樣說。你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詩歌……”
於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褲的醜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鄉村學生圍蹲在開水龍頭旁邊時的窩囊,就憑這些瞧不起我嗎?就憑這些判斷我不能寫出兩首詩來嗎?我失控了,一把從作文本上撕下那兩首詩,再撕下他用紅色墨水寫下的評語。在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剎那,我看見一雙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顫,就把那些紙用雙手一揉,塞到衣袋裡去了,然後一轉身,不辭而別。
我躺在集體宿舍的床板上,屬於我的那一綹床板是光的,沒有褥子也沒有床單,唯一不可或缺的是頭下枕著的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鋪一半再蓋一半。我已經做好了接受開除的思想準備。這樣受罪的念書生活還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戀。
晚自習開始了,我攤開了書本和作業本,卻做不出一道習題來,著筆,盯著桌面,我不知做這些習題還有什麼用。由於這件事,期末的操行等級降到了“乙”。
打這以後,車老師的語文課上,我對於他的提問從不舉手,他也點我的名要我回答問題,校園裡或校外碰見時,我就遠遠地避開。
又一次作文課,又一次自選作文。我寫下一篇小說,名日《桃園波》,竟有三四千字,這是我平生寫下的第一篇小說,取材於我們村里果園入社時發生的一些事。隨之又是作文評講,車老師仍然沒有提我的作文,於好於劣都不曾提及,我心裡的底火又死灰復燃。作文本下來,揭到末尾的評語欄,連篇的好話竟然寫下兩頁作文紙,最後的分欄里,有一個神采飛揚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號,這就是說,比滿分還要滿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評語和“5”’的高分,為什麼評講時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約意識到小視“鄉下人”的難堪了,我猜想,心裡也就膨脹愉悅和報復,這下該有憑證證明前頭那場說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繼續著。
入冬後的第一場大雪是夜間降落的,校園裡一片白。早操臨時取消,改為掃雪,我們班清掃西邊的籃球場,雪下竟是乾燥的沙土。我正掃著,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揚頭,是車老師。他笑著。在我看來,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說:“跟我到語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裡疑慮重重,又有什麼麻煩了?
走出籃球場,車老師的一隻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無措了。那隻胳膊從我的右肩繞過脖頸,就摟住我的左肩。這樣一個超級親昵友好的舉動,頓然冰釋了我心頭的疑慮,卻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進教研室的門,裡面坐著兩位老師,一男一女。車老師說:“‘二兩壺’、‘錢串子’來了。”兩位老師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臉上發燒。“二兩壺”和“錢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說的兩個人物的綽號。我當時頂崇拜趙樹理,他的小說的人物都有外號,極有趣,我總是記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記住外號。我也給我的人物用上外號了。
車老師從他的抽屜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訴我,市里要搞中學生作文比賽,每箇中學要選送兩篇。本校已評選出兩篇來,一篇是議論文,初三一位同學寫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過望,我不知該說什麼了。
“我已經把錯別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車老師說,“你看看,修改得合適不合適?”說著又摟住我的肩頭,摟得離他更近了,指著被他修改過的字句一一徵詢我的意見。我連忙點頭,說修改得都很合適。其實,我連一句也沒聽清楚。
他說:“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寫一遍,周六以前交給我。”
我點點頭,準備走了。
他又說:“我想把這篇作品投給《延河》。你知道嗎,《延河》雜誌?我看你的字兒不太硬氣,學習也忙,就由我來抄寫投寄。”
我那時還不知道投稿,第一次聽說了《延河》。多年以後,當我走進《延河》編輯部的大門深宅以及在《延河》上發表作品的時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過車老師曾為我抄寫投寄的第一篇稿。
這天傍晚,住宿的同學有的活躍在操場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個死貪學習的女生。我破例坐在書桌前,攤開了作文本和車老師送給我的一紮稿紙,心裡怎么也穩定不下來。我感到愧悔,想哭,卻又說不清是什麼情緒。
第二天的語文課,車老師的課前提問一提出,我就舉起了左手,為了我的可憎的狹隘而舉起了懺悔的手,向車老師投誠……他一眼就看見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來後,卻說不出話來,喉頭哽塞了棉花似的。自動舉手而又回答不出來,後排的同學鬨笑起來。我窘急中又湧出眼淚來……
我上到初三時,轉學了,暑假辦理轉學手續時,車老師探家尚未回校。後來,當我再探問車老師的所在時,只說早調回甘肅了。當我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處女作的時候,我想到了車老師,應該寄一份報紙去,去慰藉被我冒犯過的那顆美好的心!當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出版時,我在開著給朋友們贈書的名單時又想到車老師,終不得音訊,這債就依然拖欠著。